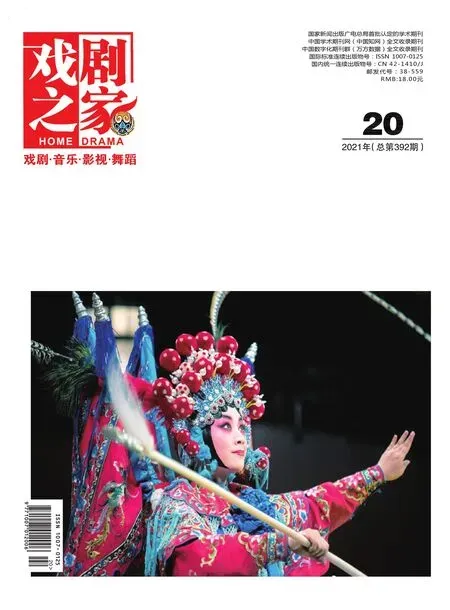論樊粹庭在唱腔音樂創作方面的改革
郭路遙
(上海師范大學 上海 200000)
在豫劇發展史上,曾有三次大的改革,其中,樊粹庭對豫劇所進行的改革影響最大。他以崇高的使命感獻身于豫劇改革事業當中,成功地實現了豫劇的現代化轉型,把豫劇推向了一個時代高峰,成就了豫劇的輝煌,被學術界譽為“現代豫劇之父”。在樊粹庭對豫劇所進行的全方位的改革中,在豫劇的音樂創作實踐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文就此作一簡要探討。
一、唱腔音域及其調式
豫劇的母調是起源于開封的祥符調,在祥符調逐漸成熟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樊粹庭不僅是親身實踐的劇作家和導演,更是推進其改革的先行者,是真正意義上將豫劇祥符調推向高峰的人。從1934 年開始,樊粹庭和豫劇大師陳素真合作,創作出了一大批“樊戲”經典劇目。筆者將樊粹庭先生改革劇目中的唱腔變化進行歸納整理,并將其改編、創作的劇目進行舉例分析,進一步探究樊粹庭在劇目中對唱腔的改革和應用。

譜例1:《三上轎》選段

譜例2:《三上轎》選段
旦角比例的增加使豫劇唱腔音域發生變化。作為豫劇界第一代女演員,陳素真在20 世紀30 年代中期,就以卓越的表演藝術贏得“河南梅蘭芳”、“豫劇皇后”和“梆子大王”的稱號。在陳素真從藝初期,也即河南梆子尚未在城市立足之前,旦角主要由男性扮演。由于生理原因,男女發音有別,音區差別大,所以,一些劇目改用女演員演唱時,以原有調(A、A、B)唱中央C 到小字二組的f 的音時,音色暗淡。唱返腔時,又因缺乏男性特有的胸腔共鳴而缺少厚重感。原來劇目的調式音域已經無法適應新的演員唱腔需要,極易被市場淘汰,因此,劇目的唱腔亟需一次較大的更改。于是,通過女演員提高音區的辦法,利用女性特有的明麗、婉轉的單色,求得最佳的藝術效果。在這一過程中,陳素真在樊粹庭的指導下,通過《反長安》《撿柴》《三上轎》等劇目的排練,反復推敲,不斷創新。在演唱風格上力求新穎脫俗,在旋律上填平補齊,在男女聲結合上達到協調一致。功夫不負有心人,樊粹庭終于在豫劇舞臺上形成了一套適應女聲演唱的祥符調旦角唱腔。
以《三上轎》為例,該劇是一個大悲劇,沒有過于復雜的情節,三次“上轎”是全劇的重點。運用哭腔的唱法可以更好地表達悲劇情感,樊粹庭建議陳素真以深沉、舒緩、淳樸的音調,哀婉、凄涼地表達女主人公崔金定將萬般苦澀壓抑胸中的情緒(見譜例1):
哭腔屬于拖腔的一種,但哭腔與一般性的拖腔不同的是,哭腔常用在【飛板】類唱腔中,無板無眼,節奏自由。“第一行的‘婆’后面是一個哭腔,旋律時斷時續,抽泣聲、各種裝飾音的運用,使得曲調盡顯凄涼。旋律的調式主音雖然是sol,但樂音la 多次出現,使得曲調羽調式色彩濃厚,哀婉凄涼。”旋律第一個小分句結束時連續出現三次還原fa(首調),并使用顫音演唱,凸顯悲涼氣氛。第二分句開頭sol 作為倚音與la 交替出現,模仿哭泣聲,并從la 突然大跳到高音re 后返回,形象地表達了崔金定壓抑痛苦之情。
陳素真基于對現實生活的體驗,充分感受劇中女主角崔氏內心的情感世界,演唱得情真意切。雖輕聲慢語,卻讓人感到字字千鈞,句句入心。特別是當崔氏第二次上轎時,聽見了不滿周歲嬌兒的哭聲。此時此刻,她悲痛萬分。她不忍撇下自己的親生骨肉,但為了報仇,她強忍著悲痛,勸說公婆。樊粹庭認為,要恰如其分地表達此時崔氏的心情,就不能一味地嚎啕大哭,而是要哭中有怒,悲中帶憤(見譜例2):
“在正式上演時,陳素真剛唱完這一段,觀眾的喝彩聲便連綿不絕,如泣如訴的新腔,成功地塑造了貧婦崔金定凄楚感人的形象。從此,《三上轎》便成為河南觀眾百看不厭、百聽不煩的優秀劇目,也是陳素真早期經常上演的拿手戲。”可以說,豫劇唱腔的變革離不開樊粹庭和陳素真的共同努力,如果沒有樊粹庭對豫劇唱腔改革的迫切意識和創新意識,僅憑陳素真一己之力,恐怕也難以推動豫劇唱腔的發展。
二、唱腔板式
樊粹庭在與陳素真合作過程中,進一步豐富了豫劇的唱腔板式。祥符調作為豫劇一個流派,發源于河南開封,有著古樸醇厚、委婉含蓄、俏麗典雅的風格特點。“但早期的祥符調只有四個正板,即慢板、二八板、流水板和飛板,略顯單薄和呆板。樊粹庭先生結合陳素真等人在演唱過程中的行腔變化,逐步豐富了四大板式的內涵和表現形式,拓展擴充為五十四個支板式。這些新增的板式不僅適用于旦角,也同樣適用于生角和凈、丑、末”。樊粹庭對器樂的改革以及與陳素真等藝人對唱腔的探討,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加速了豫劇的唱腔變革和發展。
我們再以《洛陽橋》為例進行分析。《洛陽橋》是清代花部亂彈作品,又名《梵王宮》或《葉含嫣》,作者不詳,主要流傳于梆子系統各劇種。《洛陽橋》共九個場次,其中第三場《相思成疾》是全戲的小高潮。本場的情節、表演、唱段三部分是最核心的內容,筆者擇取本唱段一部分進行具體分析。

圖示:1=bE 《洛陽橋》中《相思成疾》部分唱段
“整個唱段板式為【慢板】轉【慢二八板】,一共五句,具有抒情性,表達了葉含嫣對花云的愛慕之情。句式為基本腔與擴充腔交替”。《洛陽橋》是“樊悴庭的改良戲,劇中的少女葉含嫣對愛情執著,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在當時社會具有一定的進步性。”
三、伴奏樂器的變化
在豫劇的發展史上,樊粹庭對于豫劇伴奏樂器的改革也是不容忽視的。伴奏樂器對于一場劇目的演出效果,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豫劇整體的音樂效果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隨著對豫劇改革的深入,樊粹庭關注到了伴奏樂隊的問題。在伴奏樂器方面,與京劇相比,豫劇主弦是大弦、二弦,不如京胡音色那么明亮,在伴奏樂器中特點鮮明,難以起到領弦的作用;同時,“樂隊還缺少像京二胡這樣能與京胡高低呼應、能夠襯托出京胡聲音、使整體音效更加圓潤渾厚的樂器”。所以,樊粹庭進行了改革:
(一)添置新樂器
隨著豫劇的發展,樂隊人員的個人素養和演奏水平不斷提高。“為了增強豫劇唱腔的表現力,使其更加優美動聽,適應時代發展和觀眾的審美需求,樊粹庭先生廢除了豫劇以前常用的樂器大弦、二弦,引進了板胡”。
板胡的音色剛好與旦角明亮、清脆的音色相匹配,使得豫劇音樂中唱腔與伴奏樂器達到完美融合,并逐漸發展成了豫劇戲班樂隊的主要演奏樂器。在伴奏時,板胡要突出唱腔中的裝飾音,運弓要平穩,旋律要柔美,要把唱腔中所表達的內心情感充分表現出來。后來,樊粹庭先生認為弦樂伴奏剛性有余而柔性不足,便在之后的演出中加上二胡,配合主弦,以柔化音樂。“豫劇中的二胡也和板胡一樣,可以說是被樊先生借用過來的,還有后來的笙,這都是樊先生在認真聆聽唱片后對豫劇樂隊進行的改進”。
(二)調高變化
由于女演員在豫劇舞臺上嶄露頭角,為適應女聲唱腔的需求,伴奏樂器的定調也必須隨之改變。“20 世紀20 年代,豫劇聲腔呈高、尖、銳的狀態,板胡一般采用F 或者G 調為固定調”。所以,如前所述,至20 世紀40 年代,各大劇團大多采用E 調定弦二胡、板胡,如樊粹庭為豫劇名家陳素真寫的《三上轎》《霄壤恨》中,旦角唱腔選用E調為標準調。新的伴奏樂器的變革促進了豫劇音樂和唱腔的發展,增強了豫劇祥符調的表現張力和抒情性,極大地推動了豫劇的發展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