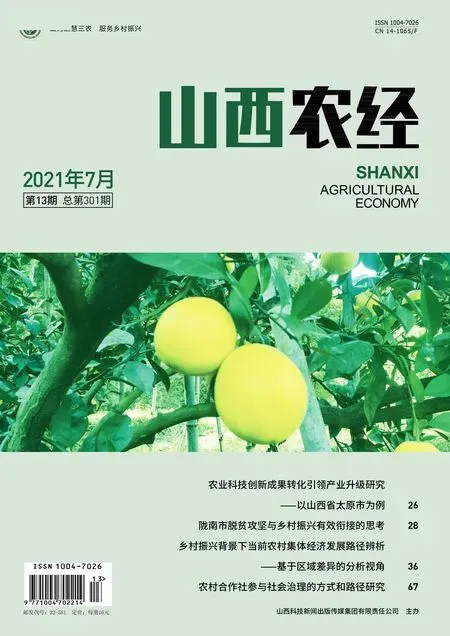我國耕地資源動態變化與糧食生產關系剖析
□黃舒婷,范樹平
(安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安徽 合肥 230036)
1 我國耕地資源基本情況
1.1 我國耕地資源的現狀
1.1.1 耕地面積呈下降趨勢
雖然我國幅員遼闊,土地資源豐富,但是多為山地丘陵,耕地資源僅占國土總面積的12.5%。再加上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耕地占有量遠遠低于世界人均耕地占有量的平均水平。
據《2017 中國土地礦產海洋資源統計公報》可知,我國耕地增量遠低于耕地減量,耕地面積總體呈下降趨勢。截至2016 年,我國耕地面積為13 492.09 萬hm2,相比2015 年耕地面積凈減少7.69 萬hm2,與2012 年相比減少了24.75 萬hm2,每年約以5 萬hm2的速度在減少。按照這個減速,守住“18 億畝耕地紅線”這個任務異常艱難。
1.1.2 耕地質量堪憂,耕地集約利用水平低下
由于我國農民利用土地時存在“重用輕養,重產出輕投入,重化肥輕有機肥”的思想,且觀念根深蒂固,長期不合理使用化肥、農藥,導致目前我國耕地地力下滑趨勢嚴重。再加上受到城市工業大規模排放“三廢”和鄉鎮工業污染的雙重影響,大量土壤被污染,污染由單一拓展為多元。此外,由于水土流失、鹽漬化等原因導致耕地退化日趨嚴重[1],我國耕地質量問題堪憂。
1.2.3 耕地后備資源匱乏
我國耕地后備資源非常稀缺,集中連片的后備耕地資源僅占整體的40%左右,分散零碎的后備資源占絕大部分,且多分布在我國西北欠發達區域,而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卻很匱乏。另外,我國擁有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史,生產條件好的土地大部分都已被開墾利用。可供開發利用的合格后備資源十分有限,很多是生態環境脆弱的邊緣地區。
1.2 耕地的重要性
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源,農以地為本,耕地是農業生產的重要載體。據有關部門估算,耕地供給人類88%的食物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農民大部分的經濟收入來源于耕地,但占用耕地現象、社會無業人員增多無疑加重了社會負擔。耕地不僅是農業的重要生產資源,更是人民生活安定和諧的保障。
2 我國糧食生產基本情況
2.1 糧食產量穩中有升
2012—2015 年,我國糧食總產量一直保持不斷增長的態勢。2015 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6 214.35 億kg,是1949 年總產量(1 131.8 億kg)的近6 倍,遠遠超過了我國人口的增長速度。但是,2016 年我國糧食總產量為6 162.4 億kg,相比2015 年減少52.0 億kg,減少了0.8%。從2015 年至今,我國糧食總產量均保持在6000 億kg 的水平之上。預計2021 年仍是豐收年。
2.2 糧食結構失衡結構性過剩明顯
我國糧食生產的總體大環境是產量連年攀升,但是近年來糧食結構比重失衡愈顯嚴重。玉米、稻谷結構性過剩問題日趨突出,高品質的小麥、大豆等供不應求。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國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效。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國已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隨著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糧食的傳統消費觀念發生了質的轉變,城鄉居民的糧食消費結構不斷升級,是否“吃得好”成為社會熱門話題。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很多人居家手工烘焙,弱筋、強筋小麥等銷售額大幅增加。但是,我國糧食庫存很大部分為普通小麥品種。這些糧食品種不符合國內外的市場需求,導致的后果是滯銷積壓。可見,我國糧食結構性過剩問題是既成事實。
2.3 進口糧依賴度漸漲
雖然我國糧食總產量總體不斷上升,但同時糧食的進口量也在快速增長。我國水稻、小麥、玉米三大主糧的進口量遠超出口量。在過去幾年中,我國糧食進口量有小幅波動變化,但進口量均在1 億t 以上,尤其在2017 年創下高位。2017 年我國稻米進口量達到399 萬t,小麥進口量達到430 萬t,大麥進口886 萬t,相較于前幾年翻了好幾番[2]。在產量上升的同時,糧食缺口也隨之增大。這也預示著我國正向農產品進口國轉變。
3 耕地動態變化對糧食生產的影響
3.1 耕地非農化下的糧食生產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推進,耕地非農化成為該進程中不可忽視的問題。耕地非農化帶來的結果可以直接概括為兩方面,一是耕地面積,二是耕地質量。在耕地面積上,耕地非農化意味著耕地被占用。而在耕地質量方面,雖然有政策支持——“占優補優”,可一般被占用的耕地都位于城郊,地勢平坦且土壤地力水平高。而補充進來的土地多為剛進行過復墾整理,管理和投入相較前者更顯薄弱,耕地質量不盡如人意[3]。
從糧食生產函數的角度看,可以把耕地質量看成糧食生產函數中的一種類似技術投入要素,影響糧食單產,從而使糧食總產量上下變動。由圖1 可以清楚地看出,隨著耕地質量上升,在其他要素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糧食生產函數上移,糧食產量提高;反之,糧食生產函數下移,糧食產量降低。由此可以明顯得出,耕地非農化與糧食產量呈負相關。
3.2 耕地資源與糧食產量的空間變化
根據地理國情監測云平臺2012—2016 年土地利用分布圖可以看出我國耕地面積的空間變化,耕地面積減少的城市大部分為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耕地面積向我國北方地區新疆、內蒙古推進。
再觀我國在這個時間段的糧食產量空間變化,我國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糧食產量呈下降趨勢,北方地區糧食產量不斷攀升,逐漸成為我國糧食生產的中流砥柱。
我國糧食產量的空間變化與耕地面積的空間變化大致具有同向性,總體移動方向的大趨勢是“北進中移”。由于糧食產量受制度、氣候等多種因素共同影響,與耕地面積的變化具有一定的差異性。
3.3 耕地質量等級空間分布對糧食生產的影響
我國為耕地劃分了15 個質量等級標準,其中一等耕地糧食生產潛力最大。總體耕地質量等級排名前三位的區域分別是長江中下游區、華南區、江南區;排名后三位的區域分別為黃土高原區、青藏高原區、內蒙古高原區。我國耕地質量變化趨勢是由東南向西北遞減。一等地往往分布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地區,這些地區的氣候條件非常適宜農業生產。但這些地區的耕地面積僅占總體的一小部分,并且耕地遞減速率在逐年提高。劣等地的面積占了絕大部分,導致我國糧食生產空間供需完全不匹配[4]。
4 對策建議
4.1 優化耕地占補平衡舉措
耕地占補平衡是我國堅守耕地紅線目標的重要戰略舉措之一。事實上,讓補充進來的土地質量達到占用土地質量水平,在本質上實現的可能性幾乎為零。為了盡量實現糧食質量的平衡,要嚴格貫徹占補新政中“補改結合”方式;盡可能不占或者少占土地質量水平等級高的耕地;摒棄以往以土地開發為主的理念;對補充的土地加大人力、物力投資,通過后天高質量的投入來彌補先天的不足[5]。
4.2 大力推進土壤污染防治
耕地質量下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土壤污染,土壤污染嚴重威脅著我國糧食安全。我國相關部門應抓緊完善土壤污染調查與評價機制,進行全國范圍內的土壤污染普查,查明、查清土壤污染的源頭,綜合整治已被污染的土壤,嚴格遵守、執行土壤污染防治的相關法律法規。在城鎮建設規劃中,把生態環保放在首位,對于重度污染工業嚴禁批準,建立問責制度,嚴防死守土地污染。
4.3 讓科學種田成為常態
充分挖掘耕地的潛在生產力,因地制宜地種植農作物。順應自然規律,以不破壞生態環境為前提,加大科學技術的投入,挖掘耕地的潛在生產力。我國將每年的6月25 日確定為“土地日”,政府可通過此類的宣傳活動向農民普及耕種知識,在潛移默化中引領農民科學合理種田。村民委員會可與各大高校合作,邀請專家教授開展培訓班,實踐與理論相結合,傳授專業知識,指導農民科學合理地使用化肥、農藥。
4.4 創新耕地保護制度
耕地保護制度是我國土地制度的底線。黨中央對耕地保護問題一直保持著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考察時再次強調:“要像保護大熊貓一樣保護耕地”。對此,要不斷對耕地保護制度優化創新,不僅談耕地保護,還要突破原有的耕地保護禁錮,統籌協調區域的經濟利益與耕地保護,在耕地保護中注入市場機制,建立耕地保護與經濟發展良性循環的長效機制,為耕地保護制度添加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