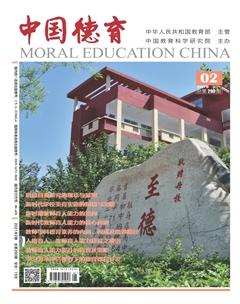高中階段勞動育人困境的突破
勞動育人并不總是非要大張旗鼓地開展,有時可以潛移默化地實現“借力打力”,借助于學校現有課程或實踐活動,實現勞動教育在課程之間或學科之間的滲透,適時對學生稍加引導,同樣也是實現勞動育人的有效路徑。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強調勞動教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制度的重要內容。但在高中階段,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高中生對勞動教育存在著一系列異化、窄化、弱化的認知傾向。如何將勞動教育與班集體建設相融合?如何提升學生核心素養的同時滲透勞動育人的價值?是班主任亟須思考的問題。
魯班,是我們班的班名。同學們起這個名字的時候,一語雙關。其一,我來自山東,是一名歷史老師,“魯”是山東的簡稱,魯班,歷史名人,班名凸顯了班主任的個人特質和學科屬性。其二,同學們希望以著名工匠魯班的“工匠精神”為指引,踏踏實實面對高中的學習生活。以“魯班”這兩個字為班級命名,以“工匠精神”為指引,彰顯了班集體建設中滲透“以勞育人”的理念初見成效。
一、拒絕異化:培育勞動崗位意識
高一建班之初,我鼓勵學生們自薦班委會成員,結果勞動委員又沒人報名。不僅我們班是這個情況,其他班也是如此,班長和團支書這些“實權崗位”競爭激烈,副班長這種所謂的“虛銜”更是受人追捧,唯獨“勞動委員”無人問津。為此,我對班級42位學生開展為何不愿意做勞動委員的調查。數據顯示,36%的學生認為勞動委員“很土”,聽著不是很體面;32%的學生認為勞動委員干活多,影響學習;21%的學生認為學校勞動是老師懲罰犯錯同學的方式;其余的學生則表明自己不擅長勞動或不喜歡勞動。勞動委員一職的尷尬缺席,折射出的是學生們對勞動的異化認知。
學生們對勞動的異化認知,深受傳統固化思維和錯誤教育行為的影響。其一,社會中流行著“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等級觀念,導致現在很多青少年存在輕視,甚至丑化勞動的現象,認為勞動者是社會底層低賤的職業,取而代之的是享樂主義及坐享其成的風氣抬頭。其二,在目前的學校教育中,存在著將勞動作為懲罰犯錯學生的方式,這種不恰當的做法,使勞動由一種育人的路徑變成一種懲罰的手段,這也是一種勞動教育的異化,與勞動教育的初衷相違。學生們潛移默化地養成了逃避勞動的習慣,勞動的價值觀念被扭曲,勞動的育人價值也沒有得到體現。
面對班級建設的“痛點”,作為班主任,我希望在班級中重塑“勞動光榮”的信念。于是,我組織班級開展以“大國工匠”為主題的班會課。“發動機焊接第一人”高鳳林,將看似平常的焊接技術發揮到極致,攻克近百項難關,先后為90多發火箭焊接過“心臟”;孟劍鋒百萬次的精雕細琢,雕刻出令人嘆為觀止的“絲巾”;鐘南山院士雖84歲高齡,仍身先士卒,為抗擊SARS、新冠肺炎疫情貢獻著自己的力量。通過案例介紹,引導學生明白在平凡的崗位上也能創造奇跡,扭轉學生們對于勞動外延和價值的認識。
之后,我又組織班級開展了“勞模進課堂”“生涯職業規劃”等主題課,內化學生們對“勞動光榮”這一美德的認識。通過對“魯班”“工匠精神大家談”“父母職業訪談”的主題討論,深化學生們對勞動價值的感悟和認識。接著,我將“勞動委員”的職責拆分,設置28個“班級文明崗”;實行崗位積分末位淘汰制和定時輪崗制,樹立競爭機制。這不僅增強了學生們的責任心,也增加了他們對勞動本身的切身體驗。最后,通過勞動成果展示、勞動之星評選、文明班級獎勵等活動,讓學生們認識到勞動顯性和隱性的價值,樹立勞動最光榮的信念。
勞動崗位意識培育機制充分調動了學生們的主觀能動性,讓班級由最初的“勞動委員無人問津”,到現在形成了“人人皆是勞動委員”的崗位認同。勞動崗位意識的培育,提升了班級的凝聚力。
二、拒絕窄化:建構勞動課程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發表講話,強調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隨著國家對勞動教育的重視,一些學校安排了每周1課時的勞技課。但事實上,勞動教育在高中階段仍處于相對邊緣化的狀態。因為高中階段,學生們學業壓力大,學校和家長對學業成績的期待導致勞技課經常被其他學科占用。加之勞技課缺乏專門的師資配備,也沒有統一的教材,而且不是高考的科目,極容易被忽視。
面對勞動教育現有課程的局限性,班主任要改變的是自己的育人思維。班主任勞動教育的思維不能被窄化,要提升對勞動教育的認識,深刻理解勞動教育的內涵,擴展勞動教育的外延。勞動育人并不總是非要大張旗鼓地開展,有時可以潛移默化地實現“借力打力”,借助于學校現有課程或實踐活動,實現勞動教育在課程之間或學科之間的滲透,適時對學生稍加引導,同樣也是實現勞動育人的有效路徑。
比如,在魯班的建設中,整合現有資源,結合核心素養的要素,形成具有自己班級特色的“魯班勞動課程體系”,以“全面發展的人”為中心,拓展勞動育人的多元化路徑。從“文化基礎”“自主發展”“社會參與”三個方面,落實“理性思維”“勇于探究”“自我管理”“健全人格”“勞動意識”“技術運用”6個核心素養。在課程體系中,勞動育人并不是割裂開來的,而是多學科、多種課程之間的融合與滲透。
勞動教育,不只是在講臺上講勞動,而是綜合課程中的一種創造性勞動。比如,通過開展學農、學工等活動,讓學生們對勞動有一個真實的體驗;借助于融合了科學、技術等多學科交叉的STEAM課程,不僅能讓學生們體驗動手操作,還能讓學生們獲得學識上的提升;在校本拓展課中,引入“陶藝工作坊”“校園烘焙”“手工刺繡”等課程,不僅能鍛煉學生們的動手能力,而且還能讓他們獲得滿足感和幸福感;參加暑期社會志愿活動,不僅能讓學生們收獲勞動技能,更能收獲快樂。在這些勞動中,學生們不再認為勞動是體力活的單調與重復,他們收獲的是對勞動價值更深一層的認知,增強了對勞動最光榮的認識。
三、拒絕弱化:養成勞動自立品格
勞動教育也是一種生活教育。“重智輕勞”在家庭教育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相比于學習,家長對勞動有弱化的傾向,只希望學生們“兩手不做家務事,一心一意為考試”。這不僅剝奪了學生們在家務勞動中成長的機會,也錯過了在共同進行家務勞動時親子溝通和相處的機會。因此,進行必要的勞動自立教育迫在眉睫。
高一時期,我開設了“魯班自立整理課”,列出“魯班寢室內務自立清單”。學生們根據清單自主完成,由生活老師作指導員和監督員。經過一個學年的努力,原先學生周五放學將積攢一周的臟衣服帶回家洗的現象大為減少,家長們見證了學生們的成長,也逐漸開始配合學校,放手讓學生們走向自立。
疫情突然暴發,學生們只能居家進行線上學習,面對特殊的學習環境,我將“魯班寢室內務自立清單”改為“魯班家務自立清單”。除了每天常規性的網課學習和作業外,還會額外布置一個家務作業,實行“5+X”計劃,即疫情居家學習期間,周一至周五,自主選擇一項為家人做的家務,諸如“為家人做一頓晚餐”“拖一次地”“出門時為家人量體溫”“進門時為家人衣物清潔消毒”等。家長作為學生的直接監督者,監督學生完成并予以評價,并且每周將結果通過微信發給我,我匯總統計,每月評選“勞動達人”。得益于這種家庭勞動教育的形式,“魯班”不僅形成了家庭—學校有效互動的協同機制,同時也避免了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割裂的境地。
“魯班自立清單”實施近兩年以來,生活老師和家長擔任學生自立習慣養成的監督員和測評員,從近兩年的數據反饋來看,學生們的自理能力、內務整理能力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以勞育人,自立品行,內化了對“勞動光榮”的認知,增強了班集體的凝聚力和榮譽感。同時,增進了家長與學生之間的聯系。這不僅讓學生們實現了自立,也有助于健全人格的形成。
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在《一塊面包》中對父母在孩子勞動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有詳細的描寫。他指導孩子們一起種小麥,麥子收了磨成面粉,烤成面包,邀請所有家長來吃,孩子烤的面包只有自己的父母覺得香甜,但這很重要,因為家長的鼓勵是對孩子勞動成果的尊重,使得孩子們感受到了勞動的意義和價值。因此,要轉變家長對于孩子參加勞動的觀念,讓家長們認識到勞動對于孩子一生發展的重要意義。
圍繞“魯班”的勞動育人實踐,尚在探索之中,應持續推進勞動教育在班集體建設中的開展,將勞動育人與班集體建設相融合,消除對勞動教育異化、窄化、弱化的認知。在“五育并舉”的背景下,勞動教育也要朝著“以勞樹德”“以勞增智”“以勞強體”“以勞育美”的方向努力,實現“五育融合”。
【陳文濤,上海外國語大學閔行外國語中學】
責任編輯︱孫格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