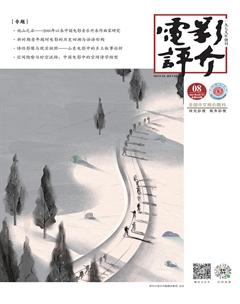“導演”抑或“作者”:盧鳳崗“鄉(xiāng)土紀錄片”口述歷史研究訪談
陳藝 盧鳳崗

2019年6月10日,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司指導,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間文藝發(fā)展中心、國家圖書館聯(lián)合主辦的2019文化和自然遺產(chǎn)日非遺影像展在浙江象山閉幕,貴州省推送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記錄:王景才——苗族蘆笙舞(滾山珠)綜述片》(以下簡稱《王景才》)被組委會列為“評委會推薦影片”。
本屆非遺影像展的主題為“非遺影像 中國實踐”,共征集到260部作品,經(jīng)專家評審委員會評審,組委會共選出主題鮮明、內(nèi)容翔實、表現(xiàn)力出眾的入圍影片30部(套),并組織影像和非遺領域專家對入圍影片進行了評選,從中選出包括《王景才》等在內(nèi)的10部(套)“非遺影像展專家評委會推薦影片”。
專家評委一致認為,《王景才》不光綜合體現(xiàn)了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傳承人王景才為核心的苗族蘆笙舞(滾山珠)的舞蹈技藝,還通過影片深入傳承人的生活,走進傳承人的心靈,感受傳承人的喜憂,充分記錄并融入了相關民俗活動,是一部展現(xiàn)苗族蘆笙舞(滾山珠)及非遺傳承人王景才獨特魅力的影片。同時,更是非遺工作者和實踐者向共和國70周年華誕獻禮的一部優(yōu)秀作品。
苗族蘆笙舞“滾山珠”得名于小花苗蘆笙舞的一個動作“地龍滾荊”,苗語叫“子落奪”。這個舞蹈與貴州西部苗族小花苗支系的先民遷徙經(jīng)歷有關,舞蹈動作表達了祖先在遷徙途中披荊斬棘的過程。
為了解紀錄片的拍攝過程,傾聽片子拍攝背后的故事,本文作者采訪了導演盧鳳崗。
一、對民族文化有一份天然的熱愛
陳藝:請介紹下您和您的團隊。
盧鳳崗:我大學學的物理,畢業(yè)后在貴州省科學院新技術所工作了一年多。后來離開單位,成立個人工作室。因為從小喜歡畫畫,做過數(shù)字三維影像,因此對拍片子比較感興趣。
從1994年到2005年,工作室主要做廣告片和專題片,當時工作室只有3個人。從2005年起,與好友彭鍵共同注冊成立了貴陽華彩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最早我們和電視臺合作,拍廣告片。從2007年起,開始拍專題片、宣傳片。2007年至2014年期間,主要做政府及企事業(yè)單位的項目,做一些宣傳片。
2014年,承接了貴州電視臺唐亞平擔任總編導的貴州省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系列紀錄片《山脈人脈文脈》的加榜、大利、黃崗三個古村落的拍攝制作,從這一年起,公司全面轉型,主要從事紀錄片項目。影視設備(包括攝影、錄音、輔助設備)全面升級,拍攝的自由度打開了。
2014年拍攝加榜,完成《禾的故事》,拿了幾個獎:比如2016西津渡國際紀錄片節(jié)最佳攝影作品,2016“金熊貓”國際紀錄片節(jié)人文類最佳提名,《禾的故事》還參加了2016“金熊貓”國際紀錄片節(jié)優(yōu)秀節(jié)目展演;此外,2016年完成了《苗族古歌》《苗族獨木龍舟節(jié)》;2018年完成了貴州歷史題材八集紀錄片《川鹽入黔》,30集微紀錄片系列《紀錄貴州》;2019年完成第二批傳承人搶救記錄工作《苗族蘆笙舞——王景才》和《反排木鼓舞——萬政文》,王景才項目除獲得2019年象山非遺影展十佳作品外,還獲得多個影展獎項:國家圖書館記錄成果展觀眾最喜愛作品獎,入圍中國第三屆民族志紀錄片展等。木鼓舞則獲得2019第三屆深圳青年影像節(jié)最佳人文類作品,上海音樂影像志紀錄片節(jié)最佳提名;2020完成第三批傳承人記錄工作《八音坐唱——梁秀江》和《苗族刺繡——吳通英》,八音坐唱獲文化部2020傳承人記錄工作優(yōu)秀成果。2020還完成了微紀錄片系列《紀錄貴州》第二季共五十集;2021年將完成《山脈人脈文脈》第二季的九集。
陳藝:真是碩果累累。回到《王景才》這部片子,創(chuàng)作背景是什么?是什么契機讓您有了創(chuàng)作這個題材的念頭?
盧鳳崗:非遺代表性傳承人搶救性紀錄系列片是國家級非遺文化傳承人的記錄項目,國家非遺司委托給國家圖書館來做這個事情,而我們公司參與投標拿到了其中的項目。
早幾年前,國家就有一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共享工程”指的是充分利用現(xiàn)代高新技術手段,將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積淀的各種類型的文化信息資源精華以及貼近大眾生活的現(xiàn)代社會文化信息資源,進行數(shù)字化加工處理與整合;建成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中華文化信息中心和網(wǎng)絡中心,并通過覆蓋全國所有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和大部分地(市)、縣(市)以及部分鄉(xiāng)鎮(zhèn)、街道(社區(qū))的文化信息資源網(wǎng)絡傳輸系統(tǒng),實現(xiàn)優(yōu)秀文化信息在全國范圍內(nèi)的共建共享。其中,國家圖書館是主要的整合實施機構,而把歷史文化的非遺內(nèi)容拍成文獻片、建立資源庫、與社會共享是其中一個內(nèi)容。
陳藝:拍非遺系列僅僅是項目的需要呢還是另有什么原因?
盧鳳崗:我自幼生長在鄉(xiāng)村,對民族文化有一份天然的熱愛。貴州農(nóng)村,尤其是黔東南的古村落,特別美,處處是天然的山水畫:小橋流水古樹古屋,村落里的人物也特別樸實,認識不認識的人見面都會點頭微笑。所以我非常喜歡進入貴州的鄉(xiāng)村拍片,我把自己拍的這一類片子叫做鄉(xiāng)土紀錄片。近幾年我拍的片子,比如《禾的故事》《木鼓舞》《滾山珠》其實就是“農(nóng)耕稻作三部曲”,對應講《禾的故事》—稻之作,《木鼓舞》—稻之舞,《滾山珠》—山之魂,這三部剛好表達了典型的貴州山地農(nóng)耕特點。而我創(chuàng)作的比較個人化表達的片子《蹌山魁》《大利》,則是直接表達小時候鄉(xiāng)村生活印象的紀錄片,是我自己的鄉(xiāng)戀情結,表述當下,回溯過往。
我們除了拍有國家資助的項目,也找一些重點的有特色的古村落來拍。這幾年,古村落在變化,有的被改造,有的被搬空。我們深入古村落,拍攝那些在變化或者是將要消失的影像。一些少數(shù)民族節(jié)日,我們聽到也會趕過去拍。作為一個影像記錄人和記錄觀察者,我有一個情懷,想把這些東西拍攝記錄下來,把正在變化或者即將消失的古村落、非遺景象,搶救性地記錄下來。從2011年起這樣的記錄工作沒有斷過,因此積累了大量的素材,現(xiàn)在這些記錄過的古村寨的現(xiàn)狀和過往比較,大多已經(jīng)面目全非。遺憾的是不能對所有古村落做視頻記錄。
二、紀錄片最重要的是拍到節(jié)點鏡頭
陳藝:看來拍非遺系列、拍鄉(xiāng)村紀錄片是您樂于去做,并且投入熱情的一件事,再舉例談談拍片的過程。
盧鳳崗:前面我提到,最早是參與貴州省文化廳聯(lián)合貴州電視臺唐亞平工作室推出的《山脈文脈人脈》100集貴州古村落系列人文紀錄片拍攝。計劃是拍攝貴州100個古村落,把它們記錄下來。選取的標準是古村落要完好,保持它的古樸,不要有磚房等現(xiàn)代建筑。包括村寨的節(jié)日習俗、民族民間文化、個體生產(chǎn)生活都要有記錄。例如我們拍的加榜,那里的梯田非常漂亮,村寨很美,村寨里有非遺、有鬼師、有節(jié)日,很完備。比如一年中較隆重的新米節(jié),時間在秋收之后,節(jié)日的內(nèi)容豐富,如跳舞、喝酒等,平時你看不到村里的婦女喝酒,節(jié)日這一天她們挑著酒,從早上一直喝到晚上。我們的片子就拍到了這些,其中包含了人類學、社會學的內(nèi)容,片子把這種活態(tài)的情況全部記錄下來。
這個系列從2014年啟動到2015年,一年中做了10條片子,我們完成了其中的3條。之后我們自己參與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的投標。最開始的一個項目是《苗族古歌》,是比較龐大繁雜的體系,并不好做。《苗族古歌》是我?guī)ш犗氯ヅ牡模蟾排牧藢⒔肽陼r間。當時我們采用的是真正的田野拍攝,沒有找當?shù)卣亲约喝づ臄z對象。我們前后采訪了三四十個唱古歌的村民,其中包括國家級傳承人1名、省級傳承人2名,縣級傳承人1名,總共4名傳承人,其他還有大約30名非傳承人演唱者。就是這樣把這個苗族古歌采錄下來的,采錄了幾十個小時的素材。內(nèi)容包括婚禮、喪葬、農(nóng)事等,也涉及不少節(jié)日,像鼓藏節(jié)、蘆笙節(jié)、跳花節(jié)等等。由于苗族古歌表達的內(nèi)容非常豐富,涉及苗族生產(chǎn)生活諸多方面,因此需要大量的苗族節(jié)日與生活習俗的影視素材來支撐,好在我們之前拍攝了不少涉及民族民間習俗及節(jié)日的片子,在這個時候就發(fā)揮了作用。影片制作完成后,沒有大的修改,一次性就通過。我們參與的信息資源共享工程系列的第一個片子《苗族古歌》就這樣順利地完成了。
接著又接下另一個片子《獨木龍舟節(jié)》。這個片子也有難度,題材同樣宏大。開拍以后,才感覺到其中的辛苦。其中單單拍伐木做龍舟,就拍了一個多月。每天早上七八點鐘到位,跟拍工人制作龍舟到晚上七八點鐘才能收工。每天開著機器一直拍,拍片素材時間在6小時以上,不能離開,就怕拍丟了最關鍵的環(huán)節(jié)。做紀錄片最重要的就是要拍到節(jié)點鏡頭,指關鍵的敘事節(jié)點鏡頭,對一個習俗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有一個關鍵的行為是這個段落事件的節(jié)點,錯過了就是失去了關鍵表述與呈現(xiàn)。比如制作龍舟有個細節(jié),即需要把龍舟翻過來。為了拍到這個關鍵的敘事節(jié)點鏡頭,需要隨時開著機等待。而且拍攝講究有頭有尾,從第一塊板開始鋪就要拍到,如果最重要的起頭板沒有拍到,那么對這部片子來說是很遺憾甚至是失敗的。拍《獨木龍舟節(jié)》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才把項目做好做完整。
陳藝:接下非遺傳承人的項目之后,您一般會做什么?除了導演,您同時也是管理者。
盧鳳崗:在拍一個片子之前,我們要做田野調查,去找到故事、找到人物。怎樣找到這個人呢?首先找村寨,比如除了指定的寨子外,剩下的我們自己去找。好寨子的標準是:寨子里有好的非遺事項,保存了完好的節(jié)日。有些寨子有原生態(tài)的外觀、古樸的建筑,但因受現(xiàn)代文明沖擊,原先古老的文化基本沒了,淡了。所以,找到村寨里的人物、找到寨子里的非遺文化事項,研究它的節(jié)日,需要花費不少的時間做調查。一旦找到合適的寨子,探索它的文化事項和人物,就可以定下來,根據(jù)村寨和人物的不同情況設定和規(guī)劃要拍攝的內(nèi)容。然后就可以進入拍攝了。
找到傳承人,專注地挖掘他,跟他相處,跟他熟悉。因為他的傳承事項是與他的生活息息相關的,他為什么有能力去傳承這個項目?我們在拍攝時會觀察這些,包括他與周圍人的關系等等。有項目—找人—拍人,這個過程就是我拍這類項目紀錄片的一個流程。
陳藝:拍片子時,作為導演,您的介入拍攝多嗎?
盧鳳崗:在拍攝中會遇到意想不到的情況。比如拍王景才,他因為2011年摔斷腿后就不再跳舞,也沒有教徒弟了。剛開始采訪他時,很多東西他都想不起來。后來我想,他是跳滾山珠的,讓肢體語言來激發(fā)他的記憶如何?于是讓他的兒子及學生來跳舞蹈,然后把這些舞蹈動作列成表記下來給他看,他就逐漸想起來了,并一一說出這些舞蹈的原始含義。在交流的過程中,王景才還談起他去少林寺學武、雜技團學藝的經(jīng)歷。這樣就把他關于滾山珠的記憶一下子打通了,完成了滾山珠動作含義講解的口述片。這個口述片除了王景才的講述外,還一邊做示范動作一邊對他的舞蹈技巧和含義作講解,是對他口述內(nèi)容的活態(tài)補充。我覺得非常好,算是一個創(chuàng)新。
回想起來,我們的介入拍攝對片子的完成有一定作用。如果不去干預,可能就拍不到一些有故事性的畫面。我們是根據(jù)項目的特點做的一個改變和調整。從他的身上開始讓他自己來挖掘。這個過程很有意思,就像在拍一個劇情片、故事片,我們是讓王景才演他本人,比如告訴他讓他修蘆笙,給他一個啟發(fā),讓他去做。我們只是給出一個事件,其他的任何行為都不去干擾。我拍王景才時,他到山上放牛,我會讓他跳一段舞蹈或者耍一段武術,他會隨性地動起來。我們在拍片時,有時候會捕捉到一些鏡頭,就像神來之筆,那是要靠運氣。我的經(jīng)驗是:拍一個人,如果你需要有故事情節(jié),可以想辦法去創(chuàng)造,但是不要造假。更不要做違背常理的事。要呈現(xiàn)真實的狀態(tài)。
拍攝一個村寨的生活,一般周期是一年。拍攝對象千差萬別,比如王景才和他的家人在鏡頭前表現(xiàn)自如,狀態(tài)很舒服,似乎拍攝者的介入沒有干擾到他。但是《木鼓舞》里的萬政文又不一樣。過去有很多攝制團隊拍過他,他自己都會導演了,常常自己導演自己。剛開始我還沒識破他的“伎倆”,拍了半天,他突然告訴我他在演自己的生活。再比如我們拍的克蘭寨村一個唱儺戲的村民,他身上很有戲,一開口唱就會很投入,非常有意思。有的民間能人語言能力非常強,信口就來,往往出乎拍攝者的意料。
三、希望觀眾能從片子中找到自己喜歡的部分
陳藝:《王景才》這部片子拍完后,您本人的評價如何?有哪些亮點?哪些遺憾?
盧鳳崗:片子是采用敘事性的手法來拍的。片子里記錄了“登高望遠”“穿越荊棘”等舞蹈語言。舞蹈語言里有與農(nóng)耕有關的動作,也有模仿自然界生物的動作。片子里挖掘出了30多個動作,讓滾山珠立體、豐滿、有厚重感。滾山珠可以說是“山里面長出來的舞蹈”。
王景才生活的鄉(xiāng)村遠離城市的喧囂,寧靜而純樸,這樣的環(huán)境怎么會創(chuàng)作出如此精彩的舞蹈呢?圍繞這個思考,我一點點挖掘王景才這個人物,這也是我制作該片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關于片子,要說出彩的地方,我印象深刻的鏡頭有這樣幾個:
之一:放牛坡場景。片子一開始,在山上放牛的王景才一邊打拳,一邊用樹枝當?shù)谰呶杵饋怼D贻p的時候,王景才曾經(jīng)去少林寺學了一年武術,還去雜技團當了兩年演員。這些功底,讓王景才顯出和普通農(nóng)夫的差別來,再加上熱愛,才能夠創(chuàng)作出別具一格的“滾山珠”。
之二:修蘆笙吹蘆笙場景。王景才拿他的蘆笙去找修理師傅。蘆笙一修完,他就開始吹起來。先在屋里吹,又到院壩里邊吹邊舞。修完就吹奏,這些情節(jié)不是我讓他做的,是王景才自發(fā)吹的,我做好觀察和拍攝記錄就行了。這個場景來得自然,王景才身上的藝術細胞這時被激發(fā)出來,同時他身上浪漫的氣質也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
之三:王景才去看師傅。這個鏡頭是我們完全按照當時真實的狀態(tài)來拍攝的。王景才八十高齡的師傅視力不好,處于半盲狀態(tài),老人家從床上起身,衣服也沒穿好。但一提到蘆笙,眼睛一亮。這樣的敘事,既真實又有真情,既厚重又有分量。
之四:結束鏡頭。王景才在長滿荒草的訓練場轉了一圈,他已經(jīng)不教徒弟,這組鏡頭表現(xiàn)一種英雄落幕的感覺。我的原定結尾就是這樣的,有點悲壯的意味。此時,插入他兒子也是他徒弟的教學畫面,表現(xiàn)滾山珠技藝有傳承,給人以希望。
談到拍片子的遺憾,整個拍攝是有節(jié)制的拍攝,比如說一個人,他身上有陽光的一面,也有陰郁的一面。有時候,一些涉及個人隱私的東西能更深層、立體地表現(xiàn)一個人物,但出于保護人物隱私的要求,你不能無底線地拍攝。這也是紀錄片作者往往糾結的問題:你的對象向你敞開了心扉,你又有了要保守秘密的負擔。曾經(jīng)有一次和馮艷導演交流,她說紀錄片人是有原罪的,就是這個道理。項目實施我們是按一個真實紀錄電影長片的標準來拍攝,最后提交的是一個30分鐘的短片。有很多敘事沒有用上,這也是我的遺憾。國家圖書館相關負責人曾提及將《王景才》改編成紀錄電影長片,假如這事能成,這個長片就有希望與觀眾見面。
陳藝:拍完這部影片,您對王景才認識如何?
盧鳳崗:苗族其實是非常浪漫優(yōu)雅的民族,勤勞樸實。王景才熱愛舞蹈,喜歡到骨子里。舞蹈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東西。他教徒弟時是充滿精氣神的,后來腿受傷不能教學之后,一下子寂寞下來。王景才是個執(zhí)著的人,有點一根筋。他對舞蹈的熱愛不帶功利性。本性是善良、樸實、講義氣的。可以說,王景才是真正的民間藝術家。
陳藝:從保護非遺傳承的角度來說,《王景才》這部片子傳達的信息如何?從影像的角度來說,片子的效果達到了嗎?
盧鳳崗:如果最后的成片保留50分鐘的長度,關于滾山珠的內(nèi)容就基本講清楚了。我們這次拍攝的關于滾山珠的講述,文本是完整的。為了這個片子,我們采訪了18個小時,擬寫了21萬字的文字資料。我們是100%的傳達,觀眾能接收到70%就算是基本傳遞完整了。
陳藝:那您希望影片給觀眾傳達一種什么樣的感覺?
盧鳳崗:我希望我的片子平實、平和,是一種自然流露和呈現(xiàn),觀眾看后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感。比如搞音樂的人會關注音樂,搞語言的人會關注語言。希望拍出的片子是大家的片子,觀眾能從中找到自己喜歡的那部分。
四、完成有分量好題材的紀錄片是所有創(chuàng)作者的理想
陳藝:談談您對非遺搶救性記錄的認識?
盧鳳崗:每個非遺項目傳承人都是寶庫,有一種說法是如果一個非遺傳承人走了,就帶走了一個非遺圖書館。因為非遺傳承人是用他的一生來做這樣一件事情。所以說搶救性記錄很重要,真正要做到搶救性記錄,就要深入田野,發(fā)掘深藏的寶庫,把它們盡可能地記錄下來。
陳藝:其實就算是針對國家級非遺傳承人,能記錄的可能也是部分,比如說侗族大歌,傳承人可能會唱300多首,但是能錄下一二十首可能就不錯了。對嗎?
盧鳳崗:對,只能是完成,并沒有記錄完。傳承人是一座圖書館,你只是進去借閱了一些書。所以說搶救性記錄只能記錄到它的藝術特點,記錄到它的代表作。舉一個例子,記錄王景才,我算是記錄得比較多的,我問他們有多少動作,他們說有上百個動作,但是我現(xiàn)在記錄下來的只有30多個動作。我們把他們當下能夠做到的所有的動作都記錄了。原來記錄的有35個動作,但有的動作不能完成,實際上最后記錄了28個動作,包含了當前滾山珠表演的所有動作。
陳藝:您拍攝紀錄片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完成了多少?
盧鳳崗:紀錄片來自于生活,紀錄片的創(chuàng)作源于生活中的真實題材,攝制完成一部有分量、好題材的紀錄片基本上是所有創(chuàng)作者的理想。我要做的就是一個虔誠的記錄者和觀察者,所以我認為“導演”的稱呼不準確,對紀錄片創(chuàng)作來說,稱為“作者”更恰當。目前我的創(chuàng)作還在學習和摸索過程中,我在做一些個人獨立表達的影像作品,已經(jīng)完成的有《蹌山魁》《大利》,《蹌山魁》是一個實驗性的作品。正在后期制作中的有《煤村》《母親》《小花兒和他的女兒》,這些也是我在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