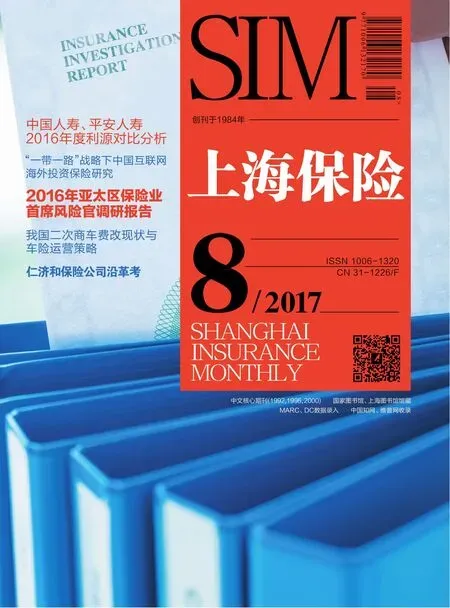行業聚焦
行業聚焦
1
8月8日21時19分,四川省阿壩州九寨溝縣發生7.0級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震中距離九寨溝景區僅39公里。截至8月13日20時,已造成500余人受傷,25人死亡,多處房屋倒塌。地震發生后,保險業迅速投入抗震救災,積極開展保險查勘和理賠服務工作。
各保險公司均于震后迅速啟動重大突發事件應急預案,及時聯系排查承保客戶情況,開通24小時地震理賠專線,多渠道受理報案,迅速開展保險理賠服務;同時積極配合各級政府及時做好應急搶險救援工作,防范次生災害。
2
7月26日,人保財險上海市分公司啟用“人身傷害賠償聯合調解中心”。據介紹,聯合調解中心是由該公司與楊浦區人民法院、楊浦區司法局共同打造的一體化理賠服務中心,突破了傳統人傷案件處理流程。此外,該公司還自行研究開發了“人傷遠程視頻調解平臺”,以聯合調解中心為支點,通過即時視頻通信,實時在線解決各區的調解需求,逐步構建完善人傷調解網絡,進一步方便被保險人和傷者就地完成調解。截至目前,普陀、楊浦、奉賢3家區級法院已實現遠程調解聯網。試點不到一月,人保財險已通過該視頻網絡系統成功完成20多個人傷案件的調解工作,支付賠款110多萬元。(陳賢)

3

7月16日,以“太平與您同行”為主題的太平人壽2017上海分公司客戶服務節在東方藝術中心開幕,為1000多位嘉賓獻上一場精彩的視聽盛宴。此次開幕式邀請了法國大型親子互動體驗魔法秀“超級喬尼”助陣,該表演為全國首演;“交通安全展示區”前,小朋友們跟著屏幕和工作人員一起認真學習交通安全知識;“涂鴉區”前人頭攢動,孩子們與家長共同描繪五彩繽紛的“太平樹”。據悉,隨著客服節的正式啟動,太平人壽還將推出“太平演說家”少兒才藝大賽等一系列客服節活動。(王雪瑩)
4
8月2日,人保財險上海市分公司與美團點評及40多家長寧區優質商戶舉行了食品安全責任險啟動儀式,“食品安全責任保險網上投保平臺”正式上線。該平臺一方面發揮“互聯網+餐飲”平臺的技術優勢,推動解決食品安全責任險投保率偏低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讓消費者獲得更多消費保障,并且利用平臺自身流量優勢,將更多消費者導向“參保商戶”,從而帶動商戶購買“食品安全責任險”的積極性,形成餐飲保障的良性循環。據悉,食品安全責任險首期試點對象為分布在長寧區的150家美團點評食品商戶。試點完成后,這一合作模式將在全國范圍推進。(陳敏華)
5

8月8日,太保安聯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與衛寧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共同開發的數字化理賠平臺上線運行,太保安聯“U享賠”服務隨之也在龍華醫院正式落地。“U享賠”是太保安聯為授權客戶提供的增值理賠服務。客戶通過在太保安聯APP中綁定該服務后,在“U享賠”的合作醫院普通門急診或住院就診,即可享受高效便捷的數字化理賠服務體驗。(陳賢)
6
近日,中美聯泰大都會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與“微醫”達成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大數據分析、定制化服務以及智能增值服務等多方面展開合作,為消費者提供便捷親切、體貼無憂的全方位健康管理解決方案。大都會人壽的客戶將可通過微醫平臺享受一系列健康管理增值服務,包括視頻問診、遠程會診、藥品配送、轉診預約、手術及住院綠色通道協助、預約掛號、導診咨詢等。而大都會人壽也將根據大數據分析及微醫平臺需求,為超過1.65億的微醫實名注冊用戶提供量身定制的保險產品及解決方案。合作初期,雙方將聯合推出“微醫都會健康保障服務”,涵蓋電話家庭醫生、高端醫療以及防癌保障等服務。(劉睿瓊)

7

日前,農銀人壽上海分公司在浦東新區世紀公園舉行“攜手農銀健康隨行”活動,以健步跑的形式揭開了第四屆客服節的序幕。農銀人壽上分全體員工參加了全程5公里健步跑活動,通過健康運動方式宣傳公司形象,展示農銀人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接下來在歷時兩個月的客服節活動中,農銀人壽上海分公司還將陸續推出少兒繪畫大賽、關注微信送流量、貴賓體檢等豐富多彩的活動,攜手客戶,做好服務,彰顯保險業的社會責任。(馬驍)
8
據最新的《財富》中國500強排行榜顯示,新華保險憑借穩健的經營與盈利能力名列該榜單第46位,這是該公司自2012年來連續第6次登榜。2017年上半年,新華保險共實現保費收入612.39億元,其中6月單月原保險保費收入達110.85億元,環比大幅提升71%。根據“十三五”規劃,新華保險將于2017年基本完成轉型,從2018年開始進入發展期。今年3月29日,穆迪和惠譽分別授予新華保險“A2”及“A”的保險公司財務實力評級,展望穩定。(李琬愔)
9
近日,在第十六屆全國大學生機器人大賽RoboMaster2017機甲大師賽全國賽上,眾安保險作為大疆無人機的戰略合作伙伴亮相。目前市面上多數無人機由眾安保險承保,如大疆無人機的DJI Care換新計劃。據介紹,DJI Care換新計劃是大疆聯合眾安保險為“曉”Spark、精靈Phantom系列、“悟”Inspire 2等系列無人機提供的售后保障服務。用戶購買DJI Care換新計劃后,在一年有效期內可享受兩次整機換新服務,每次只需支付一定的服務費,即可獲得全新或同等價值和功能的替代品。(匡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