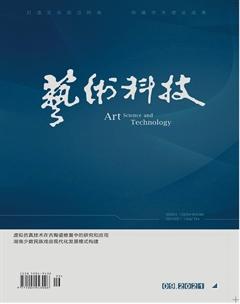探究電影《羅生門》中謊言背后體現的病態人性
宋傲 洪楚陽
摘要:電影《羅生門》是日本著名導演黑澤明的代表作。作為擅長通過電影揭露人性本質的大師,黑澤明將芥川龍之介的兩部短篇小說《竹林中》和《羅生門》合二為一,講述了一個關于人性的故事。本文通過解讀電影《羅生門》中人物編造的各種謊言,以及謊言背后的病態人性,探究《羅生門》中的人性主題,從中發現黑澤明對健康人性的真誠呼喚,并明確健康人性對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羅生門》;黑澤明;人性;病態
中圖分類號:J9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09-00-02
0 引言
“在大多數時間里我們甚至都不能對自己誠實”,這是影片中路人在羅生門下躲雨時所說的話。誠然,謊言是構成《羅生門》故事的關鍵,也是表達人性主題的核心。不同人物為了自身利益、掩飾真相說出的謊言,使案件變得撲朔迷離。然而,盡管人性中有本能的懦弱、欺騙、虛榮等病態因素,我們也不能因為謊言與黑暗否定人性中依舊存在的憐憫、同情、正義與良知。黑澤明對影片結尾的改動,正是為了挖掘人性中深藏的善與美。本文分析影片中的謊言與人性,旨在發現黑澤明對健康人性的真誠呼喚,明晰健康人性對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
1 《羅生門》角色的創立與謊言的產生
黑澤明的電影《羅生門》將芥川龍之介的小說《竹林中》與《羅生門》合二為一,故事內核為《竹林中》武士被殺的案件,敘述故事的地點則是暮色蒼茫、大雨滂沱的羅生門下。相比于原著小說,黑澤明為故事增添了主線,使故事更加連貫完整,同時在人物方面融入了自己獨具匠心的設計。在保留了主要人物武士、大盜和女人的基礎上,賦予了樵夫和云游僧人新的身份,他們不僅僅是慘劇的發現人,更成了完整事件的見證者與傾聽者,將不同口供中的謊言剔除,將真相串聯,還原了故事的本貌。除此之外,導演還增設了一個在羅生門下躲雨的路人。路人本與案件無關,導演卻通過他引出了樵夫對整個案件的敘述,并對人性的冷漠與自私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在電影結尾處,更是讓其化身“魔鬼”,剝去了棄嬰的衣服,展現了極致的惡。但是他的惡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1],是生存困境中“無奈”的選擇,這一選擇之中包含的道德意義也讓人們無從評判[2]。導演用惡叩問觀眾的同時,將生存與道德的抉擇丟給了觀眾,讓人們在沉默中陷入深思。這些角色的形象各不相同,卻共同織就了一幅人性的畫卷;他們的立場各不相同,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掩蓋真相。
故事原本并不復雜,只是審判時眾人為了減輕自己的罪惡、掩飾自己的過失,在敘述中夾雜了或多或少的謊言,讓真相變得撲朔迷離。黑澤明對原著進行再創作,撥開了真相上的層層迷霧。他借樵夫說出多囊丸和武士的決斗,絕非自愿,而是在女人的挑唆下開始的,決斗的過程也是彼此畏首畏尾的試探與流氓式的打斗,全無盜賊所說的那般精彩激烈。結果多囊丸僥幸戰勝了武士,之后卻因害怕快速逃離。至于武士妻子,早就不見了蹤影。然而,隱藏在人物背后的病態人性,最終促使了謊言的產生。
故事中,強盜知道自己殺了人,無法逃脫,便稱自己勇猛強悍,死了也能留個悍名。強烈的虛榮心令他在堂前撒了謊,說征服女人后本想放了武士,卻由于女人挑唆,在和武士光明磊落地“大戰二十三回合”以后,用長刀殺死了武士。女人是受害者,她自稱不堪丈夫蔑視冷漠的眼神,本想讓丈夫用短刀殺了自己,卻因為過度悲傷而暈厥,用短刀誤殺了丈夫。女人的丈夫,死去的武士,則借助女巫之口,痛斥自己妻子不貞不忠,連強盜都為之不齒,他也因此在心里原諒了強盜,可心中的憤恨令他痛不欲生,最后驅使他用短刀自盡。從他們各自的證詞中,我們仿佛能看出盜賊的強悍、妻子的剛烈、武士的自尊。然而每個人都在利用周圍的一切編造謊言、遮掩事實,活著的、被審判的,甚至是已經死去的人都在用謊言掩飾病態的人性。就連與事件無多大關聯的樵夫,都為了掩飾自己偷竊短刀的事實,謊稱現場沒有兇器。這樣的謊言生根于已扭曲的人性深處,以至于它的產生和真相一樣自然,難以分辨。
2 謊言背后隱藏的病態人性
人性就像河的另一面,總有暗流涌動的時候[3]。正如上文所述,每個謊言的背后,都隱藏著病態的人性。
2.1 貪婪虛偽、軟弱無能的武士
多襄丸讓武士進入竹林中的計謀并不高明,他僅僅謊稱有財寶,便將武士夫妻引向了竹林。之后,多襄丸趁機將其制服。財迷心竅的貪婪本性讓武士輕信了強盜的說辭,放松了警惕,引發了悲劇。
同時,武士又受貴族身份和武士道精神的束縛。身為武士,萬事名譽為先。作為貴族的他輸給了聲名狼藉的強盜,這個事實嚴重踐踏了他的名譽,為了保全名聲,他編造謊言,把錯誤全部歸咎于妻子的不忠不潔,想要推脫自己本該承擔的責任[4]。
武士本該是勇武智慧,但面對強盜拙劣的計謀,他卻輕易中招,以至于妻子被他人強暴時無能為力,而無能為力又成為他用來掩飾其軟弱的另一個借口。武士的亡靈借女巫之口訴說竹林案件時,謊稱自己因妻子的惡毒而悲憤自殺。他承認是自己的無能使慘劇發生在眼前,但是他的軟弱又令他在遇到事情時本能地逃避[5],他對施暴的大盜并無很深的怨恨,反而責怪受到侵害的妻子沒有“以死抗爭”,將自己的死亡歸結于妻子,將自己的軟弱隱藏于對妻子的憤恨中。
2.2 不忠的武士之妻
多襄丸與女人接吻時,黑澤明給出了一些女人的鏡頭,若有若無地展現了真砂從反抗到迎合,從痛苦到享受的完整過程。即便當著丈夫的面,她也從多襄丸的強暴中體會到了快樂。但女人敘述時,卻刻意回避了自己被強暴時的快感,強調是因為丈夫冷漠自己才失手誤殺。但實際上,妻子是挑唆盜賊與丈夫決斗的罪魁禍首,間接導致了丈夫的死亡,這些都是女人對丈夫不忠的表現,與她對自己“剛烈”的正面描述背道而馳。
2.3 虛榮險惡的大盜多襄丸
多襄丸被真砂女菩薩般的面容吸引,起了淫邪之心,不惜動了殺人的念頭,強暴了真砂,將真砂當作發泄自身欲望的工具。他用卑劣的計謀將武士夫妻倆騙進竹林中,當著武士的面強暴了真砂。但當他描述自己時,卻將自己形容得高大偉岸,聲稱自己完全征服了女人,并出于愛慕向女人賠罪,要娶其為妻子,放開武士同他公平較量,即使武士頗為厲害,也在大戰中敗給了他。之后的真相卻叫人失笑,原來大盜知道難逃一死,選擇用謊言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3 《羅生門》的創作背景與人性主題
電影開篇,雨中殘破的羅生門,使沉重感和壓抑感撲面而來[6]。不管是原著還是電影,都沒有點明故事發生的時代,但是我們不難看出場景布置和人物對話所體現的時代特點——兵荒馬亂、時局動蕩、民不聊生。而這樣的時代特點,也同樣契合影片上映時期的日本。黑澤明生于1910年,在他人生觀形成和確立的青年時代,正是日本歷史上的大變革時期,物質生產和社會制度的劇變導致其他方面嚴重脫節。日本在長期閉關鎖國后,受到了西方近代工業生產和資本主義思想意識的強烈沖擊,源源不斷涌入的新思想將日本與傳統強行割裂。封建的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念與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發生碰撞,使過去的社會結構和秩序分崩離析,而看似正確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西方思想背后,卻存在著唯利是圖、物化世界的屬性,這些與傳統相悖的精神更使人們無所適從。處在新舊交替時期的日本人,內心在斗爭中掙扎,又在掙扎中被腐蝕[7],變得愈發迷惘彷徨,尤其是日本戰敗后,負面情緒猙獰地生長、蔓延[8],人性在復雜的社會現實下愈發不堪,剛剛建立的價值觀念也支離破碎,現實社會在人性的病態與虛偽之下充斥著腐朽與絕望,精神世界的崩毀使人們無處可逃。
這樣的社會狀態,無疑讓武士階級出生、從小接受武士道德教育的黑澤明失望透頂,他對生命的本質和人的生存意義產生了懷疑[9]。面對日本近代化的嬗變,他不時體會到社會中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也一直觀望著人們在社會中的種種表現,從而發掘出更多有關人性的問題。痛苦滄桑又豐富多樣的人生經歷,使黑澤明得以創作出包括《羅生門》在內的眾多經典影視作品。這些作品無情地披露了人性中極致的黑暗,將陰影中的病態人性拉到大眾面前,讓人們避無可避。但是,黑澤明的目的絕不在于“揭露”,他實際上期盼著在黑暗人性之間散發出微弱光芒的“善”與“美”。在極致的黑暗中,一絲一毫的光亮都會顯得格外醒目,都會被人們當作救命稻草所攀附,使其從深淵里解脫[10]。就如《羅生門》結尾時和尚所說:“虧得你,我還是可以相信人的。”樵夫最后救贖般的行為,讓我們感受到了“善”的溫暖[11],同時也展現了黑澤明真正想表達的人性主題——幫助人們發現健康善良人性的可貴,拯救病態的人性,構筑起牢固的精神世界[12],重塑有良知的社會。
小說《竹林中》的案件撲朔迷離,而黑澤明增添的真相則闡述了無情的事實——人世黑暗邪惡,謊言無處不在。電影的重點并非探尋真相,而是表現謊言背后的病態人性。影片中,路人道:“撒謊是人之本性。”游僧卻說,是人性的脆弱帶來了謊言。長期行走于黑暗,使人們閉上了雙眼,而黑澤明安排讓樵夫抱走棄嬰,則使眾生睜開了警覺的眼,開始追求健康人性。“虧得你,我還是可以相信人的。”樵夫的善舉雖小,卻有振聾發聵之效。健康的人性是柔軟溫暖且極富感染力的善良與仁愛,支撐著我們追求精神信仰[13],讓人們不由得去追尋社會的美好,這也正是黑澤明作品的特點——在揭露、批判惡與病態的同時,又給予善與健康的期望。黑澤明用簡單的黑白,展現出最真實的人性,使我們被銀幕上的真實所撼動[14],告訴我們不應任由惡如藤蔓一樣自由生長[15],他揭示惡是為了突出善,如此人們才能進一步理解善的可貴。
4 結語
“美,人性,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放眼現實社會,世俗丑惡數不勝數,人們樂觀堅強的生存意志淡化了苦難,化解了矛盾,沖破了黑暗,超越了本身丑的面目,堅定地追求世間的美。在導演眼中,理想的社會能夠呼喚自然的人性,只有擁有追求美和健康人性的能力的社會,才能夠真正蓬勃發展,充滿生機,使每個人都從陰暗里走出來,沐浴在陽光下。
參考文獻:
[1] 張越.淺析電影《幽靈公主》中的生態美[J].漢字文化,2020(S2):162-163.
[2] 薛芳芳,徐紫薇.淺析門羅筆下女性命運的選擇——以《逃離》、《激情》、《播弄》為例[J].大眾文藝,2018(14):36-37.
[3] 陳心怡.淺析沈從文小說《邊城》中的生態美學意蘊[J].漢字文化,2020(19):53-54.
[4] 高涵晶.松本清張推理小說中的人性探析[J].漢字文化,2020(06):97-98.
[5] 袁晨霏.淺析《面紗》中吉娣愛情悲劇的必然性[J].漢字文化,2020(03):86-87,139.
[6] 楊元元.淺析電影《無名之輩》的藝術特色[J].漢字文化,2019(12):69-70.
[7] 繆依蕾.黃金枷鎖下的人性掙扎——論《金鎖記》中曹七巧命運的悲劇性[J].漢字文化,2020(07):66-67.
[8] 江逸華,劉雪芹.試論短片《Wrapped(毀滅)》中的生態美學思想[J].藝術科技,2020(15):47,50.
[9] 王學韜.一個干凈明亮的地方:虛無籠罩之下的個體生命追求[J].漢字文化,2020(19):120-121.
[10] 薛芳芳.唯有愛能治愈一切——讀羅賓·本韋《無法別離》[J].藝術科技,2019,32(05):187.
[11] 劉麗麗,徐爽.淺析《水形物語》中的再現藝術與表現藝術[J].大眾文藝,2019(10):16-17.
[12] 馬煥蘭.新時代條件下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J].黃河之聲,2018(21):143,145.
[13] 侯婷.論陳應松《像白云一樣生活》中的生態美學意蘊[J].漢字文化,2020(16):163-164,190.
[14] 羅奇瑩,陸文憬.論電影《熔爐》的現實主義美學[J].青年文學家,2018(32):149-150.
[15] 雷澳佳.淺析電影《驛路》中人性的隱惡[J].戲劇之家,2019(23):109,111.
作者簡介:宋傲(2000—),男,江蘇南京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影視藝術。
洪楚陽(2001—),女,江蘇南京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影視藝術。
指導老師:鄒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