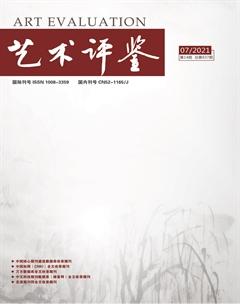略論周稚廉戲曲作品的敘事藝術(shù)
張雪純
摘要:周稚廉是明清文人傳奇的一個(gè)代表性人物,文學(xué)成就甚高,被時(shí)人認(rèn)為可與關(guān)漢卿、湯顯祖等比肩。周稚廉一生創(chuàng)作了大批優(yōu)秀劇作,然傳世的僅有《容居堂三種曲》,為清傳奇的代表之作。本文擬從敘事主題、敘事結(jié)構(gòu)、敘事模式、敘事時(shí)空和人物塑造等五個(gè)方面探討周稚廉戲曲作品的敘事藝術(shù)。
關(guān)鍵詞:周稚廉? 《容居堂三種曲》? 敘事藝術(shù)? 明清傳奇
中圖分類號(hào):J805?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 ??文章編號(hào):1008-3359(2021)14-0158-03
周稚廉的《容居堂三種曲》作為明清傳奇中具有代表性的優(yōu)秀作品,在敘事藝術(shù)上既有明清傳奇敘事方式的共性,同時(shí)也呈現(xiàn)出了其自身的獨(dú)特性。本文通過(guò)具體剖析《容居堂三種曲》在敘事主題、敘事結(jié)構(gòu)、敘事模式、敘事時(shí)空和人物塑造等五個(gè)方面的敘事藝術(shù),探討明清傳奇在敘事上的共同特色,挖掘出周稚廉戲曲創(chuàng)作的獨(dú)特性。
一、敘事主題
明末清初這一特殊的歷史時(shí)期造就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劇作家和戲曲作品,這些劇作家思想的復(fù)雜性充分體現(xiàn)在他們的作品之中。戲曲是他們針砭時(shí)弊、傳達(dá)思想的重要途徑,因而戲曲中的敘事成分受到了相當(dāng)大的影響。但我們?nèi)阅軓闹懈Q見(jiàn)這些作品中傳達(dá)出的關(guān)于思想教化、朝代興亡、情與理的碰撞等一系列敘事主題,這些無(wú)一不反映出戲曲家們?yōu)閼蚯楣?jié)化做出的不斷努力。
戲曲家們大都極為重視戲曲的教化功用,高明曾在《琵琶記》中提出“不關(guān)風(fēng)化體,縱好也徒然”。周稚廉的作品即是忠孝節(jié)義教化題材的代表之作。“明清傳奇呈現(xiàn)出了三種不同傾向:一是對(duì)教化主題的機(jī)械圖解方式,傳奇多從抽象的主題入手而相應(yīng)的地設(shè)置出故事情節(jié)與人物;二是通過(guò)傳奇反映生活的真實(shí),教化目的通過(guò)生活中的實(shí)例而自然地歸納出來(lái)”。周稚廉的作品顯然是第二種,不再是直白的教化,而是用帶有良好品質(zhì)的藝術(shù)形象施以隱喻,注重作品的故事性,逐步接近敘事化的戲曲創(chuàng)作。《珊瑚玦》中的晏繼光即是忠與孝的化身。他主動(dòng)進(jìn)入敵營(yíng),成為臥底,最終消滅賊人,后又努力找尋自己的親父。雖然也是以教化為旨意的作品,但整個(gè)故事符合生活邏輯,對(duì)人物的刻畫(huà)也鮮明生動(dòng),不再是單純?yōu)榱私袒茉斐鲆粋€(gè)生硬的人物與背離生活邏輯的故事。
周稚廉的作品還顯露出了對(duì)奸臣權(quán)相的批斗以及對(duì)普通民眾的深切關(guān)注。《珊瑚玦》中的晏繼光、《元寶媒》中的乞兒都體現(xiàn)出普通人身上的閃光點(diǎn)。《雙忠廟》則批判了宦官劉瑾的專權(quán)誤國(guó)。由于思想局限性,如周稚廉等一批戲曲文人終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出對(duì)平民的關(guān)切之意,卻無(wú)力解決現(xiàn)實(shí)中的實(shí)際困境。但盡管如此,對(duì)平民階層的深入關(guān)注使得作品的敘事性大大增強(qiáng),這樣的作品更易被觀眾接受。
二、敘事結(jié)構(gòu)
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提出了“結(jié)構(gòu)第一”。“至于‘結(jié)構(gòu)二字,則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賦形,當(dāng)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為制定全形,使點(diǎn)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勢(shì)。倘先無(wú)成局,而由頂及踵,逐段滋生,則人之一身,當(dāng)有無(wú)數(shù)斷續(xù)之痕,而血?dú)鉃橹凶枰印薄@顫O說(shuō)的結(jié)構(gòu)實(shí)際上就是對(duì)劇作的整體構(gòu)思與布局。在開(kāi)始創(chuàng)作之前,首先要形成一個(gè)框架。戲曲作品篇幅有限,不可能做到枝枝節(jié)節(jié)為之,即“立主腦”“減頭緒”。周稚廉的作品對(duì)結(jié)構(gòu)的運(yùn)用已臻成熟,大多采用雙線結(jié)構(gòu)。雙線結(jié)構(gòu)在明代已經(jīng)被戲曲家們使用,但當(dāng)時(shí)還處于初步階段,及至清初,戲曲家們有了前人豐富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支撐,在情節(jié)的架構(gòu)上更加完善自然。周稚廉的《容居堂三種曲》都采用了雙線敘事的結(jié)構(gòu)手法。《珊瑚玦》中,卜青與祁式分為兩條敘事線,劇作開(kāi)端兩人共同逃難,后在戰(zhàn)亂中離散。其后兩條線并進(jìn),又以祁式為主線。劇作最后晏繼光憑借珊瑚玦找到卜青,雙線合一。《元寶媒》中的兩條線索為乞兒與陶湘珠、乞兒與淑珠。《雙忠廟》則把舒真和王寶、石氏和廉小姐分作兩條線。縱觀這三部作品,雖為雙線敘事,但兩條線之間并非毫無(wú)關(guān)聯(lián)、各行其是,而是彼此穿插、相互聯(lián)結(jié)的。《元寶媒》中,乞兒先是救了淑珠,淑珠成為皇妃之后賜予乞兒元寶,乞兒以元寶救助湘珠,環(huán)環(huán)相扣。這種敘事手法使得傳奇的結(jié)構(gòu)變得更加復(fù)雜化,有利于展現(xiàn)更豐富的人物形象。
周稚廉的劇作在結(jié)構(gòu)手法上運(yùn)用了很多敘事技巧,既包含了對(duì)忠孝節(jié)義、懲惡除奸的教化,也同時(shí)兼顧了曲折、突轉(zhuǎn)、誤會(huì)及巧合等劇作技巧的運(yùn)用。誤會(huì)與巧合的劇作手法在戲曲作品中比比皆是,巧合促成故事發(fā)展,而誤會(huì)往往用來(lái)延宕。《珊瑚玦》中,卜青與妻子曾各持一半珊瑚玦作為信物,二人離散之后,卜青由于巧合剛好來(lái)到晏府做了馬夫,才得以被祁氏認(rèn)出。道具的運(yùn)用也是周稚廉結(jié)構(gòu)技巧的一大特色。珊瑚玦既象征了離散,也象征了團(tuán)圓,承載著主人公或喜或悲的情感。通過(guò)信物珊瑚玦貫穿起整部劇作,對(duì)傳奇作品而言無(wú)疑是巧思了。同樣是在《元寶媒》中,元寶作為整部作品的一個(gè)重要道具,與主人公乞兒的命運(yùn)休戚相關(guān)。乞兒因救助淑珠被皇上賞賜元寶,又因用元寶救助湘珠惹出是非,最終迎娶湘珠并成為了皇親國(guó)戚。元寶這一道具使得劇情得以不斷向前推動(dòng),下文將對(duì)此進(jìn)行詳細(xì)論述。
三、敘事模式
戲曲的“曲本位”思想使抒情性成為了戲曲藝術(shù)的一大主要特性,劇作家們借劇寫(xiě)心,在作品中大力抒寫(xiě)褒揚(yáng)或批判之情。在研究明清傳奇作品時(shí),往往對(duì)抒情成分的關(guān)注多于對(duì)敘事模式的關(guān)注。但明清時(shí)期的劇作家們實(shí)際上對(duì)故事模式做出了很多嘗試,其中運(yùn)用最為頻繁的主要有誤會(huì)與巧合、道具與超自然因素,這三種模式分別在周稚廉的劇作中得到了體現(xiàn)。
超自然因素為戲曲創(chuàng)造了更廣闊的敘事空間,實(shí)現(xiàn)了相當(dāng)大的創(chuàng)作自由,或?yàn)楣砘辍⒒驗(yàn)樯耢`,他們身上往往寄寓著劇作家們的深層思考。《雙忠廟》中,公孫杵臼與程嬰是雙忠廟里的兩位神仙,這兩個(gè)人物形象均取自《趙氏孤兒》,公孫杵臼與程嬰為救趙氏孤兒,前赴后繼的獻(xiàn)出自己的生命,是忠義之士的代表。《雙忠廟》將二人寫(xiě)作保護(hù)凡間具有忠義精神之人的神仙。在宦官劉瑾及其黨羽禍害舒真與廉國(guó)寶一家時(shí),公孫杵臼與程嬰感念王保救護(hù)舒真之子的忠勇,賜予其乳汁以哺幼嬰,又賜予放走廉小姐的駱善胡須,使其避于朝廷追殺。超自然因素的運(yùn)用即是將虛幻的事物展現(xiàn)出來(lái),讓其在戲曲空間里成為真實(shí)。這種手法往往易于被觀眾接受,這些虛幻的事物寄托著人們心底深處的殷殷期盼。在封建傳統(tǒng)的控制之下,戲曲家們無(wú)法自由表達(dá)出心中所思所想,只能借由神靈或魂夢(mèng)傳遞出來(lái)。
誤會(huì)與巧合是中西戲劇家們都慣常使用的一種敘事模式。所謂“無(wú)巧不成書(shū)”,隨著傳奇作品的不斷發(fā)展,新傳奇之所以能夠精彩于舊傳奇,很大程度上源于新傳奇愈發(fā)強(qiáng)調(diào)誤會(huì)與巧合的寫(xiě)法,為傳奇作品增添了故事性與曲折性。周稚廉的作品也采用了此種敘事模式,并且并不顯刻意。《雙忠廟》里,由于乳娘王氏自盡,徒留孤苦無(wú)依的廉小姐一人,恰好廉小姐遇到的是心懷良善的太監(jiān)駱善,廉小姐才得以逃脫。駱善與廉小姐以賣(mài)字畫(huà)為生,又剛巧與舒家公子相逢,舒家公子向駱善拜師學(xué)畫(huà),并與廉小姐成親。這一系列的巧合自然流暢,符合生活情理。《珊瑚玦》中,卜青與祁氏在戰(zhàn)亂中離散,祁氏進(jìn)入晏府,晏夫人多年無(wú)子,遂將祁氏之子過(guò)繼在自己名下,起名繼光,并予以撫養(yǎng)。若非晏夫人無(wú)子,晏總兵不會(huì)想納懷有身孕的祁氏為妾,晏夫人也不會(huì)過(guò)繼祁氏之子。繼光長(zhǎng)大后,一直努力尋找生父卜青。戰(zhàn)亂之后,卜青一路流散,巧合之下,行至晏府,在晏府謀求了一份喂馬的差事。卜青喂馬之后在檐下休憩時(shí)露出了自己的那一半珊瑚玦,被游逛花園的祁氏所見(jiàn),遂得團(tuán)圓。《元寶媒》同樣運(yùn)用了多重巧合。乞兒樂(lè)善好施,救助了父母雙亡的劉淑珠,淑巧遇天子,成為妃嬪,深得天子寵愛(ài)。乞兒一路輾轉(zhuǎn),與跟隨天子出巡的淑珠一齊來(lái)到大同,饑寒交迫的乞兒在此巧遇淑珠。淑珠向天子陳情,得到了一個(gè)元寶的賞賜。乞兒行至大名府時(shí),用天子賞賜的元寶幫助湘珠,且未料被誤以為偷盜官銀,所幸最終真相大白。誤會(huì)與巧合在這三部劇作中占比甚多,成為了情節(jié)發(fā)展的重要催化劑,是構(gòu)成“發(fā)現(xiàn)”與“突轉(zhuǎn)”的必要方式,為劇作家們編排故事創(chuàng)造了巨大方便。
道具的運(yùn)用也是周稚廉戲曲作品的一大重要特色。在《容居堂三種曲》中,《元寶媒》和《珊瑚玦》都使用了道具作為敘事手段,作品的生動(dòng)性和豐富性都得到了很大增強(qiáng)。道具的運(yùn)用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愛(ài)情劇中充當(dāng)男女之間情感聯(lián)系的信物,一類是貫穿全劇中心事件與主要情節(jié)發(fā)展變化的重要道具。《珊瑚玦》中,珊瑚玦是卜青與妻子祁式感情的信物,二人隨著珊瑚玦的分裂而分離,最終由于珊瑚玦重逢。借用珊瑚玦這一道具作為劇作的名字,隱喻了人物的悲歡離合。珊瑚玦也是構(gòu)建全劇的重要線索,若是沒(méi)有珊瑚玦,改名成韋正的卜青與祁氏恐難以相認(rèn),無(wú)法成就最終的大團(tuán)圓結(jié)局。這種金玉之類的配飾,或諸如手帕、絲絹等,常在才子佳人戲中作為愛(ài)情的象征。《元寶媒》中的元寶則是貫穿全劇重要轉(zhuǎn)折的重要道具。主人公乞兒的命運(yùn)與元寶緊密連結(jié),乞兒獲賜元寶,卻因用元寶幫助湘珠而身陷牢獄,生死攸關(guān)。天子意識(shí)到賞賜元寶行為的不妥,派人前去探訪,救乞兒于牢獄,并給乞兒和湘珠賜婚,可以說(shuō)乞兒是因?yàn)樵獙毑懦删土俗约号c湘珠的一樁良緣。不同于珊瑚玦所代表的象征意義,元寶僅作為發(fā)展延伸劇情的道具,作品的敘事性大大增強(qiáng)。
四、敘事時(shí)空
戲曲創(chuàng)作的最終目的是要實(shí)現(xiàn)登臺(tái)演出,而不能僅作為“案頭之曲”。舞臺(tái)演出的特性要求戲曲作品須高度關(guān)注時(shí)間與空間的調(diào)配。“明清傳奇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時(shí)間處理的總體特性是整體上加以極大地壓縮,而在局部段落中又往往加以渲染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這種壓縮和延伸是基于故事時(shí)間和情節(jié)時(shí)間完成的”。一個(gè)完整的戲曲故事時(shí)間長(zhǎng)度可達(dá)數(shù)年,但搬演到舞臺(tái)上時(shí)就要進(jìn)行大幅度壓縮。《珊瑚玦》中,卜青自與妻子離散到重逢歷經(jīng)十幾年的時(shí)間,劇作家需要對(duì)主要的事件情節(jié)多施筆墨,對(duì)無(wú)關(guān)緊要的事件予以刪減。寫(xiě)到卜青至軍營(yíng)尋找祁式,隨后情節(jié)直接跨越至十幾年后,中間的十二年全被省去,這樣的安排有利于敘事的集中性,使觀眾對(duì)故事保持興趣。
傳奇對(duì)空間的表現(xiàn)也很自由。不同于西方戲劇的寫(xiě)實(shí)性,戲曲在空間的控制上更為靈活,往往以演員的表演決定空間的轉(zhuǎn)換,不像西方戲劇一般將人物的活動(dòng)限于一個(gè)固定的場(chǎng)所,空間的轉(zhuǎn)換需要重新更換場(chǎng)景道具。但戲曲雖然在時(shí)空的設(shè)置上相對(duì)自由,卻也不是毫無(wú)邏輯的肆意轉(zhuǎn)換,而是根據(jù)劇情的發(fā)展變換時(shí)空。《雙忠廟》里,王保與石氏互為兩條線索,處于不同的時(shí)空。第九出《出乳》與第十出《依侄》在舞臺(tái)不變的情況下完成了空間轉(zhuǎn)換,二者全依靠于劇作家對(duì)戲曲人物語(yǔ)言和動(dòng)作的編排。
五、人物塑造
作為宣傳忠孝節(jié)義的教化之作,周稚廉三部劇作中的人物塑造難脫傳奇作品中人物形象類型化的窠臼。《雙忠廟》中的舒真與廉國(guó)寶均為至忠之人,他們不畏強(qiáng)權(quán),大膽進(jìn)諫彈劾奸臣,即便因此家破人亡。二人死后,舒真府上的王保和廉國(guó)寶府上的石乳母繼續(xù)將這種忠義精神發(fā)揚(yáng)下去,竭盡全力保護(hù)舒真與廉國(guó)寶的后代。《珊瑚玦》中的祁氏則是忠貞賢妻良母的典型代表。祁氏與卜青走散,遇到晏總兵,在晏總兵因無(wú)子欲納其為妾時(shí),祁氏秉持著“一女不事二夫”的思想堅(jiān)決不從,毫不畏懼晏總兵的權(quán)力。為了孩子更好地長(zhǎng)大,即使心有不舍,還是將孩子過(guò)繼給晏夫人,甚至不讓孩子知道自己是他的生母,如此隱忍了十幾年才得以一家團(tuán)聚。《元寶媒》中的淑珠與湘珠也是美好女性形象的代表。淑珠父母雙亡,得到乞兒的救助后一直感念于心,時(shí)刻不忘恩情。得到天子寵幸后仍舊不斷尋找恩人乞兒的下落。湘珠出身貧困,被迫進(jìn)入員外府為婢,員外想要霸占湘珠時(shí),湘珠因不舍母親獨(dú)自受苦,放棄逃走的機(jī)會(huì)。這樣心懷良善的人最終都收獲了美滿的結(jié)局,這也是中國(guó)戲曲大團(tuán)圓結(jié)局的常用模式。
《元寶媒》中的乞兒形象凸顯出了周稚廉人物塑造的獨(dú)特性。戲曲作品在營(yíng)造俠義之士的形象時(shí),很少會(huì)將俠義精神放在一個(gè)乞丐身上。乞兒雖行乞,但絕不向同一個(gè)地方行二次乞討。他行乞得來(lái)的錢(qián)物幾乎全被用來(lái)幫助其他需要幫助之人。這樣鮮明獨(dú)特的人物形象在過(guò)往的戲曲作品中是極為少見(jiàn)的,由此可以看出周稚廉在劇作構(gòu)思上的奇巧以及他對(duì)底層百姓的深切關(guān)注。
明清傳奇歷經(jīng)戲曲家們的不斷探索與實(shí)踐,在敘事藝術(shù)上顯現(xiàn)出了系統(tǒng)化的特征。周稚廉的劇作在集合傳奇藝術(shù)特色的同時(shí),在敘事結(jié)構(gòu)與人物形象的設(shè)置上均呈現(xiàn)出區(qū)別于其他作品的獨(dú)特性,是兼具文學(xué)性與舞臺(tái)性的優(yōu)秀劇作。
參考文獻(xiàn):
[1]劉志宏.明清傳奇敘事藝術(shù)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xué),2008年.
[2]李漁.《閑情偶寄》卷之三[M].北京: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1959.
[3]焦艷云.周稚廉及其《容居堂三種曲》研究[D].臨汾:山西師范大學(xué),2018年.
[4]劉其榮.周稚廉戲劇作品研究[D].淮北:淮北師范大學(xué),2010年.
[5]朱萬(wàn)曙.明清戲曲小說(shuō)評(píng)點(diǎn)的敘事理論建構(gòu)[J].中國(guó)高校社會(huì)科學(xué),2020(04):148-158+162.
[6]孫書(shū)磊.論明清之際戲曲敘事的類型化[J].齊魯學(xué)刊,2004(06):85-89.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為江蘇師范大學(xué)“研究生科研與實(shí)踐創(chuàng)新計(jì)劃”校級(jí)項(xiàng)目的階段性成果,項(xiàng)目名稱:周稚廉《容居堂三種曲》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2020XKT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