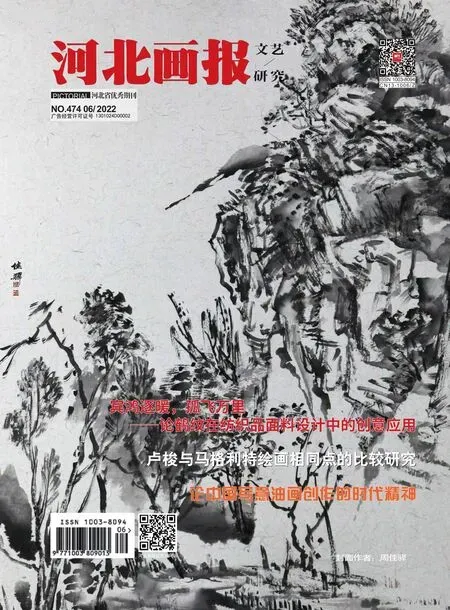試以席勒美育思想談舞劇《運(yùn)》中身體語言的融合運(yùn)用
張嵐月
沈陽師范大學(xué)
在眾多藝術(shù)起源的觀點(diǎn)中,有這樣一種觀點(diǎn)“游戲說——藝術(shù)起源于人類的游戲沖動(dòng)”。席勒在《美育書簡(jiǎn)》中,通過對(duì)游戲和審美自由之間關(guān)系的比較研究,首先提出了藝術(shù)起源于游戲的觀點(diǎn),認(rèn)為藝術(shù)是一種以創(chuàng)造形式外觀為目的的審美自由的游戲。“游戲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沒有實(shí)際的功利目的,它并不是維持生存必須的活動(dòng),而是為例消耗掉肌體中過剩的經(jīng)歷,并在自由發(fā)泄這種過剩精力時(shí)獲得快感。”[1]當(dāng)下,舞蹈美育的實(shí)施途徑存在多中形式,其中尤以對(duì)學(xué)生實(shí)施專業(yè)化的舞蹈訓(xùn)練為主,但并未發(fā)揮其應(yīng)有的作用。席勒的這一思想為我們當(dāng)下實(shí)施舞蹈美育的教學(xué)實(shí)踐方式仍有借鑒意義,而舞劇《運(yùn)》的編排與演出便是符合這種“審美自由”理論的有效實(shí)踐,具體體現(xiàn)在“以典型動(dòng)作‘規(guī)訓(xùn)’非專業(yè)舞蹈學(xué)生的身體”、“以生活化動(dòng)作地提煉弱化舞者專業(yè)度”、“對(duì)文化的感性與理性認(rèn)同”三方面。
一、以典型動(dòng)作“規(guī)訓(xùn)”非專業(yè)舞蹈學(xué)生的身體
舞蹈美育并不是僅僅指處于兒童時(shí)期、青少年時(shí)期的一種審美教育的方式,其在人的成長(zhǎng)過程中,甚至對(duì)于成人也會(huì)起到不同的教育作用——培養(yǎng)人的真、善、美。在大多數(shù)人的視野中,對(duì)舞蹈教育、舞蹈美育的認(rèn)識(shí)更多停留在舞臺(tái)上優(yōu)美的肢體和外表,并不了解舞蹈美育的真正內(nèi)涵到底是什么,大多數(shù)人認(rèn)為舞蹈并不是一般人能從事的了的一項(xiàng)高難度的活動(dòng)。其實(shí),在當(dāng)下的現(xiàn)實(shí)生活中,舞蹈成為許多人茶余飯后打發(fā)時(shí)間、發(fā)泄自己過剩精力的方式,或以舞蹈的形式來達(dá)到強(qiáng)身健體、抒發(fā)情感、人際交往的目的,還有。他們并不是來自專業(yè)藝術(shù)院校或有舞蹈專業(yè)教育背景的學(xué)生,而他們卻能夠用自身最真實(shí)的肢體動(dòng)作來表達(dá)自己內(nèi)心最真實(shí)的情緒與情感,一定程度上來講也是他們“游戲”的一種方式。雖然他們也會(huì)受到一些身體上的某種規(guī)訓(xùn),但相對(duì)于學(xué)院派的專業(yè)舞者來說,他們的肢體就如同席勒在“游戲說”理論中所概述的一般,是“自由”的。舞劇《運(yùn)》是由北京舞蹈學(xué)院和北京物資學(xué)院合作,由專業(yè)舞者和非專業(yè)舞者合作完成的一部作品。但筆者認(rèn)為,雖然有許多非專業(yè)舞者的參演,但并不影響整部舞劇的表演效果,反而為其增添異彩。筆者認(rèn)為演員的構(gòu)成是這個(gè)舞劇最主要的特點(diǎn)之一,因此筆者想要進(jìn)一步探索舞劇中的非專業(yè)舞蹈肢體與專業(yè)舞蹈肢體的關(guān)系,想明確除了加強(qiáng)專業(yè)化訓(xùn)練外,編導(dǎo)是如何將兩種不同的身體舞蹈融合到一起的。
具體訓(xùn)練過程中,教師并未采用系統(tǒng)化的舞蹈訓(xùn)練模式,而是提取舞劇中的主要典型動(dòng)作對(duì)非舞蹈專業(yè)學(xué)生的身體素質(zhì)與能力以及美譽(yù)度進(jìn)行強(qiáng)化訓(xùn)練。在舞劇中,大部分領(lǐng)舞與群舞之間都有相似的典型動(dòng)作,從而使群舞的作用不再僅是背景或者陪襯,而是推動(dòng)情節(jié)發(fā)展不可缺少的一步。比如,在第二幕——黎明,北京舞蹈學(xué)院青年舞團(tuán)演員蒲宇領(lǐng)舞為解放軍搭橋迎接他們的那一段。首先,巨大的木板分別立在舞臺(tái)中,像運(yùn)河畔千千萬萬戶的人家,蒲宇象征性的敲了幾扇門,他作為領(lǐng)頭人,召集大家為解放軍搭橋迎接他們到來。隨后,蒲宇的舞蹈語匯便與群舞的動(dòng)作語匯大致相同,背木板艱難行走,放下木板轉(zhuǎn)身等等。有了木板這一推動(dòng)情節(jié)發(fā)展的道具的存在,觀眾不會(huì)把眼神聚焦于舞者們的語匯上,更多的去關(guān)注木板被拼出的形狀以及舞者們與木板的關(guān)系。在第四幕——風(fēng)雨,最初群舞在暴雨中上下場(chǎng)口間的橫線調(diào)度,奠定了這一舞段壓抑與希望的基調(diào)。蒲宇穿梭在人群中,成為人群中的一員。他們一齊舞蹈,雖蒲宇是最前方的領(lǐng)舞,相同的動(dòng)作也表明他們其實(shí)有相同的經(jīng)歷。似乎在這現(xiàn)代社會(huì)中,愈見丟失運(yùn)河精神。而后青年舞團(tuán)演員汪子涵則以一位年邁的運(yùn)河志愿者的身份出現(xiàn)在舞臺(tái),步履踉蹌但又急迫,雖與亂了陣腳的群舞目的不同,對(duì)比明顯,但是此處舞者們都是在暴雨中奔跑,動(dòng)律較為一致。在暴雨的襲擊下,人們亂了陣腳。此處群舞緊張壓抑的氣氛為汪子涵的領(lǐng)舞營(yíng)造出急迫的大環(huán)境,汪子涵作為志愿者焦急地去指揮現(xiàn)場(chǎng),但群舞四處亂跑,沒有人聽他在喊什么。到底是領(lǐng)舞(專業(yè)舞蹈身體)復(fù)合于群舞(非專業(yè)舞蹈身體),或者群舞復(fù)合于領(lǐng)舞,其實(shí)并不重要,編導(dǎo)提取典型的動(dòng)作元素,讓非專業(yè)舞者更好的去認(rèn)識(shí)舞段的整體以及部分,從而更容易融入到“舞蹈化”的舞劇中,使兩種身體產(chǎn)生相互的認(rèn)同不再建立在非專業(yè)舞者經(jīng)受長(zhǎng)時(shí)間專業(yè)化的規(guī)訓(xùn)。
二、以生活化動(dòng)作地提煉弱化舞者專業(yè)度
大量生活化動(dòng)作的加入,進(jìn)一步弱化專業(yè)舞者的專業(yè)化肢體的主導(dǎo)地位,也是編導(dǎo)將兩種不同的身體融合的很好的原因之一。當(dāng)然,在舞劇中使用生活化動(dòng)作確實(shí)是很常見的形式,但在《運(yùn)》中卻有了新的意義與闡釋。這些生活化動(dòng)作地使用的確發(fā)揮了推動(dòng)劇情發(fā)展的作用,換言之,這些由非專業(yè)舞者作為主體所表現(xiàn)得生活化動(dòng)作并非是充當(dāng)背景烘托氣氛。在第三幕——“浪潮”中,改革開放沖擊之下,經(jīng)濟(jì)水平大幅提高的環(huán)境之下,新事物大量涌入的氛圍下,比起他們?cè)緢?jiān)守的運(yùn)河,許多人更喜歡跟隨時(shí)代潮流。北京舞蹈學(xué)院青年舞團(tuán)演員邵俊婷在劇中便是追趕潮流的一員,編導(dǎo)在此處相對(duì)弱化了邵俊婷的領(lǐng)舞,她與群舞相同,一起跳起Disco。在跳Disco時(shí),物資學(xué)院學(xué)生的群舞更加放得開、更加接地氣,由于他們并未長(zhǎng)期受到系統(tǒng)化、體系化的專業(yè)舞蹈訓(xùn)練,他們的身體動(dòng)作行為并未受到專業(yè)舞蹈地規(guī)訓(xùn),因此他們對(duì)于像Disco這樣的非學(xué)院派的流行舞蹈有著更加深刻的身體體會(huì),所以顯現(xiàn)出更加自然的身體姿態(tài)。身著現(xiàn)代服飾的他們與身著補(bǔ)丁布衣的男主角形成鮮明對(duì)比,女主角想要讓丈夫也加入他們的行列,但男主角頻頻拒絕了,但他拒絕的過程沒有過多舞蹈化的修飾,臉上緊張羞愧的神情、胳膊顫抖且堅(jiān)定地推開等這些生活化的動(dòng)作與在Disco的群舞和妻子邵俊婷在整體身體動(dòng)律上毫無違和感。
生活化的動(dòng)作,其實(shí)就來自于我們的日常生活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只要稍加修飾,如改變大小、改變速度、改變方向等,就能真實(shí)地傳達(dá)舞者的內(nèi)心情感。在舞臺(tái)上,這些生活化的動(dòng)作更是“游戲”中發(fā)泄他們過剩精力的真實(shí)存在的行為,它們更貼近于舞者與觀者的真實(shí)生活,更能喚起舞者與觀者心中對(duì)于運(yùn)河的認(rèn)同之感。舞臺(tái)上生活化的動(dòng)作,相對(duì)于純舞蹈動(dòng)作來說,其更加的自由,他們的這些真實(shí)體驗(yàn)而發(fā)的舞蹈動(dòng)作與行為更屬于“自由的沖動(dòng)”和“游戲的沖動(dòng)”,從而使這些舞蹈動(dòng)作熠熠生輝,且在整個(gè)作品中發(fā)揮出實(shí)際效用。并且,我們需要注意到,日常娛樂中的Disco對(duì)學(xué)生產(chǎn)生的實(shí)際教育價(jià)值微乎其微,而搬上舞臺(tái)的Disco卻有了嶄新的意義,其通過非專業(yè)學(xué)生的自然演繹而作為推動(dòng)整部舞劇故事發(fā)展的動(dòng)力。生活化動(dòng)作地提煉,使非舞蹈專業(yè)學(xué)生以相對(duì)專業(yè)的方式參與到舞蹈活動(dòng)中來,使他們?cè)谘堇[舞劇作品時(shí)既受到了舞蹈美育教育,而且也證明了這種打破專業(yè)化舞蹈的身體規(guī)訓(xùn)、舞蹈理論講授以及作為旁觀者的舞蹈鑒賞等傳統(tǒng)舞蹈美育的教育模式,轉(zhuǎn)而通過親身在場(chǎng)參與演繹舞蹈作品而受到審美教育的新型舞蹈美育教育教學(xué)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三、對(duì)文化的感性與理性認(rèn)同
“席勒認(rèn)為,造成人性‘破碎化’的原因是人性中‘感性’和‘理性’的分裂。‘感性’和‘理性’必須保持統(tǒng)一與平衡,人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2]由于北京物資學(xué)院坐落于京杭運(yùn)河旁,深受運(yùn)河文化教化與影響,對(duì)京杭運(yùn)河有特殊的情感。所以來自物資學(xué)院的舞者們對(duì)于京杭運(yùn)河有著很深的感情,他們更加了解運(yùn)河文化,可以說他們是新時(shí)代運(yùn)河文化的締造者和見證者,他們肩上扛有這份傳承和發(fā)揚(yáng)運(yùn)河文化的責(zé)任。雖然他們對(duì)舞蹈并不理解,并不擅長(zhǎng),可能也不感興趣,但并不代表他們不能將內(nèi)心對(duì)運(yùn)河文化的理解和情感以舞蹈的方式抒發(fā)出來。情感表達(dá)有很多種方式,只要他們的內(nèi)心有對(duì)運(yùn)河文化的堅(jiān)定信念,加之時(shí)間并不長(zhǎng)的“專業(yè)化”的訓(xùn)練,一定可以將他們內(nèi)心對(duì)于運(yùn)河的真實(shí)情感轉(zhuǎn)換為“理性”的舞蹈動(dòng)作而抒發(fā)出來。
整部舞劇中最能體現(xiàn)他們文化認(rèn)同感的舞段便是尾聲中群舞組成的那艘承載世代傳承運(yùn)河文化和運(yùn)河精神的船的舞段。此處群舞用身體共同凝聚成了一艘大船,男主角汪子涵作為清末運(yùn)河人和作為現(xiàn)代人的演員蒲宇共同掌舵。這就猶如賽龍舟一般,若想獲勝,必須同心協(xié)力;若想將這運(yùn)河精神發(fā)揚(yáng)光大,就必須經(jīng)過一代又一代地傳承與努力。從舞蹈語匯本身來講,他們?nèi)绻雽⑦@艘身體凝聚而成的船劃好,缺少不了動(dòng)作一致的訓(xùn)練。但對(duì)于沒有接觸過專業(yè)訓(xùn)練的他們來說,比起專業(yè)化訓(xùn)練,更重要的是他們由內(nèi)心的理解和認(rèn)同再作用到身體上,從而表現(xiàn)出的舞蹈更加真實(shí)、更加具有說服力和凝聚力。比起道具實(shí)物船,用身體發(fā)出的舞蹈動(dòng)作凝聚而成的船更加生動(dòng)、更具精神、更有靈魂,更能激起舞者們和觀眾們內(nèi)心對(duì)運(yùn)河文化以及中國(guó)文化的傳承欲望與熱愛之情。經(jīng)過真實(shí)的感受,從內(nèi)心生發(fā)出的認(rèn)同,去豐富肢體的內(nèi)涵;再由有內(nèi)涵的肢體去更好的展現(xiàn)心靈,這樣內(nèi)外相互滲透的教化方式,一定意義上達(dá)到了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情感活動(dòng)和實(shí)踐活動(dòng)的統(tǒng)一,使演員們真正做到跳出的舞蹈所表達(dá)的意思符合自己內(nèi)心的真實(shí)想法,達(dá)到“理性”和“感性”的統(tǒng)一,使該作品能夠真正的體現(xiàn)出運(yùn)河文化的內(nèi)涵,而不是單純的完成任務(wù),更是一種以舞蹈的方式對(duì)學(xué)生進(jìn)行美育教育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xué)方法。
從舞劇的創(chuàng)作角度來看,以典型動(dòng)作“規(guī)訓(xùn)”非專業(yè)舞蹈學(xué)生的身體,以生活化動(dòng)作地提煉弱化舞者專業(yè)度,由內(nèi)而外心靈和身體的互相認(rèn)同(對(duì)文化的感性與理性認(rèn)同),共同造就了舞劇《運(yùn)》中專業(yè)演員和非專業(yè)演員兩種身體的融合運(yùn)用,使該舞劇得到觀眾的廣泛認(rèn)可,并且達(dá)到了喚醒運(yùn)河文化、繼承和發(fā)揚(yáng)運(yùn)河文化的情感。不僅如此,從這種舞劇的合作方式以及社會(huì)功能來看,它還使得一個(gè)表演性質(zhì)的舞蹈作品擺脫了“被觀賞”外衣的限制,使之成為一種以“審美自由”和“‘感性’與‘理性’統(tǒng)一平衡”的人人參與進(jìn)正規(guī)舞蹈演出的參與性活動(dòng),其有效地以舞蹈的方式使普通高校的學(xué)生接受美育教育,為普通高校甚至基礎(chǔ)教育中舞蹈美育的教學(xué)方式與實(shí)踐方式提供借鑒和參考。
- 河北畫報(bào)的其它文章
- 人機(jī)對(duì)話測(cè)試背景下的農(nóng)村初中英語口語教學(xué)策略探究
- 基于抽象美學(xué)提升兒童設(shè)計(jì)思維的應(yīng)用與研究
——以“讓我們一起點(diǎn)線面”課程為例 - 基于數(shù)字媒體應(yīng)用型人才培養(yǎng)的現(xiàn)代版式設(shè)計(jì)發(fā)展與變革研究
- 《曲式與作品分析》研究生入學(xué)考試復(fù)習(xí)攻略與個(gè)案分析
- 淺談考古報(bào)告
——以《安陽殷墟郭家莊商代墓葬1982-1992》為例 - 行動(dòng)導(dǎo)向教學(xué)模式的設(shè)計(jì)與實(shí)踐
——以集裝箱運(yùn)輸實(shí)務(wù)課程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