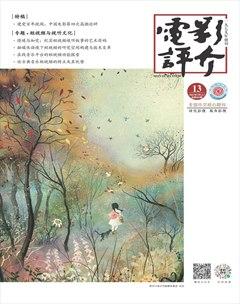村莊、故土與記憶:我國實驗性影片的詩意表達
杜宏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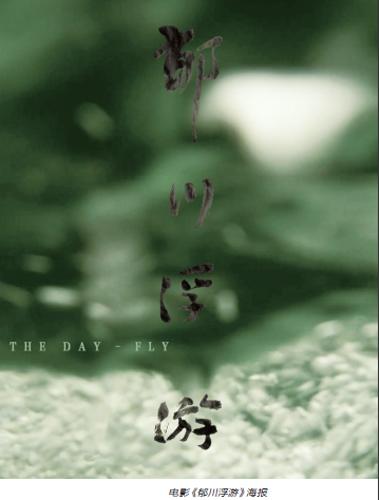
故土歷來是電影創作者鏡頭下的重要表達題材,對于中國的創作者們來說尤為如此。縱觀全世界,像中國這般在短短數十年間實現社會轉型、城鄉結構變遷的國家屈指可數。環境的劇烈變動會自然而然地在自覺的創作者心中營造出一種“反環境”。“反環境”的概念來自于知名媒介學者麥克盧漢,他試圖使用這個概念描述新媒介對于舊媒介的沖擊、舊媒介如何構成新媒介的內容以及新媒介所導致的感知偏差。[1]在麥克盧漢的眼中,“反環境”不僅是一個描述性的名詞,更是一種方法、一種工具、一種獨特的參照體系。此外,對于麥克盧漢而言,媒介的定義從來不應當只是狹隘的傳輸信息的工具。在他的眼中,公路、馬匹都可以被稱之為媒介。因此,將“反環境”這一概念套用至更為寬泛的社會語境中,并非牽強附會。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現,任何社會急劇變遷的時期都需要這樣一種“反環境”去洞察時代變化對于個體的心靈和感知帶來的影響。城市的興盛和鄉土的衰弱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是一種多數人的共識。當然,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無法描述復雜的社會現狀。事實上,鄉土的變化進程絕不僅僅是“衰弱”那么簡單。一方面,它受到現代化、社會發展等宏大敘事的呼喚,自覺地進行著一系列的變遷,另一方面,這些變遷往往與傳統相悖。這便構成了巨大的張力以及親歷者們的陣痛。
因此,電影創作者們將鏡頭對準故土和村莊,展現故鄉的種種元素也不足為奇了。在創作者的眼中,這些歷程絕不是自然而然的。它必然伴隨著人在精神狀態上的種種彷徨,這是社會形態的變化對人的感知的刺痛。意識到這一點,創作者們才能更加接近這個時代的本質。在《郁川浮游》中,主人公余中便是這么一個身處轉型期的存在。影片的大多數篇幅都在呈現郁川的種種風貌,對故事近乎只是三言兩語的帶過。而這種捎帶學生氣的拍攝手法卻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種“反環境”,能夠令觀眾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體會“故土”在今天的內涵,以及生活在故土上的人的面貌。在《路邊野餐》中,導演畢贛則用40分鐘的長鏡頭再現了一種頗具傳奇色彩的追溯,將詩意與個體的過往完美交融。本文將以這兩部影片為例,試分析我國實驗性影片對故土的詩意表達。
一、《郁川浮游》:夾縫之中的人
《郁川浮游》是由邵然執導,胡紅曦主演的影片。它講述了在2007年夏天,千島湖一個叫郁川的地方修建水庫,一個身患塵肺病的石匠回到那里,將母親的墳遷進公墓的故事。在郁川,他回憶起母親被迫上吊的慘案,發現自己的一生都生活在至親死亡的陰影里;適逢仇人刑滿出獄,他決定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為所有事情做一個了斷。影片的片頭由一組黑白色調的影像組成。導演先是將鏡頭對準屋外一個棄置浴缸中的蜉蝣生物,再通過鏡頭的緩慢推移,逐步展現出周遭的環境與人物:這是一棟農村的私房,一個男人無聊地坐在屋前,一個老人坐在屋內,帶著與他相仿的神情,隨后鏡頭一切,伴隨著旁白,一個女人與一條狗出現在銀幕之上,她先是撫摸它,然后又直起身子,看向鏡頭,不知在凝望誰。在這段時長2分鐘的畫面中,觀眾可以清晰地看到每個人的精神狀態。對于男人和老人而言,他們的身影與房屋是緊緊綁定,他們的表情顯示出他們的疲憊與低落,對于女人而言,她所處的位置遠離房屋。這種鏡頭下的位置關系表明,男人將與這片土地相連,但女人卻不一定。后續的影片果然也印證了這一點。男人——余中決定在郁川了卻余生,女人則與他離婚。她勸他離開,得到的回應是“我只會干敲石頭,我哪里都去不了”。而后,影片按照二十四節氣的順序開始敘事,分時段展現出余中的行動和精神狀態。
費孝通曾在《鄉土中國》中界定過中國人的鄉土性,他認為中國社會的基層是鄉土性的,這“鄉土性”帶有三方面特點:其一,“鄉下人離不了泥土”。鄉下人以種地為最普通的謀生方法,因而也最明白泥土的可貴。其二,不流動性。靠農業謀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并不是說鄉村人口是固定的,而是說在人與空間的關系上是不流動的,安土重遷,各自保持著孤立與隔膜。其三,熟人社會。鄉土社會的這種人口流動性緩慢的特點使鄉村生活很富于“地方性”特點,聚村而居,終老是鄉。所以,鄉土社會是個熟人之間的社會,這才有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2]將這一點映射到《郁川浮游》中,可以清晰地看見余中、老豬、出租車司機、理發師等人身上的鄉土性。在影片所處的時代,單純依靠種地作為謀生手段已經過時,但他們仍然通過不同的方式與故土和彼此之間發生了強有力的關聯。就如余中在妻子送來離婚證明,要求他簽字時所說的那樣,他哪里都去不了。盡管世界變得前所未有的遼闊,余中卻只能夠停留在郁川。他的名字此刻也與他的行為構成了一種巧妙的互文:余中——愚忠。
究其原因,大概對于他們來說,故土發生過事情,并且這項事情意義重大,以至于他們的余生再也無法與其分割。余中母親的死將他拴在了郁川。他本以為是母親的墳墓束縛著他,讓他無法脫身,但興建水庫帶來的遷墳也沒能令他遠離郁川半步。從影片提供的人物背景來看,余中身患塵肺病,只會一門手藝,這自然是十分有力的依據。但這無法從根本上解釋他對于去觀看前妻所在劇團演出的猶豫。事實上,對于余中而言,任何的改變都是可怕的。在他的心中已經形成了濃烈的故土意識。核桃樹、石碑、水庫、浮在湖水之上的房屋,這些反復出現的要素構成了余中眼中的故土,也是囚禁他的牢籠。
將影片延展至更為廣闊的維度,余中所代表的絕不僅僅是他本身:一個因往事而固步自封的男人。從社會學的意義上來說,他是一個夾縫當中的人。故土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遷,就像那個主管當地水庫拆遷事務的大學生村官所言,郁川馬上就會變得和其他地方一樣好,但在當下,它仍然保有著傳統中的大部分模樣。現代化的進程尚未徹底實現,而傳統亦已經開始轉變,那么余中便成為了一個被夾在了中間的人。母親之死和故土的轉變互為表里。在影片所處的時段,變遷已然降臨,余中卻主動抵抗著這一切。他抗拒著改變,乃至于最終在面對仇人時放下了殺魚的刀,并說余中這個人已經死了。此刻,一種超乎于風景的詩意躍然而出。它滲透于余中為母親遷墳時和他人的對話,舅舅的兒子為他送別時吹響的口琴,最終在余中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無根之人時猛烈地向觀眾襲來。
千島湖作為影片中的另一大背景,它存在的功能也絕非僅僅是提供那些山巒淹沒在湖水中的奇觀。千島湖在影片中的反復出現不只是審美意義上的考量,更是導演對故土的追望和思索。千島湖的形成過程在影片的前半段曾通過電視新聞播報的方式予以呈現。水庫興建、當地人搬遷構成了時代的一幅縮影,當千島湖形成的一刻,曾經居住在此地的居民們的故土便徹底的失落。那他們的故土究竟在何處呢?導演借余中的自白表現了這一點:蛇、猴子、孔雀各自爬到山上,隨著水位的升高,它們永恒地留在了那里。不過蛇會游泳,孔雀會飛,它們為什么不主動離開呢?答案十分清楚:它們和影片中的人物一樣,選擇了固步自封。與余中形成對照的則是猴子,“只有千島湖的猴子是后來別人運上山去的。”他本有機會擺脫這一切,但他因為外力,即母親之死,永恒地留在了郁川。
在這種敘事當中,導演的故土意識方才顯露而出。故土遲早會像千島湖湖底的那些村落一般,被水淹沒,變得再也無法復歸。而余中卻只能像刻舟求劍的人一樣,徒勞地守在一個位置。同時,導演還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即余中舅舅的兒子。他的確是遠遠地離開了故土,但他也未曾得到過半分救贖。借用德國哲學家本雅明筆下歷史天使的形象,“他凝視著前方,他的嘴微張,他的翅膀張開了。人們就是這樣描繪歷史天使的。他的臉朝著過去。在我們認為是一連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場單一的災難。這場災難堆積著尸骸,將它們拋棄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來喚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補完整。可是從天堂吹來了一陣風暴,它猛烈地吹擊著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無法把它們收攏。這風暴無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對著的未來,而他面前的殘垣斷壁卻越堆越高,直逼天際。這場風暴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3]那么余中便是天使眼中的歷史的塵埃和尸體,他充分地意識到了這一切,但外界的力量制約著他,天使無法拯救他。他只能身處時代的夾縫,被傳統和進步這兩者共同擠壓,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死者,成為他自己口中“十八歲便死去了的人”。
二、《路邊野餐》:故土的另類時間
《路邊野餐》由畢贛執導,陳永忠、余世學、郭月等聯合主演。它講述了一個生活在貴州凱里的鄉村醫生,為了幫一個老女人送東西給她的舊情人以及尋找被弟弟拋棄的侄子,來到陌生的小鎮蕩麥,在這個亦真亦幻的小鎮中,他與逝去的愛人在一個神秘時空獲得重逢,并獲得撫慰的故事。如果說《郁川浮游》注重的是人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的話,那么《路邊野餐》的著力點則更加私人化和情感化。在《路邊野餐》中,故土的時間與空間被拆分、重組,最終形成了一個個體在其中獲得撫慰的場所,角色的設定也更加得奇妙:一個曾經的混混、赤腳醫生和蹩腳詩人。因此,《路邊野餐》詩意的抒發也更加自然和坦率:它直接借由文本與影像的交織來構造詩意。
在影片中,關于故土的呈現可以分為三個維度:文本、時間與空間。影片的片頭借用《金剛經》中的句子“過去之心不可得,現在之心不可得,未來之心不可得”指明影片的主題。故土之所以令人著迷,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不可復歸的性質,它在當下的不可得。和余中對于故土的執著一樣,陳升流連于凱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出于他對妻子的愧疚,對往日的懷念。陳升寫下的詩句根植于凱里,與凱里的氣候、風景和人文氣質密切相連。或者可以這么說,當陳升離開監獄之時,除卻故土,他一無所有。
此時,故土對于陳升開始分裂為數個不同意義上的存在。首先是作為文本上的故土,一個他通過個人的經驗和感受予以再度復現的凱里,其次是作為空間意義上的故土,一個他生活在其中的場域,最后是時間意義上的故土,它與過去、現在和將來相互交融,并直接指涉影片的主題。當陳升行至蕩麥這個虛構意義上的空間之時,三重維度上的故土開始交織,并經此呈現出與“不可得”截然不同的復歸性質。個人的傷痛除卻重返那片故土,沒有其他任何能夠給予撫慰的方法。
倒著轉的時鐘是影片對于其時間觀念最明顯的表述。它連通了不同時段的時間,重塑了陳升和故土的關系。當現實令人不滿,乃至造成實際上的傷痛之時,人便傾向于陷入懷舊的情緒當中。但懷舊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想象,它無法從人的腦海中抵達確切的現實。因此,導演畢贛在那段長達40分鐘的長鏡頭中大量采用了主體鏡頭,就是為了營造身臨其境的感覺。通往過去的道路已經悄然展開,但當事人尚一無所知。這種敘事方式加強了故土的不確定性,使它在現實意義中的失去和夢境意義中的獲得之間不斷搖擺。從這一點來看,故土的迷人之處可以被劃分為兩種:它的失落與復歸。蕩麥之旅成功地將文本中的故土搬移至實在界的空間和時間中,令陳升放下執念,走上了和余中完全不同的道路,同時它也為觀眾提供了一個詩意地進入凱里的途徑。
此外,如何令銀幕前的觀眾同銀幕中的人物感同身受,這是某些地域性極強的影片需要處理的一個重要問題。當影片題材涉及到對故土的呈現時,單純的風景的堆疊或許只能取到反效果。電影歸根結底還是一門敘事的藝術,從這個角度上來說,《路邊野餐》的手法是危險的。當觀眾不能以陳升的視角來審視凱里的風光時,那么影片就難免淪為一出旅游宣傳片。任何風景的意義都要由人來主動地賦予。故土必須要有人的介入才能抵達觀眾的內心,獲得他們的認可。從這個角度來說,是陳升個人的經歷賦予了凱里詩意。
結語
和故土相關的影片往往難免牽涉到個人的記憶。這也是上述兩部影片的切入方式:通過個體的經驗和感受,重現故土對于他們的意義。個人的記憶和故土的變遷相互作用,便產生了一種迷人的張力。無論是堅守抑或遠離,故土都以其獨特的存在持續地對人物施加影響。將這份影響放大、細致地呈現,詩意便出現了。但在當下,我國實驗性影片對于故土的詩意表達往往側重于詩意的展現,而疏忽了敘事內容。即便是廣受贊譽的《路邊野餐》,它在情節方面的薄弱也常常遭受詬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詩意和流暢的敘事也往往相互矛盾。詩要求對瞬間的捕捉,這是一種對現實某一刻的中斷,這不可避免地會掩蓋敘事意義上的進展。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如何做到不因文害意,創作者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參考文獻:
[1][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申[M].江蘇:譯林出版社,2011:76.
[2]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5.
[3][美]摩西.歷史的天使:羅森茨維格、本雅明、肖勒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