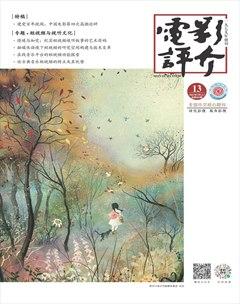文牧野現實主義題材長短片的主題表達路徑
望海軍 劉景港
一、美學路徑:缺憾美與當下感
一部好電影需要具有獨特的美學價值,而美學價值的產生則需經由美學路徑,即美學路徑是直抵故事深層主題的重要通道。不同導演會在自己的創作經歷中總結最具特色亦最有效的美學表達路徑。綜觀文牧野的一系列作品,其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是不夠完美的邊緣群體,故事結局總是余留一股淡淡的哀傷氣息。人物與情節的不完滿并未削弱作品的藝術價值,反而為其制造出獨有的缺憾美。這種缺憾美學導向的是對現代人生存危機的思考,是對活在當下之生存觀的強調。
(一)人物之缺憾
文牧野電影中的人物在人性方面幾乎無可指摘,他們雖不是偉大的英雄,卻都具有令人贊嘆的人性美;同時,這些角色往往具有某種性格缺陷,這便使其具有真實性,且能引起觀眾共鳴。不完滿人物的塑造從正面或反面揭示了生活之真諦:于當下存留,則于當下生產意義。
《石頭》是文牧野初次執導的一部劇情短片,無業青年與狗的相依為命、人和狗對土地的歸屬感在故事中一一展現。毫無疑問,這則故事中的主人公具有人性閃光點,他身無長物,卻愿意花大價錢為狗治病,其善良、單純的品質可見一斑。尤其應該注意的是,在人物為數不多的臺詞中,有一句話交代了這只名為“石頭”的狗的由來——“我也不知道什么品種,撿來的”,看似毫無感情的冷漠敘述凸顯主人公人性之善良。按照這一思路走下去,這似乎應該是一部人帶著狗走出困境的勵志故事,但導演顯然意不在此,主人公近乎完美的品質需要被打破、需要缺陷。于是在短片開頭,主人公的出場并無任何光輝可言,他居住在破舊的土坯房子里,周遭的老式物件顯露其窘迫,房子外圍墻壁上大大的“拆”字預示著生活的某種變故,一人一狗只能進入城市謀生。這時出現了一個新的空間,即城市中的租房。這個空間依然破舊,畫面里墻壁上的石灰掉落在地板上,簡單到近乎簡陋的陳設在主人公的注視下漸次展現,而人與狗席地而睡的場景似乎與前一空間的臟亂差形成了某種呼應關系。從兩個空間的相似之處可看出主人公對生活的消極態度,這種隨意甚至讓他懶怠于為自己打造一個稍顯舒適的床鋪。主人公的生活態度作為反面典型突出了“當下感”這一美學主題,瞬息萬變的現代世界需要人們對當下與自我的尊重和關注。
影片《我不是藥神》中的程勇則被視作白血病病友的救世主,從前期以賺錢為目的倒賣藥品到后期為無錢買藥的凄慘患病者而堅持,程勇轉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完美圣人。但這完美之中便無一點缺憾嗎?顯然不是,早年靠賣保健品為生的程勇一身落魄,甚至對妻子大打出手、毫無情緒控制能力,在與妻子和律師談話的那場戲中,他甚至想對律師動粗。在與劉思慧交往的過程中,程勇的好色特質更是展露無遺。然而,性格缺點并不影響其人性中的美好與善良,相反,我們可以將此種缺憾作為切入點走進人物的真實內心與故事的終極主題世界。
(二)情節之缺憾
文牧野短片的結局方式近乎相同,讓觀眾覺得故事并沒有結束,看上去好像沒有一個明確的結局,他善于用一個相對比較溫情的結局來彌補故事本身的絕望感[1]。
《我和我的祖國》“護航”篇中,宋佳飾演的女飛行員憑借優秀的應變能力、豐富的飛行經驗和極高的團隊責任感完成了任務,結局停留在主人公的微笑弧度里,也停留在男性飛行員對女主人公表達敬意之時,仿佛一切遺憾都在這樣的結局里被彌補。然而這種奉獻式的結局成功背后的運作機制究竟是什么?為何女主人公失去了領飛巡航機會卻仍舊不失完滿?這便是文牧野的高超之處,他用一種個人意義上的缺憾成就了集體意義層面的完美。當女主人公自我夢想成為遺憾之時,一切行動為國家、為他人的鮮明主題被凸顯出來,如此便將故事中的缺口打造為了一個具有藝術特色的風格化特征。
與之類似的是《戀愛中的城市》,在這部由多個短片集合而成的影片里,文牧野執導“布拉格”篇,他同樣為身處布拉格的主角設置了一個充滿遺憾但又余韻悠長的結局。為父親遺愿而走遍世界的瀟灑女孩與街頭混混的偶遇,已然超越常規邏輯中的戀愛定理,但卻產生了獨特而奇妙的浪漫感。素不相識的主人公在這座文藝氣息濃厚的城市里對彼此萌發悸動,相識、相戀繼而相守是每一對有情人的目標,然而當導演在悠長而緩慢的弦樂伴奏中設計出一場離別的戲份,這個故事便格外令人回味。值得注意的是最后兩人分別的場景——呼嘯而過的列車帶走女主人公的身影,當男主人公遙望著戀人的離去,他的面部表情是放松、釋然的,甚至帶了些許笑意。對于這個飽受地頭蛇欺凌的少年而言,能夠保護并且傾聽自己所愛女孩的秘密未必不是一種完美,那么在這完滿結局里的分別不過是微不足道的遺憾。對于女主人公又何嘗不是如此?她的前路必須走完,因此必須離開,但她在這座城市中感受到的美好會始終存留。當列車開走,人們繼續自己的生活,結局的缺憾凸顯了主人公對當下生活的關注與理解。只要正在生活,即使是當下的分離也是物哀之美。
《我不是藥神》同樣通過結局的缺憾美凸顯了“活在當下”這一主題。劇情推至后半段,已經成為老板的程勇選擇重新前往印度為患者購買格列寧,并以低于成本價的價格銷售。在這一刻他已經做好了舍生取義的準備,結局必定會充滿缺憾,但主人公卻選擇不問前路風疏馬聚,只顧當下救世仁心。當他坐在囚車里時,觀眾或許會為這法不容情的結尾發出無限感慨,但街道上的白血病人紛紛脫下口罩向其表示敬意時,充滿不甘的結尾仿佛被程勇活在當下的勇氣填平。
二、鏡頭路徑:飽和與稀釋
法國著名學者德勒茲(Deleuze)認為,景框可被劃分為兩種類型,即飽和與稀釋。飽和鏡頭是“寬熒幕和景深攝影,使各自獨立的給定內容多樣化……稀釋鏡頭則將整個重點置放于單一客體上”[2]。文牧野將飽和鏡頭與稀釋鏡頭相結合,打造出不失美感又足夠真實的藝術特色,通過不同鏡頭展現復雜而深刻的主題。
根據德勒茲的定義可知,飽和鏡頭中蘊含多重客體,前景與后景交叉出現,增強影像的層次感,通過眾聲喧嘩般的囂鬧進一步深化故事主題。在2011年的短片《金蘭桂芹》中,文牧野通過展現兩個東北老人一天的活動揭示了陪伴與友誼對老年人的重要性,其表達路徑正是依靠對飽和鏡頭的精妙把握。短片開頭一分鐘里,金蘭來到桂芹家中為她檢查電視,此時熒幕以寬幅度呈現,左邊的掛歷和右邊的老式立柜打造出一個對稱結構,位于中間位置的電視機首先進入觀眾眼簾。當兩位老太太走向電視,她們便成為了前景,作為中心的電視機在縱深基礎上被推往后景,桂芹的離去再次使電視機重新獲得焦點位置,但當金蘭擦電視機時她的身體又再次將其推向后景。如此一來,電視機作為陪伴機器所象征的意義便忽閃忽現——它確實作為桂芹的“伙伴”存在于這個空間中,但金蘭的出現又使它的陪伴屬性被取代,于是鏡頭中的這個主要客體時而顯現、時而隱沒。所有的客體交雜一處,不僅使電視機與金蘭的位置產生了復雜意義,從而推演出“陪伴”這一主旨,而且令觀眾感受到飽和鏡頭多元化的復雜美感。短片結尾處頗有深意,兩位老太太相伴而坐,空間已然從桂芹家置換到金蘭家,但左側的風扇與右側的紅色窗簾依然使電視機位于對稱結構之中心。攝影機將兩位老人認真觀看的模樣納入其中,同時也將電視機中的人物納入其中,電視機正在播放《機靈小不懂》中的不懂老師與人探討“朋友,什么是朋友”。當鏡頭焦點置于這一行字幕時,影片主題也就呼之欲出——電視機中的人是朋友,電視機外、電影鏡頭內的人亦是如此。多層次的鏡頭將老人間的友誼刻畫得入木三分,揭示了陪伴和理解對于人的重要性。
電影空間系統是依靠攝影機取景,以二維銀幕為界,景框內包含了所有事物的空間的集合。電影畫面所呈現內容的取舍,是電影制作的最初要義……電影就是一種由運動幻想和縱深幻想產生的“三維”空間[3]。稀釋鏡頭通常會舍棄大部分無用客體,而將攝影機焦點置于一個主要部分,被關注的事物通常與故事內涵有著不易察覺卻又足夠綿長的聯系。例如,《安魂曲》的開頭,文牧野將手持攝影機對焦于男主人公,這是一位歷經滄桑的男人,他眉宇間閃動著狠厲氣息,嘴角和額頭上的擦傷預示著某種事故的發生。當鏡頭被男人帶傷的面龐所充滿,觀眾會對他的身份和經歷感到好奇。緊接著劇情正式展開,一場車禍帶走了他的妻子,兒子也因此躺在急救室里,人物的悲慘命運逐漸呈現,絕望感與宿命感充斥在二維銀幕中。需要注意的是,這一短片使用了大量稀釋鏡頭,男主人公的整個面部時常出現,其中不僅有悲苦絕望,到后期則又增添了出賣妻子尸體的掙扎無奈和救下兒子后的期冀。另外,短片結尾對冥婚場面的處理也以稀釋鏡頭為主——大紅色的紙人在熊熊烈火中燃燒殆盡,火舌自微小起而蔓延至整個鏡頭空間,明明是一場祭奠兩個年輕人死亡的場景,卻在這一暖調影像中獲得了某種涅槃新生的跡象,這新生指的是孩子的被救,也是男主人公對生活的重新認知。
三、敘事路徑:角色與時間的疊加
電影敘事是以日常生活經驗為核心,構成一個相對獨立、封閉的想象性領域[4]。在這一領域中,故事內核往往通過敘述過程被揭露,合適、新穎的敘事路徑更利于主題表達。文牧野擅長使用雙線結構的敘事路徑:一方面是角色的雙重疊加;另一方面是時間線的雙重疊加。不同路徑彼此重疊,最終在情節高潮處相遇,使敘述趨于完善。
(一)角色疊加
文牧野很多作品皆是短片,這意味著角色數量不可太多,必須適量才能使情節得以展開、形象得以立體。因此,他通常安排兩個主要角色,劇情也在角色的一來一往中和盤托出,達到流暢自然的陳述效果。
例如,《金蘭桂芹》的主要人物便是兩位老太太,從影片開始的相互吐槽到最后的相視一笑,她們各自的敘事路徑從遠離到趨近,最后指向導演著重渲染的主題。金蘭幫桂芹查看電視問題、擦電視柜到陪同交電費等一系列行為作為單線敘事,陳述著金蘭在二人關系中的主導地位,她往往是友誼兩端的付出一方,微有抱怨卻又甘之如飴。在她的敘事線條中,電視不重要、西瓜買不買也無甚關系,這些瑣碎行為背后的真正本質應該是老有所依的陪伴。而在桂芹的敘事線索中,事物仿佛超越了朋友存在,她的出場是為了找金蘭修電視機,往后的一切行動也是為了交電費,甚至于路上的西瓜也能使其敘事線陡轉。桂芹的單線敘事看似與金蘭的敘事核心遠離,實則其最終訴求同樣亦是陪伴。所以在結尾當金蘭說“留下陪我嘮會嗑”時,倔強的桂芹老太太轉頭一笑,二人內心皆是釋然的同時,兩條敘事線也就此重疊,指向友誼與陪伴的核心思想。
《石頭》這部看似只有唯一主人公的短片同樣采用了雙線敘事模式,只是另一條線索不比文牧野其他作品那樣明晰,于是便被潛藏為暗線。加入暗線敘事,增強了短片情節的吸引力,開拓刻畫角色的新空間[5]。男主人公從最初在農村蝸居到后來進城學習務工,他的行動與路徑完全展現在觀眾眼前。在這條敘事線里,被遺留下的鄉土似乎不值得被惦念,以至于影片過半,人們仍很難理解這個故事的真諦為何。在故事后半部分,暗線漸漸顯露,只是另一條角色暗線不再是人類,而是那只被叫作“石頭”的狗。當石頭進入城市后問題逐漸顯露,他開始生病、不吃不喝且沒有精神,故事圍繞著主人公付出僅有的錢財為狗治病甚至丟掉工作展開,最終他實在無力負擔治療費用,只能帶石頭回到老家。在這一片段里,原本無精打采的石頭在和暖的陽光下奔向那片荒蕪的土地,重獲生機。當石頭這一暗線敘述結束,主人公的敘述漸漸清晰,觀眾的疑惑亦隨之消散。狗的生病源于對鄉土的遠離,人的不適、對飲水機的泄憤同樣源于對故土歸屬感的喪失,安土重遷之主題在兩條明暗敘述線條中漸漸明朗。
(二)時間疊加
時間線的疊加敘事在文牧野作品中不算常見,但卻尤顯精妙。影片情節在不同的時間線中展開,雙重時間重合,最終將劇情推向高潮。
文牧野唯一一部長片《我不是藥神》,這也是一部極為顯示其功力的經典作品,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便是影片前半段與后半段所呈現的悲歡反差。故事開頭,賣印度保健品的程勇在頗具熱帶風情的伴奏聲中出現,這個失敗邊緣人的一舉一動都成為觀眾的笑料。接著他遇到白血病人呂受益,兩人的奇妙組合更是引人發笑,印度格列寧“商機”為程勇生活帶來了轉機。在這條敘述時間線中,主人公漸漸糾集黃毛、牧師、思慧幾人一同販賣印度格列寧,事情似乎正在往好的方面發展,但假藥販子張長林的出現卻將這條時間線生生截斷,劇情直轉急下,程勇猛然醒悟自己的行為觸發法律,于是將“商機”讓給張長林。可以看到,在上述時間線中,主人公對自己的未來走向是混沌未知的。當呂受益死后,程勇決定重拾舊業,在這條重新接續的時間線里,他低價賣藥給人們,最后甚至將范銷售圍擴大至外省,這些行為的背后隱藏著他對自己結局的了悟——終將為法所束,但卻愿意以一人之力喚起人們對這個病人群體的關注,繼而推動相關體制改革。兩條時間線,以呂受益的死為分界,但同時也在此處接續,程勇從不知自己將會怎樣到明明知道結局卻仍舊選擇賣藥,英雄主義式的崇高主題逐漸展露。
《我和我的祖國》“護航”篇中,導演最初使用正常敘述時間線,即女飛行員接受護航任務到完成任務,接著又在其中穿插人物從幼時到長大的時間線。兩條時間線交匯于她正式成為領航員、實現自己幼時夢想的那一刻,正常時間線中對隊友的奉獻、對集體的責任感,與穿插時間線中小女孩對理想的堅持與熱愛相互和解,最終表征故事主題——個人自我與社會集體的融合。
結語
文牧野是中國青年導演中的佼佼者,他擅長以靜默而溫情的鏡頭記錄邊緣人群的生活狀態,塑造極具個體風格的現實主義題材故事。作為一個以質量取勝的創作者,文牧野目前僅有五部短片和一部長片,但已足可見其不俗功力。他執著于拍攝真實且主題鮮明的影片,對故事內涵的把握極其細微,同時又以多種表達路徑建構藝術世界。雙重疊加的敘事模式、對立化的鏡頭運用技巧以及溫情與悲劇性相融合的美學色彩成為其系列作品之特色。
參考文獻:
[1]付湛元.淺議文牧野的長短片風格[ J ].視聽,2019(10):88-90.
[2][法]吉爾·德勒茲.電影1:運動-影像[M].黃建宏,譯.中國香港:遠流出版公司,2003:46.
[3]馬騰.空無空間與靜物影像——德勒茲對小津安二郎電影空間的評析[ J ].藝術當代,2017,16(08):36-39.
[4]陳林俠.凝視的理論嬗變及其與電影敘事的抵牾——以齊澤克電影批評為核心[ J ].中州學刊,2020(05):144-151.
[5]顧云驄.論《聊齋志異·辛十四娘》的敘事藝術[ J ].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6(04):7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