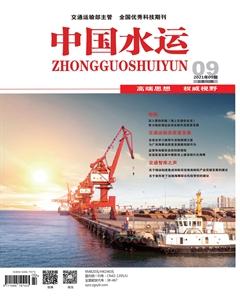清代京杭運河水馬驛考證札記
摘 要:自明初以來,一改元代海運為主、漕運為輔之政,以京杭運河為南北水路交通命脈,河運漕糧。清承明制,京杭運河及其漕運在溝通南北經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沿線城市、經濟、交通、社會等等藉此融為一體。直至清末,漕運或有衰落,河道或有湮塞,而京杭運河的交通作用仍然足夠突出,與此同時,沿線驛站隨之設置,在傳統郵驛與近代文報局、海關試辦兼辦近代郵政、大清郵政并存的時期,于沿線經濟、社會發展仍然是重要維系。在京杭運河于2014年申遺成功和當前大力建設京杭運河文化帶、加強運河文化傳承保護的背景下,對于清代京杭運河水馬驛站設置進行考辨,或能為遺產保護和文化建設提供一些有益的歷史依據。
關鍵詞:清代;京杭運河;水馬驛站
中圖分類號:G255.1?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文章編號:1006—7973(2021)09-0155-03
明朝會通河浚通后,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余里”[1]。自明初以來,一改元代海運為主、漕運為輔之政,河運漕糧,于是京杭大運河日益成為明朝南北交通命脈,也是其漕糧運輸、官宦兵丁與客商大賈往來的重要通道,誠如歷史所載:“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脈,血脈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2]。
清承明制,京杭運河沿線仍然廣置水馬驛站,期間或興或廢,先后設置共計50余處。清朝京杭運河及其漕運“在溝通南北經濟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沿運一線融為有機的整體。”[3]與前代郵驛相比,清朝京杭運河水馬驛站仍然兼具水路與陸路功能,仍然是以傳遞政府文書和軍事情報為主,同時也滿足了來往官吏、商旅、驛卒于中途停歇、食宿、更換馬匹、車船補給的需要。直至清末,京杭運河的發展日漸式微,但其交通作用仍然足夠突出,而沿線驛站隨之設置,在傳統郵驛與近代文報局、海關試辦兼辦近代郵政、大清郵政并存的時期,在客郵“客觀上刺激了近代中國郵政的發展”,又“在很大程度上侵奪了中國的郵政自主權”[4]的情勢下,于沿線經濟、社會發展仍然是重要維系。
1清代京杭運河水馬驛設置概況
按地理位置,京杭運河習慣上被分作七段,即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魯運河、中運河、里運河、江南運河,途經今北京通州至天津武清,歷河北廊坊、滄州、衡水、邢臺,至山東德州、臨清、聊城、濟寧、滕州、微山,復經江蘇徐州、宿遷、淮安、揚州、鎮江、常州、無錫、蘇州,至浙江嘉興、湖州,最后達于杭州。
清代京杭運河沿途所置驛站,多為兼具水路、陸路功能的水馬驛站。清代驛站之間距離設置,多承明制,以60里為準。有研究據明人黃訓《名臣經濟錄》等史料考證指出,明代京杭運河“兩相鄰驛站間的里程為60里的最多,70里的位居其次,其平均里程是71.4里,這既便于船只更換,又便于人員的休整與安頓”[5],時至清代,京杭運河水馬驛設置也大略如此。
《清代驛站考》可謂迄今為止大陸地區關于清代驛站最為全面的研究成果之一,為學界乃至社會了解清代驛站設置情況,提供了重要參考。其驛站考證以清代區劃為限,兼及水路驛站的路線、里程。考證指出,“由京城之東的通州沿運河南下,可至山東、江蘇蘇州和江寧、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各省省城。”[6]其中,京杭運河沿線水馬驛自北向南,計有通州潞河、通州和合、武清河西、武清楊村、天津楊青、靜海奉新、青縣流河、青縣干寧、滄州磚河、南皮新橋、吳橋連窩、德州良店、德州安德、德州梁家莊、武城甲馬營、臨清渡口、清州清源、清平清陽、聊城崇武、陽谷荊門、東平安山、汶上開河、濟寧南城、魚臺河橋、沛縣泗亭、嶧縣萬家、邳州趙村、宿遷鐘吾、揚州儀征、元和姑蘇、杭州武林諸驛。兩驛之間的距離,近則為40里,遠則為80里、90里,甚至110里至120里,然以60里、70里為常。
2清代京杭運河水馬驛可考數量
自明朝初年開始,即于京杭運河按一定距離大量設置水馬驛站。與明代相較而言,清代京杭運河沿線水馬驛設置或有革廢,所考者至少有50余處。
其一,《明宣宗實錄》記載,“通州至儀真,視水驛路程遠近增置之。宜蓋通州至儀真驛,俱洪武永樂中所設,路程無甚相遠,惟通州楊村至揚青,山東梁家莊至甲馬營,開河至濟寧州南城驛,比之他驛稍遠”[7]。
又,明人程春宇《士商類要·水驛捷要歌》記載:“試問南京至北京,水程經過幾州城。皇華四十有六處,途遠三千三百零。從此龍江大江下,龍潭送過儀真壩。廣陵邵伯達盂城,界首安平近淮陰。一出黃河是清口,桃源才過古城臨。鍾吾直河連下邳,辛安房村彭城期。夾溝泗亭沙河驛,魯橋城南夫馬齊。長溝四十到開河,安山水驛近張秋。崇武北送清陽去,清源水順衛河流。渡口相接夾馬營,梁家莊住安德行。良店連窩新橋到,磚河驛過又乾寧。流河遠望奉新步,楊青直沽楊村渡。河西和合歸潞河,只隔京師四十路。逐一編歌記驛名,行人識此無差誤。”[8]
按:龍潭驛,馬驛,治今江蘇南京棲霞區西北,清時屬南直隸江寧府句容縣,《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七四《江寧府二》載曰:“在句容縣盤龍山北。”《清代驛站考》引《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兵部·郵政·置驛二》載曰:“龍潭驛,馬二十五匹,馬夫十五名,差夫一百二名。”城南,一作南城,治今山東濟寧城區,《清代驛站考》引《雍正山東通志》卷十七《驛遞志》考曰:“南城水馬驛,在(濟寧)州南門外,驛丞管理。”夾馬營,一作甲馬營,治今山東德州武城縣甲馬營鄉,《清代驛站考》引《嘉慶大清會典事例·兵部·郵政·置驛一》載曰:“甲馬營驛,水驛夫一百六十一名。”
又,《士商類要》刻印于天啟六年(1626年),根據其記載,這一時期,自南京出發,不計龍潭驛,沿京杭運河北上達于北京,所歷水馬驛共45處。后世或革或改,至弘治年間,此線水馬驛所存計38處。魯橋、長溝、衛河、直沽4驛,《明朝驛站考》引成書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明會典》所載,此間已革。張秋,一作章邱,又作章丘,治今山東濟南章丘區,后改義倉。《道光章邱縣志》卷二《建置》載曰:“舊在縣治西南,今改義倉。”辛安、直河,嘉靖年間(1522-1566年)改為鎮。《乾隆江南通志》卷二十六《輿地志·關津二》載:“直河鎮,邳州東南六十里。明初,置直河驛,嘉靖中改置”;辛安,一作新安,治今江蘇邳州邳城鎮泇口街道,同卷載:“新安鎮,(邳)州西六十里,濱河接睢寧界。明初,置新安驛,嘉靖中改置。”
其二,據黃汴《一統路程圖記》卷一《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驛路》所載,從南京出發,自龍潭驛始,沿京杭運河南下,歷經丹徒京口驛、丹陽云陽驛、呂城驛、武進毗陵驛、無錫錫山驛、吳縣姑蘇驛、吳江松陵驛、吳江平望驛、秀水西水驛、崇德皂林驛、錢塘武林驛,至于杭州[9]。
按:《一統路程圖記》撰于隆慶四年(1570年),存呂城、松陵2驛,然據《明朝驛站考》引成書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明會典》所載,此間呂城、松陵2驛已革。應是《一統路程圖記》存其地名地址,而實際并未使驛。此線計水驛9處,結合《士商類要》所載水馬驛興廢,至弘治年間,存47處。
其三,弘治元年(1488年)朝鮮崔溥來華,自浙東走陸路至杭州,自杭州走水路至北京,“自武林驛過吳山(此間為水路中之陸路)、長安、皂林、西水、平望、松陵、姑蘇、錫山、毗陵、云陽等驛至鎮江府京口驛”,“自京口驛過揚子江(長江)至揚州府廣陵驛”,“過邵伯、盂城、界首、安平、淮陰、清口、桃源、古城、鐘吾、直河、下邳、新安、房村、彭城、夾溝、泗亭、沙河、魯橋、南城、開河、安山、荊門、崇武、清陽、清源、渡口、甲馬營、梁家莊、安德、良店、連窩、新橋、磚河、乾寧、流河、奉新、楊青、楊村、河西、和合等驛至通州潞河水馬驛。”[10]
按:崔溥所記,自武林至潞河,驛站共55處。其中,吳山為陸驛。長安驛,據《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十八《驛傳上》載:“在(海寧)縣西北二十里。唐貞觀五年置桑亭驛,八年改義亭驛,宋因之,元設水馬二站,至元間改長安水驛,明革。”魯橋、松陵2驛已革,直河、新安2驛已改為鎮,所考見上。然又興有開河、荊門2驛。
據此統計,至弘治年間,京杭運河所存水馬驛至少有50處可考。清代一度沿用上述諸驛,或至康乾時期,或至清末,《清代驛站考》對此皆有所考。其中沙河驛考,可參考“榆河驛”考。《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一《北直二》載,沙河“即榆河也”。另,彭城、泗亭、夾溝、桃源、儀征諸驛考證分別置于“榆河驛”、“銅山縣銅山夫廠”、“沛縣泗亭夫廠”、“邳州趙村驛”、“桃源縣桃園驛”、“儀征縣并水驛”名下。
3清代京杭運河水馬驛始設時間
關于清代京杭運河水馬驛始設時間問題,嘉慶朝《清會典》、《清會典事例》、《嘉慶重修一統志》等典籍文獻是用以考證的重要史料基礎。除此之外,清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賀次君、施和金點校本,中華書局2005年版)、明人陳循、彭時纂修《寰宇通志》及《乾隆大清一統志》等史料文獻也有特別的記載,對于部分驛站始設時間或沿革可考者,略作考證,以備查詢。
(1)彭城驛:《乾隆大清一統志》卷六十九《徐州府》載:“在銅山縣東黃河西岸。舊本在城南二里許,明正德中圮于水。嘉靖二十二年徙于此。舊有驛丞。本朝雍正十三年裁。《寰宇通志》卷二二、《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九存史事。
(2)邳州趙村驛:《乾隆大清一統志》卷六十九《徐州府》載:“在邳州南新泇口下。明萬歷四十四年置,南通直河口,北接韓莊閘。今有驛丞。”
(3)西水驛:《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十八《驛傳上》:“元初置,至正末毀於兵。明洪武元年四月,除授站提領為驛丞,明末毀。國朝康煕十一年知府王師夔重新之。”《寰宇通志》卷二四、《讀史方輿紀要》卷九一存史事。
(4)皂林驛:《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十八《驛傳上》:“嘉靖甲午御史張景以驛去府治不一站,長安驛偏迂,乃度中置。”《寰宇通志》卷二四、《讀史方輿紀要》卷九一存史事。
4結語
有清一代,京杭運河的興廢變化也有其特別性,漕運或有衰落、河道或有湮塞,與其相互影響。清朝京杭運河的興廢既與明清時期京杭運河的地形變遷有關,也與政府漕運政策及其方式的變化相聯,對于沿線城市及其經濟、社會的發展也帶來了歷史性的影響。2014年,京杭運河申遺成功;2020 年 11 月 14 日,南京博物院舉辦“大運河博物館聯盟”成立活動,大運河沿線32家博物館共同提出了“高質量推進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發展規劃,在如此大力建設京杭運河文化帶、加強運河文化傳承保護的背景下,對于清代京杭運河水馬驛設置進行考辨,或能為遺產保護和文化建設提供一些有益的歷史依據。
參考文獻:
[1](清)張廷玉.明史:卷八五[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明)明穆宗實錄:卷六八[Z].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3]葉美蘭,張可輝.清代漕運興廢與江蘇運河城鎮經濟的發展[J].南京社會科學,2012(9).
[4]金燕.英國郵政改革與社會變遷[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253-254.
[5]岳廣燕.明代運河沿線的水馬驛站[J].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
[6]劉立鵬.清代驛站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
[7](明)明宣宗實錄:卷一一三[Z].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8](明)程春宇.士商類要//楊正泰.明代驛站考·附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93.
[9](明)黃汴.一統路程圖記//楊正泰.明代驛站考·附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07.
[10]葛振家.崔溥《漂海錄》評注[M].北京:線裝書局,2002:7.
基金項目:南京郵電大學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申報培育課題“中國近代郵政電信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GPY219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