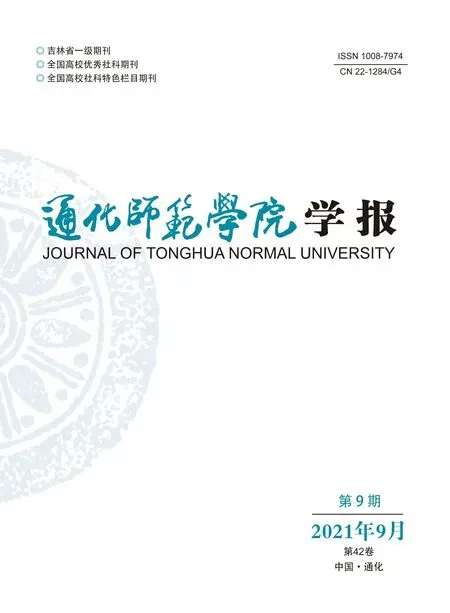唐鴻臚井刻石相關史實辨析
倪屹
現藏于日本皇宮的唐鴻臚井刻石(圖1),原本立于遼寧旅順口黃金山下。其銘文為:“敕持節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為記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關于這些文字揭示的歷史本事,中外學界一般認為,所謂“敕持節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即《舊唐書》所記唐睿宗先天二年(713年)出使渤海國冊封大祚榮的“郎將崔?”。但關于崔忻的本名、出使時間、出使身份、“井兩口”的含義等,目前仍有一些不同意見。本文試在鑒別吸收各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相關文獻,就上述問題再作進一步辨析。

圖1 日本拓本(錄自《唐鴻臚井碑》)
一、崔忻的本名
20世紀30年代,金毓黻先生編纂《東北通史》時提出:“案刻石之崔忻,即舊書之崔?,蓋?忻二字以形似而誤寫耳,自當以忻為正”[1]262。但時隔六十年后,王仁富先生則提出,刻石正文本應斷為“敕持節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為記驗。”“崔”即“崔?”的略稱,《舊唐書》的書寫并無錯誤[2]。其理由主要有三種:其一,忻本為動詞,“即開也”,“忻井兩口”即“鑿井兩口”。從上下文的修辭關系看,“忻井兩口,永為記驗”,不僅對仗工整,讀起來也朗朗上口,符合古文的行文特點。其二,《新唐書》記載文學家崔行功有孫“崔?”,雖然沒有說該“崔?”曾出使渤海,但從崔行功的卒年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推斷,其孫所處時代與唐朝冊封渤海國大祚榮的時間正相吻合。其三,唐代修史,層層校對,抄工都受過專業的培訓,寫錯人名的概率很低[3]。
杜鳳剛先生曾從語言學的角度對王先生的意見作過詳細的駁議,指出在古漢語中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忻井”一詞,“忻”字本身并沒有開鑿之義,“井兩口”本身也可以釋為“鑿井兩口”[4]325-340。除語言學的問題外,還有一個問題,王先生也始終沒有給出圓滿解釋,即崔、忻兩字上下分開斷句后,題刻者的自稱就成了存姓略名的崔某。而存姓略名的自稱,在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紀事碑刻中從未發生。既然崔忻作為出使者要為后人留下見證,“永為記驗”,按常理來說,題刻石碑時不可能不署全姓名。唐德宗時期袁滋出使南詔冊封異牟尋,在云南豆沙關留下的摩崖石刻不但一字不漏地記錄了使行團的所有名單,而且還在落款上特別注明“袁滋題”。
王先生過去曾舉明朝永樂年間留下的吉林阿什哈達摩崖石刻第一碑,作為“自謙而存姓略名”的例證,因為該石刻的正文只有“驃騎將軍遼東都指揮使劉”字樣,而沒有提到這位將軍的具體名字“劉清”。但據李澍田先生經過反復捶拓、制作模型得出的研究成果,該石刻的落款日期之下本來還有“甲兵李任記”五個字[5]。這說明所謂“驃騎將軍遼東都指揮使劉”,并不是題刻者的自稱,而是他的部下題刻時對上級使用的尊稱。查劉清以自己名義題刻的阿什哈達摩崖第二碑,上面則明確刻上了他的全職全名。
至于王先生所說的史書寫錯人名的概率,有人發現,不用說名字,甚至姓氏,精細校對過的正史也曾經寫錯。比如,曾在武則天萬歲通天年間(696—697年)參與平定契丹營州叛亂的名將陽玄基,《新唐書》[6]6196和《資治通鑒》[7]6521都寫作了“楊玄基”。幸虧陽玄基墓志的出土,我們才知道其“陽”姓本來源于籍貫“陽樊”[8]174。如果墓志一直沒有出土,我們根本不會察覺到古書的錯誤。《說文解字》等字典解釋?、忻兩字,皆稱異體同源,而從書寫經驗上看,同源字是人名中最容易混淆和誤寫的字。
我們非常尊重王先生質疑成說的學術勇氣,但目前來說,刻石建立者名字的正確書寫仍應是“崔忻”,而非“崔?”。
二、崔忻出使渤海國冊封大祚榮的時間
關于崔忻出使渤海國冊封大祚榮的時間,有學者認為古籍表述中存有疑點[9]。如《舊唐書·渤海靺鞨傳》稱:“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將崔訢往冊拜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統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歲遣使朝貢”[10]5360。《新唐書·渤海傳》載:“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統為忽汗州,領忽汗州都督,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6]6180。《資治通鑒》開元元年二月條記:“至是,以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為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7]6680。《冊府元龜·外臣部》玄宗先天二年條云:“二月拜高麗大首領高定傅為特進,是月封靺鞨大祚榮為渤海郡王”[11]11171。《舊唐書》給人的印象,似強調在睿宗先天二年,唐朝作出冊封大祚榮為渤海郡王的決定后,即派遣郎將崔忻執行使命。《新唐書》則似強調唐朝派使和冊封大祚榮均發生在睿宗先天的兩年間(即公元712—713年)。《資治通鑒》和《冊府元龜》似未記崔忻出使時間,只是強調唐朝冊封大祚榮的時間是在睿宗先天二年的二月。
造成上述理解歧義的根本原因在于,過去我們并未考慮史書所記冊封大祚榮的時間,究竟是以唐朝制定冊書的時間為準,還是以冊封使崔忻向大祚榮宣布冊命的時間為準。查《冊府元龜·外臣部·封冊》唐玄宗開元五年五月條云:
五年五月,冊命勃律國王蘇弗舍利支離泥為勃律王,冊曰:“維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五月庚子朔,一十七日丙寅,皇帝若曰:於戲!夫象賢踵德,匪直諸華;開國承家,無隔殊俗。咨爾勃律國王蘇弗舍利支離泥,卿歷代酋渠,執心忠肅,遙申誠款,克修職貢。謝知信繇其遠略,郭虔瓘所以足兵,行觀郁成授首,何止匈奴斷臂。是用命爾為勃律國王。爾宜善始令終,長奉正朔,寧人保國,慶及苗裔。往欽哉!其先膺典冊,祗朕寵命,可不慎歟?”[11]11172
天寶四載九月條云:
命罽賓國王男勃準襲父位,冊曰“維天寶四載,歲次乙酉,九月乙卯朔二十二日景子,皇帝詔曰:於戲!遠方恭順,襃錫宜優,累代忠勤,寵章斯及。咨爾罽賓國王男勃準,宿承信義,早竭款誠,寧彼下人,二蕃安靜。繼其舊業,萬里來朝,秉節不逾,懇懷彌著。愿情之至,深可嘉焉!是用冊命襲罽賓國王及烏萇國王,仍授右驍衛將軍。往欽哉!爾其肅恭典冊,保尚忠義。承膺於寵命,以率於遐蕃,可不慎歟?”[11]11179
天寶十一載正月壬寅條云:
十一載正月壬寅,冊骨咄國王羅全節為葉護,冊曰:“維天寶十一載,歲次壬寅,正月己卯,二十四日壬辰,皇帝詔曰:於戲!疇賞懋功,無隔於中外,懷荒恤遠,諒歸於典謨。咨爾骨咄國王羅全節,夙遵聲教,志尚忠節,作捍邊疆,勤效斯著。頃者以群丑撥動,方欲脅從,而忠懇不渝,始終彌固。言念於此,嘉尚良深。是用授爾驃騎大將軍,仍冊為葉護。爾其祗膺典禮,慎守封疆,貽慶子孫,受茲寵錫,豈不美歟?”[11]11179
從上引唐玄宗冊封勃律、罽賓、骨咄國王的冊書看,唐朝對冊封藩屬時間的認定,顯然并非界定在冊封使向被冊封者宣布冊命、履行冊封儀式的時間,而是界定在了唐朝皇帝制定冊書、決定派遣冊封使的時間。由此推知,唐朝所認定的冊立大祚榮為渤海郡王的時間實際就是制定冊書、派遣郎將崔忻出使渤海國的時間,即睿宗先天二年二月。《資治通鑒》《冊府元龜》與《新唐書》《舊唐書》的相關記載在文意上并不存在任何矛盾。
既然崔忻出使的時間我們可確定為唐睿宗先天二年二月,那么,根據鴻臚井刻石標注的題字日期,他建立刻石距自長安出發,間隔即為十五個月。這一時程與唐文宗時期幽州司馬張建章聘問渤海國的時程大致相當[12]。據《張建章墓志》[13],張自幽州出發前往渤海國都上京城,單程就用去了約一年時間。而張“歲換而返”,至仲秋八月方到幽州復命,返程也用了將近八個月時間。崔忻出使時,渤海國都城在現今吉林省延邊州敦化市;而張建章交聘時,渤海王城已遷到現今黑龍江省寧安市[14]。敦化與寧安雖有一段旅程,而長安到幽州也有相當的距離,所以崔忻自長安至渤海國,再返至旅順口黃金山刻石題詞總共用約十五個月的時間也算是在可能的范圍。
三、崔忻出使的身份和使命
鴻臚井刻石記載崔忻當時出使渤海國的身份為“敕持節宣勞靺羯使鴻臚卿”。所謂“靺羯”,原意本指靺鞨族。因為渤海國的主體和主導民族皆為靺鞨族,所以唐朝有時也把渤海稱為“靺羯”或靺鞨。有學者認為,刻石上的“靺羯”本來是指渤海最初的國號,《新唐書》所云大祚榮接受崔忻冊封,“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即指大祚榮從此不再使用原來的“靺鞨”國號而改用“渤海”稱謂自己的政權[15]。但馬一虹先生認為,“靺鞨”或“靺羯”只是中原王朝賦予靺鞨族的蔑稱,而非靺鞨族的自稱,渤海不可能以唐朝的蔑稱命名自己的國號[16]。鄭永振先生強調,與渤海同時代的新羅人崔致遠曾于唐乾寧四年(897年)代新羅王撰寫《謝不許北國居上表》,明確交代大祚榮建國“始稱振國”,其史料價值最具權威性,撰寫《新唐書》《舊唐書》者就靠這些信息才記錄渤海初創時大祚榮“自立為振國王”或“自號震國王”,因此渤海最初的國號只能是“振國”或“震國”[17]68-70。劉曉東先生特別指出,目前尚未發現渤海自稱靺鞨或“靺羯”的任何文獻史料,《新唐書》所謂“自是始去靺鞨號,專稱渤海”,只是對渤海國名由來所作的解釋,即“渤海”之名源自唐廷賜予大祚榮的“渤海郡王”封號,此前唐廷一直是以渤海立國的主體民族“靺羯”來稱謂大祚榮政權[18]。
查《冊府元龜·外臣部》敘述靺鞨國邑稱:“其地在營州之東二千里,南與新羅相接,越憙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編戶十余萬,兵數萬人”[11]11085。又,《土風》卷振國條云:“振國,本高麗(別種),其地在營州之東二千里,南與新羅相接,西接越憙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11]11112。這里的“靺鞨國”和“振國”,與《舊唐書》所記大祚榮政權初立情形——“其地在營州之東二千里,南與新羅相接,越憙靺鞨東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二千里,編戶十余萬,勝兵數萬人”[10]5360,無論文字還是實質內容幾乎完全相同。這種同一政權兩個名稱的記載方式,以及前引“是月封靺鞨大祚榮為渤海郡王”的措詞,說明可能“振國”或“震國”是大祚榮政權初立時期的國號,而后為增強統治下“靺羯”各部族的凝聚力,大祚榮又將國號改稱“靺羯”,直到崔忻履行完冊封儀式才專稱“渤海”。
事實上,“靺羯”或“靺鞨”的稱謂,只是古代中原王朝根據靺鞨語對靺鞨族名的一種音譯,本身并不帶有我們單純從漢字語源所理解的輕蔑或侮辱性質。我們知道,唐神龜元年(705年),中宗即位,曾“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大祚榮,祚榮亦以“遣子入侍”迎合,雙方就冊封渤海的主要事宜已經達成基本共識,只是因為此后“會契丹、突厥連歲寇邊”,才“使命不達”[10]5360。先天二年唐朝派遣崔忻出使渤海只是在張行岌原議基礎上履行必要的程序和儀式。假如“靺羯”并非雅詞,為渤海人或其他靺鞨族人所忌諱,唐朝授予崔忻的職銜不可能是“宣勞靺羯使”。從當時東北地區的形勢來看,大祚榮政權為謀求生存正推行兩面外交,一方面遣使朝唐“請就市交易,入寺禮拜”[11]11237,一方面又潛通突厥。而臣屬突厥的奚族在延和元年(712年)六月于冷陘重創幽州都督孫佺軍隊后[7]6672-6673,與契丹給幽州和安東都護府的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此時大祚榮一旦背棄此前與張行岌的約定,拒絕向唐朝臣服,整個東北極有可能出現失控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唐朝不能不考慮使用帶有輕蔑或侮辱意味的語詞稱呼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鴻臚井刻石所在的地方,即唐朝的都里鎮馬石山,學界一致認為是渤海使臣向大唐朝貢的必經之路。如果“靺羯”是蔑稱,頻繁向唐朝朝貢、“頗知文字和書記”[10]5360的渤海國對此不可能隱忍二百余年。
日本學者酒寄雅志考證鴻臚井刻石時,注意到《大唐開元禮》中的嘉禮有“皇帝遣使詣蕃宣勞”的式次[19]610,講的是唐玄宗如何對入朝蕃主進行“宣勞”的禮儀。即由鴻臚客館派使者,使者與拿著皇帝詔書的“持節者”同行,在皇帝沒有出御的場合,“持節者”近侍使者,在使者宣詔前,“持節者”脫“節衣”,以示皇帝的權限已委派給使者。據此,他對照刻石銘文“敕持節宣勞靺羯使”推斷,崔忻出使渤海國的“宣勞”也是代表唐玄宗行使類似的權限,其“宣勞”的任務應包括“冊封”和“宣慰”兩項內容[20]295。但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宣勞”和“冊封”屬于兩個不同概念,“宣勞”應釋為“宣諭、慰勞”,等同于“宣慰”,“宣勞靺羯使”實際是“宣勞、冊封靺羯使”的簡寫。查在崔忻出使渤海國的前一年,唐睿宗改元先天,決定與玄宗共同執政時,考慮“天下至廣,未達朕心”,曾頒布詔書分遣多位宣勞使前往內地各道:
睿宗先天元年,太上皇詔曰:“朕恭己無為,留神元默,俯順歷數,僉謀公卿,式命元子,祗膺寶位。今庶政逌新,光華肇啟,但恐天下至廣,未達朕心,故臨遣使臣,宣揚朝典。宜以膳部郎中蕭瑗為河南道宣勞使,諫議大夫楊虛受為河北道宣勞使,贊善大夫薛植為淮南道宣勞使,殿中丞薛麟為隴右道宣勞使,宗正卿姜晞為河東道宣勞使,司門郎中李誠為關內道宣勞使,工部郎中高紹為劍南道宣勞使,太子右諭德蕭憲為山南道宣勞使,宋王府司馬裴綱為江南道宣勞使,諫議大夫寧悌原為嶺南道宣勞使”[11]1800。
從詔書的內容看,這些宣勞使的職責只是向所派往的區域宣揚大唐的禮制和政令,并未領受宣讀地方官員任命的任務。因此,如果僅看“宣勞靺羯使”的字面名稱,只能解讀出崔忻肯定也向渤海靺鞨宣揚過大唐朝典,但并不能揭示出崔忻曾冊封過大祚榮。正因為“宣勞”并不等同于“冊封”,也不一定包含“冊封”,所以唐朝為使崔忻的“宣勞”同時具有冊封大祚榮的權限,特別在其“郎將”職務上臨時加官兼攝鴻臚卿。唐玄宗主持編纂的《唐六典》規定,“鴻臚卿之職,掌賓客及兇儀之事,……若諸蕃大酋渠有封建禮命,則受冊而往其國”[21]505。崔忻在鴻臚井刻石題詞上刻意強調自己的鴻臚卿身份,實際就是在間接說明,他的“宣勞”與普通的“宣勞”意義不同,同時也領受了“冊封”的使命。
四、關于“井兩口”
明代畢恭編纂《遼東志》記述鴻臚井刻石,將銘文“井兩口”改錄成了“鑿井兩口”,后世相關研究者據此大都也認為“井兩口”應解作“鑿井兩口”,而“鑿井兩口”的目的則是為解決當地水源,恩澤后人。瀛云萍先生推測,“井兩口”的故事是崔忻出使來到旅順港見到此地缺少淡水井,于是令當地安東都護府都里鎮有司挖掘井泉,但他自己并沒有主持或參與打井,而是率領使行團直接前往渤海國的都城。等到完成宣勞、冊封的任務后,返回旅順港,崔忻發現都里鎮有司已經在黃金山下打好兩口深井,于是他決定在旁邊的駝形石頭上題詞以作紀念[22]371。日本學者垣內良平認為,如果崔忻只是想在黃金山單純紀念自己出使渤海國,立一塊石碑就足夠了,沒必要再挖兩口井。他根據《易經》“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井泉之便而后居之也”的說法,懷疑崔忻鑿井具有祭祀或信仰方面的意義[22]346。田啟霖先生認為,“井兩口”的典故出自《周公解夢·兩口井》(古本),一口井有土,一口井有水。“井里有土者,是上坤下兌,以臨卦。臨,大也。以陽之浸長,其德壯大,可以監臨于下,故曰臨也。……臨卦主仁政,治民以感化、溫和,憂民之憂”。而“井里有水者,是兌下坎上,為節卦。節,止也,然則節者,制度之名。節,止之義,制度有節,其通乃亨,故曰節亨。”“雙井者,震下震上,為震卦。震,動也。此象雷之卦,天之威動,故以震為名。震既威動,莫不驚懼。驚懼以威,則物皆整齊。由懼而獲通,所以懼有亨德,故曰震亨也。”崔忻挖掘“井兩口”并立碑留念,意在警示自己,雖然出使渤海靺鞨為國為民立下大功,但仍要保持謙虛謹慎,繼續精忠報國,以實現天下大同[23]。而王若先生在認真考察了黃金山附近的地理形勢后推斷,“井兩口”只是借來比喻站在黃金山上望見的海面景致,旅順口港灣內有一條狹長的自然防波堤,恰好將港灣分割成兩個“井”狀水域[24]。
筆者認為,上述各家的說法都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我們不能排除還有另外一種更大的可能,即“井兩口”是指安東都護府在接到崔忻出使渤海國的消息后專門為崔忻使團挖掘了兩口井。眾所周知,古代中原王朝使臣出行,除特殊情況外,朝廷一般都會事先通知沿途必經之路的地方官予以接洽,提供必要的食宿和交通方便,崔忻出使也當如此。當初安東都護府,尤其是都里鎮,獲悉崔忻出使渤海國后,不能不想到使團經過漫長的海途勞頓,到達旅順港拋錨登陸黃金山下,最需要的就是淡水,打井應是接待使臣的首要任務。而崔忻完成宣勞、冊封使命重返都里鎮,尤其是準備登船下海辭別送行的安東都護府官員時,對當地提供的各種幫助按理肯定也要表示誠摯的感謝。細繹鴻臚井刻石題詞,所謂“敕持節宣勞靺羯使、鴻臚卿崔忻”只是敘述了題詞者的名字,而“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也只是標注了題刻的日期,“井兩口,永為記驗”才是銘文的重心。崔忻之所以特別強調“井兩口”,一方面固然是為了紀念他此次具有重大而深遠意義的出使,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紀念其間安東都護府給予的周到安排和殷勤照顧。
五、結語
綜上所述,唐鴻臚井刻石銘文的斷句,無論按語言學還是碑志慣例,都應將“忻”字上斷,與“崔”字相連。“崔忻”是刻石建立者,即唐朝派遣的冊封渤海國大祚榮的使者姓名的正確書寫。崔忻出使渤海國的時間,與唐朝制定冊書在法律程序上認定大祚榮為渤海郡王的時間,均應以唐睿宗先天二年二月為準。除冊封外,崔忻同時還領有向渤海“宣揚朝典”的使命。刻石銘文中的“靺羯”,是指大祚榮政權曾經根據其主體民族使用的短期國號,而非唐朝對靺鞨民族的蔑稱。而“井兩口”的含義,存在多種可能,最大的可能是指安東都護府為接待崔忻使團事先特別挖掘的兩口淡水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