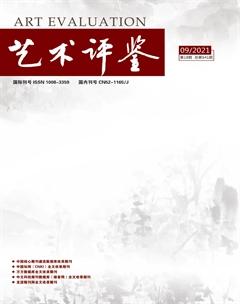戲劇教育作為美育的教育潛力
王琳娜
摘要:審美教育的核心是審美經(jīng)驗(yàn),是以引起反思為目標(biāo)并取決于審美經(jīng)驗(yàn)而設(shè)計(jì)的教育過程。戲劇教育作為美育的巨大教育潛力,主要體現(xiàn)在戲劇表演方面。從廣泛的意義上講,團(tuán)隊(duì)能力、溝通和互動(dòng)能力、道德能力、社會(huì)能力和方法能力以及自我效能感,還包括藝術(shù)能力以及審美能力等一系列的關(guān)鍵能力,都將通過戲劇教育的方法進(jìn)行傳授,并促使這些能力進(jìn)一步得到繼續(xù)發(fā)展。
關(guān)鍵詞:審美? 美育? 戲劇教育? 教育潛力
中圖分類號(hào):J805?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8-3359(2021)18-0149-04
一、戲劇教育作為一種體驗(yàn)教育
通過戲劇發(fā)起或支持學(xué)習(xí)和教育的觀點(diǎn)由來已久,許多生效模式描述了戲劇在社會(huì)和教育等方面的潛力。從2000年開始對(duì)戲劇教育的理解集中在審美實(shí)踐、創(chuàng)造體驗(yàn)、交流體驗(yàn)和舞臺(tái)展示方面。在發(fā)展過程中,以制作為導(dǎo)向的戲劇教育涵蓋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工作的整個(gè)過程:從題材的選擇、撰寫、改編和戲劇化的結(jié)構(gòu);從排練過程中產(chǎn)生的社會(huì)影響到作品的成型以及舞臺(tái)演出這一完整的過程作為團(tuán)隊(duì)工作。由此可見,戲劇教育的這種社會(huì)美學(xué)既體現(xiàn)在獨(dú)立的表達(dá)形式上,又表現(xiàn)在一個(gè)社會(huì)群體力量和協(xié)作生產(chǎn)上。我們今天談戲劇教育的時(shí)候,已經(jīng)不能僅僅從藝術(shù)的范疇來說,而是要從藝術(shù)、社會(huì)、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結(jié)合起來進(jìn)行討論。由于戲劇的工作過程具有密集的社會(huì)交流和集體合作的特點(diǎn),因此戲劇也被稱為社會(huì)藝術(shù)。
如果將戲劇理解為審美與社會(huì)交流和體驗(yàn)的空間,那么戲劇教育在理論和實(shí)踐方面、在藝術(shù)和教育方面都與這些空間的框架、分配、形態(tài)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審美和社會(huì)體驗(yàn)相關(guān)。除了戲劇觀賞,當(dāng)今戲劇教育的概念促使人們主動(dòng)參與戲劇表演,使之成為一種審美和表演的實(shí)踐,使自己和他人的經(jīng)歷變得多樣化,從而可以啟動(dòng)學(xué)習(xí)和教育過程。在文化教育方面,今天的戲劇教育被理解為一種應(yīng)用藝術(shù),從賦權(quán)和參與的意義上講,要促使參與者積極的行動(dòng)和表達(dá)。只有通過審美實(shí)踐,才能在戲劇中產(chǎn)生學(xué)習(xí)和受教育的可能。我們可以把戲劇比喻為一所學(xué)校,一所可以觀賞、可以自我展示的學(xué)校;一所可以盡情表達(dá)、可以提出質(zhì)疑的學(xué)校;一所與自我、與他人相遇互動(dòng)的學(xué)校;一所參與到文化和社會(huì)當(dāng)中的學(xué)校。
美育一方面提供了不同的體驗(yàn)空間,在其中所產(chǎn)生的不同體驗(yàn)成為了戲劇審美體驗(yàn)的特殊屬性;而另一方面則是關(guān)于內(nèi)容、主題以及反思的工作。依據(jù)亨舍爾的觀點(diǎn):“戲劇媒介所固有的雙重體驗(yàn)結(jié)構(gòu),使參與者在表演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一種特殊的現(xiàn)實(shí)構(gòu)造得以實(shí)現(xiàn)。在戲劇語境中,主要的審美感知和學(xué)習(xí)類別被稱為差異體驗(yàn)”。這種差異體驗(yàn)可以發(fā)生在戲劇創(chuàng)作的不同層面上:演員與角色之間,演員與演員之間,演員和觀眾的交流之間,在“有形”與“化形”之間,在理性與感性之間,還有日常生活與表演之間的差異。
二、戲劇空間中的差異體驗(yàn)
“戲劇不是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或人們?nèi)粘I畹膹?fù)制品。戲劇空間的特點(diǎn)是具有可塑性,可以創(chuàng)造新的‘現(xiàn)實(shí),從而促使人們嘗試新的事物或在新的環(huán)境中了解熟悉的事物”。此外,戲劇空間還為人們提供了一個(gè)可以專心進(jìn)行探索和研究的地方,是一個(gè)不必?fù)?dān)心約束和評(píng)判的安全空間,這是審美教育的決定性前提,奧古斯托·波瓦也將其稱之為“審美空間”。拉斯認(rèn)為通過表演、體驗(yàn)、探索和改變戲劇空間,表演者可以構(gòu)建不同的現(xiàn)實(shí),并在不同的情境中進(jìn)行嘗試。換而言之,一個(gè)參與者即表演者,通過將其生活和文化背景轉(zhuǎn)換為戲劇背景,從而使質(zhì)量發(fā)生改變。通過戲劇空間虛構(gòu)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并非純粹是出于真實(shí)性的要求,而是在這種關(guān)系中,始終要求參與者不斷地建立框架和打破框架。更確切的說,就是去語境化和再建語境化的表現(xiàn)方法。繼而,藝術(shù)和社會(huì)行為之間的界限不會(huì)消失,反而以新的方式變得更加清晰。
“除了這些被構(gòu)造出來的‘現(xiàn)實(shí)經(jīng)歷之外,體驗(yàn)的差異尤其表現(xiàn)在促進(jìn)感知力、想象力、表現(xiàn)力、在群體中的行為方式以及自我反思能力的發(fā)展方面”。由于差異體驗(yàn)對(duì)審美教育至關(guān)重要,因此在這里將亨舍爾所創(chuàng)建的差異體驗(yàn)的類型進(jìn)行介紹:
演員與角色的差異體驗(yàn)。通過將一個(gè)角色和與角色具有相同或類似個(gè)性、態(tài)度、價(jià)值觀的演員進(jìn)行比較,由于角色在某些特征上與演員類似,那么該特征就會(huì)得到確認(rèn)和增強(qiáng)。但是,如果角色的行為態(tài)度與表演者相反,則為演員提供了角色保護(hù),以便嘗試新的動(dòng)作和行為方式。當(dāng)差異體驗(yàn)最小時(shí),演員自我與角色自我之間的差異可以增強(qiáng)表演者的個(gè)性,而當(dāng)體驗(yàn)差異很大時(shí),就可以開辟出新的視角。
創(chuàng)造與體驗(yàn)之間的差異體驗(yàn)。為了體現(xiàn)角色,演員必須學(xué)會(huì)改變自己的身體,并將其視為多變和可塑的。通過尋找不同角色的立體性,要以不同的方式體會(huì)自己的身體。這樣,關(guān)于角色的主觀感覺就會(huì)外化,并嘗試傳達(dá)給觀眾。要把主觀感受塑造成為清晰、立體的可視化形象,“就需要表演者由內(nèi)而外的感知觀念發(fā)生變化,表演者必須要更注重體會(huì)內(nèi)部感受與外部表達(dá)之間的聯(lián)系。這種可變性的體驗(yàn)和發(fā)展身份的能力……也可以影響表演者的人格形成”。
演員與觀眾的差異體驗(yàn)。演員一方面必須專注于舞臺(tái)上的表演,另一方面,他們也必須專注于觀眾。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將這種狀態(tài)描述為“當(dāng)眾孤獨(dú)”。無論是否具有第四堵墻的表演,注意力的這種不斷交替都會(huì)發(fā)生并一直存在,這需要有意識(shí)的感知以及對(duì)這種感知進(jìn)行反思。那么在表演過程中,“主體與自身的反思關(guān)系開始發(fā)揮作用”。
有形與化形之間的差異體驗(yàn)。“從外部觀察自己的身體,并在自身內(nèi)部進(jìn)行活動(dòng)和體驗(yàn)時(shí)”,演員會(huì)體驗(yàn)到感知與視角之間的變化。這種差異體驗(yàn)已經(jīng)在演員和角色之間的差異體驗(yàn)中進(jìn)行了描述,但是在這里更多地將重點(diǎn)放在身份方面。不同的表演理論描述了內(nèi)部體驗(yàn)和外部觀察以及它們對(duì)角色處理的影響。無論使用哪種表演理論,都屬于有意識(shí)地體驗(yàn)——獲得身份和成為身份,即有形和化形之間的區(qū)別。
思想含義與感性之間的差異體驗(yàn)。在表演時(shí),將文本臺(tái)詞變?yōu)榭陬^語言,由于媒介發(fā)生了改變,所以不能只對(duì)文本進(jìn)行復(fù)述,而是要當(dāng)作主觀的闡述,這是尋找和體現(xiàn)角色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此,演員必須處理劇本及其含義,并且要以一種感性的方式對(duì)文本進(jìn)行塑造,將其置于語境中并與對(duì)手建立關(guān)系。這要求表演者深入分析文本所包含的規(guī)定情境,這就成為再次體現(xiàn),而不是照本宣科,是要將意圖清晰的表現(xiàn)出來。
(一)內(nèi)容的研究與分析
在一個(gè)戲劇作品創(chuàng)作前,人們總是需要表演沖動(dòng)或戲劇情境,以便能夠在戲劇中實(shí)現(xiàn)它們。它可以是完整的劇本、一個(gè)焦點(diǎn)問題,也可以是每個(gè)人都感興趣的場景或情境。如果已經(jīng)有劇本為前提,就需要表演者識(shí)別角色、分析角色行動(dòng)的動(dòng)機(jī),需要找到文本中角色的起始,并在自己生活環(huán)境中找尋相似之處,其目的重點(diǎn)不是僅僅遵從劇作者的藝術(shù)表達(dá),而需要演員發(fā)起自我詢問,究竟劇本中的字里行間對(duì)自己意味著什么?并需要將它作為自己主觀感受的基礎(chǔ)。
在一個(gè)戲劇作品創(chuàng)作中,所有的表演者在一起生活的文本世界成為了演員學(xué)習(xí)和研究的對(duì)象。以個(gè)人生活環(huán)境中的傳記題材作為主題基礎(chǔ),那么內(nèi)容以及藝術(shù)性的分析和調(diào)查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對(duì)于主題的分析討論就是激發(fā)演員進(jìn)行分析、思考并將其轉(zhuǎn)化為藝術(shù)活動(dòng)的過程,然后將總結(jié)的結(jié)果置于戲劇的形式中,再將收集的關(guān)聯(lián)材料進(jìn)行補(bǔ)充。
最終通過藝術(shù)的加工處理,社會(huì)的焦點(diǎn)在排演過程中形成,并獲得了雙重的交流:在工作過程中演員和演員之間進(jìn)行的一種內(nèi)部交流,另一種是通過作品呈現(xiàn)與觀眾進(jìn)行的外部交流。
這一完整的過程一方面具有藝術(shù)性,另一方面又是一種研究方式,能夠使表演者在技術(shù)和方法、個(gè)人和社會(huì)能力方面受益。
(二)反思所取得的經(jīng)驗(yàn)
在生活的各個(gè)領(lǐng)域中,表演無處不在,戲劇教育所具有的情境反思和自我反思功能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審美教育的核心是審美經(jīng)驗(yàn),是以引起反思為目標(biāo)并取決于審美經(jīng)驗(yàn)而設(shè)計(jì)的教育過程,因此戲劇教育作為審美教育必須集中在戲劇經(jīng)驗(yàn)上。戲劇的行動(dòng)是積極的,是要求不斷的去“做”。戲劇不同于其他藝術(shù)的特殊之處在于,創(chuàng)作主體既是作品又是創(chuàng)作者。在審美活動(dòng)中,經(jīng)驗(yàn)不僅僅意味著情感上的參與。審美經(jīng)驗(yàn)不是審美體驗(yàn)的代名詞,審美體驗(yàn)是審美經(jīng)驗(yàn)的前提,審美經(jīng)驗(yàn)是審美體驗(yàn)或?qū)徝烙∠蟮姆此紳B透。
為了使主觀體驗(yàn)成為一種經(jīng)驗(yàn)并進(jìn)入演員的意識(shí),就需要反思。只有這樣,戲劇中的審美經(jīng)驗(yàn)才能充分發(fā)揮其教育潛力,而表演者才能將其經(jīng)驗(yàn)轉(zhuǎn)移到自己的生活中,否則將僅僅停留在無法概括和客觀化的主觀經(jīng)驗(yàn)上。反思不僅應(yīng)該發(fā)生在過程的最后,更應(yīng)該是表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戈·謝勒提出了三種在戲劇的語境中反思審美經(jīng)驗(yàn)的方式:
首先,角色的反思:表演者從扮演角色的角度談?wù)撍闹饔^體驗(yàn),這可以引起情感或角色的主觀視角。
其次,觀察者的反思:觀察者會(huì)反思他們所看到的事物并反思他們的觀察結(jié)果,因此“不僅可以通過具體的態(tài)度看清不同的感知方式和事件的表達(dá),表演者還可以從外部感知到關(guān)于他們表演的反饋”。
最后,表演者的反思:由于演員(自我)與角色(自我)之間的差異,以及通過角色與其他表演者之間的體驗(yàn),常常需要表演者進(jìn)行反思,以區(qū)分“自己與角色”。
當(dāng)然在工作的結(jié)束階段,始終需要對(duì)整個(gè)創(chuàng)作過程、所取得的經(jīng)驗(yàn)以及共同創(chuàng)作的作品分步驟的進(jìn)行反思,這是將獲得的知識(shí)轉(zhuǎn)移到自己生活中的唯一方法。
三、戲劇背景下審美體驗(yàn)的教育潛力
在學(xué)習(xí)過程中,戲劇教育作為美育的巨大教育潛力主要體現(xiàn)在戲劇表演方面。在表演中,參與者有機(jī)會(huì)重復(fù)真實(shí)世界的經(jīng)歷。在表演中改變經(jīng)歷的機(jī)會(huì)也為找到解決問題的策略奠定了基礎(chǔ)。戲劇表演還可能引發(fā)自我疏離、與世界疏離的過程,并可能成為社交舞臺(tái)和表演實(shí)踐的研究工具。因此,表演不會(huì)僅僅停留在模仿現(xiàn)實(shí),而是為個(gè)體重新評(píng)估和改變自身所處的真實(shí)世界提供了潛在的空間和機(jī)會(huì)。通過表演,參與者進(jìn)入了主體和世界之間的關(guān)系當(dāng)中,現(xiàn)實(shí)被認(rèn)為是可變的、多變的。
亨舍爾對(duì)戲劇背景下審美體驗(yàn)的教育潛力從差異體驗(yàn)、感知和表達(dá)的同時(shí)性、體驗(yàn)與忘我能力、無法表演的現(xiàn)實(shí)、自省性等五個(gè)維度進(jìn)行了闡述,并認(rèn)為它們是相互依存和重疊的經(jīng)驗(yàn)領(lǐng)域。她指出,差異體驗(yàn)是參與者在表演的情境中同時(shí)體驗(yàn)了兩種不同的真實(shí),也可以看作是“構(gòu)建不同的現(xiàn)實(shí)并使其共存的能力”,這就是一種受教育的可能性。這樣的體驗(yàn)表明了物質(zhì)和社會(huì)狀況發(fā)生改變的可能性。有意識(shí)地跨越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與戲劇現(xiàn)實(shí)之間的屏障,對(duì)于戲劇教育中的創(chuàng)作尤為重要,而在表演中獲得的體驗(yàn)和能力往往有助于這種交叉。斯汀認(rèn)為戲劇教育的教學(xué)模式依據(jù)參與者的社會(huì)觀點(diǎn)和表達(dá),審美教育建立了自己的“社會(huì)美學(xué)”。
在戲劇創(chuàng)作過程中,表演者總是意識(shí)到他們既是自己又是角色。戲劇人類學(xué)家理查德·舍奇納將這種身份的“分裂”歸為一種“兩者兼而有之”的狀態(tài),他將這種在不同身份之間搖擺的能力描述為戲劇的基本體驗(yàn)。亨特舍爾認(rèn)為“以一部分自我參與當(dāng)下的體驗(yàn),同時(shí)保留先前的體驗(yàn)和對(duì)未來發(fā)展的認(rèn)識(shí)。如果人們認(rèn)為身份是可變的,那么表明戲劇表演會(huì)影響身份的形成,因?yàn)樵谒囆g(shù)創(chuàng)作過程中與其他參與者相遇時(shí),自己的想法可能發(fā)生變化和轉(zhuǎn)移”。
在表演中一個(gè)非常重要的認(rèn)知就是“要認(rèn)識(shí)到真正的現(xiàn)實(shí)是無法表演的”,但必須為其找到表達(dá)的象征性符號(hào)。例如,不能在舞臺(tái)上體現(xiàn)真正的死亡,必須用觀眾可以理解的戲劇符號(hào)來體現(xiàn)。戲劇符號(hào)的使用就表明現(xiàn)實(shí)不能在舞臺(tái)上被完全一致地表現(xiàn)出來。
通過處理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表現(xiàn)媒介和表現(xiàn)意圖,演員的審美能力得到了擴(kuò)展,對(duì)自我的思考引發(fā)了自我反思,再次使自己與世界疏離,所有這些都是美育的維度。在上文中闡述了通過反思獲得經(jīng)驗(yàn)的重要性。所有的學(xué)習(xí)和創(chuàng)作過程最后都將歸于反思才能獲得寶貴的經(jīng)驗(yàn),否則僅僅是感知體驗(yàn)而不是經(jīng)驗(yàn)。因此體驗(yàn)和經(jīng)驗(yàn)相結(jié)合,才能真正的獲得能力,開啟新的視角,打開新世界的大門。
“戲劇所創(chuàng)造的美學(xué)空間是二分的,即空間中的空間”。它是可塑的、可延展的,在戲劇創(chuàng)造的空間中:過去可以變成現(xiàn)在,虛構(gòu)可以變成現(xiàn)實(shí),而現(xiàn)實(shí)可以變成虛構(gòu)。審美空間釋放了記憶力和想象力、感覺和聯(lián)想,它可以像望遠(yuǎn)鏡一樣將遠(yuǎn)處微小的事物拉近放大觀看,也可以將日常的事件和經(jīng)過或前或后的滾動(dòng),或者以其他的方式間離化,以便個(gè)體可以在日常中展現(xiàn)并觀察自己,這樣就可以觀察和理解人類的行為。
除了個(gè)人層面之外,戲劇創(chuàng)造的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可能還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構(gòu)成提供了深刻見解。用自己的身體創(chuàng)造戲劇化的真實(shí),可以感性體驗(yàn)身體行為和動(dòng)作基本的可構(gòu)造性。通過這種方式,可以自然而然地體驗(yàn)到不言而喻的具體社會(huì)關(guān)系。
如今,很多戲劇活動(dòng)通常不完全根據(jù)計(jì)劃進(jìn)行工作,而是嘗試以情境和相關(guān)語境的方式形成目標(biāo)和工作方法,并對(duì)其進(jìn)行不斷的調(diào)整,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fā)揮出其實(shí)力和潛力。在情境化、框架調(diào)整的方式下,審美實(shí)踐作為一種體驗(yàn)和契合的空間,可以不斷的為文化教育方面的發(fā)展注入新的動(dòng)力。
四、戲劇教育中審美教育的局限性
在上文中,描述了通過戲劇實(shí)踐所產(chǎn)生的審美教育的潛力。審美體驗(yàn)源于戲劇的工作方式和素材性,并且不會(huì)出現(xiàn)表演者的教育目的,這些審美經(jīng)驗(yàn)是非常主觀和個(gè)性化的。此外,還取決于每個(gè)人的決定和能力。作為表演的引導(dǎo)者,“不可能對(duì)參與者所獲得的某種審美體驗(yàn)進(jìn)行引導(dǎo)和操控,只能創(chuàng)造出具備必要條件的空間以進(jìn)行審美教育。因此,就社會(huì)理想目標(biāo)而言,無法得出直接的結(jié)論”。某些超越期待范圍的實(shí)施會(huì)危及美育的質(zhì)量,因此不能完全實(shí)現(xiàn)功能化。根據(jù)亨舍爾的觀點(diǎn),與已知的、固定的思想價(jià)值關(guān)系的改寫相比,戲劇教育的美育實(shí)踐應(yīng)盡可能被廣泛的領(lǐng)域所接受。
藝術(shù)過程及其產(chǎn)生的結(jié)果無法被不同的人群和參與者進(jìn)行比較,因?yàn)樗鼈兪仟?dú)特的、無與倫比的,并且高度依賴于具體情況的。因此,關(guān)于戲劇表演的教育效果方面的研究很少,因?yàn)閷徝澜逃脑u(píng)估是很難證實(shí)的,而且無法憑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證明。
提到的審美經(jīng)驗(yàn)當(dāng)然是主觀的,教育效果僅描述了戲劇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性和接受性研究所包括的可能性。戲劇塑造的過程是必然具有教育潛力的,從這個(gè)角度來看,預(yù)先制定教育目標(biāo)變得過時(shí)了。不是預(yù)先為主體或者特定的目標(biāo)群體制定理想的教育目標(biāo),而是根據(jù)藝術(shù)創(chuàng)作過程的現(xiàn)象,提出戲劇制作相關(guān)的特定條件和方式,將個(gè)體的特殊經(jīng)歷、體驗(yàn)、領(lǐng)悟和經(jīng)驗(yàn)結(jié)合在一起的教育過程才具有真正的教育潛力。因此在實(shí)踐中既不應(yīng)確定規(guī)范的、與內(nèi)容相關(guān)的審美教育目標(biāo),也不能在教學(xué)和方法上僅僅依靠先前的審美經(jīng)驗(yàn)。因此,沒有統(tǒng)一指定的標(biāo)準(zhǔn)方法,而應(yīng)該是創(chuàng)造必要的前提條件,在此條件下審美教育過程成為可能。
當(dāng)人們面對(duì)未知時(shí)所進(jìn)行的嘗試和思考,這種探尋未知的過程具有獨(dú)一無二的創(chuàng)造力,對(duì)于人類的發(fā)展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和深遠(yuǎn)的意義。
五、結(jié)語
在教育背景下,戲劇表演通常被認(rèn)為是非常有希望的媒介。從廣泛的意義上講,團(tuán)隊(duì)能力、溝通和互動(dòng)能力、道德能力、社會(huì)能力和方法能力以及自我效能感,還包括藝術(shù)能力以及審美能力等一系列的關(guān)鍵能力,都將通過戲劇教育的方法進(jìn)行傳授,并促使這些能力進(jìn)一步得到繼續(xù)發(fā)展。這樣的目標(biāo)是基于個(gè)人和社會(huì)的理想構(gòu)想,并使用戲劇作為實(shí)現(xiàn)這些目標(biāo)的載體。
“教育是過程的結(jié)果,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個(gè)體與世界對(duì)于人類,或個(gè)體與人類為了世界的積極討論與分析被引發(fā)出來。通過分析討論,個(gè)體找到了合適的相處方式,認(rèn)識(shí)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并能夠明確的、獨(dú)立的、負(fù)責(zé)任的面對(duì)自己的生活”。從這個(gè)意義上來說,美育提供了對(duì)感知的積極分析。在戲劇教育的背景下,這一過程被看作是通過感知和創(chuàng)造所形成的全新藝術(shù)解釋。
最后根據(jù)利奧波德·克萊帕奇的說法:在戲劇中人類生存的所有核心方面都變得極為重要,人類生存的主觀性、物理性、文化性、歷史性、社會(huì)性和時(shí)空性在戲劇中得到反思。
參考文獻(xiàn):
[1]Hentschel, Ulrike(2000). Theaterspielen als ?sthetische Bildung. Weinheim: Deutscher Studien-Verlag,S.19-248.
[2]Ritter, Caroline (2013). Darstellendes Spiel und ?sthetische Bildung: Eine empirische Studie zur Theaterarbeit in der Grundschule. Zentrum für Lehrerbildung an der Universit?t Kassel (Hrsg.). Kassel,S. 40-41.
[3]Scheller, Ingo(1998). Szenisches Spiel: Handbuch für die p?dagogische Praxis. Mannheim: Cornelson Scriptor, S. 130-144.
[4]Hentschel, Ulrike(2012). Theaterspielen als asthetische Bildung. In: Nix, Christph/ Sachser, Dietmar/ Streisand, Marianne (Hrsg.): Lektionen 5. Theaterpadagogik. Berlin: Verlag Theater der Zeit, S.64-71.
[5]Boal, Augusto (1999): Der Regenbogen der Wu?nsche: Methoden aus Theater und Therapie. Seelze: Velber, S.27-39
[6]Hobmair, Hermann (Hg): P?dagogik. Stam Verlag, Berlin 1996, S.93.
[7]陳伯海.人為什么需要美——審美性能論[J].學(xué)術(shù)月刊,2003(06):65-70.
[8]陳伯海.再論人為什么需要美——兼談審美的可能性[J].江海學(xué)刊,2009(03):12-18.
[9]戴勇.從審美關(guān)系看人生美學(xué)——對(duì)朱志榮教授人生美學(xué)的解讀和再思[J].美與時(shí)代(下),2011(02):24-26.
[10]龔鄭勇.讀書·審美·教育·人——朱光潛美學(xué)教育思想再審視[J].太原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4(06):1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