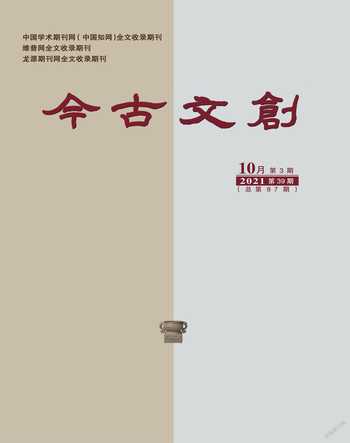語言的塑造功能
魏德武
【摘要】譚恩美作為女性華裔作家創作了許多名篇。其中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例如《喜福會》中的吳精妹,《接骨師之女》中的劉茹靈。話語對人物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將以《灶神之妻》中的人物為例,以話語分析的角度,分析其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語言如何在人物塑造之中發揮功能。
【關鍵詞】《灶神之妻》;人物塑造;話語分析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39-0019-02
《灶神之妻》作為長篇小說是筆者話語的材料。筆語有兩個主要功能:1.使得超越時空的交際成為可能的儲存功能;2.讓詞語脫離原始語境仍能得到分析和研究的轉換功能。這使得研究《灶神之妻》的語言和人物塑造成為可能。
一、《灶神之妻》的人物形象
雯妮是一個飽受男權思想欺壓的婦女。她在結婚之前幻想著婚姻幸福,然而在和文福的接觸中,她逐漸感受到文福的乖戾和暴躁。在雯妮與婆婆的相處之中,通過分析語境就可以看出她人物形象中被欺壓的一面。通過海姆斯對語境特征的分類,信息如下:(1)發話者:雯妮的婆婆(2)受話者:雯妮(3)話題:雯妮怎樣做一個她小兒子的好老婆(4)背景:婚后在婆家住的個把月(5)交際渠道:語言(6)語碼:中國方言(7)交際形式:布道(8)事件:教育雯妮如何為了丈夫忍受痛苦。從以上的話語內容可知,雯妮將如何做一個好老婆理解為:為了丈夫而忍受痛苦,后來的情節中,雯妮也以“好妻子”為目標忍受痛苦。當文福表達出不滿時,雯妮的話語內容為:“我知道丈夫仍不滿意我,我不得不接受更多的痛苦向他證明我是一個好妻子。”
雯妮的父親是一個傳統的中國式家長,在選擇結婚對象時,父親只是“一只眼睛的眉毛往上一挑,大家又沉寂下來”。這種交際渠道的肢體描寫,在語境中樹立了父親的威嚴。在面對政治形勢時,父親雖然有氣節但是缺少強大的內心,擁有軟弱和妥協的一面。但父親智慧的一面不能被忽視,如父親在臨死之前對文福進行的誘騙利用了人理解話語的方式。羅伯特·布格蘭德指出:人們對話語中發生了什么的理解與他們對世界上發生什么一樣的理解是相同的。明斯基也提出了框架理論,即當遇到新情況時,人會從記憶中選擇出結構,也就是框架。這種框架會在必要的時刻修改細節以適應現實。父親在話語中包含金條的藏匿,文福理解為父親在這棟房子里面藏匿金條,文福對話語的理解轉變為對金條已經被藏匿的事實的理解。在文福過去的經歷中,父親是富有的,這種認識形成了固有的框架,在新的語境中文福將過去的框架提出,形成了“墻里有金條”的框架以適應無錢可花的現實。從理論的角度來看,父親是十分智慧的。
文福在《灶神之妻》中的形象無疑是負面的,然而譚恩美沒有對文福的邪惡之處進行直接描寫,一開始以書信的方式介紹雯妮和文福之間不友善的關系,然后從回憶兩人的相遇對文福進行全新描寫。對于文福側面的描寫和對文福正面的描寫相輔相成,譚恩美利用視角和話語結構影響讀者對文福的理解。話語的表現呈線性排列,話語發出者在交際時必須選擇一個起點,這個起點會影響聽者和讀者對于對話的理解。開始作者利用書信來確定文福形象的基調,這個基調會影響讀者對人物的理解,所以,即使文福在出場時大方有禮,讀者對于他的形象理解也不會出現偏頗。《灶神之妻》的故事是建立在雯妮向女兒介紹過去的對話,這就意味著作者可以利用插入,改變自然順序和感知順序,讀者的視角可以從過去短暫地回到宴會,利用這種方式產出特殊效果,如文化背景的解讀和輸入。在雯妮拒絕送信之后,文福忍受不了去找人提親,此刻視角轉換,指出“你明白吧,文福決定娶花生為妻,不是因為他真的喜歡花生,而是想借婚姻進入她的家庭。”總之,作者擅長利用視角和改變視點,不斷地使文福的形象變化和立體化。
二、《灶神之妻》的人物關系轉變
文福與雯妮關系的轉變。雯妮和文福關系的最初轉變發生在廟中,他們不受文福母親的影響獨立的生活,文福的本性以及他人格的兩面性也開始逐漸顯現。一方面,他強迫雯妮說一些污穢的詞語,另一方面他又裝出友善的樣子討好雯妮。在他們的對話中,雯妮逐漸屈服于文福,文福獲得了主導權。賽爾指出:并不是所有言語行為都是通過說出那些其字面意義表達說話人所意圖的意義的語句來執行的。文福的話語不是直接的言語行為,而是間接的言語行為。例如,“說!”他突然喊道。他重復說了三四個臟字眼。“說!”他又一次喊道……“說。”他用平靜的口氣說。這是包含間接言語行為的祈使句,以命令的方式達到“說”以外的目的。也就是通過話語的方式使雯妮對自己絕對的服從。文福一共說了三次“說”。具體分析,每一次“說”的目的各不相同,第一次的“說”為請求或者命令,第二次的“說”雖然在形式上和第一次一致,但是體現文福對雯妮的不滿,第三次的“說”建立自己在雯妮心中的權威。雯妮沒有回答而選擇倒在地上,標志著文福的間接言語行為沒有成功,于是他選擇把雯妮拖到走廊上,雯妮一開始仍然沒有答應,話語為“開門”,幾分鐘后勉強同意,話語為“我說”。這間接言語行為表明文福權威地位的確立。該事件之后,雙方的地位開始改變,雯妮在兩人的關系中失去了話語權,于是才有了“打那以后,每天晚上都是這樣”。
雯妮與吉米關系的轉變。雯妮與吉米相遇時,雯妮已婚,雖然吉米對雯妮一見鐘情,但是兩人的關系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次相見時,兩人只是相互了解,初步建立話語關系。奧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一書中闡述了言語行為理論的核心內容:人類說出的所有話語都是利用語言做事情,即“說某事即是做某事,或通過說某事來做某事”。最開始吉米以自我介紹為主,盡管其話語是信息介紹,但信息介紹是樹立形象的手段之一,所以雯妮獲取話語以后,她才會“我感到他已經把我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愿望表達出來了,就是總有一天我也會被這種幸福之感所捕捉,就像魚落在網里一樣。”吉米話語的取效行為改變了他們的關系。雯妮出獄后第二天,是兩個人關系變化的又一個轉折點。“他還是管我叫他的小夫人,可他不再為了對我的偉大愛情寫上滿滿的三大張了。好像兩張是寫對我的愛的,還有一張是寫對上帝的愛。過了幾個月,一張寫給我,兩張寫給上帝。”在信中,吉米仍然在以言行事,他表現了他對上帝的愛為以后成為牧師埋下了伏筆。說話就是做事,語言是可以改變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的,對于雯妮來說,為了發展她和吉米的關系,解決“舊賬”是必須的,這也就是為什么雯妮執意離婚。作者安排離婚的劇情,不僅是因為女性意識的覺醒,也是出于對她和吉米關系發展的安排。
三、人物對現實的影響和塑造
維特根斯坦曾經說過:“實際上我們使用句子來做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事。日常生活的言語行為如此,文學藝術的言語行為更是如此。”米勒從言語行為的角度談到文學對讀者所產生的影響時,也提出過文學作品的言語行為。一般來說,藝術作品的創作者間接言語行為意圖分為三類:“告知”類、“傳情”類、“勸導”類。本作也不例外。
(一)《灶神之妻》人物塑造的告知作用
告知作用指的是文藝作品告知人們世界的真相,告訴人們作者生活的時代是什么樣子的。該作品橫跨二戰和解放戰爭,通過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如花生、雯妮等,體現當時人們生活的時代背景。例如,雯妮的逆來順受與童年經歷有關,也和當時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欺壓有關,后面雯妮移民美國的艱辛,體現了華人移民者的生活不易;花生變得干練,投身革命運動,也是當時中國人民在時代的十字路口救亡圖存的寫照;角色文福以小見大是父權社會反動者的真實描繪。
(二)《灶神之妻》人物塑造的傳情和勸導作用
創造審美藝術幻象的主要意圖是為了傳達對某些事物的感受和情感,以獲得人們的同情和共鳴。女權主義運動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席卷歐美,出發點是不平等的兩性地位,主要目的是倡導女性由壓迫走向反抗。雯妮經歷著國家動蕩和家庭不幸,從國家層面來講,中國處于戰爭狀態,人人自危。從家庭層面來講,雯妮的生活并不幸福,要忍受文福的拳腳相加。這引起了女性群體的共鳴,有很強的傳情作用。《灶神之妻》的人物塑造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女性發聲,獲得人們對女性問題的關注,在以前的文學作品中,女性的形象往往是天使或者惡魔,但在本作中,雯妮的女性意識不斷覺醒,形象也從封建女性轉換成為平權斗士,書中通過雯妮的斗爭倡導女性為了自己的權益發聲。《灶神之妻》的人物塑造對于作品的傳情和勸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總結
《灶神之妻》作為譚恩美的名篇,其中的人物塑造有其過人之處。以話語分析的角度看本書中的人物形象與故事發展,可以更好地把握書中人物關系發展和事件的邏輯關系。從微觀的層面來看,書中人物的對話和語境因素值得分析研究;從宏觀角度來看,《灶神之妻》的言后效力對于社會的構建和重塑有著重要的作用,不僅引起了讀者的回應,還能通過這種回應現實的改造著讀者的社會屬性。
參考文獻:
[1]譚恩美.灶神之妻[M].張德明,張德強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
[2]吉利恩·布朗.話語分析[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
[3]趙昱榮.“惡棍”與“英雄”——從形象學角度解讀譚恩美筆下的男性形象[J].惠州學院學報,2014,34(04).
[4]邢蘭娟.論譚恩美長篇小說中的母親形象[D].山東師范大學,2015.
[5]邵莉.淺析《灶神之妻》中的男性形象[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6,(02).
[6]劉怡.譚恩美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探析[D].貴州師范大學,2016.
[7]燕思如.譚恩美長篇小說中的華人男性形象研究[D].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2015.
[8]馬大康.話語行為與文學虛構[J].文藝理論研究,2014,3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