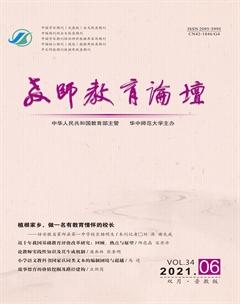教師形象的哲學研究
摘 要 在學生面前保持何種形象是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經常碰到的問題。高速發展的當代社會沖擊著教育多元和開放的思潮,促進社會的進步的同時也給教師形象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例如,教師部分形象被異化甚至消失。每位教師都有強烈個人意味的形象與氣質,但教師個人形象的建立存在一些共性的基本原則,例如,教師具有知識的形象和榜樣的形象。從教育哲學的角度來看,研究教師的形象是對教師自身的認識問題,即教師“是什么”的本體論思考。從教育哲學的角度對教師形象進行反思性和批判性研究能夠幫助教師更好地建立起關于自身形象的哲學認知。
關鍵詞 教師形象;哲學演變;教育哲學;教師;反思
中圖分類號 G45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5995(2021)06-0029-03
教師的哲學是關于教師個體在教育實踐中進行的個體性、反思性和實踐性活動的哲學。[1]在教育實踐過程中,教師通過反思教育理論、研究教育實踐問題、感悟教育真相而逐漸形成獨特的教育風格和氣質,從而形成關于教師形象的哲學。
一、教師形象的哲學史演變
教師常常被比喻為“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春蠶”“蠟燭”等。正是因為這些職業、動物和物體在某些方面與教師的形象有相似的地方,才能使其成為教師的喻體。但這些隱喻已經不足以勾勒出教師在當代社會立體而靈動的形象。從本質上說,對“教師是什么”的哲學探討是研究人如何成為教師,是教師專業特性本原意義上的價值內核在社會關系中的折射。
教師的形象在哲學史上也經歷了漫長的演變。2000多年前,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洞穴理論,描述了教育是如何發生的:一群被束縛的人處在一個洞穴之中,無法感受到外界的光。他們的影子和洞外的事物被火光投射到穴壁上,因此,他們相信自己看到的影子是真實的東西,直到其中一個囚徒被牽引著來到洞穴之外,看到真實的太陽以后他才意識到洞內的影子其實是虛幻的。在柏拉圖看來,做這種牽引工作或者說教學活動的人就是哲學家,就是教師。教師對學生進行啟蒙,利用記憶和重復的教育活動教授真理、引導學生走出“洞穴”,這是哲學上對教師形象最初的定義——教師作為主人將權力施加到學生的意愿和思想之上,教師的任務就是讓學生看到真實。在任何情況下,教師都要肩負起作為學生主人的責任,自覺服務于學生知識發展以及自由的需要。
但是很快,“教師作為學生主人”的觀點受到了批判,取而代之的是“教師是學生的仆人”的觀念。這種觀念下,教師把自己定位在服務于社會、政治以及歷史偶在性的感覺下,服務于偶在之下的權力和暗示。[2]在這個階段,教師仍然是學生的主人,卻已經是服從于歷史偶在性的“仆人”,教師在“權力形態變化面前被動地就范”。蘇格拉底是較早發現教師的這種兩難處境的哲學家。因此,他以存有、知識與價值序階為其教育理論基礎,提出了“產婆術”理論,認為在任何時候自己都沒有知識可以教給任何人。正是由于他缺乏智慧才能使他為了檢驗別人的思想而產生懷疑,因此,他主動將自己的地位放在學生的仆人的位置上,從“傳道者”轉變為“對話者”,避免向學生灌輸知識,而是任由學生自由和懷疑思想的發展。[3]但是這種教學方式也無可避免地受到了質疑:教師做學生的仆人一定會比做學生的主人產生更好的教育效果嗎?是什么真正決定了主人和仆人的地位?教師在這種形象的矛盾掙扎中不斷進行更加深刻的反思和學習。
隨著愈發多元化的教育哲學觀念的出現,關于教師形象的探討也有了更加多樣化的表述。羅杰斯批判傳統教師形象,認為教師是一個滿腹經綸的知識富翁,而學生僅僅作為“容器”,機械記憶教師所傳授的“金科玉律”,這是一種純粹的“壺與杯”的教育。在逐漸發展起來的人本主義的教師觀中,教師和學生不再是毫無感情的教與學的機器,教師成為“愛的實踐者”、“激勵者”和“提供方便的人”。猶太思想家馬丁·布伯同樣提到教師具有“包容的愛”的形象,教師通過“愛”發揮教育的力量,協助學生學習,激發學生潛能,師生之間不分你我,“就如同這種被創造的宇宙,他的一瞥歡迎并接受了他們”[4]。這種富有“愛”的形象存在于并為了教師的工作而存在,也存在于教師形象的哲學之中。
在現代教育觀下,教師依然是學生的朋友,師生關系不局限于教育教學活動本身,而是有了更廣闊的外延,教師以一種更獨特的形式關注學生。在這種教師形象觀下,教師不是簡單野蠻的馴化者,師生之間通過“主體間性”以及“交往理性”等達到幫助學生發展與提升的可能性意義。正如馬丁·布伯所言:“孩子建設自我所需要的力量必須是通過教育家選擇的……教育家要教育自己成為這些孩子的媒介。”[5]
二、教師形象是個人的哲學
正如所有科學領域都包含著一個使一切真實知識得以形成的“個人系數”那樣,每位教師都有獨屬于自己的形象哲學。[6]從教育哲學與教育實踐的關系看,無論是公理性的教育哲學還是普遍的、大眾的教育哲學實踐,都依托于具體的個人教育實踐與實際生活所產生的緊密聯系。教師開展的教育活動以及他傳遞的思想帶有個體獨有的和連貫的傾向性;教學活動背后的哲學假設,對自身教育實踐和教育問題的反思以及批判性哲學實踐活動,促使教師在教學中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甚至是與他人完全不同的價值判斷,也即“人人都有自己的教育哲學”。
不同的為師之道使得每位教師都有自己獨特的和有強烈個人意味的形象與氣質。例如,盧梭的自然教育思想認為理想的教師是“守護兒童善性的生命導師”,把教師形象定義為兒童尋求快樂的“知心人和決定人”。[7]黑格爾則認為教師是學生心中的“權威人物”般的存在,是兒童心中最神圣的偶像。弗萊雷從批判教育學的角度,認為在傳統的教育環境下,教師形象等同于一個儲存知識的“銀行系統”,學生則是被動地接受知識。因此,教師要摒棄這種麻木的、沉默的教育,代以更有創造性的教育,創造新的教師形象,即教師應當“像藝術家一樣采取一些創意方式來教授學術性知識,以創意來瓦解被動性教育”。[8]對教師形象的不同理解又反過來促使教師以此為目標去提高其教學水平。實際上,教師在教育場域中引導學生實現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過程,也是教師形成理想自我形象的過程。[9]
三、當代教師形象中出現的問題
教師的職業形象既受獨有的中心價值取向和哲學思想體系的影響,也受社會流行價值觀念和哲學思想的影響。高速發展的當代社會沖擊著教育多元和開放的思潮,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但也給教師形象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一方面,教師這份工作被看作是謀生的手段而非“立德樹人”崇高理想的踐行者。有的教師個人品德失范,與“學者良師”的教師形象有所背離。有的教師甚至在道德底線的邊緣試探,對權力、金錢的欲望遠遠大于教書育人所獲得的成就感。學校不再是純粹的“象牙塔”,而是教師功名利祿的追逐場。還有的教師無意識地或自我沉淪地踐行著“平庸的惡”——“我”服務于“我”的薪資和酬勞,而不對學生承擔任何責任和義務。
另一方面,由于冗雜的教學安排、科研任務以及名目繁多的政治學習和形式主義的要求,部分以教書育人為畢生追求的教師的“學高身正”形象逐漸消失,強勢的教育行政管理將相對而言處在弱勢地位的教師群體拖進了沒完沒了的“空幻的雜務”之中。[10]“我們教育的危險不是來自于作為一個整體的科學家……而是來自公眾中一部分沒有研究過教育卻對教育高談闊論的人(而且用一種非常不科學的態度)。”[11]教師由傳統的教學主體變為教育行政管理者意志的執行者,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大大削弱,陷入被教育行政拖累的被動且尷尬的困境,難以實現自身職業形象發展的規劃和追求。
在現代性背景下,教師需要對教師形象進行內在的反思性思考,而不是走向自我削弱、扭曲乃至自我剝奪的哲學。[12]事實上,對自我形象的反思是教師的一種自我修正機制,是教師自我驅動的車輪。通過自我反思來認識自我的形式被稱為“鏡中我”,教師可以通過對“鏡中我”映像與理想教師形象的對比印證,真正理解與認同教師的哲學形象。
四、教師個人形象的建立
教師個人形象的哲學建立不是要求每位教師都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學體系或理念,而是指教師個人要對教師形象的哲學有一定認知和了解,能形成自己的教育價值觀,并以此指導自己的教育實踐活動。教師個人形象的建立有一些共性的基本原則。
第一,教師具有知識的形象,無論教師間的形象氣質如何不同,但總體上都回歸于知識的形象,回歸于立德樹人的道德品質要求。當前,教師的知識形象岌岌可危,對教師知識形象的漠視會導致不良的教育后果:當教師的精力被教育行政牽制而無暇精進知識性教學時,教師的知識話語權必然旁落,從而在潛移默化中導致學生對知識相對冷漠甚至不屑一顧。學生對知識的此種態度,是無法僅靠強調教育的重要性或實施填鴨式應試教育而能有所改變,歸根結底,還是要將實施教育的權力歸還給教師,明確教師與行政之間的職責與權力邊界,讓教師群體擁有更為強勢的“學術事務”治理權。[13]
第二,教師具有榜樣的形象。與其他職業不同的是,教師面對的受眾是學生群體,大部分情況下,學生的心智尚未成熟,其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缺乏完善引導。教師除了教授學生學習課本知識以外,還需要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塑造學生的品格。對知識的好奇、對真理的熱愛、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及對新鮮事物的探索欲和敏銳性,往往無法通過教科書獲取,而要通過周圍的榜樣行為獲得。在學校環境中,學生更多的是從教師的榜樣行為中學習。“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也就是說,教師要德才兼備。如果教師僅僅為了功利性的目的而在教學中照本宣科,敷衍了事,就十分不利于學生的成長。
沒有完美的教師,也不存在完美的教師個體形象,探討教師形象的意義就在于使教師們盡可能地去貼近理想的教師形象,幫助教師認識自我,豐富自我,從而讓自身形成正確的教師形象哲學觀。
(陳璐瑤,北京體育大學教育學院,北京 100000)
參考文獻:
[1] 戚萬學.論教師的哲學[J].教育研究,2014(12):85-93.
[2] [英]尼格爾·塔布斯.教師的哲學[M].王紅艷,楊帆,沈文欽,等,譯.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14:73-74.
[3] 宋學紅,張鴿.教師:對話者抑或傳道者?——從蘇格拉底及其“產婆術”看教師的本質[J].淮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35):136.
[4] 林逢祺,洪仁進.教師不可不知的哲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172-173.
[5] [德]馬丁·布伯,我與你[M].陳維鋼,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86.
[6] [英]邁克爾·波蘭尼.個人知識——邁向后批判哲學[M].許澤民,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25.
[7] [蘇]B.A.蘇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學[M].趙瑋,王義高,蔡興文,等,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5.
[8] 呂娜.論保羅·弗萊雷的教師觀[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報),2017(1):149-154.
[9] 王坤慶.教師專業發展的境界:形成教師個人的教育哲學[J].高等教育研究,2011(5):26-32.
[10] 鐘啟泉,劉徽.我國教師形象重建的課題[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6(8):40-47.
[11] 余小茅.保衛古典教育[J].中國圖書評論,2012(11):76-80.
[12] 伍雪輝,張艷輝.基于現代身體哲學意義的教師形象分析[J].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5):108-112.
[13] 李莎莎,李思思.制度理論視域下比利時弗萊芒大區高等教育治理權的特點及啟示[J].復旦教育論壇,2020(1):105-112.
實習編輯:劉 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