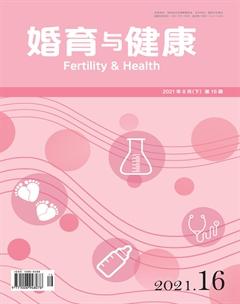良肢位擺放在腦卒中偏癱患者早期康復護理中的應用效果分析
移轉菊 張云霞 李明慧
【摘 要】目的:研究腦卒中偏癱患者行良肢位擺放護理的效果。方法:數據遴選我院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期間收治的88例腦卒中偏癱患者,按照“信封法”分為常規組(傳統護理,n=44)、康復組(良肢位擺放護理,n=44),兩組護理效果比較分析。結果:護理前比較兩組臨床指標無差異(P>0.05);護理后與常規組比較,康復組FMA、BI值更高;有效率更高(P>0.05)。結論:良肢位擺放護理可改善腦卒中偏癱患者的肢體功能、提高康復效果,值得推崇。
【關鍵詞】良肢位擺放;腦卒中偏癱;早期康復;應用效果
腦卒中患病率、致殘率較高,相關報道指出[1],予以此病患者對癥治療后,約有近89%的群體呈不同程度功能障礙,對自身身心健康造成影響,也給家庭帶來沉重負擔,因此早期如何制定康復護理方案、成為相關領域亟待解決要點。王晴[2]認為,口頭宣講、情志疏導及常規指導均屬傳統內容,未重視個體差異性、護理效果單一,患者依從性較差,鑒于此,本文分析腦卒中偏癱患者行對癥護理的價值,匯總。
1 資料和方法
1.1 基線資料
回顧性研究,樣本取自本院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期間收治的88例腦卒中偏癱患者。康復組(44例),男23例,女21例,年齡53歲~74歲,平均年齡(62.41±5.39)歲;肌張力分級:0級有30例,Ⅰ級有14例;常規組(44例),男24例,女20例,年齡54歲~75歲,平均年齡(62.58±5.41)歲;肌張力分級:0級有32例,Ⅰ級有12例。P>0.05,可比較。患者對“知情同意書”簽字,經倫理委員會審批同意。
1.2 方法
1.2.1 常規組(傳統護理):口頭宣講、情志疏導、常規肢體功能鍛煉等。
1.2.2 康復組(良肢位擺放護理):①仰臥位:指導患者平躺于床上、頭放于枕頭且手臂放在兩側,盡量伸直手臂、微屈手指,伸直下肢、微屈膝關節;②患側臥位:指導患者患側肢體在下方、伸直上肢并伸展手指,伸展患側下肢,屈曲膝關節,屈曲健側下肢髖關節呈90度,將部分壓力作用于癱瘓部位,使本體感覺增加;③健側臥位:指導患者健側在肢位下方,伸展上肢,將肘關節、肩關節放在枕頭,屈曲腕關節,確保膝關節、患側髖關節呈彎曲狀態。
1.3 觀察指標
臨床指標:評價兩組肢體功能(參考Fugl-Meyer平衡量表[3]-FMA,涉及上肢、下肢2部分,百分制)、生活自理能力(參照Barthel指數-BI,總分100分),各量表分值與護理效果呈正相關。
康復效果:顯效:癥狀減緩、生活可自理;有效:癥狀改善一般、生活基本自理;無效:疾病加重、生活難自理[4],有效率=[(顯效+有效)例數]/44×100%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采用(%)表示,進行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χ±s)表示,進行t檢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臨床指標
護理前兩組無差異(P>0.05);與護理前比較,護理后FMA、BI值均升高,且康復組高于常規組(P<0.05),見表1。
2.2 康復效果
與常規組比較,康復組有效率更高(P<0.05),見表2。
3 討論
有文獻報道,良肢位擺放護理用于腦卒中偏癱患者中具有可行性,分析發現:其屬新型護理模式,以持續控制、控制靜止性反射為基點,達到改善異常運動的目的,促進分離運動、利于盡早開展良肢位擺放,避免患者發生肌肉攣縮、足內翻等并發癥,且該模式通過健側臥位、仰臥位及換側臥位等護理,利于改善局部血液循環、促進靜脈回流,可避免機體發生壓瘡、深靜脈血栓等并發癥,促進疾病恢復、利于改善預后;早期提供良肢位擺放可達到抗痙攣作用,穩定偏癱后的關節,避免機體出現上肢屈肌、下肢伸肌等痙攣模式,對預防病理性運動發生有積極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示:①與常規組比較,康復組FMA、BI值更高(P<0.05),表示對癥護理可改善患者肢體功能、縮短療程,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對改善預后效果有積極重要作用;②與常規組比較,康復組康復有效率更高(P<0.05),說明本文與楊 勛樂[5]文獻相似,因此對癥護理可改善局部血液循環、避免壓瘡等并發癥出現。
綜上,腦卒中偏癱患者行良肢位擺放護理可改善肢體功能、促進患者早期回到日常生活,達到預期康復效果、療效確切。
參考文獻
[1] 曹霞.對比分析探討良肢位擺放在腦卒中患者早期康復護理過程中的影響[J].中國農村衛生,2020,12(23):39-40.
[2] 王晴.良肢位擺放在腦卒中偏癱患者早期康復護理的效果[J].當代臨床醫刊,2019,32(1):61.
[3] 楊冬花.良肢位擺放在腦卒中偏癱患者早期康復護理中的應用[J].當代醫學,2018,24(8):26-28.
[4] 范宇笑.良肢位擺放標識護理在腦卒中偏癱病人中的應用[J].全科護理,2017,15(31):3922-3923.
[5] 楊勛樂,羅紅,卜歡.良肢位擺放在腦卒中偏癱早期康復護理中的應用[J].內蒙古中醫藥,2017,36(11):14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