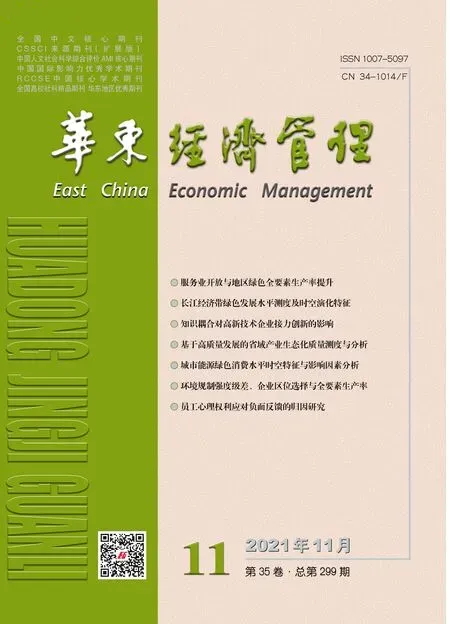環境規制強度級差、企業區位選擇與全要素生產率
2021-11-05 09:23:14肖涵月
華東經濟管理
2021年11期
肖涵月,孫 慧,王 慧,辛 龍
(新疆大學a.新疆創新管理研究中心;b.經濟與管理學院,新疆 烏魯木齊830046)
一、引 言
以環境治理為抓手推動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環節。然而,在環境分權和經濟競爭背景下,地方政府間逐漸形成環境規制“逐底競爭”和“逐頂競爭”并存的局面,加深了水平型環境規制執行程度的差異,由此產生地區間環境規制強度級差(張華,2016;韓超等,2021)[1-2]。在微觀層面,環境規制強度級差的擴大成為污染密集型企業遷移的一個誘因;在宏觀層面,地區間“污染避難所”效應和城市間環境規制“灰邊效應”使環境區域性矛盾更加凸顯,為污染協同治理帶來了挑戰(Fc和Ed,2017;徐志偉和劉晨詩,2020;秦炳濤和葛力銘,2018)[3-5]。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十四五”期間,將更加注重完善生態文明統籌協調機制,不僅要關注環境規制區域治理效果,還應當關注治理的整體性、經濟發展的系統性。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能,地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否會受到環境規制強度級差的影響?該問題的研究,能夠為完善環境規制功能、協同推進污染防治、提質增效提供理論依據。
理論上,環境規制主要通過兩種路徑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遵循成本”假說認為,一定強度的環境規制將提高污染企業的環境合規成本,抑制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波特”假說則認為,合理設計的環境規制能夠促進企業創新,并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從而提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Ambec等,2013)[6]。……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當代水產(2022年5期)2022-06-05 07:55:06
當代水產(2022年3期)2022-04-26 14:27:04
當代水產(2022年2期)2022-04-26 14:25:10
核科學與工程(2021年4期)2022-01-12 06:30:26
中老年保健(2021年12期)2021-08-24 03:30:40
中國傳媒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21年1期)2021-06-09 08:43:00
今日農業(2020年19期)2020-12-14 14:16:52
云南畫報(2020年9期)2020-10-27 02:03:26
中國生殖健康(2020年6期)2020-02-01 06:28:50
中國生殖健康(2019年11期)2019-01-07 01:2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