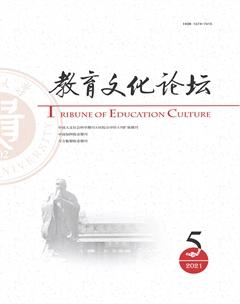抗戰時期高校西遷對貴州教育的影響與當代啟示
李華玲 韓繼偉
摘 要: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為保存高等教育的有生力量,實現民族復興,一大批高校向抗戰后方大轉移,形成了歷史上著名的“西遷運動”。部分高校向貴州“西遷”,使得當時貴州各類教育規模快速擴大,完善和優化了貴州省當時的教育體系結構和區域分布,并且在辦學層次和辦學質量方面得到了明顯提高。以史為鑒,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應將愛國情懷作為教育發展的核心邏輯,并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地位。
關鍵詞:高校內遷;貴州教育;當代價值
中圖分類號:G5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615(2021)05-0044-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5.007
大學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明的象征,現代大學也是一個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科技與文化策源地,因此,沒有現代大學就沒有國家的文明,也就沒有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以19世紀末天津北洋西學學堂的成立為標志,我國近代高等教育逐步成型,特別是1912年的“壬子學制”極大地推動了我國近代高等教育體系的建設。在抗戰前,我國高等教育的規范化與體系化特征非常明顯,在國際上也開始形成了一定的競爭力,但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全面升級,日本侵略者也開始對我國高等教育進行了有預謀的、持續性的和深度的破壞,絕大多數高校失去了正常辦學的教育資源與外部環境,為了在這場苦難中搶救和保存中華民族的“文脈”,國民政府及社會力量通過向西部省份遷移、重建大學的方式來拯救淪陷區與半淪陷區的高校,避免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高等教育的毀滅性打擊。這種快速果斷而規模宏大的高校戰時“西遷”運動,彰顯了中華民族堅強不屈、剛毅堅卓的民族精神,不但為我國教育事業保存了有生力量,還為我國西部地區的教育發展與社會現代化進程奠定了基礎。
貴州省因為地處丘陵山區、遠離戰區等自然地理條件的限制,加上我國武裝力量的抗爭而沒有成為日軍的占領區,也就成為當時一些高校內遷的主要省份之一,其中就有國立浙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等大批卓越的大學遷入貴州辦學,不但給這些西遷高校的戰時避難與戰后恢復創造了條件,還在一定程度上為貴州省各級教育發展帶來了契機。
一、抗戰時期高校西遷貴州的歷史背景
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國知識分子開展的各種抗日救亡活動聲勢尤為浩大和激烈,引起了日本政府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極端仇視,并認定“各級學校均為反日集團,所有知識青年均系危險分子”[1]。于是,日本軍國主義采取各種破壞手段摧毀中國教育和文化機構,特別是企圖消滅中國文化根基而大肆破壞中國高等學校的校舍建筑與文化典籍,“轟炸破壞,亦以高等教育機關為主要之目標”[2],使得當時的高等教育損失慘重。以南開大學被徹底毀損為開端,至1938年8月,全國108所專科以上高校中有91所被破壞[2];至當年10月,因校舍被毀而被迫遷移或停辦的高校達到94所,只有10余所能基本勉強維持[3]。為抗日救亡,維系民族文脈,保存高等教育的有生力量,實現民族復興,1938年,國民政府制定了“抗日建國”的基本國策,提出了“戰時須作平時看”的教育方針,采取了史無前例、中外罕見的教育大轉移,將國民政府管轄的各類高等學校向西南、西北等抗戰的大后方遷移。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貴州成為陪都重慶的天然屏障和抗戰的大后方,其戰略地位和重要性明顯提升。這一時期,國民政府教育部將國立浙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湘雅醫學院、國立廣西大學、國立桂林師范學院、私立大夏大學、私立之江大學和鄉鎮學院等9所普通高校遷入貴州分布各地辦學,在校學生人數達到4 233人之多,教員達524人[4]。并有陸軍大學、陸軍步兵學校、陸軍炮兵學校、陸軍軍輜學校、陸軍通訊兵學校、中央陸軍軍醫學校、陸軍獸醫學校、國民革命軍防空學校、中華民國海軍學校、中央陸地測量學校和軍訓部軍官外語班等12所軍事院校內遷至貴州各地。至1945年,貴州擁有21所高校,高校數量之多,可以說達到了貴州近代高等教育的鼎盛時期,大批博聞強識、才華橫溢,且向來就有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的專家學者紛紛涌入,貴州近代教育迎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推動和加速了貴州教育近代化發展的歷史進程。
二、抗戰時期高校內遷對貴州教育的影響
20世紀以前,包括貴州省在內的山區邊疆省份因自然環境惡劣而在政治、經濟、教育和文化等方面全面落后。辛亥革命光照貴州之時,貴州國民臨時政府制定和實施了各項教育改革政策,推動和加速了貴州近代教育發展。但隨后各派軍閥混戰,打亂了貴州近代教育發展的進程,阻礙了發展步伐。可以說,在抗戰全面爆發前的二十多年時間里,經歷了各派軍閥和國民政府統治,貴州教育在劇烈動蕩的社會政治旋渦中艱難曲折地前行,教育發展十分落后。“邊疆教育,乃因抗戰開展而成長”[5],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而導致的部分高校與知識精英內遷貴州,在客觀上使得貴州省的各級教育事業得到了空前發展。
(一)各類教育規模快速擴大
1.小學教育較快發展
貴州省地處偏遠、交通險阻,歷來就是我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地區,在民國之前基本沒有官辦的教育體系,基礎教育的唯一模式就是為貴族階層提供教育的私塾教育。即使后來國民政府強制性地推行改造私塾,設立小學,推行新式教育,但這一制度只是在城市得到一定的落實,在廣大的農村地區遭遇的阻力較大,新式小學教育嚴重落后于西南其他省份。以1914年為例,四川、廣西、云南和貴州的新式小學數量分別是13 284、1 622、4 527和1 135所,貴州遠遠低于西南其他省份[6]。據1916年貴州省公署報教育部的文件表明:“高等小學、國民學校共計一千五百余所中,多學校其名,私塾其實,以學校與私塾比較,學校不過十之二三,而私塾居其七八焉,學生數亦不過十之三四,而私塾學童居其六七焉。”[7]一直到抗戰全面爆發前,由于貴州政局不穩,軍閥混戰,教育管理機構混亂,教育經費投入嚴重不足甚至常常被軍閥挪作軍費,加之社會動蕩,學校師生安全常常受到威脅,很多學校時開時停,這一時期小學教育未被重視,甚至遭受重創,發展滯后。據統計,1930年貴州省有小學1 752所,學生83 000多人[8]。隨著抗戰全面爆發,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高校內遷,貴州人口劇增,原有學校難以容納流亡學生就讀需要,貴州國民政府通過改組教育行政機構,通過實施義務教育,采取舉辦短期小學、鼓勵私人辦學、開展巡回式教學、改良私塾等教育改革措施和推行國民教育等手段,使得全面抗戰時期貴州省的小學教育規模和數量得到較快發展。據統計,全面抗戰時期僅貴陽興辦的小學就達24所。至1945年抗戰結束時,貴州省共有新式小學10 577所,其中中心國民學校1 595所,國民學校8 693所[9]。
2.中等教育規模擴大
貴州中等教育自辛亥革命到全面抗戰前,經歷了20余年的發展,雖已積淀了一定基礎,但與同期其他省相比,貴州省中等教育的發展較為落后。據統計,1915年,貴州省有6所中學,學生人數達738人[10]285;1918年,有省立中學學生2 235人,僅占全國中學生總人數的1.9%[11];1935年,全省中學教育機構33所,學生8 548人[10]286;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全省有46所中學,學生12 457人,僅占當時貴州人口的1‰左右。而且,這一時期的中學多數集中于省會貴陽及部分較大城鎮,多數縣沒有中學。但在全面抗戰時期,隨著國民政府內遷重慶,華東、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區高校、工礦企業、文化團體內遷貴州,貴州人口隨之劇增,教育需求迅速擴大,迎來了貴州中等教育發展的大好契機。截至1945年抗戰勝利,貴州省有國立高級中學38所,省立中學5所,87個縣(市)中就有25個縣(市)設立了國立中學[12]。
3.高等教育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躍升
抗戰前,貴州省僅有兩所高等學校:貴州省立政法專門學校和貴州大學。1913年,貴州省將原有的“官立法政學堂”改造為“貴州公立政法專門學校”,1920年將其改為“貴州省立政法專門學校”。1928年,時任貴州省教育廳廳長周西成在原有“貴州省立政法專門學校”和“南明中學”的基礎上創立“省立貴州大學”,主要培養經濟、醫學人才,并為桐梓系軍閥培養軍事人才。但后來通過“并”“停”措施,1930年該校停辦。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確定了“抗戰建國”的基本國策,提出了“戰時須作平時看”的教育方針,為“維系民族文脈,保存國家精英”,國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將包括軍事院校在內的二十多所高校內遷貴州,分布在以貴陽、遵義、安順為中心的全省各地。此外,國民政府吳鼎昌省長充分利用高校內遷帶來的人才、資源、政策等優勢和歷史機遇,著手創辦貴州自己的高校。1938年,貴州省歷史上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高等學校——貴陽醫學院成立。為解決此時中等教育快速發展帶來的師資嚴重匱乏問題,1941年創立了國立貴陽師范學院,為抗戰建國培養各方面人才。1942年,在原農工學院的基礎上成立了“國立貴州大學”。可以說,高校內遷不僅壯大了貴州近代高等教育規模,同時開創了貴州真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歷史。
4.民族教育、職業教育和社會教育成績斐然
民族教育實現了較之以前量的突破。貴州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受教育程度低,國家民族觀念淡薄。抗戰爆發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國民政府認識到要鞏固國防,爭取抗戰的勝利,不僅要壯大軍事力量,更要發展邊疆少數民族文化教育,開啟民智,凝聚各民族力量。于是,貴州省政府進一步重視民族教育,成立專門教育機構,制定和頒布民族教育方案;改善辦學條件,增加經費投入;培養優秀師資隊伍。一系列措施的有效實施,貴州民族教育取得了較大成就。1942年,貴州省政府明確規定1/3的國民小學要辦民族教育,少數民族分布區域內的46所中學“予以少數民族學生優待”,明令大夏大學、貴州大學等高校要招收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學生。
在職業教育方面,抗戰前貴州省只有醫科職業學校、貴陽初級農業職業學校等幾所職業教育機構。抗戰開始后,貴州省頒布《貴州省職業教育調整辦法》《貴州省職業教育分期輔導實施辦法》等法規,成立“貴州省農工職業教育委員會”組織,規范職業教育辦學,到抗戰結束時已有職業學校13所,涉及工、農、醫、林等行業。由于各類學校的增多,貴州省面臨師資缺口,因此,隨著抗戰時期部分高校西遷貴州,國民政府在貴州省開始大力創辦師范教育,在全省設立了貴陽、黔東南、黔南、盤縣、遵義和黔西南等6個師范學區,使得貴州師范教育機構從寥寥幾個迅速增加到上百個。以黔東南地區為例,自1942年在從江開始設置“從江教師暑期講習班”開始,陸續在施秉、黃平、余慶、臺江、丹寨、劍河等地都設立了簡易師范學校,為“蠻荒之地”的新式教育培養了大量師資。
社會教育方面成績較為突出。民眾教育主要是針對學齡階段卻失學、未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成年人而開展的文化補習教育,主要為識字教育、生計教育與塑造新風俗。自1940年起,通過多種方式進行社會教育:一是舉辦戰時民眾教育。在全省沿公路的30個縣(市)開設了1 588個戰時民眾補習班或補習學校,開展“初等語文教育為主,公民生計教育為輔的社會性教育”,抗戰掃除近3萬名文盲,至1946年貴州作為民眾教育優秀省份,掃盲比例超過全國57%的平均水平[13]。戰時民眾教育既傳授文化知識,又培養社會的新禮俗,喚醒了民眾的民族意識,激發了民眾的民族精神,為培養“新國民”作出了貢獻。二是實施和加大電化教育與“巡回施教”力度。1936年始,國民政府出臺了《各省市實施電影教育辦法》《各省市實施播音教育辦法》,以推行電化教育。由于高校西遷之前,貴州省電化教育人員奇缺,貴州省的電化教育推行較慢,西遷高校帶來了現代電化教育的設備與人才,為貴州省的電化教育提供了可能。1943年,貴州省設立了“電化教育服務處”(后改稱“電化教育輔導處”),開展全省電教技術輔導及示范施教工作,主要通過影片向社會民眾進行識字教育和知識普及教育。部分高校還派出教員在公路通達的縣里運用巡回施教車,擴大了受眾范圍,如1944年上半年巡回施教車在黔東南地區就“行程789公里,施教……451小時,施教人數達81萬余人”[14]。三是利用各類學校舉辦抗戰宣傳、衛生指導、戰時救護、軍事訓練等。
(二)優化了貴州省的教育體系結構和區域分布
抗戰期間,貴州教育實現了由原來的小學教育一枝獨秀向各級各類教育共同發展和區域平衡化發展的轉變。抗戰前,貴州省教育結構和地區分布極不合理,據統計,1930年全省共有小學1 935所,在全國排名第33位[15]。對當時的貴州而言,初等教育是貴州教育結構中的主體,且在軍閥混戰時期,受戰亂影響,政局動蕩不安,這些學校大部分集中在貴陽、遵義等中心城市,各縣小學“虛有其名”,尤其是邊遠地區和農村學校更是寥寥無幾。中等教育中,1932年全省有中學28所,占全國中學數量的1.46%;在校學生6 770人,占全國中學生總數的1.65%[16],不到全省總人口的0.1%。主要分布在當時經濟、交通較為發達的貴陽、遵義、安順、都勻等地,大部分縣無中學。貴州省最早的現代高等教育是清末辦起來的貴州大學堂,后來陸續建立了貴州高等學堂及幾所政法學堂,這些學校都因為軍閥混戰、政權更迭頻繁而相繼停辦。周西成創辦了省立貴州大學,但由于經費不足而不到兩年就停辦了。抗日戰爭以前貴州基本沒有高等教育,只有貴州省甲科農業學校、省立師范學校和女子師范學校等幾所中等學校,但在戰前也通過“并”“停”已處于“休克”狀態。
全面抗戰開始以后,貴州省接受了來自浙江、江西、湖南、廣西等地的大批高等學校、軍事院校與國立中學,高等院校就有上海私立大夏大學、國立湘雅醫學院、國立浙江大學等9所,軍事院校就有陸軍大學、陸軍步兵專科學校等10余所,貴州很快就成為全國矚目的高等教育重地,被李約瑟博士稱為“東方的劍橋”。抗戰時期的高校西遷運動,不但快速提升了貴州高等教育的發展速度與結構層次,還構建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學科結構,高等學校的學科基本涵蓋了理、工、農、醫、文、史、軍、教等各學科;同時,還優化了貴州省的高等教育區域結構,高校不僅分布在貴陽、遵義、安順等中心城市,就連較為偏僻的榕江、福泉等縣級城鎮也都有高校入駐。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實施國民教育,頒布的《國民教育法》《強迫入學條例》等法規規定,“每保必設一國民學校(初級小學),每鎮必設一中心國民學校(高級小學)”,使得貴州的初等教育合理分布在各地,尤其是彌補了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無學校的短板。在這一時期,部分教育部直管的國立中學如國立三中、國立十四中、國立二十中等都遷到貴州省,改善了貴州省的中學布局。貴州省還充分利用了大批專家、學者內遷的人才資源優勢,設立了大批中學,極大地推進了中等教育發展。到1945年,全省每個專區都有中學,87個縣中有25個縣(市)設有國立中學,推動了中等教育的大發展和普及,中等教育地區分布更為均衡。到抗戰結束時,貴州已形成了由學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等組成的各級各類較為合理的教育體系結構,區域分布較為均衡。
(三)辦學層次和質量明顯提高
辛亥革命以后,國民政權只維持了3個月就結束了,之后就處于二十多年的軍閥混戰時期,戰事頻繁,軍閥無暇顧及教育發展。在“新學入黔”時期,貴州先后斷斷續續地舉辦過高等教育,但隨著1930年省立貴州大學的停辦,貴州省的高等教育幾乎成為空白,整個貴州省的辦學層次全面低于全國水平。隨著抗戰的全面爆發,國立浙江大學等9所高校內遷,加之本省的貴州大學和貴陽師范學院,貴州省的高等教育體系得到了重建,填補了高等教育的空白,幾乎重構了中國當時的高等教育“版圖”。
隨著辦學層次的提高,辦學質量明顯提升。大批知識分子、專家、學者和學術精英紛紛沓至貴州,形成了貴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群英薈萃、人才鼎盛時期。竺可楨、蘇步青、豐子愷、茅以升等一大批專家學者、教授,將他們嚴謹治學的學風帶入貴州大地,在國難當頭的艱難困苦下,嘔心瀝血、枵腹從公,或在當地中小學兼課,或創辦學校,為當地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極大地舒緩了貴州中小學教育師資嚴重短缺的狀況,提升了貴州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和教育質量。如當時內遷湄潭的浙江大學師范學院設有中學部,著名教授胡家健擔任校長,教師大多都是知識淵博的大學講師或助教,學生多是從江浙流亡而來或從湘川桂黔慕名而來,第一屆畢業生多數考上高等學府。再如1943年,由江西、貴州、甘肅3省聯合舉辦的高中會考和升學考試中,貴陽中學名列第7,升學率達90%多,創下當時貴州乃至全國一流水平。
三、抗戰時期高校西遷貴州的當代啟示
盡管抗戰時期的大學“西遷運動”是民族危難時代的一次退讓,但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義,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一次變革與重生,有效地保護了我國高等教育的有生力量與民族文化成果,為國家輸送抗戰與建設人才以及完善西部高等教育體系和布局作出了卓越貢獻。部分高校西遷貴州在當時高校“西遷運動”中最為突出,不但為貴州當時的經濟社會與教育發展作出了貢獻,更為當今高等教育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
1.愛國情懷是教育發展的核心邏輯
抗戰時期高校內遷正值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艱難時期,高校中廣大愛國民主人士和進步學生在食不飽腹、衣不御寒,辦學經費和設備異常奇缺的艱苦環境下,絲毫沒有動搖立志教育救國、興學抗戰的意志,反而堅定了救國圖存的信念。正是他們時常懷揣一種教書不忘抗戰、讀書不忘救國的強烈愛國主義熱忱,飽含深厚的愛國情懷,不畏艱苦、團結一致,保存和傳承了中華民族的教育文化根基和基本力量,推動了貴州等落后地區教育文化乃至社會的全面發展。
教育是愛國主義傳承與發揚光大的永恒主題,教育事業必須承擔這一重任。愛國主義是與歷史時代密不可分,是動態變化發展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豐富內涵。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愛國主義的具體內容,看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來決定。”[17]在抗戰時期,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爭取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就是愛國主義的靈魂。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時代,愛國主義的鮮明主題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本質是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突出特征是愛國情懷與改革精神、世界眼光相結合。當今教育工作必須吸取抗戰時期的教育文化傳統思想精華,將培養愛國主義精神、厚植愛國情懷置于教育工作的邏輯起點,作出教育要“為誰培養人、怎樣培養人、培養什么人”的正確回答,強化學校立德樹人的辦學目的,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作出貢獻。
2.要堅持教育的優先發展地位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說明教育的價值需要較長時期才能得以顯現。教育可以為國家儲備未來的建設者與創造者,教育在國家建設中應該具有優先地位。抗戰時期,中日民族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當時的國民政府,都把教育作為抗戰的重要內容之一,將教育放在優先發展的地位。1937年,毛澤東同志在論《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指出:“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國民政府也認為:“抗戰、建國應同時并進,教育尤為建國之基礎。”[18]正是因為抗戰時期國共兩黨都非常重視教育的優先發展權,始終把教育作為推動國家發展、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重要基石,才使得高校的“西遷運動”得以順利實施并達到了預期效果。
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新時代,發展是第一要務,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第一資源。當今時代,我國對科學知識和卓越人才的渴望超越以往任何時候,教育作為國家發展的智力支撐和人才保障,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關鍵,關乎中國夢能否順利實現。因此,我們必須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地位,遵循全面從嚴治黨規律推進各級各類學校黨建科學化[19],凸顯教育的基礎性、先導性和全局性的地位與作用,倍加重視教育的服務和支撐功能,堅定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在全社會形成教育合力和重視教育、崇尚科學、尊重人才的良好風氣。
參考文獻:
[1] 吳家瑩.中華民國教育發展史[M].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
[2]顧毓琇.抗戰以來我國文化教育之損失[J].時事月報,1938(5):34.
[3]曲士培.中國大學教育發展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339.
[4]李治壁.抗戰時期貴州的小學教育[J].產業與科技教育,2019(14):158.
[5]杜元載.抗戰時期教育[M].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2:94.
[6]李桂林,等.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85-87.
[7]沈云龍.中國近代史料叢刊(第10輯)[M].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245-246.
[8]遵義市志教育志編委會.貴州省志·教育志[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304.
[9]韓繼偉.抗戰的貴州[M].貴陽:貴州出版集團貴州教育出版社,2019:295.
[10]孔令中.貴州教育史[M].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4.
[11]周元春,何長風,張祥光.貴州近代史[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7:266.
[12]張羽瓊,郭樹高,安尊華.貴州教育發展的軌跡[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272.
[13]李良品.論國民時期的貴州民眾教育[J].貴州文史叢刊,2004(4):83-84.
[14]周慧梅.新國民的想象:民國時期民眾學校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46.
[15]傅宏.民國時期的貴州教育[J].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66-69.
[16]熊宗仁,肖良武,羅凌.貴州區域地位的博弈[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197.
[17]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青年運動文件選編[G].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18]陳永蓮.抗戰時期國共兩黨教育政策論析[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06.
[19]朱洪波,馬彥濤,任彧.遵循全面從嚴治黨規律推進高校黨建科學化[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0(7):142-146.
(責任編輯:楊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