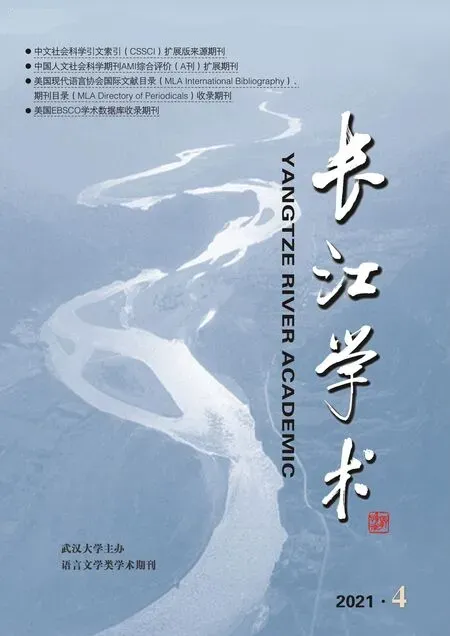“跨文化”與戲曲研究的新視域
——“戲曲跨文化研究專題”編者按
程蕓
“跨文化”(intercultural)的觀念來自西方學界,“跨文化戲劇”(intercultural theatre)來自歐美的前沿戲劇實踐者和理論家,然而我們也注意到,21 世紀以來,這兩個作為“舶來品”的術語、概念,日益頻繁地出現在中國傳統戲劇(所謂“戲曲”)研究者的筆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是:“跨文化”+“戲曲”的表達方式,屢屢成為各種論文、著作的標題。以專著為例,據筆者粗略檢索,有孫玫《中國戲曲跨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06)、林一和馬萱《中國戲曲的跨文化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劉珺主編《中國戲曲跨文化傳播與人才培養戰略研究》(文化藝術出版社,2016)、江棘《穿過“巨龍之眼”:跨文化對話中的戲曲藝術(1919—1937)》(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凌來芳等《中國戲曲跨文化傳播及外宣翻譯研究:以越劇為例》(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2019),等等。即便一些大體沿襲已有“中西(中外)戲劇比較”或“東亞傳統戲劇研究”框架的成果,如盧昂《東西方戲劇的比較與融合——從舞臺假定性的創造看民族戲劇的構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都文偉《百老匯的中國題材和中國戲曲》(上海三聯出版社,2002)、劉彥君的《東西方戲劇進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廖奔《東西方戲劇的對峙與解構》(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范希衡的《〈趙氏孤兒〉與〈中國孤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等,不管是平行研究,還是影響研究,也經常將論題延伸到“跨文化”的視域之中,由此,理論性、思辨性得到了明顯的提高或深化。
至于什么是“跨文化戲劇”,其戲劇實踐、理論探討和個案考察之間的關系,應該如何處理,學人或各自有其認知和取向。或許可以這么說,“跨文化”“跨文化戲劇”雖然是舶來品,但經過戲曲研究者的“創造性”轉換,“跨文化”“戲劇”與“跨文化戲劇”都已不再拘泥于原來的理論語境、話語邏輯和對象范圍,既能夠用于考察、細究中國傳統戲劇(“戲曲”)“走出中國”“走向世界”的種種歷史場景,也成為了分析當下某些戲曲創新現象的利器。可以確切地認為,“跨文化”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近20 年來的戲曲和戲曲史研究,既極大地豐富了史料、文獻的范圍,更進一步擴充或延伸了研究者的視域,成為戲曲研究者日益自覺的一種方法論。事實上,很多研究者在擴充對象、史料范圍的同時,更明確地賦予了“跨文化”以“新方法”“新視域”的意義。
當然,戲曲的越境或跨國并不能等同于“跨文化”,戲曲在漢字文化圈的流播與其在歐美等非漢字文化圈的流播,也不能等而視之。而我國本土戲曲對域外戲劇的創造性借鑒和改編,其利弊得失、優缺短長如何,亦尚難有共識或定論。但顯然,“跨文化”作為一種日益自覺的方法論,一方面,既為中國傳統戲劇的研究推蕩出了一片廣闊的新空間,甚至制造出熱點話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回應某些跨學科的前沿話題,從而更進一步地展現傳統戲曲研究之于當下作為整體的中國人文學術的新價值。
本期所刊發的三篇文章,其選題對象、切入視角和討論方式都有極大的差別,然而,從史料發掘、視野方法到理論分析來看,都表現出“跨文化”影響下的某些自覺,值得學界關注,也期待有更多的學者來參與這一“新方法”“新視域”框架之下相關論題的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