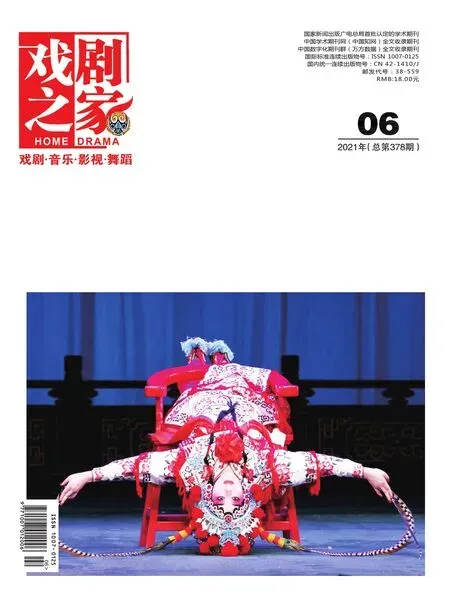試論京胡曲牌在劇目中的應用
(中國戲曲學院 北京 100710)
一、胡琴曲牌的淵源
曲牌是傳統填詞制譜用的曲調調名系統,俗稱“牌子”。老一輩藝術家詞曲創作原是“選詞配樂”,也就是說原始曲牌配有唱詞大字,而這樣的唱腔被稱為“曲牌體”。從先秦歌舞、秦漢散樂、百戲、隋唐歌舞戲、參軍戲、宋金雜劇,再到元雜劇、明清傳奇直至戲曲誕生前期,“依音填詞”一直是戲曲唱段的主要形式。隨著京劇板腔體的出現,曲牌漸漸脫離唱詞,獨立成句的曲牌演奏形式開始出現。關于曲牌的來源,明王驥德《曲律》說:“曲之調名,今俗曰‘牌名’”。喬建中先生在論文集《土地與歌》中的曲牌論涉及曲牌的形成期:唐宋大曲、宋詞、北方民間音樂和金元音樂形成的北曲(元雜劇);唐宋大曲、宋詞和南方民間音樂形成南曲(元明雜劇傳奇);北曲和南曲構成明傳奇(曲牌體戲曲)。明沈璟《九宮詞譜》共列曲牌685 種;清乾隆十一年編成《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匯集南北曲曲牌高達2094 種,可見曲牌數量之廣。總而言之,曲牌來源于南北曲和民間小調,有特定名稱,用于戲曲、曲藝的填詞創作或器樂演奏。
二、絲弦曲牌的分類
曲牌數量繁多、包含甚廣,是京劇音樂的一大分支。胡琴曲牌是其中重要一脈,首先按曲牌的音韻來分則分為西皮、二黃兩種。西皮音色尖銳響亮、清脆悠揚,適用于急促或歡快的情景,如【洞房贊】、【西皮小開門】等。二黃結合自身音色的特點,運用溫厚隆重、寬亮端莊的色韻營造出莊重嚴肅或悲傷煩悶的情境,如【哭皇天】、【二黃春日景和】等。其次,按曲牌色彩劃分則范圍較廣,如歡快類的【柳青娘】、【八板】;憂傷類的【哭皇天】、【鷓鴣天】;急切類的【雙小開門】等等。最后是按其音樂性質大致分為兩種,即戲中應用及獨奏應用。獨奏應用是相對于戲中應用而言的,自身獨立成曲,并不襯托動作或特殊劇情,如家喻戶曉的【夜深沉】、【迎春】等。獨奏版【夜深沉】共有兩種:其一是傳統色彩濃厚的鼓樂【夜深沉】,著重于演奏者技巧展現及強調古香古色的韻味;另一版是由吳華先生由鼓樂這版后期改編而成,著墨于夜色空靈氛圍的渲染,由抒情與急速兩部分構成。兩版各有千秋,獨具特色,廣為后世流傳。
本篇文章側重于論述胡琴曲牌戲中運用,因此對獨奏牌子不做贅述。戲中應用的牌子為伴奏曲牌,大多數是由昆曲牌子移植、演變而來,在戲中唱段間的連接上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在戲中無唱段、無唱詞的情景處以巧妙代替了蒼白,使之更為傳神、生動。胡琴曲牌以“清牌子”為主,簡單來講就是不填詞。根據戲中所需要的時間長短可采用“整曲牌”或“部分曲牌”兩種形式。由于曲牌自身可隨劇情逐句而收,每句都配有一個收頭,也可隨劇情無限反復,為京劇這一程式化表演方式尤其在無行腔的表演情況時,可以填補舞臺上的空白,大大增強念詞、動作的韻律性、線條性及趣味性,無愧于“戲曲音樂之魂”的美譽。
三、胡琴曲牌在劇目中的實際應用
(一)《貴妃醉酒》中曲牌與唱腔的結合
《貴妃醉酒》又名《百花亭》,源于乾隆時一部地方戲《醉楊妃》的京劇劇目,該劇經京劇大師梅蘭芳傾盡畢生心血精雕細刻、加工點綴,成為梅派經典代表劇目之一。劇中唐玄宗先一日與楊貴妃約,命其設宴百花亭,同往賞花飲酒,至次日,楊貴妃先赴百花亭,備齊筵席候駕,許久,卻不見唐玄宗車馬來到。此時,高、裴二士忽報皇上已去往西宮。貴妃聞訊,懊惱不已,萬種情懷一時難以排遣,加之酒入愁腸,三杯亦醉。整出戲以貴妃情感作為線索,與故事情節相得益彰,映射了貴妃心理變化全過程。
此出劇目音樂是傳統戲曲最優秀的繼承品,也是最偉大的創新品。“四平調”的唱段穿插許多傳統曲牌,是唱腔與音樂的成功結合,是傳統戲曲劇目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全劇首個曲牌在開場時便大展身手,戲中一改“撤鑼”開場的傳統手段,而是將曲牌【朝天子】作為氣氛渲染和色彩方向的制定。伴著清亮優雅的樂符,悠長的胡琴音籠罩著場內的每寸空氣和土地。金色幕簾緩緩走向兩側,臺中央金色的燈光灑下來,古代宮廷的金碧輝煌、風姿綽約的盛世大唐頓時營造得淋漓盡致。劇調此時轉為另一曲牌【小開門】,踩著曲點的是左右兩路開道的宮女。【小開門】是京劇伴奏中的常見曲牌,與【朝天子】相較應用更加廣泛,由于其變化靈活,且能單雙搭配,因此除了可用于演員內心獨白戲外,同時也可用來營造宮廷氛圍或表達帝王將相上場的氣派。劇目伊始,兩段極具宮廷音樂特色的曲牌充分映射出古代紅墻綠瓦內的氛圍環境,當宮女太監站定兩廂時,樂曲音律隨之漸落,搭配巧妙節奏銜接靈敏,又側面烘托出“楊娘娘”貴妃的排場。
第一段“海島冰輪”的四平結束,用正二黃【萬年歡】銜接。這首曲牌的旋律基調歡快,使用“二黃”演奏為其增加了幾分莊重。在戲中此曲牌運用在唱段結束后,除了緊托宮廷景象的節奏,還能夠映襯演員的動作——“楊娘娘”一曲作罷整戴衣冠,接受朝官的拜見。曲調一直持續到貴妃入座,一來保持了宮廷景象的氛圍,使觀眾實時沉浸其中;二來避免了演員在舞臺上無唱詞表演時的單調。
第二段四平中嵌入了曲牌【回回曲】的片段,曲調連貫流暢,穿插于唱腔中,一則新穎出奇,二則當作演員對白時的背景音樂,三則也是此段承上啟下的紐帶,并同時給予演員喉嚨片刻的休息時間。娘娘從宮中到百花亭一路走來,帶著愉悅的心情觀看鴛鴦戲水、鯉魚朝拜,一段“碰板”結束后再次運用【萬年歡】。與之前不同的是,這次的【萬年歡】是反二黃把位,正調唱腔灌入反調曲牌,是京劇音韻上一次偉大的革新,不僅增強了唱段的生命力,也提高了觀眾的興趣。
此時劇情來到了百花亭中,貴妃娘娘款坐亭苑,忽聞萬歲駕轉西宮,花容失色,遂借酒澆愁。念白過后,配合貴妃嗔怒心境的曲牌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傍妝臺】。旋律采用中速演奏,內外弦對比鮮明,好似用音符將愁緒串連,傳達給觀眾。裴力士進酒,緊托單雙反二黃【小開門】,宮娥們與高力士進酒,以單雙正二黃【小開門】為點綴。音律映襯演員動作的同時,利用單雙結合,將滿腔的心煩意亂、如麻的愁緒也一并托出。得知萬歲爽約的消息,貴妃心中有千萬般的不情愿,卻礙于君臣、礙于身份、礙于在侍者面前,為不失華儀只得自怨自艾,煩亂、焦躁正是用中快速曲調烘托最為妥當。三個人物,三種曲牌,三面渲染,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既充滿傳統色彩,又不失創新風范,不僅是京劇中視為瑰寶的新穎,同時也將京劇曲牌的作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酒過三巡,微醺的楊妃仍覺心中苦悶難以排遣,此時劇作的旋律線到達高潮。接下來的曲牌在整部戲中舉足輕重,是劇情承上啟下的橋梁。貴妃吟唱醉酒之意,戲弄太監端花盆、雕杯盞,一系列的鋪墊為傳統曲牌【柳搖金】。這一段戲,演員既無唱詞也無念白,而是運用“聞花、扇舞、臥魚、醉步、下腰”等肢體動作,演繹醉酒之態。此曲節奏流暢,變化度高且旋律性強。舞臺上演員用肢體表演,樂池中樂隊用音符表達,默契配合、相輔相成。旋律的流動不僅使演員的動作飽滿有生氣,并使得觀眾的意識時刻沉浸在劇情中,同時又是演員對白時得當的背景音樂。通過單雙緩急,映襯著“楊娘娘”時緩時促的動作形態,二者相互襯托,“醉態”畢現。早先,徐蘭沅與王少卿二位先生在【柳搖金】一曲中使用“反二黃”把位,經過創新,現也可用五個調門將其奏出,即“41 52 63 74 15”。這樣的改革,不僅使旋律更加彰顯音樂特性,并充分展現了大師的創新精神,同時也是京劇傳統曲牌的一個重大突破。因此,用【柳搖金】一曲襯托貴妃娘娘的醉意,是與梅先生“唱念做舞”的巧妙結合,彰顯出老一輩藝術家高超的欣賞水平、創作水平和藝術素養。
劇情發展的此時,來到了戲作的后半場。當高、裴二士想讓娘娘早些回宮誆駕后,其動作、念白予以點綴的是曲牌【行弦】。末尾兩唱段與兩位侍者的對白分別采用【鷓鴣天】與【正反八叉】作唱腔后的銜接工作,娘娘由微醺到下半場的酩酊大醉,一路由各式不同的曲牌搭配,隨著故事線得當穿插,充分烘托演員在場中的一舉一動。落幕時的“皮黃”尾聲稱得上是整部戲的點睛之筆。曲牌的不斷變換使《貴妃醉酒》一戲成為傳統戲曲最忠實的繼承者,也是最巧妙的曲目創新者。京劇唱腔、曲牌博大精深,梅先生與徐、王二位先生的巧妙結合更是為京劇音韻寶庫貢獻出難以超越的智慧。
四、結語
京劇樂隊在一場演出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對演員而言能引導其情感抒發,對舞臺來說是營造氣氛的一把好手,對于觀眾而言是深入了解戲劇作品的鑰匙。談及京劇音樂,人們較為熟識的是其托腔保調的責任,而本文著重于演員并無唱腔,只通過面部表情肢體動作、只字片語的念詞的表演情境,此時京劇樂隊的重要性可謂凸顯之至。戲中這些“節骨眼兒”是劇作的精華所在,演員在臺上用肢體表演,樂隊在幕后用音符演繹,臺上的一抿一笑,一半是演員在演,一半是樂隊在演,唯有兩者天衣無縫的配合,才能呈現一出精彩好戲。京劇音樂尤其是曲牌是一堂樂隊實踐經驗之所在,是一場戲烘托氣氛關鍵之所在,亦是京劇畫龍點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