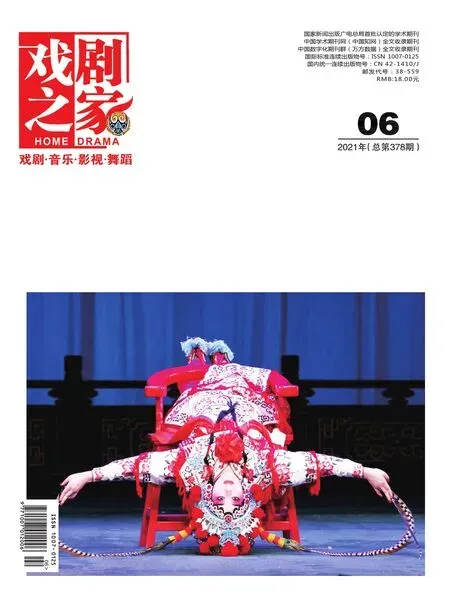《金陵十三釵》的影視化改編
(西南民族大學(xué) 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0200)
伴隨科技革命的不斷推進(jìn),現(xiàn)代科技得到了迅猛發(fā)展,由此帶來了大眾傳播媒介的日益多樣化。傳播媒介的多樣化又促進(jìn)了文學(xué)作品傳播方式的多樣化。越來越多的文學(xué)作品被改編為具有強(qiáng)烈視聽性的影視作品。電影《金陵十三釵》便是其中一例。它改編自嚴(yán)歌苓的同名小說,由劉恒、嚴(yán)歌苓擔(dān)任編劇,張藝謀執(zhí)導(dǎo)。影片以南京大屠殺為大背景,講述了南京的一座教堂中,一位假神父,一群生死未卜的女學(xué)生,十四名躲避戰(zhàn)火的風(fēng)塵女子,以及殊死抵抗的中國軍人一起面對孰生孰死之艱難抉擇的故事。
一、人物形象的改編
首先,是對角色約翰的改編。影片最大的問題就是約翰為何突然從一個(gè)貪財(cái)好色的酒鬼變成了一個(gè)主動(dòng)放棄逃生機(jī)會(huì)、努力幫助女學(xué)生們逃離日軍魔爪的神父。相較于本片另一主要人物趙玉墨來說,他的這種轉(zhuǎn)變實(shí)在太缺乏動(dòng)機(jī)。
縱觀整部影片,玉墨的轉(zhuǎn)變還是有跡可循的。隨著影片情節(jié)的發(fā)展,可以歸納出幾層鋪墊。第一,她和姐妹的到來,占據(jù)了本該讓女學(xué)生們躲避危險(xiǎn)的地窖。日軍第一次沖進(jìn)教堂,書娟和其他女學(xué)生在慌忙奔逃的過程中,來到了玉墨及其姐妹藏身的地窖口。在這里書娟和玉墨有過一次短暫的對視鏡頭。兩個(gè)同樣面臨困境的群體,兩個(gè)群體的代表,在短暫的安靜中,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書娟的選擇讓玉墨及其姐妹免遭暴露,卻讓女學(xué)生們險(xiǎn)遭日軍侮辱,其中一名學(xué)生更不幸墜樓身亡。對玉墨來說,這是一份尤為珍重的救命之恩。第二,李教官和玉墨有過一次談話,玉墨因此得知李教官及其兄弟原本可以撤出南京城,正是為了保護(hù)這群女學(xué)生而選擇與日軍同歸于盡,只剩下他一人。這件事進(jìn)一步震撼了玉墨的心靈。第三,約翰向玉墨坦白豆蔻的慘死,這讓玉墨深切地體會(huì)到日軍的殘暴。她又聯(lián)想到自己的身世,她也曾是教會(huì)學(xué)校里單純的女學(xué)生,后來無奈淪落風(fēng)塵。基于內(nèi)心對單純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身邊姐妹的悲慘遭遇,她不忍讓這些學(xué)生遭受同樣的凌辱,甚至虐殺。第四,面對日軍的“表演邀約”,書娟和其他女學(xué)生清楚地知道自己將要面臨的悲慘境遇。她們選擇集體爬上高樓,想要跳樓自殺以求解脫。在這危急的時(shí)刻,玉墨立刻答應(yīng)代替女學(xué)生去“赴宴”,其他妓女在玉墨的感召下,也都紛紛答應(yīng)下來。
綜上,玉墨的轉(zhuǎn)變,在故事發(fā)展過程中得到了鋪墊。多重因素的影響,導(dǎo)致她做出了最后的抉擇。令人難解的是她的姐妹們在其感召下,迅速地做出了同樣的選擇。大多數(shù)妓女在影片中并未有太多鏡頭,甚至沒有點(diǎn)出姓名,很難看到她們決絕選擇背后的層層鋪墊,很難感受到她們內(nèi)心的掙扎。大多數(shù)妓女仍然更像是處在被動(dòng)地位、沒有獨(dú)立判斷和思考能力的簡單個(gè)體。當(dāng)然,這個(gè)問題自原著帶來,不能歸咎于影視改編。
回到約翰的人物形象上來,當(dāng)日軍第一次沖進(jìn)教堂想要強(qiáng)奸女學(xué)生時(shí),約翰的挺身而出可以看作是一種帶有普適性的人道主義以及個(gè)人英雄主義;而當(dāng)他外出尋找妓女,遇到同鄉(xiāng),有機(jī)會(huì)可以逃離南京卻果斷選擇放棄時(shí),人物的行為邏輯就并未得到很好的梳理,與前面的約翰形象相比,具有明顯的割裂感。另外,曾目睹兩個(gè)女人被日軍虐殺后的血腥場景的約翰,在妓女代替女學(xué)生這一事件中,面對所愛之人玉墨做出的選擇,表現(xiàn)出的痛苦與糾結(jié)顯得很輕微,不符合一般人的情感邏輯。
如果是小說中真正的神父英格曼,情節(jié)的安排或許會(huì)更為合理。英格曼神父作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認(rèn)為人人都有平等的尊嚴(yán)。原本可以袖手旁觀的他,甘冒風(fēng)險(xiǎn),收留了妓女和中國軍人,并提供給他們?nèi)萆碇捅疽褏T乏的物資。面對日軍的刺刀,英格曼神父毫不畏懼。可以說,他的威嚴(yán)和正直在與日軍的數(shù)次交鋒中展露無遺。而在南京城淪陷后,他讓所有女學(xué)生為國家、民族而哀悼,又體現(xiàn)了他的血性與良知。因此,當(dāng)他心中產(chǎn)生妓女代替女學(xué)生的想法時(shí),他對十字架進(jìn)行禱告。他知道“他將要說的和做的太殘忍了,為了保護(hù)一些生命,他必得犧牲另一些生命”,他安慰自己,“那些生命之所以被犧牲,是因?yàn)樗齻儾粔蚣儯谴我坏鹊纳恢档檬艿剿⒏衤谋Wo(hù),不值得受到他的教堂和他的上帝的保護(hù)。他被迫做出這個(gè)決定,把不太純的、次一等的生命擇出來,奉上犧牲祭臺(tái),以保有那更純的、更值得保存的生命”。但他隨后又懷疑自己是否有替上帝評判優(yōu)劣的選擇權(quán),這體現(xiàn)了信仰與現(xiàn)實(shí)的殘酷對沖。這也是嚴(yán)歌苓原著小說中的一個(gè)出彩之處。人物的兩難選擇造成內(nèi)心的矛盾沖突,展現(xiàn)人性復(fù)雜的同時(shí),也讓故事顯得更有張力。
而電影《金陵十三釵》,為讓入殮師約翰有足夠的理由登場,將英格曼神父設(shè)定為被炸而亡的狀態(tài),約翰為其收殮,因而進(jìn)入教堂。約翰實(shí)際上更像是張藝謀為實(shí)現(xiàn)自己沖擊奧斯卡的愿望而專門設(shè)置的一個(gè)角色。他在電影中經(jīng)歷了由“二流子”向“救世主”的角色轉(zhuǎn)變,符合美國電影中混混變英雄的普遍設(shè)置,但將其置身于南京大屠殺這一沉重的中國歷史背景下,未免顯得有些水土不服。尤其是影片為了重點(diǎn)刻畫其英雄形象,還為他安排了好萊塢式的浪漫愛情橋段,這顯然有異于原著中對少校戴濤和玉墨之間朦朧隱約的好感、副神甫法比對玉墨難以言說的情愫的描摹,與原著的情感表達(dá)方式相去甚遠(yuǎn)。
其次,就是長谷川這個(gè)人物。他是小說中“少佐”形象的影視化改編。小說中對少佐沒有做太多具體描繪,電影中對長谷川的塑造則有不少鏡頭,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在教堂里彈奏日本童謠《故鄉(xiāng)》,這首曲子讓當(dāng)時(shí)在場的士兵都不自覺地哼唱了起來。長谷川受過西方教育,其溫文爾雅的外表和嫻熟流利的英語,讓人感到他實(shí)在是一位上流社會(huì)的謙謙“君子”。但面對約翰的質(zhì)疑時(shí),他稍作停頓,仿佛內(nèi)心有所掙扎,卻還是冷冷地拋下一句“只是執(zhí)行軍令”來結(jié)束對話。本尼迪克特認(rèn)為,“刀與菊,兩者都是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極其好斗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可以說,日本人是優(yōu)雅與殘忍的矛盾統(tǒng)一體。影片中的長谷川,正是對日本人性格中“菊”與“刀”特色的一個(gè)較好詮釋。正如影片中約翰所說,少佐是一位文明人,但是當(dāng)他強(qiáng)令女學(xué)生們?nèi)⒓尤毡救怂^的宴會(huì)時(shí),卻暴露了他野蠻殘忍的一面。這種人物形象的刻畫,既真實(shí)可信,又有觸及人性復(fù)雜的深度,不同于過去一般抗日影片中對日軍軍官的臉譜式塑造。然而,這樣一個(gè)具有復(fù)雜性的人物形象,在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出場中,不僅沒有揭示第一次出場的意圖,更徹底成為了提線木偶,之前對其形象的特寫設(shè)計(jì)也顯得有些多余。
二、敘事情節(jié)的改編
首先,是對數(shù)字“十三”的影視化再創(chuàng)造。電影對“十三”這一數(shù)字的戲劇化演繹,使得情節(jié)曲折多變。小說名為《金陵十三釵》,是因?yàn)樵谛≌f中,教堂一共收留了十四個(gè)妓女,而豆蔻獨(dú)自去找琵琶弦,被日軍所害,就只剩下十三人。而在小說開頭,女學(xué)生共有十六個(gè),中途徐小愚、劉安娜和蘇菲被徐小愚的漢奸父親接走,使女學(xué)生的數(shù)量變?yōu)槭齻€(gè)。最后十三個(gè)妓女代替十三個(gè)女學(xué)生,其間對數(shù)字“十三”未做太多戲劇化處理。
而影片開頭,教堂里的女學(xué)生有十四人,來教堂避難的妓女正好也是十四人。后來,一位女學(xué)生在教堂里不幸被流彈擊中身亡,另一位在與日軍的激烈爭執(zhí)中墜樓身亡,只剩下十二人。接著,電影在描述豆蔻回到青樓尋找琵琶弦的情節(jié)時(shí),設(shè)置了妓女香蘭陪她一起遇害。豆蔻拿琵琶弦,是為了給瀕死的小兵王浦生彈奏一首完整動(dòng)人的曲子,是危境下的一份善意和身處泥淖中對美好單純生活的憧憬。反觀香蘭,她冒著巨大風(fēng)險(xiǎn)回去,僅僅是為了一雙耳墜,這未免有些不可思議。或許有人會(huì)說這雙耳墜對香蘭的意義不一般,但在情勢如此危險(xiǎn)且沒有任何情節(jié)鋪墊的情況下,就安排她陪豆蔻一起遇害,未免有強(qiáng)行拼湊情節(jié)的嫌疑。此外,小蚊子這個(gè)人物與她的寵物貓,也是為了數(shù)字“十三”而專門設(shè)置的。小蚊子是電影中新設(shè)置的人物,她在日軍清算人數(shù)時(shí)為尋貓而暴露,成為引出“十三”這個(gè)數(shù)字的一個(gè)關(guān)鍵設(shè)置。
但是,仔細(xì)梳理,會(huì)發(fā)現(xiàn)圍繞數(shù)字“十三”演繹的巧合實(shí)在過多:豆蔻和香蘭本來已經(jīng)順利拿到琵琶弦和耳墜,偏巧回程途中香蘭的琵琶弦不慎遺失,再次撿回后又正好看見血腥的場面,以致大聲地叫喊引來了本已擺脫的日軍;小蚊子冒生命危險(xiǎn)去尋找一只貓,而且是在豆蔻等人剛遇害不久的情況下,并且這只貓正好在關(guān)鍵時(shí)刻跑了出來,直接導(dǎo)致小蚊子暴露在日軍的視線下。這一切都顯得過于巧合,設(shè)計(jì)感太強(qiáng),匠氣過重。
其次,電影中“生死”話題的反復(fù)重申,讓人乏味。以女學(xué)生的生與死為主要話題,影片相繼插入了國民黨軍隊(duì)、小兵浦生、妓女豆蔻等多方對象、不同身份人物在生與死之間的矛盾與掙扎,較好地設(shè)計(jì)了每一幕的高潮,給觀者以強(qiáng)烈的震撼感。但正是因?yàn)槊恳荒坏母叱倍既绱藦?qiáng)烈且主題相同,以至于觀眾會(huì)在觀影時(shí)產(chǎn)生重復(fù)感。
這一點(diǎn)可以對照原著中的幾處情節(jié)。第一,徐小愚父親的出現(xiàn)引發(fā)了一個(gè)小高潮。他利用漢奸身份,成功拿到暢通無阻的通行證,在女兒的請求下,答應(yīng)帶其中一個(gè)女學(xué)生劉安娜一起離開。這導(dǎo)致另一個(gè)學(xué)生蘇菲的不滿,她點(diǎn)明徐小愚也曾答應(yīng)過帶她離開。小說從這里開始了對書娟的心理描寫,一方面她內(nèi)心極度渴望徐小愚可以摒棄前嫌,主動(dòng)提出帶她離開;另一方面,強(qiáng)烈的自尊不允許她先向徐小愚開這個(gè)口。徐小愚最后決定抓鬮來確定可以跟隨自己離開的人選,書娟卻直接放棄了這一機(jī)會(huì),并且最后也沒有接受徐小愚父親帶來的巧克力。注意小說中將抓鬮這一行為定義為“玩弄”,這是以書娟侄女的視角進(jìn)行評價(jià)的。其實(shí)梳理前文徐小愚和孟書娟的相處,可以看出徐小愚是很樂意讓書娟成為自己的長久密友的。所以筆者認(rèn)為徐小愚說出抓鬮這種方式,乃是在當(dāng)時(shí)與書娟僵持不下的情況下,作出的最后一點(diǎn)努力。她希望書娟是那個(gè)幸運(yùn)的人,但孟書娟的倔強(qiáng)與自尊讓她直接放棄了最后的機(jī)會(huì),她不接受徐小愚父親的巧克力的行為實(shí)際上是和徐小愚賭氣的表現(xiàn)。原著的這處情節(jié),反映出女學(xué)生們雖然隱約感受到局勢的危急,但少年意氣仍然使她們做出看似幼稚的行為。然而反過來看,跟隨徐小愚父親離開也未必是件值得高興的事。為日本人辦事的他,大概率沒有什么好下場,這時(shí)徐小愚和其他兩個(gè)女學(xué)生又該何去何從。由此可以看出徐小愚父親的出現(xiàn)使得小說張力十足,也為后續(xù)“十三釵”作了鋪墊。第二,中國軍隊(duì)不戰(zhàn)而降。中國軍人受對外界情況缺乏認(rèn)知、饑餓、日軍會(huì)優(yōu)待俘虜?shù)尿_局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選擇投降,讓日軍捆綁了雙手,最后被趕到江邊,集體遭到屠殺。行進(jìn)隊(duì)伍中一聲聲反復(fù)詢問的話語,反映出士兵們內(nèi)心對生的極度渴望,以及在絕望困厄中喪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終致慘死的結(jié)局。第三,李全有與王浦生的相識(shí)。兩人在日軍進(jìn)行江邊屠殺后得以幸存,并互幫互助求得一點(diǎn)生機(jī)。在王浦生傷重昏迷和隨時(shí)會(huì)被日軍發(fā)現(xiàn)的情況下,李全有并未丟下他獨(dú)自逃生,反映了戰(zhàn)亂中人與人之間難得的一絲溫情。
以上三個(gè)情節(jié),或多或少也摻雜有生與死的話題,但更多的是容易引起我們對人性的思考,讓小說的節(jié)奏轉(zhuǎn)向低緩平和,從而使整個(gè)故事的發(fā)展有張有弛,也讓整部小說更具有張力。
三、結(jié)語
綜上所述,張藝謀導(dǎo)演的電影版《金陵十三釵》是一個(gè)藝術(shù)性向商業(yè)性有所妥協(xié)的產(chǎn)物。影片對故事人物形象及相應(yīng)情節(jié)的改編,使故事情節(jié)相較原著更加跌宕起伏,迎合了觀眾口味,有利于增加票房收益。但在展現(xiàn)情節(jié)邏輯的合理性、人物性格的復(fù)雜性上,不如原著小說。
文學(xué)作品的影視化改編,實(shí)際上涉及到文學(xué)的跨學(xué)科研究問題。學(xué)科融合的文化發(fā)展大趨勢、繁榮的圖像“跨界”時(shí)代、審美化的日常生活,都表明跨學(xué)科研究是當(dāng)今世界文化發(fā)展的要求。在這種情形下,當(dāng)代中國電影,更需要的是國際眼光、全球視野和民族特色。“當(dāng)我們看改編自文學(xué)作品的電影時(shí),我們看到的是以影像重構(gòu)的歷史與過去的文化、社會(huì),以及在重構(gòu)的過程中,影像如何透露電影導(dǎo)演的時(shí)代背景與電影制作方式的創(chuàng)新與革命,或是摻入了東方與西方、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歷史與今天進(jìn)行對話的聲音。”在全球化運(yùn)動(dòng)中,電影藝術(shù)的力量正在于它能夠?yàn)楝F(xiàn)代人的心靈開拓新的自由空間,改編自文學(xué)作品的電影更應(yīng)如此。努力做到文學(xué)作品藝術(shù)靈魂和電影商業(yè)性質(zhì)的有機(jī)統(tǒng)一,是文學(xué)作品影視化改編過程中的一個(gè)關(guān)鍵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