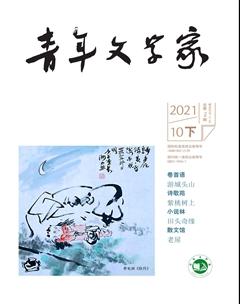生態女性主義視角下的《黑駿馬》
林玲
《黑駿馬》是中國尋根文學的代表作,作家張承志在作品中講述了白音寶力格和索米婭在遼闊壯美的草原上的愛情悲劇。《黑駿馬》中對草原和女性給予了熱切關注和高度贊揚,同時通過白音寶力格最終的精神還鄉傳達了自然和女性的共同魅力對于現代文明“失根”現象的感召力。在這一點上《黑駿馬》的意旨與生態女性主義不謀而合。
生態女性主義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是婦女解放運動與生態主義運動結合的產物。生態女性主義關注自然和女性之間的關系,“由于女性具有創造和養育生命的能力(像大自然那樣),女性歷來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靈更適合于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同時,生態女性主義還注意到女性和自然所遭受的壓迫與統治存在著某種相似性,即同為人類中心主義和父權制中心文化統治下的“他者”。因而,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從女性和生態雙重視角出發,質疑和批判現存的二元思維方式,旨在解放自然和女性,從而改變自然和女性“缺席”“他者”的邊緣地位,建構一個人類與自然、男性與女性的和諧世界。
一、女性與自然的同一性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相較男性,女性與自然有著更大的親近性,自然和女性是相互融合、相互交織的。《黑駿馬》中的草原有著天然的女性氣質,女性可以孕育和撫養生命,草原母親也孕育著無數的生命。生于斯長于斯的奶奶額吉和索米婭早已和草原融為一體,她們逐水草而居,和草原共呼吸、同命運。草原人死后,要把自己還給草原。額吉奶奶天葬在這里,通過這種魂歸自然的方式達到了與自然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草原上的女性有著和草原一樣的氣息:自然質樸、堅忍頑強、博大包容。《黑駿馬》中的伯勒根草原被嚴寒酷暑輪番改造了無數個世紀,有著質樸、粗獷的原生態的美。深受草原母親養育萬物的博大情懷的感染,奶奶和索米婭兩代草原女性心懷對萬物的包容仁慈之心和對諸般生命的呵護敬畏之情。白音寶力格本和奶奶一家沒有血緣關系,但奶奶慷慨仁慈地接納了他并把他撫養成草原上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早產的其其格在別人看來像怪物,有人勸說奶奶扔掉這孩子,可奶奶說:“這是一條命呀!命!我活了七十多歲,從來沒有把一條活著的命扔到野草灘上。”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一匹剛產下不久的小馬駒倒在氈包的外面,奶奶顫巍巍地把小馬駒摟在懷里。奶奶認為,每一個生命都是神靈賜予的,都是大自然的饋贈,都值得人們珍視和尊重。女人孕育生命如同大地孕育萬物一樣,女性天然地對生命有著和男性不一樣的感受,奶奶就像地母一樣,用她的博大胸懷愛護著每一個生命。
索米婭承襲了奶奶的這種品格,在白音寶力格外出學習的大半年中,索米婭被無恥的黃毛希拉玷污并有了身孕。白音寶力格知道后,一時之間不能接受,而此時的索米婭雖然憎恨希拉但卻接受了這個孩子,她和奶奶一起為未出世的小嬰兒準備衣物,索米婭的母愛取代了情愛,她和奶奶一樣認為生命的價值高于一切。當她見到昔日戀人時,她沒有責怪、抱怨他,也沒有流露出對往事的感傷,她默默承受著生活的艱辛。索米婭代表著生活在草原上的所有女性,她經歷了她們都經歷過的快樂、艱難、忍受和侮辱,在她的身上,最令人動容的就是如大地一樣的堅韌、寬容的精神,一如那片被嚴寒酷暑輪番改造了無數個世紀的草原。
二、女性與男性二元對立的緩和
生態女性主義認為,自然和女性往往一道成為人類中心主義和男性中心主義下受壓迫與統治的弱者。在父權制的社會中,“自然與人類,女性與男性,被認為是兩對矛盾,自然低于人類,女性低于男性,因此,人類統治自然,男性壓迫女性就是合理的”。《黑駿馬》中的索米婭被認為是充滿地母能量的女性,但在現實生活中,索米婭卻飽受男權世界的擠壓。她善良美好,卻遭到黃毛希拉的玷污,即便是真心愛著她的白音寶力格也并非真正的理解她。當得知索米婭懷有別人的孩子時,白音寶力格勃然大怒,抓住索米婭要問個明白,索米婭為了保護腹中胎兒咬破了白音寶力格的手,白音寶力格等著索米婭將滿腹的委屈和痛苦向他訴說,然而索米婭始終沒有。在白音寶力格居高臨下的大男子主義的想象里,索米婭是弱者,是被動且需要尋求庇護的。男權文化的貞操觀也給女性帶來了巨大的性別壓迫。被玷污的索米婭是受害者,出于對索米婭的愛,白音寶力格在冷靜之后能接受她,但卻不能接受她腹中的胎兒,在他看來這正是他恥辱的印記,可現實中,索米婭雖然也痛恨希拉,卻對腹中的嬰兒充滿了期待,悄悄地和奶奶一起給孩子準備衣服,這深深刺痛了白音寶力格并導致他拋棄了索米婭。他以為索米婭會撲在他懷里痛哭然后打掉孩子和他在一起繼續兩個人的戀情,可看似柔弱的索米婭無聲地反抗著男權社會強加給她的各種偏見,她不是被動的,不是白音寶力格的附屬品,他們是平等的,她也有鮮明的自我主體意識,她違背白音寶力格的意愿選擇接受腹中的嬰兒,在白音寶力格離開后,她更是獨自撐起了這個家,照顧奶奶和女兒其其格。
索米婭的堅強和堅韌有助于她獨立人格的實現。九年后,當再次見到白音寶力格時,她沒有“哇”地哭出來,更沒有一下子撲進昔日戀人的懷里,她甚至絲毫沒有流露出對往事的傷感和辛苦生活的委屈。索米婭平靜而有分寸,白音寶力格再次低估了索米婭,已經有了好幾個孩子的索米婭沒有被生活沉重的擔子壓垮。生態女性主義所謂的女性,“不僅指女人,而且是一種代表了看護、和解、智慧、行善的文化隱喻,也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男性積極追求的思維方式和思想境界”。索米婭和奶奶就是這樣一種文化隱喻,她們守護著這片草原及草原上的一切生命,魯樞元在《生態文藝學》中提到,“西方現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頗,一切過錯,一切邪惡,都是由于女人天性的嚴重流失、男人意志的惡性膨脹造成的結果”。白音寶力格認為自己要循著一條純潔的理想之路走向未來,在舉手之間便割舍了自己的過去,把故鄉拋在了身后。九年后,心中無法割舍對草原和索米婭及奶奶的眷念,他再次回到草原。草原、索米婭和奶奶,自然和女性給予白音寶力格家園意識,她們喚回了在喧囂生活中迷失的白音寶力格,也讓他重新審視自己的過往,進而在精神得到升華后繼續自己的心靈跋涉。
《黑駿馬》中展現了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圖景,雖然還有男性中心主義思想的體現,但最終我們看到的是白音寶力格在經歷精神無所歸屬和懺悔之后最終理解了索米婭,沖突得到了緩解。這種對于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關系的探究和生態女性主義關于構建和諧理想的人類關系的愿望非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