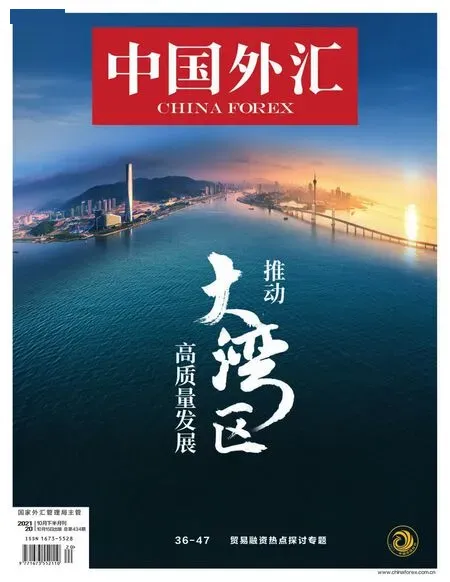國際業務數字化轉型探索
文/汪玨 編輯/韓英彤
隨著數字化轉型日益成為社會的廣泛共識,銀行也在經歷著從數字金融生態的參與者向締造者的角色轉變。國際業務作為銀行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傳統外貿轉向線上化、無紙化,貿易新業態呈現出的碎片化、高頻次,跨境交易出現的反洗錢及合規風險等,都是對銀行國際業務數字化經營能力的考驗。在數字化轉型競爭中,銀行需要借助金融科技,充分調動員工創新力,以更好地發揮拓客引流效應和溢出效應。
拓客引流效應
單據電子化
從2002年eUCP1.0問世至2017年eUCP2.0生效以來,國際貿易結算已呈現出電子化趨勢。傳統貿易企業基于單據安全性、傳遞效率、成本控制、特殊貿易方式(如離岸轉手買賣)等因素考慮,主動選擇了將單據電子化。其中,作為貨權憑證的海運提單的電子化,即電子簽發、線上轉移和回收電子單據已成為重要趨勢。
銀行為企業提供電子單據處理的平臺,是獲取該部分客群的必要基礎。目前,國內銀行開展電子單證業務需要與第三方系統平臺合作,其中采用最多的是BOLERO和CARGODOCS系統。在銀行實踐層面,采用電子單證的企業主要集中在大宗商品貿易領域,如境內的鐵礦石進口企業。在信用證結算方式下,上游礦山若選擇簽發電子單據,境內企業則必須選擇有電子交單渠道的銀行進行單據處理和后續付款操作。通過與第三方平臺合作,銀行不僅提高了對存量電子單證客戶的服務能力,也對潛在客戶起到了拓客引流作用。
渠道線上化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全球企業對線上化服務的需求大幅增長,成為推動銀行加快渠道線上化建設進程的重要因素。
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不僅可節約人力成本和信息溝通成本,還將轉型訴求傳遞至合作銀行,成為銀行渠道線上化建設的外部推動力。目前,企業網上銀行、手機銀行、網點的智能化設備等均在不斷增設功能,以全面滿足企業的日常需求。除自有的渠道入口之外,銀行還與各類平臺合作,為平臺用戶提供支付結算服務。
企業的線上化訴求不僅存在資金端,也發生在貿易端。因疫情影響,企業原來通過線下展會獲客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改變。如今,線上展會、B2B的跨境電商平臺日漸興盛,逐漸成為外貿企業的重要成交方式。隨之而來的,企業電子訂單、線上支付、智能倉儲、數字物流等全流程的線上化,倒逼銀行成為其數字生態圈中的重要一環。
在數字化浪潮中,能夠不斷迭代以適應企業變化,或者主動在變革中引領新型銀企合作關系的銀行,將受到市場更多得的青睞。銀行的渠道線上化,是在為打造數字金融生態圈,從而吸引更多數字化轉型企業夯實基礎。
數字信息化
近年來,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作為新業態貿易類型之一的跨境電商迎來蓬勃發展。根據海關總署的統計,2020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2.16萬億元,同比增長1.9%;跨境電商則逆勢大幅增長,交易規模達1.69萬億元,同比增長了31.1%,其中出口規模為1.12萬億元,占比66.3%。
出口項下,跨境電商的境內賣家以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為主,境外買家為個人或企業。在跨境B2C場景中,境內賣家通常在跨境電商平臺開立店鋪,境外買家在平臺下單并支付,境內賣家進行一系列物流安排。境外買家確認收貨后,境內賣家隨即面臨跨境收匯、結匯的問題。例如,在亞馬遜美國站開店的商戶,其收款賬號通常是在第三方支付機構開立的美元賬號。商戶申請提款時,支付機構會將商戶的美元貨款跨境匯出并結匯至商戶的人民幣賬號。支付機構需要尋找境外合作銀行,實現境外資金的歸集和跨境匯出,同時尋求境內合作銀行,完成跨境收匯、結匯和分發至商戶。
與傳統對外貿易收匯不同,跨境電商的訂單與收/結匯款項不能逐筆對應,收匯主體與出口報關主體通常不一致,境外匯款人也并非最終的買家。銀行若依然沿用傳統的收匯流程,將難以為小微商戶或個體工商戶提供相關服務。銀行通常與支付機構合作,為跨境電商賣家提供高效的收/結匯服務。銀行通過與支付機構進行系統對接,引入“池”的概念,在訂單池與收/結匯指令相匹配時,實現批量收/結匯操作。銀行在此主要充當了支付機構的清算渠道。
目前,跨境電商收款已形成業界通行的操作模式,銀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從支付機構的清算渠道向服務終端商戶延伸。銀行可以通過與境外收單機構合作,利用自身成熟的清結算網絡,搭建完善的賬戶體系,為跨境電商賣家直接提供收款服務。
銀行通過不斷提高對電子訂單、支付單和物流單等形成的結構化數據信息的處理能力,不僅可為支付機構提供代理清算服務,還能直接服務于跨境電商賣家。
溢出效應
銀行在進行某項活動時,不僅會產生預期的效果,而且會達到預期目標之外的正效應。這是指國際業務數字化轉型不僅能實現拓客引流,還會達成該目標之外的積極效果,形成溢出效應。
金融普惠
傳統銀行偏好服務于大中型進出口企業,特別是能夠提供優質抵/質押品的傳統企業。與此相反,小微外貿企業往往是輕資產運營,即使財務報表表現優秀,也難以符合傳統銀行的風險偏好,因而存在融資難的問題。通過大數據技術,銀行可以更好地運用小微企業的報關、退稅、出口信用保險等信息,為小微企業的信用賦能,從而通過線上渠道為小微企業提供普惠融資服務。從銀行成本來看,線上渠道能更好地發揮批量獲客的優勢,且獲取單個客戶的邊際成本非常低。因此,銀行通過薄利多銷的方式,能夠更多地讓利給小微企業,真正實現金融普惠。
流程再造
傳統外貿企業往往有一套成熟的業務流程和管理模式,且不同部門對數字化轉型的接受程度不盡相同。業務部門會為了適應市場變化而采用更靈活的機制,比如上下游企業都開始使用電子單據,企業的業務部門也會接受電子單據的運用,從而對銀行處理電子單據的能力提出要求。財務部門則更多地要求穩健運營,比如企業的出賬通常需經過逐級授權,以確保資金安全。銀行的國際業務數字化產品可以為企業提供定制化服務,根據企業的內部授權機制設置相應的業務流程。由此,內控制度較為完善的企業,通過銀行數字化產品,將線下規章內嵌至線上流程,實現從人為控制到機器控制的轉變。內控制度比較薄弱的企業,也可借助銀行數字化產品,完善自身流程設置。
樹立匯率風險中性理念是每一家外貿企業應該追求的目標。在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背景下,外貿企業可以通過銀行數字化匯率交易產品,在即期交易中更為靈活、便捷地把握稍縱即逝的市場機會;在衍生品市場中也可獲得更大便利,使自身從匯率風險的被動接受方向主動管理者轉變。
數字合規
銀行須遵循展業三原則,充分收集企業資料,對跨境交易背景的真實性、合規性進行審核。借助大數據工具、AI技術,審核人員可以對海量企業交易信息進行建模分析,也可對企業結構化信息進行提取和甄別。數字化合規手段的運用,使審核部門能夠對分析和甄別出的高風險企業及交易采取進一步的風險控制措施,而不是耗費人力搞“一刀切”的形式審查。
銀行自身數據申報的質量也可通過數字化手段得到大幅提高。如果僅通過操作人員手工逐筆完成,國際收支申報和RCPIMIS申報的差錯和遺漏難以避免。若通過系統校驗來提高手工申報質量,或通過系統聯動申報,銀行不僅可以釋放簡單重復勞動,而且能夠保證數據申報的質量。
銀行國際業務數字化轉型的金融普惠、流程再造、數字合規等溢出效應,正在為銀行自身和社會整體的跨境金融生態發展創造價值。
數字化轉型建議
立足當下,著眼未來
大型銀行的國際業務起步早,與很多大型貿易企業建立了比較長久和深厚的銀企關系,各類產品覆蓋廣、服務滲透強。銀行對這類企業的挖潛、深耕自然是無可厚非,在與企業共同面對數字化轉型貿易背景時,應主動為其提供線上化產品,為適應企業不同的內部流程進行充分溝通,并形成定制化服務。銀行數字化轉型,不是要拋棄傳統客戶,而是立足當下,與傳統企業共同成長。
貿易新業態的蓬勃發展是無法回避的大趨勢。新的業態意味著新技術、新模式、新主體等,尤其新技術,使得越來越多的小微主體成為了跨境貿易的主體,并形成了跨境電商等新模式。參與新業態貿易時,銀行在支付機構的“包圍”中曾經或正在經歷著身份焦慮——難以適應龐大的跨境電商主體所進行的高頻小額跨境交易。銀行傳統的業務模式因此面臨挑戰。但趨勢不可逆轉。銀行應在挑戰中捕捉未來機遇,主動接觸新業態客群,了解其需求,解決其痛點,即使暫時沒有營收,也應著眼未來,為長遠發展蓄積能量。
鼓勵創新,開放包容
創新不是空洞的口號。在一個成熟的銀行組織中,從一個個針對特定項目的創新“試驗室”,到每一位員工的自主創新意識,銀行內部應逐漸形成一種人人參與的創新文化。創新來源有社會經濟改革、政策發展導向而帶來的“藍海”項目,也有對銀行傳統業務的優化、整合。鼓勵創新意味著既要在新領域開發新產品,也要用新技術、新模式升級傳統業務,更需要積極引導每位員工認真梳理現有業務流程,在深刻體悟傳統的基礎上主動思考優化、變革之道。銀行借助數字化創新平臺,能夠彌合跨部門、不同等級的鴻溝,使每位員工平等地進行表達和交流,從而真正營造一種“沉浸式”的銀行創新文化。
創新不是閉門造車。銀行與外部組織的交流、碰撞是激發自身變革力的重要環節。銀行在自身平臺搭建中,應該用開放包容的心態,主動連接G(政府)端信息、B(企業)端客群,用新技術深度挖掘大數據價值,利用平臺優勢,服務于更廣泛的社會群體。開放包容不僅意味著與社會各部門建立廣泛的合作共贏關系,也是跳出舒適圈,在新農村建設、大學生創業等領域進行深度參與,重塑銀行的社會價值。
精細管理,智慧合規
精細化管理已經是老生常談,但真正通過精細化管理來提升效益,有賴于新技術的運用。外部機構運用大數據模型進行用戶畫像,深度解讀用戶行為模式,從而進行產品的精準投放,對銀行傳統的營銷方式無疑是一種降維打擊。從大數據運用的角度,銀行的精細化管理要解決數據沉淀和大數據應用兩大問題。銀行作為傳統的金融中介,一直基于對企業各類信息的綜合判斷,對資金進行匹配,即通過整合信息流對資金流進行風險經營。為了消解“資金匹配效率低”或“資金錯配”的弊端,銀行應更好地沉淀信息流,同時開發更多的大數據應用場景,提高資金匹配效率和準確度,惠及更廣泛的社會群體。
不論數字化經營如何發展,合規始終是底線。銀行需要摒棄的跨境合規方式是,對于事前、事中和事后環節搞形式化、一刀切。銀行應通過新技術的應用,在事前環節,發揮數字化優勢,充分獲取客戶信息,完成盡職調查和客戶準入;在事中環節,對客戶資金交易或融資申請信息進行實時的自動化篩查和模型計算,實現即時反饋;在事后環節,通過特定的數字化篩查模型,進行客戶準入重檢和歷史交易回溯,對可疑交易開展進一步的人工審核,真正實現風險為本的實質合規,而非形式合規。
銀行國際業務數字化轉型,應始終立足傳統優勢領域并著眼未來長遠發展,充分調動全員創新力,打造內部平等交流的創新文化,并以開放包容的心態,積極溝通外部組織,主動參與數字化金融新生態的營造;同時,通過大數據等新技術的運用和精細化管理,創造效益,并守住合規底線,實現從形式合規向實質合規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