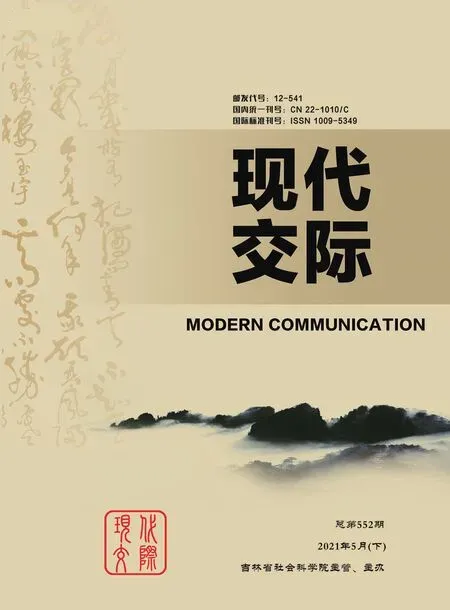羅蘭巴特游戲批評視域中的凱瑞安詩歌解讀
譚羽胭
(湖南科技大學(xué)外國語學(xué)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漢斯 -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認為游戲是人類生活的一種基本職能,沒有游戲因素的人類生活之無法想象的。[1]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是法國著名的批評學(xué)家,他經(jīng)歷了從結(jié)構(gòu)主義到后結(jié)構(gòu)主義的轉(zhuǎn)變,他在《文之悅》(The Pleasure of Text)中認為,游戲文本能給人一種愉悅感和自由感,并開創(chuàng)了“游戲批評”這一嶄新的批評形態(tài)。他認為最好的文學(xué)是“寫作”,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文學(xué)的完整性。它指的是人真正的思想敘述,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地創(chuàng)作,而不是學(xué)究式地“寫字”。在羅蘭?巴特看來,作者的快樂并不等同于讀者的快樂,讀者需要在閱讀中自行去找尋和創(chuàng)造快樂,從中發(fā)現(xiàn)一種“欲望的辯證法”:但愿游戲都沒有進行,然而卻要有一種游戲[2],即文本的意義并不是固定的。羅蘭?巴特認為批評必須建立在閱讀之上,且同一個人在每次閱讀時又會產(chǎn)生不同的體驗,因此批評活動也具有開放性。
凱·瑞安(Kay Ryan,1945—)是美國著名詩人,曾兩度榮獲美國桂冠詩人的稱號(2008—2010),被認為是美國最具有天賦的詩人之一。1983年,凱·瑞安自費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龍的開場的謝幕》(Dragon Acts to Dragon Ends),在這個時期,認識她的人還寥寥無幾。1994年,她又出版了詩集《觀賞火烈鳥》(Flamingo Watching),引起了一部分人的關(guān)注。1998年,評論家達拉·喬納亞(Dana Gioia)發(fā)表了《發(fā)現(xiàn)凱·瑞安》一文,第一次客觀地對凱·瑞安的詩歌進行正面評價,并對凱·瑞安的詩歌抒發(fā)了自己獨特的見解,使得凱?瑞安名聲大噪。達拉·喬納亞在文中提到,瑞安富有豐富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他被瑞安詩歌中非比尋常的緊湊和密度所深深吸引。[3]瑞安也被稱為“當(dāng)代狄金森”,她的詩歌短小精悍,充滿睿智和幽默色彩,她對詩歌韻律有著強烈的偏好,且善于觀察生活中的細節(jié)并不斷反思。在瑞安看來,詩歌是一種游戲,她倡導(dǎo)用一種游戲式的姿態(tài)建構(gòu)詩歌,在游戲的輕松娛樂氛圍中做出思想的審視和批判。[4]借助羅蘭·巴特的游戲批評理論,探析凱·瑞安詩歌中的藝術(shù)手法、詩歌題材,以及讀者指向。
一、詩歌中的藝術(shù)游戲
瑞安曾經(jīng)歷過不被大眾所注意和認可的時期,她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詩歌創(chuàng)作,二十幾年后,她的作品才被大多數(shù)人所認可。正是在這段冷淡期,她的經(jīng)歷使她的個性特征變得抑或是脆弱,抑或是世故。她深刻地明白她需要讀者,又不想被世俗的聲音所影響,在她看來:“藝術(shù)就是它本身和讀者的交流,如果你不發(fā)表,那么交流也就無法進行。”[5]她也想融入一個屬于詩人的大環(huán)境,最終未能成功,于是她便走上了一條屬于她自己的創(chuàng)作之路,雖歷經(jīng)坎坷,所幸也有所獲。瑞安詩歌言語具有極強的沖擊性,既幽默風(fēng)趣,又蘊含深意,給人一種“沉重的輕松”之感,其游戲詩歌的魅力之一在于這種不同傾向的對立統(tǒng)一。在她的詩歌《皇冠》(Crown)中,瑞安寫道:
滂沱大雨/會使樹木根基松動//山上巨大的橡樹/轟然跪地//你可以去觸摸/以前無法觸碰到的部位/那里只有鳥兒才能夠到達[6]187
在自然界中,尊卑貴賤、強大弱小并不都是等級森嚴、一成不變的,根據(jù)環(huán)境的不同,它可以相應(yīng)地轉(zhuǎn)換,就如同瑞安在詩歌中所描述的一樣,人們往往觸碰不到鳥兒所能輕易駐足的地方,這個地方可能暗含著某些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一旦經(jīng)過狂風(fēng)驟雨、閃電雷鳴之后,樹木轟然倒塌,權(quán)力突然瓦解,這種場面便很容易被推翻,這在常人看來這不符合常規(guī)且十分荒謬,顛覆了他們對傳統(tǒng)事物的固有認知,這不僅給讀者帶來一種強烈的驚訝感,還能拓寬他們看待事物的方式,留給讀者更大的想象空間。如詩歌《成雙成對》(Paired Things):
誰/誰能夠只看到翅膀/就推斷出/那瘦骨嶙峋的小棍/是鳥兒用于與大地接觸的工具//他們向后彎曲的態(tài)勢/他們站立時的傻樣子?//又有誰/只是在看過沙灘上小鳥留下的足跡后/便能想象到那些小叉子般的腳/已經(jīng)隨風(fēng)而揚了//這么多成雙成對的東西看似非常怪誕//可誰又曾經(jīng)想過/一只翅膀?qū)挻蟮臑貘f/在離開長空/雙腳立足于地面上時/便成了一只普通的烏鴉呢[6]79
鳥兒在天空中飛翔時,很少有人會去想象它掉落在地上時會是什么狼狽不堪的模樣,人們不會固有地把兩者聯(lián)系起來,實際上,世界上很多事物都是這種看似矛盾,卻是能夠共存的,這也體現(xiàn)了哲學(xué)上的一個思想,即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統(tǒng)一體,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布魯姆認為:“任何要與傳統(tǒng)著作進行競爭的作品必須有其原創(chuàng)魅力。”[7]原創(chuàng)在于新穎,即去熟悉化。在這首詩中,瑞安把翱翔的鳥兒與墜落后步履蹣跚的鳥兒這一對矛盾并置,使讀者產(chǎn)生一種陌生感,又留給了他們發(fā)揮想象的空間,是否世界上還存在著很多這樣或那樣的矛盾,因此,瑞安的詩歌為人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來觀察和思考這個世界。在《捉迷藏》(Hide and Seek)中,瑞安把這種矛盾沖突刻畫得更加形象:
不跳出去/等著被人發(fā)現(xiàn)/是很難的//一個人待了很久/然后聽見有人走近/真是太不容易了//這就像是/某種裸露在空氣中的外皮/還未等他自己脫落/你就等不及把它扯下來[6]250
在這樣一種你藏我找的游戲中,人的心理過程是曲折和糾結(jié)的,一方面不希望自己那么快被找到,這會使得游戲沒有體驗感;但也不想一直不被發(fā)現(xiàn),從游戲開始到結(jié)束都隱藏得極其完美,那這個游戲的過程也會十分枯燥無味。因此,把握好游戲的度是使玩家獲得最佳游戲體驗感的前提條件。游戲是如此,人亦是如此,人們總會刻意地去隱藏自己的某些缺點,而又渴望自己的光芒被發(fā)現(xiàn),想要在其中尋求一個平衡點是困難的,因此人也是矛盾的。詩人認為“一首詩應(yīng)該是一個小丑的箱子,看似空無一物,但當(dāng)小丑把它打開時,里面裝了取之不盡的東西”。好的詩歌也應(yīng)如此,看似只有短短幾行,實則暗含著豐富的蘊意,在《捉迷藏》一詩中,瑞安把“藏”和“找”這一對矛盾體并置,糅合出更加深層次的奧義,是值得令讀者深思的。
二、日常生活中的游戲因素
瑞安對日常生活的觀察細致入微,那些看起來日復(fù)一日不會被人注意的事物在瑞安筆下又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她反觀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現(xiàn)象并進行反思,探尋其獨特性和多樣性,她試圖告訴人們,生活雖然具有其重復(fù)性,但它同時也擁有者無限的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不同于大多數(shù)美國詩人所追求的宏偉敘事,瑞安關(guān)注的是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人和事物,在她看來,詩歌應(yīng)該反映現(xiàn)實生活中的實際狀態(tài)。她堅守自己內(nèi)心的創(chuàng)作原則,追求自己獨特的游戲?qū)懽黠L(fēng)格。她在詩歌中所描繪的大多是我們常見的場景,但她又對其做出新的解讀。如她的詩歌《烏龜》(Turtle):
誰會想要做一只烏龜/誰又能逃避它//一個移動緩慢的球/四片漿的頭盔/慢慢劃向她吃的那片草地/承受她必須承擔(dān)的風(fēng)險//她的行跡十分笨拙/就像是拖拽經(jīng)過一片包裝工地/幾乎任何斜坡都使她渺小的希望破滅/即使她穩(wěn)重謹慎/在尋找食物的路上仍然經(jīng)常碰到車軸/要使一切都變得最好的話/她得繞過那條溝渠/避免讓她得盔甲成為盤中之食//她生活在運氣差的水平線以下/從沒想過會中大獎/能把她的陶土變成翅膀/她唯一值得吹噓的就是耐心/這是歷經(jīng)磨難者的特長[6]81
在瑞安的筆下,這只烏龜是狼狽不堪的,緩慢移動的球、四片漿的頭盔、斜坡、溝渠都會讓她害怕、遲疑、猶豫不決,還要面臨被車軸壓和成為他人盤中餐的風(fēng)險。可見,無論是對動物還是人來說,生活絕非一件輕松愜意的事,通過這一系列的描述,人們不免會對它產(chǎn)生同情,但瑞安并沒有為它的處境感到過分擔(dān)憂和感傷,相反,她看到的是這只烏龜即使經(jīng)歷磨難,但仍堅持不懈的精神,雖心存抱怨但仍努力生存,它對自己所處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有著很清楚的認識,她不會去奢望什么,只是每天一如既往地發(fā)揮著自己的特長:忍耐,這顯然是只有歷經(jīng)磨難的人才能領(lǐng)悟的真諦。這首詩從日常現(xiàn)象中挖掘素材,從細節(jié)出發(fā)來重構(gòu)總體,語言精練樸素,沒有情感詞匯卻把作者的感情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也是瑞安游戲詩歌的魅力之一。在她的另一首詩歌《蛛網(wǎng)》(Spiderweb)中,詩人對蜘蛛的刻畫細致入微:
從另一個角度看/它的纖維/似乎非常脆弱//但是/蜘蛛可不是那樣認為的//經(jīng)常/拖著粗糙的繩索/把它/系在最好的地方//這是/沉重的工作/每時每刻/避免坍塌/不時加固/生存/從來不是/一件輕松的事[6]26
瑞安的詩歌常常有對身邊動植物的描述,生活便是每天重復(fù)地和慣常地接觸到這些日常瑣碎的事物,在《蛛網(wǎng)》中,根據(jù)詩人的描述,每一根蛛絲對于蜘蛛而言都是一個沉重的負擔(dān),像是一根根粗重的繩子,它們必須拼命拖拽,要把它們在一個好的位置編織起來絕非易事,此外,在編織好之后還需時不時地維護和修補,這對于它們來說也絕不是一個輕松的工作,但對于我們而言,它只不過是一根根輕飄飄的、絲毫不起眼的蛛絲,我們甚至可以隨時決定它的去留。讓瑞安所動容的,并不是那一種同情弱者的憐惜感,而是即使是作為弱者,也依然在為生存而努力奮斗的堅強意志。
三、指向理想讀者的游戲?qū)懽?/h2>
在瑞安看來,詩歌應(yīng)當(dāng)是個人情感的表達,是一種自娛自樂的游戲形式,讀者在閱讀詩歌時極有可能會產(chǎn)生與作者不同的理解,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閱讀,讀者腦海中詞匯與認知的不同影響了他們對詩歌深層含義的理解,只有能真正與作者產(chǎn)生心靈交流的讀者才是他們期望擁有的。瑞安認為這種理想的讀者能與詩人有精神上的互動,而詩歌的意義在閱讀的過程中也會被重新建構(gòu)。瑞安的詩歌多用非個人化的寫作手法來吸引讀者注意,即文學(xué)作品要展現(xiàn)的不僅僅是作者本人,而是包括了所有人。因此,瑞安的詩歌中極少使用“I”這樣的第一人稱,而常使用“we”這樣的復(fù)數(shù)第一人稱,即使在少數(shù)情況下使用了“I”,也并不單單代表作者本身,她的詩歌素材并不是只來源于她特有的一些生活經(jīng)歷,而是全人類共有的一種普遍體驗和情感。因此,瑞安的詩歌無關(guān)乎詩人本身也無關(guān)乎作者,關(guān)乎的只是她本身和這個世界。瑞安的文本留給讀者大片的空白去發(fā)揮,無限激發(fā)讀者的想象。如詩歌《誘餌山羊》(Bait Goat):
即使隔著一段距離/磁鐵亦會相吸//我們可以感覺到/如果把它們分開/同樣地/即使隔著一段距離/字詞亦會被吸引/放出一只/像誘餌山羊一樣/等待/然后其他七只就會慢慢湊近//但是要注意/狼群可能會把你的字拉走//你發(fā)現(xiàn)你的木樁不再堅固/還好還有那些粗壯的大木樁[6]5
正如磁鐵隔著一段距離可以相互吸引一樣,字與字之間也存在著這種吸引力,而字就像誘餌山羊一樣,面臨著會被狼群拖走的風(fēng)險,詩人接著并沒有對此做出更多的解釋與描述。但理想的讀者便能從中體會到:人就如同字一樣,要在群體中找尋一種平衡。一個人可能會被群體所壓迫,就像是誘餌山羊可能會被狼群所吞沒一樣,但也有可能會在群體中得到提升,不斷完善自我。
四、結(jié)語
瑞安的游戲詩歌具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性,她憑借天賦與智慧,在簡短的詩篇中把語言運用得十分靈活。瑞安用她獨特的觀察視角和寫作手法為讀者呈現(xiàn)了不同于當(dāng)今美國詩人同質(zhì)化的寫作模式,促進了美國詩歌的轉(zhuǎn)型發(fā)展。一直以來,美國詩人始終在提倡讓詩歌回歸生活,自由創(chuàng)作,杜絕過于學(xué)術(shù)化模式的不良走向,在經(jīng)過時間的沉淀后,她尋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創(chuàng)作之路,始終保持著一顆清醒的頭腦,正如同她詩歌的總體風(fēng)格一樣,冷峻、簡約,但其對平凡生活的刻畫又蘊含著游戲的無限魅力。她的詩歌完美地融合了創(chuàng)新性與可接受性,賦予了詩歌巨大的神秘力量,簡簡單單的詞匯語言背后蘊含著豐富的深層寓意,這也正反映了美國詩歌發(fā)展的新趨勢。瑞安的游戲詩歌是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她明白詩歌的創(chuàng)作重在參與,更需要注重的是閱讀過程所獲取的快樂,因此,瑞安的詩歌值得去細細研讀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