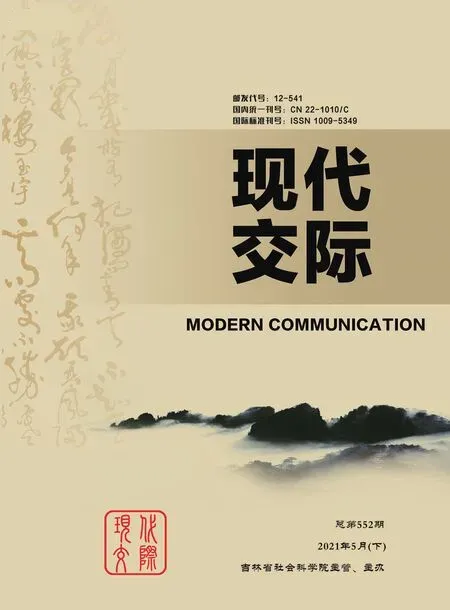休謨、里德自由意志理論之比較
孫圣潔
(湘潭大學(xué)碧泉書院哲學(xué)與歷史文化學(xué)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自由意志問題一直是耗費了偉大的哲學(xué)家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卻始終爭論不休的問題,叔本華認(rèn)為,“近代哲學(xué)的兩個最深刻、最傷腦筋的問題,即意志自由的問題和外部世界的實在性,或觀念對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問題”[1]。以霍布斯與布蘭霍爾主教就自由意志問題展開爭論為幕,掀起了近代對自由意志問題的熱烈討論。尤其是,休謨作為經(jīng)典相容主義的代表,將必然與自由的問題推至另一層面,使整個爭論有了新的視角,他將“必然”與“原因”概念相聯(lián)系,給出了對“必然性”概念的全新定義,將“必然”理解為幾個相似對象的恒常聯(lián)合和結(jié)合,或者是心靈由一個對象至另一個對象的推斷,從而將“必然性”的本質(zhì)解釋為不包含強迫的必然性,以此達(dá)到與自由的相容。
休謨的主張招致很多批評,托馬斯?里德算是第一個從各方面對休謨哲學(xué)提出質(zhì)疑的哲學(xué)家,在自由意志問題上同樣如此。在其著作《論人的行動能力》中,里德站在不相容立場上,對休謨的自由意志觀一一駁斥,主張自由與必然的對立,必然性是“道德自由的缺乏”[2]264。
一、能力概念之比較
從徹底的經(jīng)驗論立場出發(fā),休謨反對我們事實上具有“能力”的觀念。休謨指出,能力既不是能夠單獨存在的存在物,因為我們無法從運動的物體中知覺到任何“能力”,而只能知覺到物體的運動;也不是任何存在物或存在的屬性,因為物質(zhì)在休謨看來是惰性的存在,它“本身不可能傳達(dá)運動,或產(chǎn)生我們所歸之于物質(zhì)的任何一個結(jié)果”[3]。“能力”,在休謨那里,來自恒常會合的類似對象的聯(lián)系,我們從類似對象的恒常聯(lián)系中發(fā)現(xiàn)由此及彼的存在,認(rèn)為在這種聯(lián)系中產(chǎn)生了新的東西,并將這種經(jīng)驗不到的新的東西稱為“能力”。當(dāng)能力的本質(zhì)是類似例子的重復(fù),并由以構(gòu)成該觀念發(fā)生的來源時,我們才能說,能力就是如果一個人明確地這樣欲望(動機),那么意志的行為就將會發(fā)生。“對于經(jīng)典相容論的‘自由行動’概念來說,這四個要素是充分的:假設(shè)一個行動者具有某個欲望,在如何實現(xiàn)那個欲望上具有正確的目的—手段信念,有能力使世界以某種方式發(fā)生變化,以至于確實獲得了與那欲望的對象相對應(yīng)的一個事態(tài),那么他就得到了他想要的東西,于是,在經(jīng)典相容論的意義上,他的行動是自由的。”[4]400
實際上,能力概念在休謨的自由意志理論中并不重要,但在里德這里,能力概念或者說行動能力的概念從根本上構(gòu)成了他的自由意志理論的關(guān)鍵一環(huán),具有行動能力實際上已經(jīng)等同于具有他所主張的自由。里德指出,如果我們沒有對能力的觀念的話,我們就不會談?wù)撍降资鞘裁椿虿皇鞘裁矗驗椤叭藗儗τ谝粋€他們沒有任何觀念的東西,怎么能夠有什么意見?”[2]28,無論我們對能力的談?wù)撌菍Φ倪€是錯的,但僅從我們對能力觀念的討論中就能得出能力觀念確實存在的結(jié)論。
此外,能力在休謨那里被指代為能力的發(fā)揮,只有能力被發(fā)揮出來,人才能稱得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說,在休謨這里,自由意味著一個人只能做他實際上所做的事,也就是說,在任何一個時刻,行動者只能依照意志決定行動或不行動。它的含義是,行動者的行動與否實質(zhì)上是被決定了的,只要影響意志的動機條件得到滿足,意志決定就必然發(fā)生,在意志決定發(fā)生的那一時刻,行動者只能造成一種結(jié)果而沒有其他結(jié)果,造成這一種結(jié)果的過程就是行動者“能力的發(fā)揮”過程。這種能力對自由而言在里德看來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對他來說,“行動能力”的概念不僅僅意味著“能夠”,更重要的是蘊含著“能夠不”,即“造成一個結(jié)果的能力也蘊含著不造成這個結(jié)果的能力”[2]33,例如,當(dāng)一個人有能力舉起手臂時,不舉起手臂也一定在他的能力范圍內(nèi)。由此可見,這一能力概念與休謨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并不必然導(dǎo)致了意志決定,相反,它是指在我們做出一個意志決定的地方,我們原本亦能夠不做出這個意志決定,反之亦然。因此,在這種語境下,“自由行動不僅意味著行動者有能力采取其他行動(不同于實際上所履行的那個行動),而且也有能力不履行他實際上履行的行動”[4]18。
二、意志概念之比較
在休謨看來,當(dāng)把自由概念應(yīng)用于有意的動作上時,我們考慮的是人們的行為與他們的動機、傾向之間的必然聯(lián)系,他認(rèn)為,當(dāng)我們說意志是自由的時候,實質(zhì)指的就是人內(nèi)在具有的一種動機,根據(jù)這種動機,只要沒有外來強迫,人完全可以按照意志的決定從事或拒絕某種行動。也就是說,當(dāng)我們主張一個人的行動是自由的時,我們必須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內(nèi)在動機的決定;第二,外在強迫的不存在。可見,意志活動的原因在于人們不同的內(nèi)在動機或性情,而動機、性情與行為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聯(lián)系,自由是以承認(rèn)人的內(nèi)在動機與外在行為之間的恒常會合為理論前提的,簡單地說,動機與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guān)系,一旦動機出現(xiàn),行為就必然出現(xiàn),動機對行為具有因果能力。但在里德看來,“行為的動機與行動還是不行動的決定,這兩者的性質(zhì)是不一樣的”[2]57。意志作為人自身的某種類型的心理活動,首先使我們意識到的就是其做決定的能力,這種意識在我們面臨選擇時就清晰地出現(xiàn)。因此,在里德這里,意志就是做出決定的能力,并且當(dāng)他“在這部作品中說到意志的時候,并不把任何刺激或動機(它們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決定)歸屬于這個語詞之下,我所指的僅僅是決定本身及做決定的能力”[2]57。
此外,與休謨不同,里德否認(rèn)動機對人的行動的決定作用,雖然動機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會影響我們的意志,從而激發(fā)我們的行動,但它僅僅是一種建議或勸告。動機與行動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聯(lián)系,它是激發(fā)人類行為的因素,而不是導(dǎo)致行為發(fā)生的原因,我們既不能說任何一個深思熟慮的行為必然有一個動機,也不能說出現(xiàn)在人的行為前的某一個動機一定會決定能動者的行為。在這個基礎(chǔ)上,里德就將行為的動機與動因區(qū)分開來,將動機表述為哲學(xué)家們所說的“理性設(shè)想之物”,而將行為的動因概念最終放至行動者本人身上,最終形成與休謨截然不同的意志自由觀。
三、自由本質(zhì)之比較
哲學(xué)家之所以對自由意志問題感興趣,主要是因為自由意志最開始被認(rèn)為是承擔(dān)道德責(zé)任的一個必要條件,所謂道德責(zé)任問題是指,在什么情況下我們能夠?qū)ψ约旱男袨槌袚?dān)道德責(zé)任,同時能夠評價自己或他人的行為,能夠?qū)B(tài)度適當(dāng)?shù)刭x予自己或?qū)Ψ剑纱私①p罰制度,贊美好的行為,懲罰惡的行為。為了使上述這些活動能夠進行,一個普遍的觀點是,行為必須是由行為人發(fā)出的,我們才能把行為的責(zé)任歸于他,而行為必須由行為人發(fā)出就意味著行為必須是一個自由的行為,也就是說“道德責(zé)任的充分賦予是以一個人的行動是否自由為條件的”[5]。
必然論的立場難以解決道德責(zé)任的問題,在必然論的觀點下,行為必然會發(fā)生,也就是說,行為的發(fā)生與否,實際上并不取決于行動者,行動者只是承擔(dān)一個工具的功能,我們?nèi)绾文軌蜃l責(zé)一個工具呢?正如我們?nèi)绾文軌驅(qū)⑷说淖镞^歸于一把手槍?因此,為了將必然論立場與道德責(zé)任相容,休謨從自由的定義出發(fā)提出他的“調(diào)和計劃”。他指出,“所謂自由只是指可以照意志的決定來行為或不來行為的一種能力,那就是說,我們?nèi)绻敢忪o待著也可以,愿意有所動作也可以”[6]。這一定義滿足了自由的行為的基本條件,它強調(diào)了“行動者”的重要性,指出自由的行動一定是指由行動者的意志和欲望所引起的行動;并且肯定了行動的自愿性,從而將自由與強制或暴力相對,而不是與必然相對。由此,自由的、負(fù)責(zé)任的行動在休謨看來必須具備以上兩種條件,即行動必須既是由行動者的意志造成的,同時還是非強迫的。
這種自由意志觀在里德看來是難以接受的,它使行動者受制于動機和欲望的決定,與傳統(tǒng)的宿命論并沒有顯著的區(qū)別,休謨只是在決定條件上進行了改變,其基本路線沒能遠(yuǎn)離這一觀點,即“如果有一些條件的共同出現(xiàn)在邏輯上對一個事件的出現(xiàn)是充分的,那么那個事件就是被決定了的。換句話說,如果那些決定條件共同出現(xiàn),那么那個被決定的事件就會必然發(fā)生”[4]50。
重點是,如何解決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問題,即如何解釋在每一個時刻都不只有一個物理上可能的未來。里德認(rèn)為,問題就在于對自由的定義上。休謨所主張的自由并不延伸到意志的決定,而只是延伸至意志所決定的行為,并依賴于意志;而真正的自由不僅意味著他可以支配其行動,而且意味著他能支配自己的意志,如果自由僅僅意味著一個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事,那么,就這樣一種只涉及身體的實際運動與否的自由而言,任何動物和人,只要它們的運動是遵循意志,并且其運動不受自然、物質(zhì)的障礙、妨礙,我們都能說它們是自由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對自由意志的研究就沒有了意義,如果我們的行為與動物并無二致,人類社會的合理性將遭到質(zhì)疑,人類依其特殊性而制定的法律和約定俗成的道德準(zhǔn)則也將失效,最重要的是,人的尊嚴(yán)和對自我的反思都將變得虛無縹緲。因此,里德指出:“我把道德能動者的自由理解為他超越自己意志決定的一種能力。”[2]262所謂有意的、自由的行動是指,在意志的決定這一活動中既不能受外在于能動者的東西的因果決定,也不能由內(nèi)在于能動者的非理性的內(nèi)心狀態(tài)決定,一個自由的行為必須是“由我決定的”,甚至不能說是由“我”的信念和欲望決定的,也就是說,只有“我”才可以選擇是否要去做這件事,在這樣一種選擇或決定去做某事的意志活動中,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決定這類活動,除了“我”自己。
可見,“行動者”的概念在二者的自由意志理論中也有顯著區(qū)別,在里德這里,有理性的人類以區(qū)別于其他自然的機械運動得以發(fā)生的原因而對自己的行為擁有一種因果力,這使“行動者在行動的產(chǎn)生中具有一種‘不可排除’的作用……每當(dāng)我履行一個行動時,正是我,而不是我的身體的某個部分,甚至也不是我的心靈或大腦,履行了那個行動”[4]568。而在休謨那里,或者說在必然論者那里,我們的動機、欲望或性格等都被看作一個先前事件,這一先前事件對行為的因果影響是被必然化的,實際上,人還是充當(dāng)著工具的身份,本身受制于不可抑制的動機或欲望。但在里德這里,行動者能夠獨立于任何這些事件對他的因果影響而自由地選擇一個行為,即使在很多的情況下,動機、欲望和性格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行動者的意志決定。但重要的是,一個有理性的行動者能夠通過判斷和慎思來考慮這些動機狀態(tài)的影響,正是在對任何可能行動的考慮中,我們成為我們行動的有效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說,“這樣一個行動者具有一種自由的因果性,那種不受任何東西所決定、僅僅是由自己來完全決定的因果性”[4]569。
四、結(jié)語
休謨與里德的交鋒體現(xiàn)在自由意志問題的方方面面,更重要的是,二者對同一概念的不同看法一直影響著自由意志理論的進程。例如,20世紀(jì)彼特·英瓦根的后果論證直指以休謨?yōu)榇淼慕?jīng)典相容主義的不足之處,使相容主義者不得不重新正視決定論與道德責(zé)任的相容問題,并試圖給出新的回答。由里德所發(fā)展起來的行動者因果關(guān)系理論蓬勃發(fā)展,從根本上影響了羅德里克·齊碩姆、蒂莫西·奧康納的自由意志理論,并在繼承中回答了里德沒有回答的“可理解性問題”,即當(dāng)我們?yōu)榱苏f明一個具有獨立的、自發(fā)的因果能力的行動者時,必須注意一切動機和傾向與“自我”的分離,“自我”必須不被任何外在的事件所決定;然而,如果一個行動者獨立于一切信念、欲望和動機,那么該行動者做出的行為就是不可理解的,因為一個沒有任何性格特征的自我是完全不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