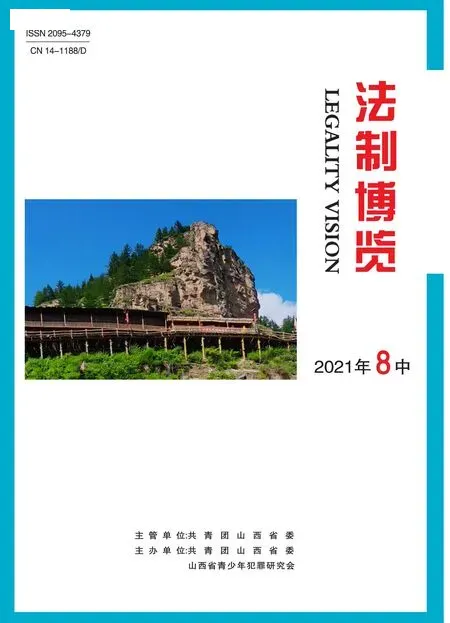高空拋物罪立法評析
杜雨晴
(北京建筑大學,北京 102600)
高空拋物行為在規制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呼喚刑法的介入,繼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依法妥善審理高空拋物、墜物案件的意見》(下文簡稱《意見》)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下文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專門設立高空拋物罪。《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公布后就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高空拋物行為如何定性,構成要件如何界定,是否應單獨成罪,法定刑是否合理等問題成為學界爭議的焦點。本文首先回顧了規制高空拋物行為的立法沿革,之后對高空拋物行為與相關概念進行了辨析,并對高空拋物行為的入罪進行了評析,最后提出了立法完善路徑。
一、規制高空拋物行為的立法沿革
(一)《侵權責任法》施行前后
我國對高空拋物行為的規制,最早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該規定只針對高空作業人員這一特殊主體提出了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歸責原則采用無過錯責任。2003年1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首次對不能確定高空拋物具體行為人的情形作出規定,統一了不明來源拋擲物案件的處理方式,回應了社會的法律需求。
《侵權責任法》施行后,將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應承擔的責任確定為補償責任,將立法重點放在對受害人的救濟上,相對平衡了對可能加害人過錯的追究。
(二)《民法典》施行前后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前述《意見》之前,我國對高空拋物行為的規制一直停留在民事法律層面。《意見》對高空拋物行為的定性集中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等罪名上。但事實上,法院在裁判時適用罪名單一,不能妥善把握不同罪名的定罪尺度。《意見》對于“多次”“重大損失”等界定不明的詞匯,造成司法實踐中適用標準混亂。
2021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下文簡稱《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條對高空拋物行為進行明確規定,新增了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追償權,明確了物業服務企業的安全保障義務及違反義務所要承擔的過錯責任,并對公安機關在高空拋物案件中的調查取證責任進行了規定。其標志著我國民事法律對高空拋物行為的規制形成了事前預防與事后調查相結合的相對完整的體系。為了全力配合民法典的貫徹,刑法也有義務提高高空拋物犯罪在刑法中的地位,而獨立入罪即是刑法溫情的回應。[1]
(三)《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后
高空拋物案件通常事發突然,沒有任何征兆,出乎人們的意料。且致害人與受害人在整個過程中不會有任何接觸,因此受害人往往不會注意到致害之物的來源,隱蔽性較強。從高空所拋擲的物品,兼具了運動過程中的動能和空間上的勢能,具有極大的破壞力。高空的不安全引起了社會公眾的極度恐慌,社會呼喚法律以其強制性來解決這一問題。
《刑法修正案(十一)》將高空拋物罪單獨入刑,列入《刑法》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一節“擾亂公共秩序罪”中,總結了司法實踐經驗,完善了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的刑事責任。2020年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的首日,江蘇常州溧陽市人民法院審理了徐某某高空拋物一案,被告人以高空拋物罪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并處罰金2000元。[2]高空拋物行為犯罪化彰顯了國家對此嚴厲打擊的明確態度。不僅讓違法者付出了應有的代價,而且讓意圖高空拋物者明白高空拋物行為不能為也使其不敢為,從而有利于構建健康、文明、有序的社會環境,涵養社會風尚。
二、高空拋物行為與相關概念的辨析
高空拋物行為,是指行為人從高空人為地對物品施加一定的力,使其由高到低發生位移,進而造成損害的行為。實務中經常將高空拋物行為與一些相似行為混同,因此有必要進行辨別。
對于高空墜物行為,行為人可能已經盡到了注意義務,也可能是因為過失而沒有預料到損害結果的發生,其主觀過錯比高空拋物行為弱。
以高空拋物方式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的行為,高空拋物只是其手段行為,其目的行為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二者是手段與目的的牽連關系。兩行為在主觀方面雖都為故意,但故意的具體內容不同。以高空拋物方式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的行為意在剝奪他人生命、造成他人損傷,行為人在實施高空拋物行為之前就已經有了犯罪預謀,已經做過前期調查、實驗,其犯罪對象也是特定的,因此人身危險性更強,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更大。
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其侵害的客體是公共安全,高空拋物只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否危害公共安全,主要取決于拋擲物。例如,從高空擲下一個啤酒瓶是否會傷人受環境和時間因素的影響,即使造成損害也只會對特定的一人造成傷害,而不會危及公共安全。高空拋物行為的行為人只具有拋擲物品的一般故意,危害到公共安全只是偶然。并不是所有高空拋物行為都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二者最明顯的區別在于是否危及公共安全。
三、高空拋物行為入罪評析
高空拋物行為與高空墜物行為,以高空拋物方式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的行為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存在差異性。《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缺乏專門懲罰高空拋物行為的罪名,實務中出入罪標準不一,存在輕罪重判或重罪輕判的現象,高空拋物罪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
首先,針對高空拋物行為是否應獨立成罪,引起了學界廣泛的討論。有學者認為高空拋物犯罪的依附式立法不能實現其規范目的,應單獨立法。也有學者認為高空拋物不宜獨立成罪,高空拋物問題可以通過民事責任解決的,刑法就不應當介入;即使刑法介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其他罪名就能夠給予罪刑相當的懲處。[3]筆者認為,對高空拋物行為獨自設立高空拋物罪的做法,給出了對不嚴重的一般性危害人身財產安全的高空拋物行為的調整方案。高空拋物罪是一種低位階的刑事犯罪,只有造成了重大損害才能根據其具體情節適用諸如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過失致人死亡罪、過失致人重傷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高位階的刑事犯罪。前述罪名的客體各異,行為后果危害性不同,既遂形態不一,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國高空拋物行為的刑法規制體系,但在罪名相互間的銜接上存在問題。
其次,《意見》和《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一審稿》都將高空拋物罪置于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當中,而《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審稿》則將其歸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如此改變使高空拋物罪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主要是因為高空拋物行為雖然可能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財產安全,具有一定程度的危害公共安全性質。但不可否認同時存在著對公共安全并沒有危害的高空拋物行為,這些高空拋物行為卻可能對公共秩序具有一定的破壞性。[4]若將其置于前罪中,易在入罪時加重對行為人的行為判斷,仍不會改變高空拋物犯罪同案不同判、出入罪任意的局面。而將其置于后罪中,并不排斥對前罪的適用,只是對輕罪行為進行了與其罪行相適應的規定。這一立法規定一改《意見》在適用過程中的僵化處理,準確、科學、合理地對這一行為進行了定位。
最后,縱觀我國對高空拋物行為的法律規制,至今沒有對“高空”“所拋擲的物品”進行準確界定。刑法作為一種行為規范指引和裁判規范依據的法律,刑法學作為一門規范法學的理論體系,都不能簡單地停留于“各種行為事實”和“表面的共同特點”來作出判斷,而必須進行所謂的規范判斷。[5]是參照《高處作業分級》對高處的規定,還是采用相對高度標準;是通過經驗法則判斷,還是包括任意物品,都需要官方解釋來對司法進行統一的、準確的指導。
四、高空拋物罪的立法完善
不可否認的是,高空拋物罪對于打擊高空拋物行為,從而構建健康、文明、有序的社會環境,涵養社會風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仍然存在個別亟需完善的問題,需要我們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明確問題的癥結,探析完善路徑。
(一)加強高空拋物相關罪名的銜接
國家應出臺相關司法解釋,對高空拋物行為進行明確分類,筆者認為可以劃分為不構罪的高空拋物行為,一般性的危害人身財產安全的高空拋物行為和嚴重危害人身財產安全的高空拋物行為,對每一類高空拋物行為的特點進行明確,使司法機關準確進行法益、行為性質定位,在實踐中不人為地拔高適用重罪。并以其行為后果作為界定依據,高空拋物沒有造成人身財產安全損害的為不構罪的高空拋物行為,要運用社會道德規范、《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調整;造成人身財產安全損害但后果并不嚴重的為一般性的危害人身財產安全的高空拋物行為,根據《刑法》高空拋物罪的規定處理;造成嚴重損害的為嚴重危害人身財產安全的高空拋物行為,根據具體情節適用《刑法》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過失致人死亡罪、過失致人重傷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的規定。總之,要加強高空拋物相關罪名的銜接,構建高空拋物行為刑法規制體系。司法工作人員在實務中要加強基本理論知識的學習,諳熟高空拋物相關法律規定,注重高空拋物相關罪名的一體化考慮。
(二)明確相關概念內涵
如今,《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經正式施行,相關部門應盡快出臺司法解釋,對“高空”“所拋擲的物品”進行統一界定,具體明確“高空”的衡量標準和高空所拋之“物”的范圍。此兩項內容事關高空拋物罪的犯罪地點和作案工具,對罪名認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置于不同的高度、拋擲不同的物品反映出行為人不同的心理態度,對量刑也有重要影響。筆者認為,高空的高度、拋擲物落下的能量與高空拋物行為的危險性成正比,“高空”的判斷和高空所拋擲“物”的確定相互不可分割。在司法實踐中,應根據物理測算和經驗法則綜合考慮。只有將相關概念進行具體明釋,在司法實務中才能更好地適用以準確地定罪量刑。
(三)明確對情節嚴重的認定
認定某罪是否情節嚴重,主要有參考該罪已公布的司法解釋和參考近似罪名的司法解釋兩種方式。高空拋物罪為新設罪名且尚無司法解釋,故只能參照其他罪名的司法解釋來認定其情節嚴重。一般對情節嚴重的認定,主要根據該行為的結果、社會影響程度、行為次數等確定。筆者認為,高空拋物罪因其案發地點、作案手段具有特殊性而不同于其他情節犯,因此在對情節的認定上應有自己的認定標準。相關部門應盡快出臺司法解釋明確如何判斷本罪的“情節嚴重”。對于本罪情節的認定,應當充分考慮犯罪手段和方法、犯罪對象、犯罪的后果、行為人的一貫表現、犯罪的時間和地點等情況進行判斷。筆者認為,借用外力高空拋擲物品的;在人流量高的時段和地點高空拋擲物品的;造成公私財產損失5000元以上或者造成他人輕傷以上后果的;多次高空拋物尚未造成嚴重后果,但屢教不改的;造成本區域內正常生活秩序混亂,影響惡劣的,都應認定為高空拋物罪的情節嚴重。
五、結論
《刑法修正案(十一)》雖將高空拋物行為單獨入罪,但高空拋物罪仍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應加強高空拋物相關罪名的銜接,對高空拋物行為進行明確分類,使之能夠與相關罪名共同構成我國高空拋物行為完整且完善的刑法規制體系。在罪名的具體認定方面,我國《刑法》在之后的修改完善中和相關司法解釋中應當充分考慮犯罪手段和方法、犯罪對象、犯罪后果、行為人的一貫表現、犯罪的時間和地點等情況來界定情節嚴重與否,應根據物理測算和經驗法則綜合起來考慮涉案的“高空”“所拋擲的物品”能否對人身和財產造成損害。《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不久,高空拋物罪的不足之處有待實踐的檢驗,也需要隨著司法審判經驗的積累進而不斷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