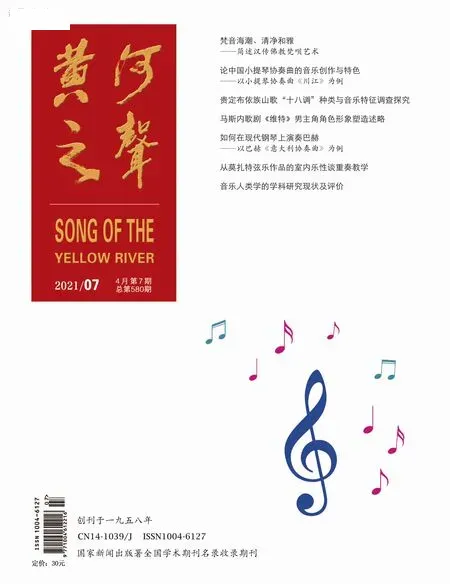音樂人類學的學科研究現狀及評價
鄒宗容
一、研究現狀
(一)國內研究現狀
音樂人類學在中國的研究起源于21世紀初。2000年后,大量西方音樂人類學理論與方法傳入我國。使中國傳統音樂的研究工作發生了轉變,為傳統音樂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主要代表人物有洛秦、管建華、蕭梅等人,他們的成果對中國音樂人類學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截至2020年7月,在中國知網以“音樂人類學”為篇名,不設時間閾限,檢索期刊類文章,共檢索到952條記錄。在碩博士論文庫中,以“音樂人類學”為篇名的,可以檢索到117篇。其中,博士論文18篇,碩士論文99篇。以“民族音樂”為名實則研究“音樂人類學”的,可以檢索到51篇。在超新數字圖書館上以“音樂人類學”為篇名,不設時間閾限,檢索著作類書籍,共檢索到124部。
目前音樂人類學研究的主要專著有:洛秦的《音樂中的文化與文化中的音樂》(2010)和《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時間文庫》(2011)、蕭梅的《田野的回聲—音樂人類學筆記》(2010)及其與韓鍾恩合作的《音樂文化人類學》(1993)、熊曉輝的《音樂人類學論綱》(2008)、薛藝兵的《神圣的娛樂—中國民間祭祀儀式及其音樂的人類學研究》(2003)和《在音樂表象的背后》(2004)、管建華的《音樂人類學的視界—全球文化視野的音樂研究》(2010)及《音樂人類學導引》(2006)、湯亞汀的《音樂人類學:歷史思潮與方法論》(2008)、曹本志與洛秦合作編撰的《ETHNOMUSICOLOGY理論與方法英文文獻導讀》(2019)、楊民康的《音樂民族志方法導論》(2008)等,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待,他們從整體與局部探索了音樂人類學的具體事像,不僅僅以音樂的角度去研究一種音樂行為,還運用了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某一族群的音樂活動以及音樂文化現象,這種具有開闊的全球文化視野和人類學視野的方法,對音樂人類學科建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目前音樂人類學研究的主要論文有:曹本冶的《一統音樂學:中國視野中的“民族音樂學”》(1996)、熊曉輝的《音樂人類學柏林學派研究》(2012)和《人類音樂視角中的民族音樂》(2009)以及《對當代音樂中國音樂人類學發展的思考》(2009)、陳銘道的《田野工作散記》(1990)、《民族音樂學地解讀〈圣經〉(上、下)》(1997)、《音樂民族志寫作—以〈蘇雅人為什么歌唱〉為例》(2009)、杜亞雄的、《“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2009)、范可的《“音”與“人”與“人”與“音”—關于音樂之人類學探索之探索》(2020)、川田順造的(羅傳開譯)《文化人類學與音樂》(1990)、熊友軍的《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看音樂的民族性和地域性》(2015)、楊曦帆的《建構與認同理論的音樂人類學反思—以嘉絨藏族為例的少數民族節日儀式與傳統文化發展研究》(2020)、洛秦的《音樂人類學的中國實踐與經驗的反思和發展構想》(發表于2019)、于亮的《音樂人類學力作—〈街頭音樂:美國社會和一個文化的縮影〉書評論述》(2005)等。從上述論文中,可看到研究者們以人類學的眼光討論民族音樂的文化研究,以及在人類學的情境中看待中國傳統音樂,透過音樂活動探索音樂的文化特征、音樂在人類社會中的形成原因,分析音樂在不同時期、不同族群中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和意義。
(二)國外研究現狀
音樂人類學在歐洲經歷了幾個重要時期。其中,在1885年,阿德勒(Guido Adler)提出的“比較音樂學”概念,開始從人類學的角度對民族音樂進行比較研究。同年,英國語言學家埃利斯(J.A.Ellis)提出音分制的概念,對多個國家的音階進行測定,認為世界上的音階不止只有一種。此外,梅里亞姆、孔斯特、胡德等人對音樂人類學也進行了不同的定義。以下按時間順序對部分著作與論文進行歸納。
目前音樂人類學研究的主要著作有:胡德《音樂民族學家》(1971)中主要包含音樂民族學領域和方法。R.萊頓《藝術人類學》(1981)、J.詹姆斯《人類與音樂》(1983)、邁耶爾斯《音樂人類學導論》(1992)、庫里《田野中的影子》(1997)、(美)布魯姆;(美)伯爾曼;(美)紐曼聯合編著的《民族音樂與現代音樂史》(2009)、(美)布魯諾的《八城市音樂文化:傳統與變遷》(2011)和《民族音樂學31個論題和概念》(2011)、威廉·A.哈維蘭《當代人類學》(1987)等,通過上述對國外主要的專著整理中發現,國外對音樂人類學的研究較早,主要是利用人類學的方法理論研究一切音樂現象,填補民族音樂學研究的不足,總結了西方音樂人類學的學科發展歷史,為我們學習音樂人類學提供了許多可參考的資料。
目前音樂人類學研究的論文主要有:2010年J.Lawrence Witzleben發 表 于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的Performing in the shadows:Learning and making music as ethnomusicological practice and theory.2010年Everett Taylor發表于The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的Intimate Distance:Andean Music in Japan by Michelle Bigenho(review).2011年Richard Widdess發表于Institute(Music & performance)的An Introduction等。
二、音樂人類學學科身份
音樂人類學是研究人的一切音樂,它既研究音樂的“聲音、概念、行為”,也研究與此相關的各種文化現象[1]10。在這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音樂人類學在不同的時期存在不同的定義。梅里亞姆認為,音樂人類學是“文化中的音樂”研究或“作為文化的音樂研究”[2]8。荷蘭學家孔斯特把它比作“比較音樂學”,認為是研究人類原始人群到文明國家的所有文化階層的傳統音樂和樂器。
音樂人類學的萌芽源于十九世紀前,受殖民主義的影響,研究學者們將目光不再投于歐洲音樂文化,而是開始向非歐洲音樂文化進行探索。例如,查爾丁(Chardin)對波斯音樂的考察以及沃爾尼(Volney)在埃及對當地民族音樂的研究,為后期音樂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提供了寶貴的民族志資料。1615年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Mattheo Ricci)對中國傳統民間音樂進行研究,并出版了《利馬竇中國札記》,向西方國家介紹了中國傳統民間音樂,也讓中國接觸了西方音樂,是將中國音樂介紹到西方的第一人,為后來音樂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做了鋪墊。但音樂研究在西方人類學的史料中,一般都認為法國耶穌會員、地理學家杜·阿爾德(J.B.Du Halde),是最早接觸到中國的西方人[3]。這些早期的音樂人類學研究主要都是靠有限的民族志材料進行研究,認為非歐洲音樂歸結于歐洲音樂史的發展模式。到了文藝復興時期,著名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認為人類的差異是由于文化而不是由于音樂,1780年出版的《音樂的辭典》中強調了音樂是文化的而不是自然的[4]7,不同民族根據自身不同的音樂來傳承不同的音樂文化,書中對中國、歐洲、伊朗等音樂進行了描述,這也是力圖證明了非歐洲音樂文化并非屬于歐洲音樂發展史的一部分。同時,反對“歐洲中心主義”,肯定非歐洲音樂價值。
到了十九世紀,在保護土著文化思潮的影響下,西方學術界產生了一種文化進化論的民族學理論,主張用比較探究的方法去探索人類社會起源和發展歷程[5]58,以研究音樂文化的交叉性來說明人類的差異性。1885年,奧地利音樂學家阿德勒(G.Adler)在《音樂學季刊》雜志創刊號上發表了《音樂學的范圍、方法和目的》的文章,提出“比較音樂學概念”,并將其界定為“從人種學的角度對民族音樂學進行比較研究”[5]11,從而確立了比較音樂學在音樂研究中的地位。同年,英國的語言學家埃利斯(J.A.Ellis)發表的《論各民族的音階》,提出音分制的概念,即八度為1200音分,每半音為100音分,并在書中分別對希臘、緬甸、印度、阿拉伯、中國等國家進行音階測定,得出不同的民族由不同的音樂體系構成。誒利斯的這一觀點與當時的“歐洲文化中心論”產生了極大的沖突,但對跨文化的音樂人類學研究邁出了重要一步,被譽為“現代音樂學之父”。前期的“比較音樂學”確實對非歐洲音樂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幫助,但由于當時人們對民族音樂學的研究不夠完善,“比較音樂學”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表現出研究者的獵奇心理和索取音樂文化資料的目的[5]58,因此到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漸漸被興起的柏林學派而取代。
柏林學派出現于十九世紀的后半葉,對于音樂人類學的開始,柏林學派做了巨大貢獻,主要代表人物是以德國音樂人類學家施圖姆夫(K.Stumpf)為代表,以柏林大學心理研究所為中心而形成的一個具有學術特色的音樂研究群體,主要的成員有阿伯拉罕(O.Abraham)、霍恩波特思(E.M.V.Hornbostel)以及赫拉曼(R.Lachmann)、薩克斯(Cart Sachs)、赫爾索格(G.Herzog)等人[5]58。其主要從事的是音樂史、音樂形態以及樂器學的研究,并運用田野工作和案頭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研究音樂,為人類音樂學創立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十世紀,音樂人類學主要是以博厄斯學派和美國學派為代表,他們反對種族、反對進化思想的觀念,認為文化是多元化的,強調“田野工作”實踐的重要性,以細致和謹慎的比較方式采集資料,注重從自身環境中來審視文化的價值與特征[2]15。該學派的學生繼承這一傳統,注重文化形態的分類和比較,尤其是赫爾佐格(Herskovits)和羅伯茨(Roberts)在“音樂文化區域研究”和“音樂文化理論研究”中起到了率先作用,成為了美國音樂人類學派的主要力量。雖然音樂人類學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已經開始,但當時還沒有音樂人類學這一概念,音樂人類學真正的提出是梅里亞姆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音樂人類學》中提出來的。音樂人類學的誕生填補了民族音樂學的不足并提供研究作為人類學行為的音樂的理論框架。
三、音樂人類學的學科評價
筆者對音樂人類學的學科評價,主要從特征評價、學科研究內容評價、學科與相關學科的關系評價、學科個案研究評價四個方面來分析。
(一)學科特征評價
音樂人類學借鑒了人類學的研究手段來研究音樂,所以它既有音樂的屬性,同時還具備了人類學的特征。因此,在音樂人類學的研究過程中,有些學者會更偏向于音樂學,有些則更靠近人類學,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的兩大音樂人類學派對此還有過爭議。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胡德(Hood)和梅里亞姆(Merriam)。胡德認為民族音樂學家應具有雙重音樂能力,只有了解這個音樂能演奏、演唱這個音樂,才能夠做好這個音樂的學問,而梅里亞姆卻認為是從人類學的觀點對音樂進行科學的研究[7]19。音樂人類學發展到至今,仍然存在爭論。目前,于音樂人類學特征相關的著作與論文有:孟凡玉的《音樂人類學的范疇、理論和方法》、熊曉輝的《對當代中國人類音樂學發展的思考》(2009)、楊民康的《音樂民族志方法導論》、管建華《音樂人類學的視界—全球文化視野的音樂研究》和《音樂人類學導引》、湯亞汀《音樂人類學》(2005)和《文化研究下的音樂人類學:兼音樂人類學與音樂學的范式差異》、洛秦的《音樂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導論》(2011)等。這些著作論文中都對音樂人類學的學科特征做了闡述,認為音樂人類學在學術思想與方法在許多方面與跨學科的“文化研究”不謀而合,為音樂學方面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視角,是未來值得研究發展的學科之一。
(二)學科研究內容評價
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內容相比民族音樂學而言更為廣泛,不僅是某一族群方面的研究更是涉及到了整個人類音樂的研究,如聲音、概念、行為等各種所能產生的音樂現象,早期的音樂人類學研究主要是對殖民地區音樂的研究,如器樂與音樂舞蹈方面,到了后來受啟蒙運動的影響,開始對非歐洲音樂的民族音樂是否存在自身是音樂體系展開研究,如1768年盧梭出版的《音樂詞典》,書中記錄了不同國家的音樂風格特征。而在比較音樂時期,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內容側重點在與音樂的本體研究和樂器分類研究。這是由于受文化人類學的啟發,以及當時社會流行實證主義哲學、古典進化論等影響,與“進化論”一樣,采用比較的方法對考察對象進行民族志性質的描述,音樂上對音高、音程、音階的關系比較注重,但在音樂的其他方面卻有所欠缺。在比較音樂學時期,最大貢獻的人物胡德,創造了“雙重音樂能力”,并在出版的《音樂人類學家》中專門論述了“雙重音樂能力”的練習方法,為音樂人類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性框架。此外還有,斯圖普夫(Carl Stumpf)的《暹羅的音體系及音樂》、薩克斯(Curt Sachs)的《樂器史》以及霍恩博斯特爾(Erich Moritz)的《樂器分類法》,這些研究的學術思想和方法影響深遠,為音樂人類學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比較音樂學”受到質疑,柏林樂派為音樂人類學做出了巨大貢獻,以音樂人類學柏林樂派的音樂家施圖姆夫(K.Stumpf)為代表,主要是對音樂資料的收集以及音體系測定研究,他的著作有《音樂的起源》、《暹羅的音體及音樂》等,并與1900年創立了柏林音響檔案館、利用留聲機記錄研究音樂,同時也使柏林音響檔案館匯集了采集于世界各地的民族音響資料,為后期音樂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音響資料。二十世紀的博厄斯學派,在音樂人類學上的研究主要強調“田野工作”的實踐,以細致謹慎的方法采集資料,偏理論性,注重文化變遷的重要性和歷史研究的必然性,主要代表人物有克魯伯(Kroeber)本尼迪(Bennedict)、赫爾佐格等,他們的著作《文化模式》、《宣言十八列》等,書中都體現了博厄斯學派對于音樂的觀點。在博厄斯學派強調田野實踐的重要性中,美國學派代表人物孔斯特對于音樂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長期涉足于對印尼佳美蘭音樂的研究。由此可見,音樂人類學研究內容豐富,不同時期不同學派,研究的側重中點也各有不同,音樂的研究方向受當時文化的影響比較大。
(三)學科與相關學科關系評價
音樂人類學是一門跨專業的學科,在音樂學的基礎上融入了人類學理論,受到民族音樂學、音樂學、音樂民俗學影響同時,吸收了各學科的知識,在學習過程中容易與其他學科混淆。因此,以下對音樂人類學與音樂學、人類學、民族音樂學、音樂民俗學的關系做出梳理,以便區分。
西方音樂學最早出現于,德國音樂學家阿德勒在他的《音樂學的范圍、方法和目的》一書中,強調西方音樂學的研究主要是歷史和體系兩個部分,歷史主要包括音樂歷史時期的國家、個人、團體、領域、藝術、流派、城市的分類[1]10-11,還有音樂的形式以及記譜法。而體系主要包括和聲、節奏、旋律等,這些原理曾被用于音樂人類學的研究中,但在長期研究的過程發現不同的民族有自身的音樂體系,并不適用于西方音樂學的理論,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就可發現音樂人類學并不等同于西方音樂學。
音樂民俗學源于東歐的匈牙利等國,主要代表人物是巴托克(Bela Bartork)和布勒伊洛尤(Constantin Brailoiu),結合“比較音樂學”和“柏林和派”的方法對傳統音樂進行研究,不僅大量收集民間音樂還注重田野工作理論和方法論問題以及文獻資料的概括,為民族音樂學的誕生做出了貢獻。鄭蘇曾對民俗音樂學這樣描述:“對搞民族音樂學的人來講搞的就是音樂民俗學、音樂民俗志,民俗學是民族音樂的‘脊梁骨’,沒有民俗學就沒有民族音樂學”[7]13。與音樂人類學相比較民俗學是民族音樂學的前身,音樂人類學借鑒了民族音樂學了理論方法,由此可以說民俗音樂學是音樂人類學發展上的一部分,它的誕生為音樂人類學學科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音樂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相比較,民族音樂學的研究相對比較狹窄,主要是根據音樂學的理論特點,運用歷史學和民族學的理論去解決問題[7]44,并把側重點主要放在音樂上。如在,胡德的觀點里,強調音樂研究的重要性,對研究者的音樂能力要求比較高。而對于音樂人類學完全是填補民族音樂的不足,吸收并結合了很多學科的理論知識,把目光不僅放在研究音樂上還對音樂的行為進行研究,在梅里亞姆的《音樂人類學》中提出音樂具有審美、娛樂、傳播、象征。總的來說音樂人類學與音樂學和民族音樂學相比較研究范圍更廣但又同時也借鑒了人類學和民族音樂學的相關理論與研究成果,音樂學人類學的發展離不開民族音樂學,民族音樂學為音樂人類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人類學(Anthropology)是研究人的一門學科,依據人類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綜合的研究人,特別是強調人類差異性以及種族文化的概念[1]3。著名人類學家L.D.霍爾姆斯與W.帕里斯在合著的《人類學導論》中,認為人類學是研究從史前時代到當代人類的體質和文化發展的一門學科。人類學的發展與其他學科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諸如語言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人類學等。其中文化人類學是人類學主要的構成部分,主要體現在人的思維、情感、交流等行為和特征上,而音樂人類學主要是研究人的一切音樂行為,因此文化人類學與音樂人類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它采用了文化人類學的基本方法對音樂進行研究,如比較分析、實地研究、整體性觀點等。目前很多民族音樂的研究都是以人類學的角度來進行分析,人類學的發展為音樂人類學的研究提供了理論性的框架,擴大了音樂的研究范圍,豐富了音樂種類,為音樂人類學學科的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四)音樂人類學的學科個案研究評價
當今對音樂人類學的研究,所采用的學術材料,都是來自人們的田野作業,這些研究材料經過研究者運動多學科的研究方法[8]44,根據民族學、心理學等相關知識將音樂與人類學相結合,對音樂進行探索。例如,在楊民康的《少數民族當代節慶儀式音樂與民族文化身份建構—以西南少數民族音樂的實踐為例》中提出少數民族當代節日與儀式音樂活動涉及文化身份與構建過程[9]7,認為應該在展開非遺音樂的傳承與保護的同時,還應重視少數民族儀式音樂活動。文中使用結合了田野的調查方法,來闡釋了西南少數民族的音樂文化的認同以及信仰體系。除此之外,還有楊曦帆的《建構與認同理論的音樂人類學反思—以嘉絨藏族為例的少數民族節慶儀式與傳統音樂發展研究》通過少數民族族群節慶儀式音樂的典型案例,討論了節慶儀式在少數民族地區具有的社會功能。此外,在音樂人類學的研究史上,美國音樂人類學家弗萊徹(Alice Cunningham Fletcher)在1893年出版的《奧馬哈音樂研究》對印第安部落音樂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對推動印第安的音樂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上案例都使用了音樂人類學的調查方法對少數民族音樂進行研究,由問題闡述到個案分析的具體研究過程,對音樂人類學科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結 語
音樂人類學在二十世紀后越來越受到重視,在吸收了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多學科的知識上,增強了音樂的歷史意識與人類學思維,開啟了音樂人類學在人類音樂生活中的整體性認識,運用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人的一切音樂活動及現象,對音樂學科的發展與擴展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但通過資料分析發現音樂人類學目前尚未建立完整的學科體系特征,由于音樂人類學目前的研究對象范圍較廣,故而失去了獨特性,以及在學科理論上利用人類學的理論框架而沒有自身的理論特點,希望通過以上整理與分析能夠使更多人了解音樂人類學學科以及對音樂人類學方向的學生提供參考資料和借鑒價值。以上論文感謝我的導師熊曉輝教授細心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