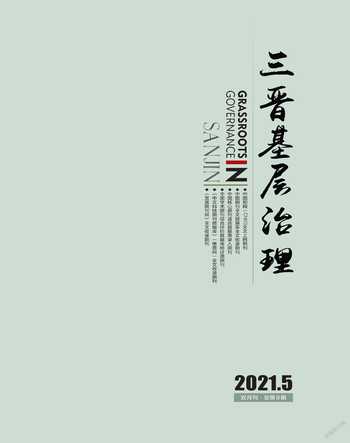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質量發展路徑選擇
苗迎春 李瑞 常婧
〔摘要〕進入新時代,中心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成為承載區域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載體,并成為吸納流動人口和集聚新增人口的主要陣地,深刻地影響著區域經濟發展。從“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視角出發,分析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在推進高質量發展過程,發現其中存在綜合經濟水平低、科技創新能力弱、被輻射帶動能力弱、可持續發展能力弱等問題。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應在因地制宜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培育汾河創新走廊、強化輻射帶動作用、促進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全面協調可持續等方面持續發力,進而推動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在新時代“黃河大合唱”中譜寫獨具特色的山西篇章。
〔關鍵詞〕沿黃中心城市;城市群;高質量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8442(2021)05-0095-05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政府信息公開執行的自由裁量差異研究”(18YCJ630252),主持人張瑜。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保護黃河是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千秋大計。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質量發展,不僅關乎民生福祉,關系城市營商環境和對外發展的形象樹立,而且維系著城市產業集聚功能、人文集聚功能、綜合服務功能、交通樞紐功能、創新高地功能〔1〕的有效發揮,對山西全方位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一、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性
(一)加強政府部門對城市智能管理的要求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是基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建設的,隨著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不斷深入,經濟社會呈現出新的增長極,城市形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信息技術為城市居民提供智能化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戰,這就倒逼政府部門改革社會治理模式,運用現代化技術和手段提高城市治理和公共服務的效率。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有助于推動政府部門對城市的智能管理,而政府部門對城市的智能管理對城市群高質量發展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能夠推動城市群達到更高質量的發展。
(二)城市經濟結構持續優化的要求
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發展差距過大,僅僅依靠資源優勢和國家戰略支持的理念,實現經濟的轉型發展,遠遠達不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要求。推動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高質量發展,有利于城市經濟結構的轉型,由粗放型發展方式轉向集聚集約式發展,一方面持續轉換發展動能,提高城市經濟發展質量,另一方面擴大城市發展規模,提升人口和產業承載力〔2〕。城市群高質量發展有助于推動城市經濟結構的持續優化,持續優化的城市經濟也刺激著城市群更高質量的發展,二者相輔相成。
(三)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
黃河流域多樣的地形、脆弱的生態和不合理的開發利用,導致嚴重的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生態問題。沿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質量發展對生態保護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要求全流域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引下,進一步提高能源開發利用效率和資源調配能力,降低能源資源消耗,減少環境污染排放,并加強生態環境的治理與修復,提高生態文明水平,從而構建資源節約型的綠色經濟增長模式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文明形態〔3〕。總而言之,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高質量發展要兼顧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二、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質量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綜合經濟水平低
2020年全國GDP為1 015 986億元,2019年全國GDP為990 865億元,全年增加25 121億元,GDP增長率為2.53%。山西省2020年GDP為17 650億元,2019年GDP為17 026.68億元,全年增加623.32億元,GDP增長率為3.66%。2020年,山西省GDP在全國排名第21位。與全國GDP增速相比,山西省GDP以微弱優勢跑贏全國平均水平,但相比于沿黃九省區中較發達區域,如四川省、山東省、陜西省、河南省,山西省經濟呈現出綜合水平不高且增長緩慢的態勢。2020年山西省GDP總量僅為四川省的36.3%,為山東省的24.1%,為陜西省的67.4%,為河南省的32.1%。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經濟的總體水平不高。
(二)科技創新能力弱
R&D經費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是R&D投入強度。R&D投入強度可以折射出地區經濟增長方式和創新水平,也可以反映出區域科技實力和核心競爭力。山西省全社會R&D經費內部支出在2015年到2019年間總體呈現上升的趨勢,2015—2019年,山西省R&D投入強度總體圍繞1%呈現輕微上下波動形態。2019年,全國R&D經費占GDP的比例高達2.23%,山西省在全國排名第22位。山西省R&D投入強度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巨大,這說明山西省R&D活動基礎薄弱,R&D投入強度小,也可表明全省鼓勵科技創新的力度小。
2019年,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中,忻州市R&D經費投入2.1億元,占全省R&D經費投入的1.10%;呂梁市R&D經費投入10.2億元,占全省R&D經費投入的5.33%;臨汾市R&D經費投入13.4億元,占全省R&D經費投入的7.01%;運城市R&D經費投入21.2億元,占全省R&D經費投入的11.09%;省會太原R&D經費投入84.2億元,占全省R&D經費投入的44.04%。在四個沿黃中心城市中,運城市R&D經費投入最多,強度最大,忻州市R&D經費投入最少,強度最低。沿黃中心城市R&D經費投入和投入強度遠遠落后于太原市,且在全省R&D經費投入中所占比重小。R&D經費投入對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R&D經費投入強度越大,越能帶動企業、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的R&D活動,越能提升整個區域的創新能力,也越能帶動區域經濟增長。
2020年,太原市發明專利授權量2258件,占全省發明專利授權量的75.59%。2020年,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中,運城市全市授予專利權3 676件,占全省專利授權量的13.47%,其中授予發明專利權121件,占全省發明專利授權量的4.05%;忻州市全市專利授權量753件,占全省專利授權量的2.76%,其中發明專利授權量43件,占全省發明專利授權量的1.44%。2019年,臨汾市發明專利申請量276件,占全省專利申請量的3.7%;呂梁市全市專利授權量422件,占全省專利授權量的2.8%,其中發明專利授權量179件,占全省發明專利授權量的7.8%。總體來說,山西省R&D產出地區之間差異較大,太原市R&D產出基本占山西省R&D總產出的一半,而沿黃中心城市R&D產出較少,且占全省的比重低。
2020年,全國科技創新發展平均水平指數為0.332,太原市科技創新發展指數為0.465,運城市科技創新發展指數為0.258,臨汾市科技創新發展指數為0.257,呂梁市科技創新發展指數為0.227,忻州市科技創新發展指數為0.222。從R&D投入產出結果來看,山西省科技創新投入和產出兩極分化嚴重,發展極不平衡,且總體水平層次不高。從科技創新發展指數來看,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R&D經費投入和產出相對均衡,都處于低水平投入和產出階段,與全國平均水平以及省會城市都有很大差距,充分顯示其科技創新能力的不足。
(三)被輻射帶動能力弱
城市的首位度是一個有效衡量城市輻射力、帶動力、集聚力、影響力的指標,其計算方法是“省會GDP排名第一區縣”/“省會GDP排名第二區縣”。城市首位度可以反映出城市的經濟勢能,并與經濟效能呈正比關系,城市經濟首位度越高,城市的經濟效能越大,吸引力和輻射力也越強;城市經濟首位度越低,城市的經濟效能越小,凝聚力和輻射力也越小。
太原市2015年首位度為21.4%,2016年首位度為22.9%,2017年首位度為22.6%,2018年首位度為23.09%,2019年首位度為23.6%,2020年首位度23.5%。按照標準,省會城市的首位度達到25%-30%,才算是一種理想比例。按照這個標準,盡管太原市的首位度整體上呈現出遞增的趨勢,但首位度不足的問題也亟待解決。首位度不足,則意味著太原市經濟勢能不足,凝聚力和認同感較差,省域協調能力弱,帶動周邊城市經濟發展的后勁不足,對區域經濟的輻射力和影響力就難以達到較高水平,沿黃中心城市被輻射和帶動的能力也就處于低水平狀態。
(四)可持續發展能力弱
把“經濟指標”“能源指標”“環境指標”三個方面作為對象來研究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經濟指標”反映了呂梁市第二產業在經濟發展中所占比重最大,忻州市、運城市和臨汾市第三產業在經濟發展中所占比重最大;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均與山西省平均水平有較大差距。
“能源指標”反映了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第二產業用電量所占比重最大,第一產業用電量所占比重最小;忻州市、呂梁市、臨汾市、運城市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所占比重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運城市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所占比重最大;忻州市、呂梁市、臨汾市、運城市一次能源生產折標準煤總量均大于二次能源生產折標準煤總量,呂梁市一次能源生產折標準煤總重最多,臨汾市二次能源生產折標準煤總重最多(見表6)。此外,2018年,全省消耗21 183萬噸標準煤,能源消費總量增速5.3%;忻州市消耗967萬噸標準煤,能源消費總量增速1.5%;呂梁市消耗1 917萬噸標準煤,能源消費總量增速12.4%;臨汾市消耗3 045萬噸標準煤,能源消費總量增速9.4%;運城市消耗2 392萬噸標準煤,能源消費總量增速9.7%。整體來看,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能源消耗較大,占全省能源消耗總量的比重大,且能源消費總量增速快,遠遠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環境指標”反映了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中,忻州市和呂梁市的綜合環境空氣質量指數較高,臨汾市和運城市的綜合環境空氣質量指數相對較低;忻州市、呂梁市、臨汾市水污染比較嚴重,運城市水資源質量較好;呂梁市、臨汾市、運城市森林覆蓋率高,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而忻州市森林覆蓋率較低,與全省平均水平有較大差距;臨汾市和運城市城市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較高,基本接近或超過全省平均水平,忻州市和呂梁市城市建成區綠化覆蓋率較低,與全省平均水平相差較大。
總之,在肯定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可持續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成果時,也應該關注其“產業結構不合理、資源能耗過大、生態環境效益低”等問題,這些潛在問題一方面不利于區域經濟的科學發展,另一方面也阻礙著區域綠色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進程。
三、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一)因地制宜構建現代產業體系
作為晉中城市群的經濟中心和龍頭帶動區域,太原市區位優越資源豐富,能源產業在經濟中占比較高,人口相對密集,產業和城市基礎較好。晉中城市群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群交通、經貿與技術交流日趨緊密,但也存在產業結構單一,旅游資源、礦產資源開發利用不合理、不充分的現象。晉中城市群要實施“三大改造”,即傳統產業的綠色改造、智能改造和技術改造。通過對傳統行業的改造,積極化解過剩產能,尤其化解鋼鐵、煤炭、有色金屬、建材等行業的產能過剩,并將“智能+”與“生態+”理念與化工、煤炭、鋼鐵、食品、服裝等傳統產業有機結合,打造“智能產業”和“生態產業”〔4〕。
運城市位于山西西南部,地處黃河金三角地區,是黃河流域中重要的支點城市,也是山西省的農業生產基地。晉西南城市群利用山西西部和南部出口的地理優勢,近年來,在調整產業結構、招商引資、培育民營企業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晉西南城市群要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就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加快劃定糧食生產功能區、基本農田保護區和重要農產品生產區,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和糧食生產,推動農業綠色發展、優質發展、特色發展,打造“晉西南金岸”,著力提高糧食產量,保障糧食安全。
(二)培育汾河創新走廊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群要以太原市為龍頭,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圍繞智能終端、軟件及系統、智慧城市設備、云計算及大數據等,發展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培育新興產業,打造汾河創新走廊。
人才是支撐城市發展的首要資源,培養人才是第一創新生產力。首先,依托山西大學、太原理工大學、山西財經大學、中北大學、太原科技大學等高等院校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其次,創新人才機制,制定高效的人才政策,營造一流創新生態和有吸引力的人才環境,集聚各地高層次創新人才;最后,建立汾河創新走廊研究院,加大對戰略型專家、學術帶頭人和科學團隊的扶持力度,構建多層次創新平臺體系,鼓勵研發平臺、科研團隊和科研成果共享,為推動汾河創新走廊高質量發展提供科技支撐。
營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汾河創新走廊,要求發展理念創新、經濟形態創新、文化創新齊頭并進,共同發展。首先,要創新發展理念,以著力提升“沿汾經濟帶”的實力為核心,以互惠共榮、互利共生為原則,科學規劃產業體系,構建利益共同體,大力推動沿汾中心城市之間的合作與交流;其次,要創新經濟形態,強化企業在經濟形態創新中的主體地位,鼓勵企業進行關鍵技術、前沿技術、現代工程技術的創新,鼓勵企業與5G、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數字經濟、基因檢測、電子商務、在線醫療、遠程教育等相結合,釋放汾河創新走廊的發展潛力〔5〕;最后,實施“文化戰略”,大力發展現代文化產業。汾河流域與其蘊含的“黃土文化”和“農耕文化”交相輝映,形成了生生不息的汾河文化,要將汾河文化資源轉化為特色文化產業,利用新媒體平臺,講好黃河流域的“山西故事”。
(三)強化輻射帶動作用
太原市以其經濟發展條件良好、人口承載能力大、集約式發展等優勢,在推進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質量發展中發揮著巨大的帶動作用。太原市是山西省中部城市群的中心。太原市要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深入推進“123”戰略的實施,即一核兩帶三軸〔6〕。構建以太原及其周圍相鄰城市為主體的核心區(太原—晉中—忻州—呂梁);打造汾河文化生態帶、農區田園風情生態帶;形成以太原為中心的輻射狀發展軸線,分別為“沿京昆線發展軸”“沿呼南線發展軸”“沿青銀線發展軸”,使中部城市發揮更大輻射帶動作用,形成“沿黃經濟帶”和“沿汾經濟帶”協同發展、優勢互補的局面。侯馬市位于山西省南部臨汾盆地與運城盆地之間、汾河與澮河交匯處,地處山西、陜西、河南三省的三角中心,區位優勢突出。地處交通要道,集晉西南人力、資本、物流、信息等資源于一身,不僅是山西省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也是新亞歐大陸橋上的重要交通樞紐,對晉西南一體化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晉西南城市群要以侯馬為中心,深入推進“2+1+1”的四維發展戰略,即打造晉西南重要的經濟中心、對外交往中心、山西開放高地、山西綜合交通樞紐,強化城市輻射功能,帶動周邊城市協同發展,提高城市群綜合競爭力,推動晉西南城市群實現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
(四)促進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全面協調可持續
全面協調可持續是山西省沿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構建生產、生活和生態協調發展格局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必然選擇。全面協調可持續要求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社會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7〕。
首先,晉南城鎮圈要與山西中部及關中平原城市群內外聯動,深化晉陜豫黃河金三角區域合作,從而不斷優化工業結構,改變生產方式,以市場為導向,強化自主創新能力,用高新技術和先進技術推動傳統產業轉型發展,優先發展信息產業,鼓勵發展對經濟增長有帶動作用的高科技產業,培育和扶持新的經濟增長點;其次,統籌城鄉發展,一方面,處理好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關系,促進城鄉共同富裕,讓廣大農民平等地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另一方面,全面改善居民生活條件,倡導形成綠色消費、低碳的生活方式;最后,要圍繞水土流失治理、荒漠化治理及鹽堿地治理等工程,加快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工程、重點生態修復治理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污水治理工程等生態保護措施。同時,完善生態環境管控體系,加強沿黃城市生態環境保護和監督執法,嚴厲打擊各類生態環境的違法行為〔8〕。
總之,推進山西沿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高質量發展,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引,堅持新舊動能轉換,建設好黃河流域山西段生態經濟帶;要堅定文化自信,挖掘文化潛力,講好黃河流域的“山西故事”。當前,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對一些行業和企業的沖擊,以及對人民生產和生活造成的不利影響,山西省要加大力度做好“六穩”工作,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穩定發展,努力建設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先行區,奮力譜寫新時代“黃河大合唱”。
〔參考文獻〕
〔1〕劉戰國.構建鄭州國家級中心城市問題探討〔J〕.河南科學,2014(06):975-979.
〔2〕何青芳.沿黃城市帶建設與同城化戰略〔J〕.東方企業文化,2015(15):341+344.
〔3〕蘇慧,張仲伍,張興毅,王娟.基于能值分析山西省生態經濟系統可持續研究〔J〕.西南農業學報,2019(05):1187-1193.
〔4〕寇有觀.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建設“智慧生態城市群”〔J〕.辦公自動化,2020(02):8-9+32.
〔5〕邸衛娜,吳園園.京津冀智慧城市群建設路徑研究〔J〕.合作經濟與科技,2020(01):16-17.
〔6〕岳宏志,鄭小寅,譚策吾,等.盡快啟動秦晉寧蒙沿黃國家級城市群建設〔J〕.西部大開發,2017(09):114-115.
〔7〕宋琳琳.改革開放40年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探索與實踐〔J〕.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18(05):14-17.
〔8〕張雪珍.西北地區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協同治理路徑研究〔D〕.蘭州:甘肅農業大學,2018.
責任編輯郭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