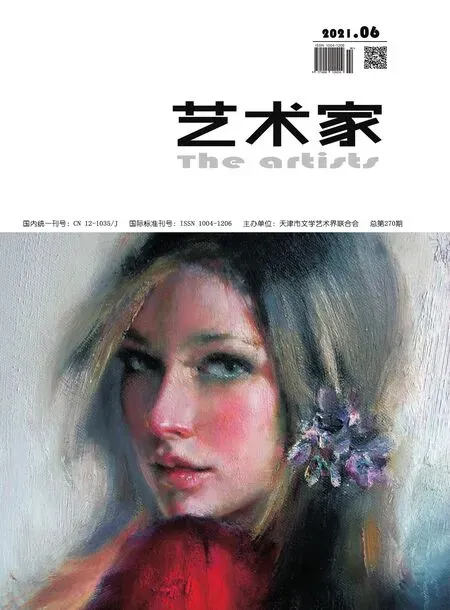河東道情音樂文化探究
□閆姝寧 運城學院
一、河東道情的發展史
道教創立于東漢,盛行于隋唐。據《永濟縣志》記載,唐時,呂洞賓(永濟永樂人,現屬芮城)曾修道于中條山,常奏漁鼓、彈簡板游唱各地。早在1987年,蒲州便發現了道教始祖李耳的一尊石像,這也為蒲州蒙上了一層神秘的宗教色彩。在芮城縣永樂觀壁畫中所刻畫的道教樂班圖及八仙圖中,便有手持漁鼓的人物形象,這與現代道情藝人所持的樂器也有著極大的相似之處。道情最為特殊的當數樂器,除了三弦、笛子等常見樂器外,道情還有分分(碰鈴的一種)、漁鼓簡板等“獨門樂器”,據傳這些均源于道教八仙的法器[1]。
目前,為保護道情的傳承,有關文化部門采取了兩種措施:靜態保護和動態保護。靜態保護是為了了解道情的發展和歷史演變,主要措施有了解民間俱樂部、民間藝術家、曲目等形成的基本條件,存儲和整理收集到的數據,以及整理現有曲目、樂譜、道具和樂器,民俗對進行保護和傳承。動態保護是以長江布口、南家村、解放路杜古和西江村為中心,創建河東實驗室,打造道情文化生態保護村和特色文化村;支持藝術家,組織課程,組織歌舞團,培養新的說唱藝術家和表演團隊,恢復傳統的曲目和表演技術,擴大外部宣傳,建立河東說唱文化品牌,同時加速文化產業化進程。
二、河東道情的文化價值探究
(一)道德教化
宗教色彩是河東道情最深層次的底蘊,盡管在今天看來,河東道情已經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宗教的色彩,已經成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一種民間藝術形式,但是實際上,河東道情不論在唱詞、音樂、劇目還是在表演形式上,都帶有濃郁的道教文化色彩,可以說“宗教”已經成為這一藝術形式的一種內在表達[2]。
河東道情與道教文化之間的關聯還體現在道德教化上,對于該表演藝術而言,其之所以能夠吸引這么多群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表演的內容貼合生活實際,也能夠反映和表達出“教人學好”及“與人為善”的樸素道教情懷。從表演題材來說,河東道情主要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是以神仙道華為主的體裁;第二種是以孝順父母為主的題材;第三種是家庭瑣事為核心的題材;第四種是以民間傳說、歷史故事為主的題材。
(二)河東道情的實用價值
河東道情作為當地人們喜聞樂見的一種文藝表演形式,不僅具有優美婉轉的唱腔,同時所應用的伴奏樂器也十分豐富[3]。在劇本內容的選擇上,其也可以延伸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隨著我國當前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深入,加強對河東道情的宣傳與弘揚,成為豐富人民群眾文化生活,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
河東道情歷史悠久,在人民群眾的心中也有著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在實際的演出過程中,因班組人員結構的優勢,其具有較強的傳播性。這種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演出本身不受場地因素的限制,表演者既可以登臺演出,又可以坐攤演唱;第二是演出所需要的樂器投資較小,演出也不需要過多奢侈的服裝與道具;第三是演出的方式便捷,表演內容具有較強的可傳播性;第四是表演形式較為靈活,可以現編現唱。這一方面能夠反映出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可以成為建設新農村、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的有效保障。總體而言,河東道情是老一輩藝人辛勤勞動的智慧結晶,挖掘、保護這一民間藝術形式,對我國民間曲藝的發展,對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都有著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4]。
三、唱腔板式
(一)板式類別及應用
根據感情的需要,河東道清的曲牌卡可以用多種風格表達,印版樣式通常具有慢對偶、對偶、硬對偶、滾動白、流動水等。而流動水有大有小,應用銅管樂器(大聲,伴奏)演唱大的流水。因此,一首特定的曲牌實際上包含三個要素:一種是旋律的形式;二板子的風格;三是曲牌的名稱,如宮調二性耍孩兒、徵調緊二性皂羅袍等。
以“運城道情”為例,在特殊情況下可以直接將曲牌名省略,而在演唱的過程中,可以選擇固定的叫法,也可以轉變旋律。一如前文所示,河東道情分為東、西兩路,西路唱腔的曲調按照“正”“宮”兩調進行分類,主要的代表曲牌有《皂羅袍》《耍孩兒》等。而東路的曲牌中雖然也有《皂羅袍》《耍孩兒》等較為完整的曲牌,但是在實際的應用中所運用的是板式亂句。板式亂句因為不是十分完整的曲調,所以也被稱為花、苦二音,其主要的板式有“撩板”“慢板”“二性”等。
(二)梆子腔劇種的借鑒
梆子腔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梆子腔以硬木梆子擊節為主要特色,也是戲曲中最早采用板式變化結構的一種聲腔。其中,陜西和陜西的蒲州梆子當屬梆子腔系統中分布最為廣泛的一種。板胡作為梆子腔的主要樂器,在句子類型上主要分為上下門結構,歌詞通常是設置為七個字母的句子或者填字游戲,旋律則主要使用七個音階,其在不同的演奏形式下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因其使用了閃光板,所以在旋轉的過程中音樂的整體表現力更強,能給欣賞者以更大膽和更刺激的感受[5]。
實際上,道情歌曲在發展過程中,也與地方戲曲音樂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交融。地方戲曲極度歡樂與極度痛苦的表現形式,也十分靈活地應用在了道情歌曲中。以《不由叫人惡氣多》為例,其整體的表現形式十分歡快,僅從譜例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其主要使用的是七聲音階旋律,唱詞也以七字句和十字句居多。這就與梆子腔的基本特征相吻合。而在《五谷豐登民安樂》中,歌曲的整體風格更偏向于苦音調式,所以從譜例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旋律本身仍舊是應用七聲音節,唱詞的設計上也更傾向于七字句,在結尾處使用一個“哎”字,完成了整個樂句的流暢演奏。
河東道情的主要板式有撩板、慢板、流水等,這些板式也與蒲劇唱腔的主要板式有著高度的相似性。所以,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河東道情充分汲取了蒲劇的養分。而相關資料顯示,河東道情在清末民初時,便與這些板式的藝術形式進行了融合,流水作為蒲劇唱腔中的主要板式,其節奏形式的特點便是有伴無言。該板式在表達靈活、自由的特性的同時也有著天然的優勢。同樣,緊流水在表現激昂豪放方面尤為突出,慢流水則更擅長表現悲壯的氛圍。除此之外,二性也是蒲劇唱腔中十分常見的板式,其節奏主要為一板一眼。在蒲劇中,二性主要用于敘事、抒情的演奏。慢二性作為在二性基礎上演化出的一種獨立板式,本身也屬于有板無眼類的節奏形式。作為二性派生出的板式,撩板的藝術形式具有較強的“無視僵化”的特性,其在融合了相關曲牌之后,也形成了一個具有明顯特點的板式唱腔。
最后,為了進一步豐富河東道情的演奏形式,道情藝人還將木魚、碰鈴、梆子等打擊樂器融入河東道情的演奏中,這在極大地豐富了打擊樂器的同時,也為豐富欣賞者的觀感體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唱腔曲牌
河東道情的唱腔曲牌是一個帶有正面語調和正式語調的曲牌名稱的統稱。正音是由sol、si、dol、re、fa和sol組成的基本音調序列。在曲牌中,downsi音是具有較低音調的si,而正式音是sol、la、dol。
對于正式音和普通音來說,其主要的區別在于普通音的主音是si、fa、sol,而官方的主音有sol、la、mi。而正調《皂羅袍》作為道教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牌風格,其的前兩個旋律極其相似,且第三個更長。在表演過程中,唱這首歌的人物形象也十分豐富,如老聲、老旦、青衣、小聲等。而《耍孩兒》作為正調唱腔中最為主要的部分,與正調的旋律之間也有著高度的契合點與相似點。但是“拉波”的旋律有所不同,且合唱中的前兩波也會有所差異。就歌詞的結構來說,《皂羅袍》的第一和第二個詞是三個字及一行弦,《耍孩兒》的第一句和第二句與之不同,是六個字一行弦。作為《耍孩兒》派生出的一種曲體,《緊耍孩》以及大、小《流水》同樣是三波曲體的結構形式,在節奏上,其比《耍孩兒》更快。其中大、小《流水》最大的區別就在于銅器伴奏的使用與否。作為道情中速度較快的一種唱腔,《流水》的節奏明快,在劇中人物情緒激憤及悲痛欲絕時使用。《亂句》的旋律同正調《耍孩兒》的旋律相似,歌詞的最后一句話只有一波。這些波與普通聲音的第一波和第二波相同,并且不受三波結構的限制,歌詞有20~30個句子。根據資深藝術家的說法,如果能唱得好《亂句》,道情的風味就算基本掌握了。
五、河東道情音樂唱腔分析
(一)運城道情唱腔的特點
運城道情在當地被稱為“環口句”,在演唱時,也具有“一環三波”的顯著特點。對于“一環三波”,我們可以理解為每首歌的曲牌共有三段,在眾人合唱部分結束之后,通常會演奏一首器樂曲牌。運城道情的唱腔形態主要分為兩種,第一種是以sol、fa、re等為基本音列而構成的曲調,在實際的演唱中,下行的si為降si,這種唱腔在運城道情中也被稱為正調,而在永濟道情中該唱腔則有著不同的稱謂——“徵調”;第一種曲調的基本音列組成有sol、la、dol、re、mi、sol,而這一音列在運城道情中被稱為宮調,同樣在永濟道情中被稱之宮調。值得一提的是,在唱腔伴奏的過程中,不論什么曲調,弦樂器都不會跟腔,除了合唱跟腔,其余唱腔也一律由伴奏過門。一般來說,銜接過門的尾音與伴奏過門的尾音是一致的。通常唱腔銜接過門的尾音為sol、do,除此之外,也會出現fa、re、mi、la、xi為結尾的音。因為落音有所不同,所以傳遞的情感也會有所不同。比如,當過門尾音落在了“5”及“1”上時,多用于承載祥和、安寧的情緒;而當過門尾音落在“4”上時,則多用于表達悲哀、傷心的情愫;當過門尾音落在“3”上時,主要用于表達輕松、愉快的情感。總體而言,過門尾音的設置有著較多的選擇,不同的選擇背后也會延伸出不同的風格。
(二)永濟道情唱腔的特點
作為戲曲音樂的核心,唱腔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對于樂器來說,其很多時候只能表達人物的情感狀態,對于劇中人物角色、故事情節的描述則只能以優美細膩的曲牌及活靈活現的角色來承載。
永濟道情的主要特征有四個。第一是抒情。顧名思義,抒情歌就是表達人物情感的歌曲,一般來說,抒情歌的歌詞復雜、稀疏,其旋律性較強,但是演奏的節奏與速度較慢。第二是敘事。敘事曲牌主要是指用于表達角色主觀感受的一種曲牌,其詞匯的設置也較為廣泛,一些詞密集而簡單,詞匯本身也能夠承載更多的信息。欣賞者可以借此推斷出更多的內容。第三是戲曲性。戲劇性曲牌主要通過外部動作、對話、內部活動等形式給觀眾展示角色的性格。一般來說,這一類型的曲牌波動較大,且節奏更為明快鮮活。劇中人物情感沖突越激烈,節奏的變化速度就越快。第四是“咳波”。“咳波”也被稱為“幫腔”及“起波”,這是道情唱腔的主要特色。通常“咳波”都是借助于虛詞去將一段旋律的線條進行哼唱,所表現出的情感時而詼諧、時而幽默,時而凄涼,時而怨恨。除此之外,還有以緊打慢唱為主要特色的“號子波”,當其力度較小時,吐字較輕;而當力度較大時,則吐字較重。同樣,吐字輕時,主要是一人演唱;而當吐字較重時,則多為眾人幫腔。
永濟道情的樂隊編制分為東路道情和西路道情兩種,在伴奏樂器的選擇上既有互通之處又各有千秋。比如,漁鼓、四胡、笛子、木魚等均有相同之處,而不同之處則體現在東路道情中融入了“蒲劇”打擊樂,西路道情則更傾向于三才板的擊拍。除此之外,東路道情還有文場和武場之分,文場主要以吹、拉、彈等民族管弦樂器進行伴奏,并以此來為故事的發展及人物情感的轉化做鋪墊;而武場則主要是在民族打擊樂器的基礎上,融入了樂隊,以此來配合演員的身段動作與念白。相比于文場,武場的節奏往往更加鮮明。
東、西兩路之間也存在很多不同之處,比如,東路的唱腔曲牌能夠結合情緒的需要根據不同的板式來進行表現,而西路唱腔曲牌則主要是通過“哭調”“平調”及“傲調”的唱腔來進行表達。對于河東道情中的兩種旋律形態來說,其在東路道情中被稱為“徵調”和“宮調”,而在西路中并沒有設置專門的稱謂。也正因如此,東、西兩路的演唱風格也存在較大的差異。對于欣賞者來說,在觀看東路道情時,往往會感受到高昂、激越的情感;而在欣賞西路道情時,則會有優美動聽及纏綿之感。同時,二者所使用的打擊樂器也存在一定的差別,比如,西路道情中的領奏為三才板,而在東路道情中,不論文場打擊樂器還是武場打擊樂器都相對比較豐富。
結語
河東道情音樂文化深得廣大群眾喜愛,對促進地方新農村文化建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應挖掘、保護和傳承民間藝術文化,讓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源源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