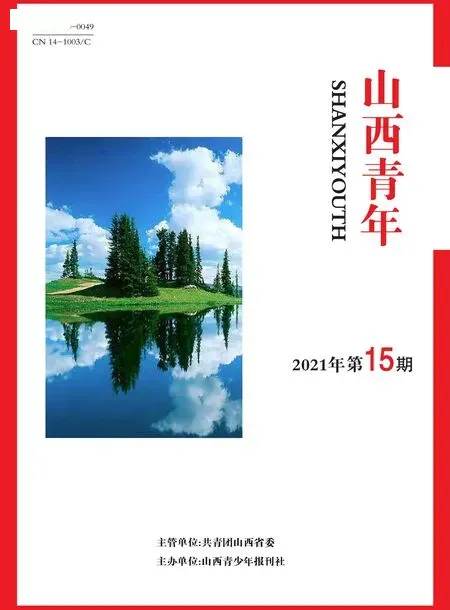杜甫《春夜喜雨》爭議綜論
武國強
(云南大學旅游文化學院,云南 麗江 674199)
一、“當春乃發生”中“發生”涵義辨析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中“發生”一詞,歷代諸家注解不一,存在四種觀點。一是指“下雨、落雨”義。如《唐詩選注》注為:“指‘發生’雨,即下雨、落雨。”《唐代文學作品選》釋義為:“指降雨。”其他有些版本亦多沿襲此說。二是指“萌發生長”義。如《唐詩一百首》解釋為:“發生:動植物生長。”《杜甫詩選》闡釋為:“發生:萌發滋長。”《四時之詩》注為:“發生:萌發生長。”三是指“下雨、落雨”或“萌發生長”義均可。如《杜詩全集校注》注為:“發生,《爾雅· 釋天· 四時》:‘春為發生。’王嗣奭曰:‘好雨知時節’,謂當春乃萬物發生之時也,若解為雨發生則陋矣。顧宸曰:‘應雨而雨,是謂好雨。’‘當春而春雨發,故曰發生。舊解添出發生萬物,便是蛇足。’兩說皆通,正如邊連賓曰:‘或以發生為萬物之發生’,則語為闕略不全。或即指雨說,則字樣太板重。姑從萬物發生,庶與下文有關會。[1]”《唐詩選注評鑒》注為:“乃,一作‘及’。發生,猶出現,指春雨。或謂指萬物生發,參下引王嗣奭評。”四是指“乃作‘及’時指萬物”說。如《杜甫詩選注(增補本)》解釋為:“乃字一作及,作及字,則‘發生’當指萬物說。”以上諸解均有道理,前兩種觀點明確,后兩種觀點較為中和頗覺曖昧,然筆者認為第三種觀點較為適宜,原因如下:
(一)符合詩歌“含蓄蘊藉”的特點。詩歌以含蓄凝練為主要特點,如果單將“發生”解釋為“下雨”過于直白,缺乏韻味;如果解釋為“萬物生發”,則意蘊深長文氣貫通,如浦起龍說:“起有悟境,從次聯得來。于‘隨風’‘潤物’悟出‘發生’,于‘發生’悟出‘知時’也。”細讀全詩會發現,“好雨知時節”中“好雨”是應春迎春之雨,是善解人意之雨,如期而至,故“當春乃發生”。如果“發生”解為“下雨”就與前文“好雨”有重復之嫌,解讀為“萬物生發”就能順理成章,此句可解釋為“好雨猶如人一樣知曉節氣,(好雨)正當萬物萌發的春天而降臨”,春天萬物的復蘇恰恰來自這“好雨”的恩賜。也正是因為這雨“潛入夜”“細無聲”來得低調、悄無聲息,才會讓人聯想到大地萬物萌動、催發生機,讓人感受到雨的“知時節”。春雨“潤物細無聲”的特點,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溫潤如玉澤被蒼生的謙謙君子,這也可以看作是杜甫個人情志的表達,也是具有典型特征的藝術形象客觀上所起的作用。
(二)符合杜甫高超的詩藝。千家注讀者多認為: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此言雖過但仍可信之。如“好雨”,申涵光云:“‘好雨知時節’,此《毛詩》所謂‘靈雨’也。”又如“花重錦官城”中稱“錦官城”而不稱“成都城”,其有深意,自漢代以來,朝廷就在成都設立錦官來管理桑蠶和織錦業,故名“錦城”。有學者認為“當春乃發生”一句,其中也暗含語典,“發生”一詞是源于《莊子》“春氣發而百草生”的命意,杜甫看到春雨想起萬物催生,想到古人的名言警句這是極有可能的,這也完全符合杜甫淵博的知識儲備以及高超的用典手法。
(三)符合成都獨特的氣候。四川盆地相較于周圍群山地勢較低,可視為“谷地”,由于受到大氣環流“山谷風”效應的影響,四川盆地多夜雨,夜雨占總雨量的60%至70%,遂有“巴山夜雨”之稱。又由于四川盆地一年四季降水不均,多呈現冬干、春旱、夏澇、秋綿的特點,所以杜甫才對這善解人意如約而至的春雨格外欣喜。細雨飄飛,無聲無息,滋潤萬物,催發生機。將“發生”解釋為“萬物生發”符合詩境,正是這“知時節”的“好雨”,瞬間點燃了詩人欣喜之情,讓他很容易想到萬物復蘇草木萌動的景象。
二、“花重錦官城”中“重”字讀音辨析
“花重錦官城”中“重”字之義,直接涉及其讀音問題,有人認為讀“zhòng”,是因花沾著雨水,變得飽滿沉重;有人認為讀“chóng”,表示重疊,形容花開茂盛;還有人認為“花重”兼有兩解,一指花兒沾滿雨水變得嬌艷沉重,一指花兒重重疊疊開滿錦官城中。目前所見注本以“zhòng”義解釋者較多,如《唐詩選注評鑒》解釋為:“花重,花經雨而沾濕,故加重。”《杜甫詩選》釋義為:“重:沉重。”《杜甫全集校注》《杜甫詩選注》亦秉承“花因雨而重”之義。筆者認為“重”應讀“zhòng”,然兼有“雨過花重”“花開繁茂”之義。
杜甫是詩歌集大成者,《春夜喜雨》是其標準的五言律詩,格律為“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最后一句“花重錦官城”是“平仄仄平平”,“重”是“仄”聲,無疑應讀“zhòng”。又據《康熙字典》有關“重”記載,《唐韻》柱用切;“《集韻》《韻會》儲用切,音緟。”《韻會》毛氏曰:“凡物不輕而重,則上聲。因其可重而重之,與再重、鄭重,皆去聲。”又《正韻》:“徒紅切,音同。”《辭源》解釋“重”為:“zhòng直隴切,上,腫韻,澄。”“chóng直容切,平,鐘韻,澄。”“tóng古今韻會舉要 徒東切。”由《康熙字典》《辭源》記載,“重”在古代有平、上、去三種讀音。此外從文字源流看,“重”的本意是“沉重”。作名詞時指分量、重量,作動詞時指增加、加重;重又有增加分量引申指重復、重疊,又引申指再,讀作“chóng”。由以上推知,“花重錦官城”中“重”字,可以引申出“重復、重疊”之義,表示花開繁茂的意思。其實杜甫借用重量來描摹花繁花密的詩還有《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的組詩,其中就有“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2]的詩句,這句詩與“花重錦官城”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重”讀“zhòng”時是仄聲,讀“chóng”時是平聲,如果解釋為“重復、重疊”之義似乎不合韻律,其實不然,查《康熙字典》可知“古人三聲通用,必謂上去異訓,不可通押,此宋人拘泥之過也”,意思是在宋代之前,“重”平、上、去三種聲調是通用的,它們平仄不同,但含義相同,可通用。換言之,就是“重”讀仄聲“zhòng”,但詞義上兼有“重復、重疊”之意。如杜甫另一首律詩《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其中首句格律為“仄仄中仄仄”,這是拗體句,救拗方式是“平平平仄平”,接下來頷聯對句“昨夜月同行”格律為“仄仄仄平平”,出句應該是“中平平仄仄”或“平平仄仄仄”,“幾時杯重把”格律顯然是“中平平仄仄”的形式,“重”一定是“仄”聲,應讀“zhòng”,然而意思是“重復”之意。又據溫庭筠《送人東游》“荒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郢門山。江上幾人在,天涯孤棹還。何當重相見,尊酒慰離顏。”其中“何當重相見,尊酒慰離顏”格律為“平平仄平仄,平仄仄平平”,“重”也是仄聲。“幾時杯重把”“何當重相見”肯定是“重復”之義,而不是“沉重”義,由此可知在唐代“重”讀仄聲,卻含有“重復、重疊”義,這是很常見的情形。在現代漢語中,其實還有“重”讀“zhòng”,但表示數量多之義的遺跡,如“重金打造”“重金求子”“濃墨重彩”。
綜上所論,“花重錦官城”應讀作“zhòng”,但是其中包含“chóng”的含義,即重復、重疊。因此,“花重”第一層面可解釋為雨后花重,沉甸甸、嬌艷欲滴;第二層面可解釋為雨后花發,重重疊疊開滿了整個錦官城。詩人說“花重”而不說“花香”“花艷”“花嬌”“花燦”,就是要體現春雨過后,百花盛開之貌,展現春意盎然、春光明媚的效果。詩人用一“重”字,點燃了整座錦官城的生機活力,表達了自己無比喜悅的心情,也讓我們感受到了他發自內心對“春雨”恩澤天下的感激之情,當然也展現了其非凡的錘字煉句的高超藝術。
三、《春夜喜雨》寫作年代考釋
有關《春夜喜雨》寫作具體年代,在學術界一直存有爭議。王洙《杜工部集》、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認為詩成于唐肅宗寶應元年(762)春天,蔡夢弼《草堂詩箋》將其列入上元元年(760)春天,黃鶴在《黃氏補千家詩集注杜工部史詩》中認為作于上元二年(761)春天。后世多數學者認同黃氏之說,如仇兆鰲《杜詩詳注》,莫礪鋒、童強《杜甫詩選》,蕭滌非《杜甫全集校注》。部分著作為了“存而不論”,往往加注一“約”字,如劉學鍇《唐詩選注評鑒》認為“約上元二年(761)春作于成都浣花草堂”[3];也有部分著作諱言此題避而不談。蕭滌非先生注杜詩作頗多,其依據杜甫寫的《說旱》一文,對黃氏之說提出質疑。黃鶴曰:“詩云:‘花重錦官城’,則是成都詩。梁權道亦編在寶應元年,然是年春旱,當是上元二年作。”“是年春旱”是指上元二年十月至寶應元年二月發生在成都一帶的旱災。蕭滌非認為正因旱災重,所以春天甘霖突至才會使詩人感覺可喜可貴,這樣就不能排除該詩作于寶應元年的可能性。
詩歌首聯是“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既然是善解人意的“好雨”,又是“當春”而至,這就與旱災無關,因而,該詩作于寶應元年之論就不攻自破。另有學者考證杜甫在成都時,寫了許多與春雨春水相關詩作,如《春水生二絕》《水檻遣心二首》《散愁二首》,以上作品注家多認為是杜甫上元二年春天所作,推論可知是年成都降水頗多,且在當年二月六日前成都已普降甘霖,雨量較大,杜甫寫道“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春水生二絕》)[4]。杜甫寫的是《春夜喜雨》,既然是“喜”,說明這是他初次感受到是年春雨的到來,頗有“人生若只如初見”之感,如果前已見過,有何欣喜可言?再者詩中尾聯寫“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既然成都春雨過后來日看到的是百花繁茂花重欲滴的盛景,就斷然不是初春所作,該詩作于暮春時節應更可信。如果說《春水生二絕》是上元二年初春所作,那《春夜喜雨》應比其早出。
杜甫有關“喜雨”的作品還有三首,皆直接提名《喜雨》,且都與春旱有關,唯獨《春夜喜雨》,突出“春夜”二字,其大有深意。因為杜甫于上元元年春天,經過“一歲四行役”抵達成都,他是中原河南人,初至蜀地備感新鮮,尤其是蜀地多夜雨,更與中原不同,因此,可推知《春夜喜雨》應作于他來成都后所遇的第一場暮春時節的春雨,所以才會格外欣喜格外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