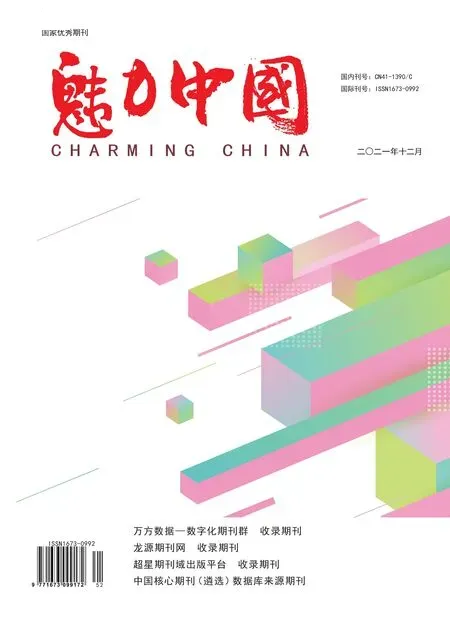淺論商標權與名人姓名的沖突與規(guī)制
劉恒
(中共德州市委黨校,山東 德州 253015)
近年來,商標權與名人姓名權之間的沖突并不少見,最高院在“喬丹案”中,就認為涉案的“喬丹”商標侵害了邁克爾·喬丹的在先姓名權,從而將其撤銷。2019 年3 月7 日,歌星鄧某棋宣布與其經紀公司解約,由于經紀公司早在2014年就將“鄧某棋”注冊為商標,關于鄧某棋是否能夠使用自己名字的討論也成為一時的熱點。
正是因為名人姓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能夠衍生出巨大的商業(yè)價值,名人姓名被注冊為商標的情形也就層出不窮。因此,打擊對名人姓名的惡意搶注行為從而保護名人的姓名權就很符合《商標法》誠實信用的立法宗旨。但是名人姓名權的保護存在著一個矛盾的處境:一方面姓名權作為人格權的一種,對其保護應當是不附加知名度的要件的,然而另一方面,不具有知名度的姓名不會與特定人物產生穩(wěn)定的聯系,又不會和已注冊的商標產生沖突。因此,對名人姓名中所蘊含的商品化權益進行保護就顯得尤為必要。
一、商標權與名人姓名沖突的本質
在目前的商業(yè)社會中,培育名人的時間成本降低,同時其自身帶來的效益也在逐漸增加,名人姓名所具有的財產價值也在逐漸升高。在這個過程中,名人姓名不再僅僅具有人格權的含義,還包含了大量的財產價值,名人的姓名也具有了商品化的權益。而商標權作為一種財產性權利,其與名人姓名的沖突實質上是與名人姓名商品化權益的沖突。
將名人姓名注冊為商標實質上是將名人的姓名與商標所對應的商品建立了聯系,其目的顯然是為了利用名人姓名中包含的商業(yè)價值。一般而言,姓名權本不具有財產屬性,正是由于名人具有的商業(yè)價值才使得其姓名具有了商品化權益,盡管搶注名人的姓名既損害了名人的人格權,也損害了名人姓名的商品化權益,但是商標導致公眾混淆的基本前提是名人的姓名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且具有對應聯系。因此,搶注的商標與名人姓名的沖突的本質仍是其損害了名人的商品化權益。
這一點可以從最高院再審的喬丹商標案中得到印證,如果認定喬丹商標損害了美國球星Jordan 的姓名權,只需要證明喬丹是球星Jordan 的中文譯名,并且喬丹公司未經本人許可將其注冊為商標即可。但是最高院在此之外卻將“知名度”和“穩(wěn)定的對應關系”作為姓名權保護的構成要件。[1]此外,最高院還將“引起公眾誤認”作為一項保護姓名權的重要因素,這事實上是考量了姓名背后的商業(yè)價值,因此,最高院對喬丹姓名權的保護實質上是保護姓名的商品化權益。
盡管姓名權既包含人格利益和財產利益,但事實上這兩種利益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是分開保護的,即姓名權的人格利益主要由民法進行保護,而姓名權的財產利益則主要是由知識產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進行保護。[2]因此,注冊商標所損害的“在先權利”更多的應當是姓名的商品化權益,以此能夠更加準確對商標權和名人姓名權的沖突進行認定。
二、商標權與名人姓名的沖突認定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何為名人的姓名,我國立法并沒有對此進行明確的規(guī)定,但是從與商標權沖突的角度分析,名人姓名的認定主要依據《商標法》第十條(八)和第三十二條的規(guī)定。即注冊商標應當是因具有“不良影響”或“損害了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而與名人姓名相沖突。
無論是將名人的姓名認定為“在先權利”還是適用“不良影響”,司法實踐中法院多數要求其具有一定知名度。例如在“喬丹案”中,最高院認為在適用商標法第三十一條的規(guī)定時,自然人就特定名稱主張姓名權保護的,該特定名稱應當符合知名度和穩(wěn)定對應聯系的要件。[3]同樣在“易建聯姓名案”中,北京高院認為,判斷姓名權是否因爭議商標申請注冊而受到損害,應當以該姓名在先具有一定知名度為前提。[4]因此,所謂名人姓名,應當是在特定行業(yè)內,在相關公眾中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的姓名。
名人姓名需要具有知名度的要求還可以從其他法律法規(guī)中得到印證,根據2017 年最高院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授權確權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當事人如果主張訴爭商標侵犯了其姓名權,需要以相關公眾認為該商標指代了自然人,并且標記有該商標的商品與該自然人存在特定聯系為標準,[5]這也從側面證明了名人的姓名需要有知名度的要求,并且商標與姓名建立了對應關系。
從競爭法和民法的角度,姓名權受到保護也有知名度的要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guī)定,“具有一定的市場知名度、為相關公眾所知悉的自然人的筆名、藝名等”,可以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意義上的姓名。[6]《民法典》第1107 條規(guī)定,“具有一定社會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眾混淆的筆名、藝名、網名、譯名、字號、姓名和名稱的簡稱等,參照適用姓名權和名稱權保護的有關規(guī)定。”[7]因此,可以推斷出,名人姓名在商標法上的保護同樣需要知名度的要求。
但是對名人姓名保護的知名度要求不必很高,例如在“KATE MOSS 案”中,原告提交的證據雖然不足以證明“KATE MOSS”在中國有較高的知名度,但是其被告在行業(yè)內對KATE MOSS 有較高的認知度,因此,被告具有不正當利用“KATE MOSS”這一姓名營利的目的。[8]此外,《商標審查與審理標準中》也規(guī)定商標是否損害姓名權,以該商標指向姓名權人或者與姓名權人建立對應聯系為前提。
因此,名人的姓名應當在市場或相關公眾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這種知名度的要求不必很高,只需要在相關公眾中建立起商標與姓名的對應聯系。在這種情況下,注冊商標才會與該名人的姓名權產生沖突,以至于引起誤認或混淆。從這一點看,對普通人姓名的商品化權進行保護也是可以的,只是由于普通人難以證明商標使用的姓名指向自己,即難以證明個人的姓名可被公眾識別。知名度的要求事實上是為了證明個人與其姓名之間的聯系程度。
在認定商標權與名人姓名的沖突時,還需要考慮名人姓名與注冊商標或使用商標的商品之間的關聯程度。盡管這種對應聯系并沒有明確的量化標準,但可以參照類似商品服務的標準。要判斷名人姓名和使用商標的商品之間的關聯程度,可以將商品的類型和名人所處行業(yè)的相近程度作為參考因素。這也就表明,如果名人所處的行業(yè)范圍較廣,并且在這些行業(yè)的相關公眾中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那么該名人的姓名可能會得到范圍較廣的保護。
商標權與名人姓名沖突最為典型的即是直接將名人的姓名或中文譯名注冊為商標,近年來,這種案例層出不窮。例如“喬丹案”、“易建聯案”、“姚明案”,乃至于有更惡劣地將抗疫英雄鐘南山、李文亮醫(yī)生的姓名申請注冊商標。這種直接將名人姓名注冊為商標的行為通常具有明顯的惡意和搭便車的意圖。
此外還有許多將名人姓名的諧音注冊為商標的行為,對于此種行為,現行法律法規(guī)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許多學者也認為這種行為并不直接侵犯名人的姓名權,[9]諧音名人商標不當然構成侵權,名人對此應當予以忍受。[10]然而,這種行為事實上也是注冊人抱有僥幸心理甚至惡意。在認定注冊名人姓名諧音的商標是否與名人姓名沖突時,需要綜合考慮注冊人的主觀惡意程度和名人姓名知名度的大小,如果名人姓名的知名度足以使相關公眾認為諧音指向該名人,則可以認定為注冊商標侵犯了名人的姓名權。
綜上所述,在認定注冊商標是否與名人姓名權構成沖突時,一是需要考慮名人姓名在相關公眾中的知名度,并且這種知名度的要求不必太高;其次是考慮名人姓名與注冊商標以及商標附著的商品之間的關聯程度,這種關聯程度越緊密,消費者產生的誤認和混淆就會也越大,注冊商標就會更加容易侵犯名人的姓名權。除此之外,還需要綜合考慮注冊人的主觀意圖,如果注冊人在使用商標的過程中具有明顯的搭便車的惡意,則就會認定為具有不正當的目的。
三、明確對姓名商品化權益的保護
在處理商標權與名人姓名的沖突時,需要將名人姓名權中的人格利益部分和財產利益部分分別對待。人格權的保護應當是平等且不附加任何條件的,而在認定商標權與名人姓名時需要考慮知名度等要素,商標權與名人姓名沖突的實質是注冊商標侵犯了名人姓名的商品化權益,也即名人姓名所蘊含的財產價值。因此,在對名人姓名進行保護時,需要將姓名權中所包含的財產利益獨立分立出來進行保護。
(一)具有“在先權利”保護的正當性
雖然我國目前沒有商品化權的制度,但這并不影響對名人姓名商品化權益的保護,明確姓名的商品化權益能夠有效地加強對名人姓名的保護。目前對名人姓名權的保護主要依據《商標法》的“在先權利”和“不良影響”條款,明確姓名的商品化權益是“在先權利”能夠使適用“在先權利”的保護更加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
姓名權作為人格權的一種,其保護應當是一視同仁,且不附加任何條件的,但這樣的保護在商標法領域可能會存在矛盾,一方面如果將“在先權利”中姓名權的保護附加知名度的要件,可能會破壞人格權保護平等性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不具有知名度和對應聯系的姓名也不會和注冊商標產生沖突,不會在相關公眾中發(fā)生混淆。事實上,包括“喬丹商標案”在內的眾多案件在適用“在先權利”對名人姓名進行保護時,均考慮了知名度和對應聯系的因素,其實質仍是對名人姓名的商品化權的保護。因此將商品化權明確為《商標法》上的在先權利,能夠使對名人姓名的保護更加具有正當性。
《商標法》對名人姓名保護的核心在于其知名度所帶來市場價值,也正是這種知名度才會造成相關公眾的混淆和誤認,如果將在先權利認定為具有人格利益的姓名權,顯然和對人格權保護的絕對性不符。顯然,一個非知名人物的姓名一般是不會與注冊商標在相關公眾中產生混淆和誤認的。因此,應當明確名人姓名的商品化權益是“在先權利”的一種,這樣將知名度作為保護要件就更加具有正當性。
(二)具有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正當性
這種對名人姓名商品化權益的保護也可從反不正當競爭法角度進行分析,《反不正當競爭法》已經明確規(guī)定經營者不得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響姓名(包括筆名、藝名、譯名等),可見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具有知名度的名人姓名。盡管有觀點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規(guī)制的是具有競爭關系的市場主體,名人并不能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主張自己姓名的保護。但在“姚明人格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法院已經明確認定,個人的影響力及形象就是商品,因此名人屬于經營者的范圍,符合市場主體的要求。此外,法院也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姓名權,不同于于一般意義上的人身權,是一種商業(yè)標識。[11]這也說明了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是名人姓名的商品化權益。因此,明確名人姓名的商品化權益保護,不僅能夠使其具有“在先權利”保護的正當性,而且可以使其具有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正當性。
四、結語
盡管名人姓名既具有人格利益,又具有財產利益,在認定商標權與姓名權的沖突時,經常囿于人格權保護的平等性和非知名人物姓名不具有商業(yè)價值之間的矛盾。司法實踐中對名人姓名知名度的要求實質上表明了其保護的是名人姓名的商品化權益,即商標權與名人姓名沖突的本質是注冊商標損害了名人姓名的商品化權益。將商標權侵犯的“在先權利”界定為名人姓名的財產利益,即商品化權益,能夠使得名人姓名的保護更加具有靈活性和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