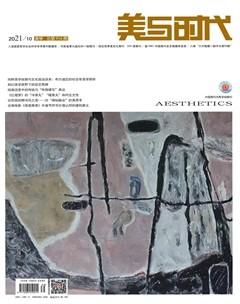論民國初期書風(fēng)之變
劉光喜

摘? 要:“碑帖融合”是考察晚清民國書法史時(shí)多被言及的一個(gè)重要概念。但對于這一說法的提出與界定,學(xué)術(shù)界未有確切所指。這也遮蔽了一些“碑學(xué)”以來書風(fēng)演進(jìn)的線索。通過界定“碑學(xué)”“帖學(xué)”與“碑帖融合”的概念,以及考察民國時(shí)期“碑帖融合”的書法實(shí)踐,從而梳理出晚清與民國初期“碑帖融合”內(nèi)涵演進(jìn)的內(nèi)在理路。
關(guān)鍵詞:碑帖融合;碑學(xué);帖學(xué);民國書風(fēng);篆分遺意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系天津師范大學(xué)教改項(xiàng)目“‘書畫印融合思維的深入與轉(zhuǎn)化——國畫專業(yè)書法、篆刻課程教學(xué)改革”(JGYB01218030)階段性研究成果。
考察民國書風(fēng),一般書法史多將“碑帖融合”“碑帖并重”作為其主導(dǎo)書風(fēng),如孫洵先生的《民國書法史》、沃興華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書法史》等。不少學(xué)者在梳理晚清書法史時(shí)亦使用此語,可見研究者是將此作為晚清民國時(shí)期的創(chuàng)作觀念而加以觀照。但對這一觀念的內(nèi)涵,學(xué)術(shù)界在實(shí)際使用時(shí)又存有分歧,以致缺乏學(xué)理上的辨識,對晚清民國書風(fēng)的演進(jìn)亦難有清晰的把握。故本文對民國初期“碑帖融合”書風(fēng)的內(nèi)涵及其演進(jìn)線索試作探究。
一、“碑學(xué)”“帖學(xué)”與“碑帖融合”的界定
“碑學(xué)”與“帖學(xué)”兩書學(xué)概念最早見于《廣藝舟雙楫》[1]754-755。但康氏在文本中的所指,一些研究者使用時(shí)較為含混,由此也造成諸多對《廣藝舟雙楫》內(nèi)在理路的缺失解讀,進(jìn)而對清代碑學(xué)的研究也出現(xiàn)分歧。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xué)》中雖將碑學(xué)(以魏碑為主)和篆書、隸書并列,但文中又云“通常談碑學(xué),是包括秦篆漢隸在內(nèi)的,不過為了敘述的便利起見,以真書為原則”[2]12,同時(shí)在后文的“顏?zhàn)帧辈糠钟謱懙馈氨酒械谋畬W(xué)帖學(xué)是狹義的”[2]22-23,可見,在民國時(shí)期“碑學(xué)”的界定已有廣義和狹義。
劉恒先生認(rèn)為“帖學(xué)”是指“宋元以來崇尚‘二王系統(tǒng)”“以晉唐以來名家墨跡、法帖為取法對象”“這一風(fēng)氣是在宋代出現(xiàn)的《淳化閣帖》等一大批刻帖的刺激和影響下形成的”;“碑學(xué)”是指“重視漢、魏、南北朝碑版石刻的書法史觀、審美主張以及主要以碑刻為取法對象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氣”[3]。文中所言“帖學(xué)”內(nèi)容包含墨跡和刻帖,尤指宋代以后的刻帖,這是站在書法發(fā)展史的角度來理解,不同于康氏所言“帖學(xué)”指屢翻失真的刻帖。劉恒先生的“碑學(xué)”把漢魏碑版也納入碑學(xué)研究和師法的范疇,大體是就“廣義的碑學(xué)”而言。誠然,漢魏時(shí)期的碑版是考察篆、隸書體演變的重要金石資料,也是清代篆隸書風(fēng)復(fù)興的審美取法對象,但從嚴(yán)格的學(xué)術(shù)角度看,它們屬于兩個(gè)不同的歷史階段,碑學(xué)的落腳點(diǎn)是六朝碑版楷書,而非篆隸古體,碑學(xué)審美理論的“古意”溯源與碑學(xué)的所指應(yīng)有所出入。叢文俊先生對此有過清晰的論述:
與帖學(xué)相對而言的碑學(xué),指北朝碑版之學(xué),亦即楷書,清代的碑學(xué)著述已論述清楚。風(fēng)尚所及,草、行亦或緩入方筆拙勢,習(xí)慣上也列入碑學(xué)。篆隸書法貫穿清代始終,不待碑學(xué)而生,通常亦不取北碑文字形質(zhì),以其和碑派書法關(guān)系緊密,成就清代書法格局,遂有碑學(xué)及碑派書法擴(kuò)大化,兼及三代秦漢篆隸古體之說。不確。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置《體變》《分變》《說分》《本漢》四節(jié)于前,本包世臣《歷下筆譚》而增廣之,旨在明確北碑宗統(tǒng)源流,正其名分。如果以倡碑導(dǎo)源于篆隸和金石學(xué),因而泛言碑派書法,則易模糊碑學(xué)與篆隸復(fù)古之自身的學(xué)術(shù)意義。[4]
此說近于學(xué)術(shù)界“狹義的碑學(xué)”。《廣藝舟雙楫·體變》言:“今學(xué)(即碑學(xué))者,北碑、漢篆也,所得以碑為主,凡鄧石如、張廉卿等是也。”此處其實(shí)仍以北碑為主。其漢篆之說,亦言鄧石如以碑派筆法入篆[1]853。但就《廣藝舟雙楫》“碑學(xué)”的界定,康氏在推崇北碑的同時(shí)還兼顧南碑。《廣藝舟雙楫·寶南》言:“書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達(dá)之為是論,蓋見南碑猶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為界,強(qiáng)分南北也。”[5]
此外,“篆分遺意”與“碑學(xué)”書風(fēng)之間一方面存在審美取向與藝術(shù)觀念上的聯(lián)系。例如,以黃惇先生為代表的研究者將清代的碑學(xué)運(yùn)動(dòng)作為一個(gè)整體進(jìn)行考察,將篆隸復(fù)興作為碑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一部分,從而將清代的“碑派”思潮分為前碑派和后碑派兩個(gè)時(shí)期[6]。站在書法發(fā)展史的角度,這無疑是一種審慎而求真的學(xué)術(shù)視角。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晚清碑學(xué)發(fā)展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取法魏碑體和重視篆隸筆意,在當(dāng)時(shí)書壇卻代表兩種不同的意見。張小莊先生在論及何紹基與趙之謙書學(xué)審美觀的分歧時(shí)寫道:
何、趙之爭,實(shí)質(zhì)上是代表了當(dāng)時(shí)書壇上關(guān)于學(xué)習(xí)碑刻的兩種意見:一種是重視篆隸筆意的創(chuàng)作審美觀,主要以取法秦、漢碑刻為主,或亦崇尚北朝魏體書,但僅汲取其中所含的篆隸筆意而已;另一種是既重視篆隸筆意,而更著力于對北魏碑刻的學(xué)習(xí)——無論形神都主動(dòng)去靠近。前者以何紹基為代表(之前的金農(nóng)等都可歸入到此類);后者是鄧石如肇其先,至趙則蔚為大觀。[7]
可見,從書法史發(fā)展角度,清代碑學(xué)運(yùn)動(dòng)在書法創(chuàng)作上經(jīng)歷了從篆隸筆意到北朝碑版書風(fēng)的轉(zhuǎn)變過程。可以推想,假如沒有鄧石如、趙之謙等人在實(shí)踐上對魏碑體筆法的開創(chuàng),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的“碑學(xué)”思想將成為無所依傍的空中樓閣。也就是說,考察晚清碑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演進(jìn),站在狹義的“碑學(xué)”內(nèi)涵上去審視能更真實(shí)地了解歷史的面目。
關(guān)于“碑帖融合”說的提出與界定,學(xué)術(shù)界未有確切所指。王鎮(zhèn)遠(yuǎn)在《中國書法理論史》中對劉熙載、沈曾植的書學(xué)思想論述時(shí)談及南北融通、碑帖相融的觀點(diǎn)。沃興華在《插圖本中國書法史》中對沈曾植也從碑帖融合的角度進(jìn)行解讀;孫洵在《民國書法史》中將民國時(shí)期的書法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分為:以碑為主(以甲骨文入書、以篆隸入書和以南碑北碑入書),以帖為主(以正楷著稱、以行書聞名和以草書精道)和碑帖兼寫、碑帖交融三種。而碑帖交融的代表人物為沈曾植、曾熙。黃惇先生談及當(dāng)代書壇格局時(shí)亦專列“碑帖融合的創(chuàng)作模式與其領(lǐng)域的拓展”一節(jié),梳理自晚清至民國時(shí)期碑帖融合的各家,包括何紹基、趙之謙、楊守敬、康有為、沈曾植、沙孟海和林散之等人。葉培貴對清代書學(xué)的分類以篆隸、北碑、晉唐以來行草小楷為基本力量,以融鑄各派為另一補(bǔ)充力量①。而熔鑄各派的代表為何紹基。可見“碑帖融合”并不是特指某一歷史時(shí)期的書法風(fēng)格,而其內(nèi)涵也在發(fā)生變化。
孫洵先生雖未對三種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界定,但從文中論述亦能得出其潛在觀念:篆隸、甲骨文皆可成為碑派的范疇,而簡牘帛書、敦煌寫經(jīng)亦可作為帖學(xué)師法的對象,相應(yīng)的碑帖交融,無論是帖筆寫碑,還是碑筆寫帖,其風(fēng)格內(nèi)容相較晚清書壇已有很大演變,應(yīng)該說“碑學(xué)”與“帖學(xué)”的使用已失去《廣藝舟雙楫》中本來的意義,而成為一種審美意識。孫洵先生“將碑帖交融的創(chuàng)作道路代表著民國書法的最高成就,作為民國書風(fēng)的新走向”[8],亦著眼于此。但此說對民國時(shí)期“碑帖融合”的考察仍不夠深入。民國時(shí)期碑學(xué)大盛,諸多理論家(如陳康、祝嘉等人)雖對康氏《廣藝舟雙楫》“尊碑貶帖”提出指責(zé),但主張以學(xué)碑(魏晉六朝碑)為根本,然后拓展至帖派諸家,最終上溯至商周秦漢。1943年出版的陳康《書學(xué)概論》評述了碑學(xué)與帖學(xué)的關(guān)系:“碑學(xué)帖學(xué)應(yīng)并重,以帖學(xué)為入,碑學(xué)為出。以帖學(xué)為輔,碑學(xué)為主……學(xué)碑不學(xué)帖,可;學(xué)帖而不學(xué)碑,則不可。蓋碑兼帖之長,而帖無碑之古也。”[9]216可見陳氏“碑帖并重”書學(xué)觀下隱含其碑學(xué)高于帖學(xué)的思想。但“碑帖并重”并非“碑帖融合”,這里牽涉到一種風(fēng)格融鑄形成的問題。故嚴(yán)格地講,當(dāng)時(shí)“碑帖融合”的觀念應(yīng)是以碑為主、以碑融帖,在創(chuàng)作中則表現(xiàn)為由不成熟的書寫面貌走向后期成熟的書法風(fēng)格。
二、對民國時(shí)期“碑帖融合”書法實(shí)踐的考察
首先,我們需要理清晚清碑帖融合的發(fā)展線索。碑帖融合的觀念與實(shí)踐自包世臣《藝舟雙楫》的時(shí)代以及之后的清代不乏其人,這在清代碑帖之爭的背后始終作為一種力量而存在。從狹義角度看,在書學(xué)觀念上包世臣已具有用碑改造帖的意識,以碑證帖、以碑溯帖,已開了碑帖融合的先河[10]。之后楊守敬在《激素飛清閣評帖記序》中對于精本刻帖與碑版,提出“合之兩美,離之兩傷”的觀點(diǎn)。而劉熙載在《書概》中的看法,則重在南北書風(fēng)的融通上,但這與碑帖融合的觀念有所出入。在書法實(shí)踐上,清代晚期以趙之謙為代表,這一時(shí)期的書家往往有深厚的帖學(xué)(包括唐碑)功底,所以他們的碑帖融合主要是以碑(北朝碑刻)破帖,是在帖學(xué)的營壘之中進(jìn)行審美的突破。此種意識從廣義碑帖融合的角度來說,金農(nóng)的“碑行”體(以漢碑入行書)書法已有醞釀[11]145,而后何紹基由唐碑而上溯秦漢“篆分遺意”,包括他涉獵北朝碑也是這一意圖。其次,“篆隸筆意”是貫穿清代書法流變的重要線索[12],在晚清時(shí)期鄧石如、包世臣、何紹基、趙之謙等都在追求著這種書法境界,包、何兩家雖然參酌北碑,但均未達(dá)到鄧、趙兩家在北碑筆法構(gòu)建上的地位,而這種北碑筆法的探索在書體意義上并未完成,尤其在北碑筆法與行草的結(jié)合上。因此在晚清時(shí)期,同時(shí)追求北碑派筆法與“篆隸筆意”在某些書家身上雖有所體現(xiàn),但尚未形成一種突破“碑學(xué)”與“帖學(xué)”的束縛、真正在書學(xué)風(fēng)格上融合碑帖的時(shí)代風(fēng)氣與潮流。以上兩點(diǎn)是晚清與民國時(shí)期碑帖融合最大的不同。
探討民國時(shí)期碑帖融合的書風(fēng),沈曾植(1850—1922)是必談及的書家。他早年精于帖學(xué),執(zhí)筆學(xué)包世臣,中年服膺張?jiān)a摚商氡砟曜叩氖恰氨诤稀钡臅鴮W(xué)道路。沃興華先生曾將沈曾植的書法分為三個(gè)階段:(一)1910年以前是沈曾植學(xué)帖的階段,主要受鍾繇、歐陽詢、黃庭堅(jiān)和米芾的影響;(二)1910-1919年,沈氏1912年由帖入碑,其間有經(jīng)歷學(xué)習(xí)黃道周、倪元璐的階段。此外,沈氏還研習(xí)過流沙墜簡。此階段基本奠定了后期碑帖結(jié)合的風(fēng)格,只是用筆結(jié)體還比較拘謹(jǐn);(三)1921-1922年,沈曾植1919年以后的書法風(fēng)格逐漸厚重生辣,趨于成熟,其生命的最后兩年,衰年變法取得很大突破[13]。從目前所見作品來看,沈氏取法頗廣,上述之外尚有唐人寫經(jīng)、索靖、《鄭文公碑》等。這說明他在碑帖之間進(jìn)行不同的嘗試,碑帖融合,意欲借古開今[14]。沈曾植書學(xué)實(shí)踐的很大成就是晚年將“二爨”和《嵩高靈廟碑》的刀刻痕跡融合到章草與行草的創(chuàng)作中。這也合乎他“異體同勢”和“古今雜糅”的書學(xué)追求。馬宗霍評價(jià)他“暮年作草,抑揚(yáng)盡致,委曲得宜……極繽紛離披之美”[15]。其風(fēng)格特征主要是生拙和雄肆。曾熙評價(jià)他是“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wěn)”。“不穩(wěn)”,即沈氏學(xué)生王蘧常所言“下筆時(shí)時(shí)有犯險(xiǎn)之心”[16]。但觀其書作,其生拙并不是熟而后生,其點(diǎn)畫為求熔鑄各體,而顯得氣韻不暢達(dá)。其實(shí),碑學(xué)與草書的結(jié)合是前代碑學(xué)大家困惑的問題,因碑派用筆的遲澀與草書的流暢本身就是一種矛盾,晚年的康有為亦對其弟子蕭嫻慨嘆:“近代草書行書大家不多,是碑學(xué)發(fā)展后是帖學(xué)衰微的另一偏向。”②
沈曾植在晚年試圖將北碑筆法與行草相結(jié)合,這種嘗試與當(dāng)時(shí)的書風(fēng)有關(guān),但也受到一些書家的指責(zé)。如楊守敬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就對當(dāng)時(shí)以碑派筆法改造行草,而拋開王羲之、顏真卿的時(shí)代書風(fēng)表示不滿。可見,在沈曾植之前這種碑學(xué)與草書結(jié)合的書風(fēng)已經(jīng)形成。沈氏的探索也屬于此時(shí)不成熟階段。而這種探索要到沙孟海與林散之的時(shí)代才顯現(xiàn)出其渾融無跡、出于自然的品格[11]147-148。
當(dāng)時(shí)海上書家,還有曾熙與李瑞清。曾熙(1861-1930),晚號農(nóng)髯,早年師法漢碑,得力于《華山》《夏承》兩碑,后又習(xí)《瘞鶴銘》《鄭道昭》和《般若》等六朝碑;中年以碑入帖,寫二王書法自然妥帖,閑雅平和之中富有拙趣。與曾熙相似,有“北李南曾”之稱的李瑞清(1867-1920),號梅庵,民國初年遁居上海,鬻書自給,自署清道人;寓居海上期間與沈曾植、鄭孝胥、曾熙等多有往來,切磋書藝,此時(shí)書風(fēng)亦有所改變。其學(xué)書經(jīng)歷,早年“習(xí)鼎彝,長學(xué)兩漢、六朝碑碣,至法帖了不留意”,后避亂滬上,以賣書為業(yè),其自述當(dāng)時(shí)“沈子培先生勖余納碑入帖,秦幼衡丈則勸余捐碑取帖,因以暇日稍稍研求法帖……其不能得其筆法者,則以碑筆求之”[17]。可見,李梅庵晚年的書風(fēng)之變是“納碑入帖”,即以碑派筆法寫帖。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稱曾農(nóng)髯“由圓筆以下窮南碑”,而李梅庵終身嗜北碑,對《鄭文公碑》用力最深,兩家在當(dāng)時(shí)均以碑來融合帖,其書風(fēng)改變的原因雖可深入探討,但其創(chuàng)作實(shí)踐體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書學(xué)觀念的轉(zhuǎn)變,即在晚清碑學(xué)思潮漸漸消退之后,帖學(xué)意識逐漸上升的態(tài)勢。正如后來白蕉所言:“所謂碑學(xué),從包慎伯到李梅庵、曾農(nóng)髯的鋸邊蚓糞為止,曾經(jīng)風(fēng)靡一時(shí),占過所謂‘帖學(xué)的上風(fēng),但到了現(xiàn)在,似乎風(fēng)水又在轉(zhuǎn)了。”[18]從書法史的發(fā)展角度來看,李、曾二人的碑帖融合依然屬于一種探索,其書法成就不免受到今人的批評③,但從書法觀念的影響看,正是沈、李、曾等人對書法新風(fēng)格的探索實(shí)踐才開啟了民國時(shí)期對碑派熱潮的反思,因而碑帖融合論的觀念才真正形成。
此外,民國時(shí)期漢晉簡牘墨跡的出土,使得此時(shí)書寫的參照系也發(fā)生了變化,即以墨跡證碑、以墨跡證帖,這已經(jīng)超出了“碑學(xué)”“帖學(xué)”的范疇,不論在狹義上還是在廣義上[19]。關(guān)于此點(diǎn),民國時(shí)期的陳康在“碑帖并重”的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提出:
學(xué)者求名家墨跡不可得,與其囿帖學(xué)而變質(zhì)品,不如取碑之真……在初學(xué)者入門時(shí),得帖學(xué)之結(jié)體法度,及其氣韻后,即宜取魏晉六朝人碑為主。習(xí)練經(jīng)年,得其骨髓,退可以去薄俗,進(jìn)可以追蹤秦漢,造石鼓、鐘鼎、甲骨之極,則書未有不成的。[9]218
陳氏言帖學(xué)得其“氣韻”,而碑學(xué)得其“骨髓”,得其“極”,其不僅肯定帖學(xué)地位,且上追秦漢書跡,擴(kuò)大了康氏《廣藝舟雙楫》中“碑學(xué)”的外延,這正是民國時(shí)期對康氏早期書學(xué)觀的發(fā)展。
三、結(jié)語
由以上考察可以看出這樣幾點(diǎn):(一)民國時(shí)期碑帖融合的觀念指以六朝碑為根本,以碑融帖、納碑入帖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與觀念;(二)晚清時(shí)期碑學(xué)運(yùn)動(dòng)由“篆分遺意”向“六朝碑版”的筆法轉(zhuǎn)換——即碑派楷、行筆法的建立后,民國時(shí)期碑帖融合的觀念以碑(六朝碑刻)、帖為根基,上溯商周秦漢“篆隸筆意”的書學(xué)觀念亦普遍受到重視,并逐漸形成書法創(chuàng)作所追求的一種風(fēng)潮;(三)碑學(xué)的取法范圍愈加廣泛,漢魏六朝碑石以外,瓦當(dāng)、石鼓、鐘鼎、甲骨皆可師法,此時(shí)碑學(xué)所指已成為廣義上的含義。
上述為晚清與民國時(shí)期碑帖融合的不同之處,可以說晚清書學(xué)背景下碑學(xué)的探索是基于對碑派筆法的研究與構(gòu)建,故碑帖融合尚未形成風(fēng)格與潮流,而在碑學(xué)熱潮過后的民國時(shí)期則表現(xiàn)為對一種書學(xué)風(fēng)格的追求,尤其在20世紀(jì)二三十年代被書壇接受后。這也形成了民國時(shí)期書法以“尚勢求變”為主要特征,以陽剛威猛之氣為主導(dǎo)的時(shí)代書風(fēng)。實(shí)際上,從晚清到民國時(shí)期,在書學(xué)觀念與書法創(chuàng)作追求上,都暗含了一條隱藏的線索,那就是康有為提出的“雜沓筆端”“體在某某之間”[20]等,即追求不同書體之間的陶鑄,從而達(dá)到“新理異態(tài)”。只是到了民國時(shí)期由書學(xué)觀念到書法實(shí)踐,在追求“篆分遺意”以及“碑學(xué)”的理路上不斷拓展,從而在書學(xué)理想上真正打破碑、帖的壁壘,融合碑帖,形成一代書風(fēng)。
注釋:
①葉培貴.“碑學(xué)”、“帖學(xué)”獻(xiàn)疑[J].書法研究,2000(6):34-42.此文構(gòu)建的書法史寫作框架是在沙孟海分類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調(diào)整。
②轉(zhuǎn)引自:楊代欣,侯忠明.劉咸炘的書學(xué)理論[J].文史雜志,2008(6):。康氏此語亦見于劉海粟《讀鄭道昭碑刻五記》,為康氏言于劉海粟的話,見:齊魯談藝錄[M].濟(jì)南:山東美術(shù)出版社,1985:13.
③如陳振濂在《現(xiàn)代中國書法史》中《北碑派的末流》一章,對此即頗有微詞。
參考文獻(xiàn):
[1]康有為.廣藝舟雙楫[C]//上海書畫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xué)古籍整理研究室,選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754-755.
[2]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xué)[C]//二十世紀(jì)書法研究叢書:歷史文脈篇.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3]劉恒.中國書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4.
[4]叢文俊.書法史鑒[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180.
[5]崔爾平.廣藝舟雙楫注[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130.
[6]黃惇.漢碑與清代前碑派[M]//風(fēng)來堂集——黃惇書學(xué)文選.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0.
[7]張小莊.趙之謙研究[M].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8:188.
[8]孫洵.民國書法史[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49.
[9]陳康.書學(xué)概論[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0.
[10]金丹.包世臣書學(xué)批評[D].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7.
[11]黃惇.當(dāng)代中國書壇格局的形成與由來[M].風(fēng)來堂集——黃惇書學(xué)文選.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9.
[12]徐利明.“篆隸筆意”與四百年書法流變考論[J].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2000(4):32-36.
[13]沃興華.插圖本中國書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4]戴家妙.沈曾植的書法藝術(shù)[J].書法,2006(9):39-44.
[15]馬宗霍.書林藻鑒·書林記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44.
[16]王蘧常.憶沈寐叟師[J].書法,1985(2):18-20.
[17]李瑞清.清道人論書嘉言錄[C]//明清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1094.
[18]白蕉.白蕉論藝》[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
[19]肖文飛.開古今書法未有之奇境——沈曾植書法評述[J].東方藝術(shù),2009(8):10-55.
[20]周勛君.碑學(xué):涵義的生成[C]//全國第九屆書學(xué)討論會(huì)論文集.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12:314-315.
作者簡介:劉光喜,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藝術(shù)學(xué)博士,天津師范大學(xué)美術(shù)與設(shè)計(jì)學(xué)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