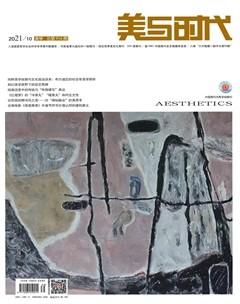淺析西西小說《我的喬治亞》的敘事藝術
摘? 要:西西是香港非常重要的作家,然而其作品在大陸并未受到足夠重視,尤其是近期以手工玩具為話題的小說更是因為“玩物喪志”而被人們忽視。西西該類作品自有其獨特的敘事風格,在《我的喬治亞》中,其敘事藝術主要表現為:敘事資源上的拼貼敘事與百科全書式寫作;敘事語言上的親切幽默;敘事策略上注重文學與手工建筑結合的跨媒介敘事。
關鍵詞:西西;我的喬治亞;敘事藝術;拼貼;跨媒介敘事
西西原名張彥,1938年生于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西西是香港非常重要的作家,數十年筆耕不綴,出版各種體裁的作品30余部。83歲高齡的她于今年年初出版了最新的歷史小說作品《欽天監》。西西的作品曾榮獲“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世界華文文學獎”“第六屆紐曼華語文學獎(詩歌獎)”等獎項。從桃李年華到耄耋之年,西西始終對世界保持好奇之心,她沉醉于文學藝術之美,也對社會中的邊緣人、亟待保護的野生動物懷抱仁慈之心。積極的心態與堅定的意志讓她在與乳腺癌的斗爭中取得了勝利,然而疾病的后遺癥也使得西西的右手逐漸喪失活動能力。為了手部康復,西西開始接觸手工制作,近年來也陸續出版了以此為題的作品:《我的喬治亞》(2008年)、《縫熊志》(2009年)、《猿猴志》(2011年)、《我的玩具》(2019年)。西西的作品在大陸一直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少量研究也主要基于其早期作品如《我城》、《飛氈》等,討論其香港本土意識及童話小說風格[1]。其近期以手工玩具為話題的系列作品并未受到關注,原因或許是連西西本人都在自嘲的“玩物喪志”。本文作者認為,西西該類作品自有其獨特的敘事風格,并以《我的喬治亞》為例,討論其中的敘事藝術。
一、敘事資源:拼貼敘事與百科全書式寫作
在諸多英式建筑中,西西偏愛喬治亞(Georigian)時期的建筑,并鐘情于“喬治亞”而非“喬治”的譯法,因此“我的喬治亞”指的就是西西喬治亞風格的木質娃娃屋。如何以娃娃屋為題寫出一本小說,西西為讀者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在《我的喬治亞》中,我們可以閱讀到四個既獨立又相互關聯的內容:喬屋裝修筆記、娃娃屋欣賞指南、十八世紀英國博覽、喬屋里的故事。全書沒有小標題,只以數字記錄共有71個小節,作者也并非按照順序講述四個話題,而是選擇穿插敘述。小說是以現實世界中購買娃娃屋的由來開始講起,接著講對包含地庫、二層主體和閣樓的娃娃屋展開裝修工作。大到房間如何分配、家具風格的選擇、天花板墻壁以及地板的鋪設,小到一塊桌布的選擇、墻角線該如何切割和粘貼,西西事無巨細地與我們分享她的裝修心得。西西有時也會停下給喬屋貼墻紙的辛苦工作,帶我們去瀏覽經典的娃娃屋,足跡遍布全球各地:荷蘭、瑞士、德國、英國、美國、臺灣地區。此外,西西也同我們講述她在娃娃屋月刊中看到的有趣爭議;與我們分享她在香港娃娃屋專門店遇到娃娃屋同好者的喜悅心情。而喬屋的故事更是由始至終陪伴我們的閱讀,我們從對喬屋主人的一無所知,漸漸了解他們的故事,最終和喬先生、喬太太、湯姆少爺、女仆瑪麗安以及前來做客的愛德華叔叔成為朋友。此外,西西拼貼了18世紀英國的方方面面:文學、藝術、歷史、建筑、社會風貌與制度等等。西西談到18世紀中英兩國的交集,講馬戛爾尼訪華雖然表面無功而返,然而同行畫家卻有機會了解中國下層人民的生活,并由其作品《賣煙桿的小販》聯想到英國人對中國人上下煙不離手的想象,鴉片戰爭似乎就有了理由,而我城(香港)也因此而來。西西也討論工業革命的前因后果,啟蒙運動與女性主義的覺醒、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何謂平等與緘默的自由都在西西的敘述范圍之內。作者還十分關注18世紀的英國的風俗與制度:她帶我們了解男孩學知識女孩學技藝的教育制度、離婚的高額代價與只能賣妻不能賣夫的不平等制度、長子繼承制與庶子的選擇、落后的醫療衛生條件與嬰兒的高夭折率等。此外,18世紀的流行服飾、暢銷小說、印刷術的流行、門窗稅的繳納、手工剪影的制作以及晚餐菜單如何配置等也都一一呈現。
“每個人都是經歷、信息、知識和幻想的一種組合,都是一本百科辭典,一個圖書館,一份物品清單,一本包括了各種風格的集錦。在他的一生中這一切都在不停地相互混合,再按各種可能的方式重新組合。”在卡爾維諾看來,20世紀偉大小說表現的思想是“開放型的百科全書”。而西西的寫作呈現出的正是這樣一種風格,《我的喬治亞》將各類知識、信息、經歷拼貼在一起,形成一部關于娃娃屋和18世紀英國的百科全書。
除了內容的拼貼,西西在排版方式上也在使用拼貼手法。小說中共有四種格式:宋體、—仿宋、○仿宋、仿宋。其中前兩種格式篇幅更大:宋體部分是西西以作者身份為我們介紹娃娃屋和18世紀英國的相關知識;—仿宋部分是對話或獨白,包括:喬治家人彼此間的對話、作者西西與屋中人對話、其它玩偶誤入娃娃屋中發生的對話、以及湯姆少爺的獨白。后兩種篇幅較小:○仿宋我將其解讀為西西與自己的對話,是表達自己的觀點。仿宋格式也是喬屋里的故事,內容為女仆瑪利亞寫給好友黛西的信。
西西的拼貼也并不是知識的簡單羅列,她將知識融入喬屋日常瑣碎之中,并用復現的方法讓讀者更容易理解和記憶。例如30小節介紹了喬治亞房子的仆人,西西提到最重要的仆人是廚師,且不管是否已婚,人人尊稱她“太太”;而在接下來36小節的喬屋對話中,我們看到喬太太與廚師商量晚餐時,便以布朗太太相稱[2]。又如11小節西西與喬太太商量室內墻飾,提議掛剪影,喬太太同意并且說自己學習過;而后15小節西西又介紹說剪影是18世紀最喜歡的玩意,少女必學:讓年輕男友坐在隔著玻璃的燈光下,替他剪影,以增進感情。
二、敘事語言:親切幽默、與讀者做朋友
西西的寫作充滿細節,且保持與讀者的互動。她為我們設置一些懸念,只有細心閱讀才能發現謎底。西西不會直言對話人身份,有時需要讀者自己去推測。例如書中44小節突然出現未知身份的湯瑪士與百麗菲的對話,他們討論了人和人偶的話題,讀者會對這兩人充滿好奇,于是繼續閱讀嘗試從后文中尋找線索,解答謎題。第57小節,百麗菲再次登臺,這次與他對話的是湯姆,我們會發現西西的細心,當兩人初次聊天時,百麗菲稱他“湯瑪士”,而兩人熟悉后,百麗菲直呼昵稱“湯姆”;直到58小節,謎底終于揭開,原來百麗菲是西西暫時寄居在喬屋中的時尚娃娃。
西西自己更偏向于喜劇的寫法。“當悲劇太多,而且都這樣寫,我就想寫的快樂些,即使人們會以為我只是寫嘻嘻哈哈俏皮的東西。”[3]她在《我的喬治亞》中也保持著這樣的寫作風格,她為喬屋虛構出生活幸福的一家人。西西充滿童心和想象力,原本誤入喬治亞房子的時尚娃娃百麗菲與湯姆少爺有了短暫的相處,產生了友情,但百麗菲很快就要搬到對面自己的房子里不能聊天了,湯姆少爺舍不得他的新伙伴,百麗菲安慰他:“我列印了一份資料留給你。我們今天不是都穿上了水手裝么?我們就扮水手吧。資料上面有旗語的圖文,你學會它,我們不是可以用旗語交談么?”
西西也善于自我解嘲揶揄,西西在自制屋頂磚紋紙時畫的歪歪斜斜,一格長一格短,于是對喬先生說,手工藝就該是不完美的。
對么,喬先生,人可不是機器。
對,我們通常不會質疑設計者。只是,如果你再認真一點,我們會更加感激。
以及西西自嘲總也無法竣工的娃娃屋裝修工程:
喬屋的裝修和布置完成了嗎?
還沒有。
好像這是裝修匠的傳統,總是沒完沒了,給他兩個星期,他會做出一個月;他告訴你兩個月,結果呢,用上半年。
三、敘事策略:文學與手工建筑結合的跨媒介敘事
西西早年關注繪畫與電影,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她從繪畫和電影中獲取靈感,并寫成圖文互涉文體和蒙太奇文體的作品。80年代以后,西西也開始她的音樂研究,并將音樂曲式結構手法運用于小說寫作實驗中,并形成了蟬聯想象曲式的文體風格[4]。近年來,西西更是擴大了她的寫作范疇,在作品《縫熊志》和《猿猴志》中,她將文學和手工縫制聯接起來,開創出新的文體——縫制體[5]。而在《我的喬治亞》中,西西則是將手工建筑空間元素也囊括于文學創作之中,形成獨具特色手工建筑文體風格。
西西認為娃娃屋很像多場景的舞臺,例如北京故宮的古典戲臺就有三層,分別是人間、天國、地獄,而娃娃屋的不同房間也可以同時上演各自的故事:喬先生在書房讀書、喬太太在沙龍和女伴聊天喝下午茶、湯姆少爺在閣樓思考和幻想、女仆瑪麗安在房間里給好友寫信分享生活等等。站在喬屋之外,西西關心生活在喬屋中的一家人和18世紀英國社會的方方面面;而身處喬屋之內的湯姆少爺,則以他的視角觀察西西的房間和21世紀的世界,他從“四方盒子(電視/電腦)”里面看到多災多難的未來世界、足球比賽、動物世界、香港時政新聞等。娃娃屋建造的過程既是西西為讀者還原英國18世紀社會風貌的過程,也是她文學創作的過程。她將對喬屋中每一個細節的推敲也融入寫作之中:廚房里是否要放置捕蠅布以體現當時衛生條件的落后;房間涂成什么顏色比較符合喬治亞風格的建筑;喬屋里可以搭配哪些當時流行的中國風元素,等等。隨著喬屋的完工,原本模糊的18世紀英國也變得清晰生動起來。
四、結語
《我的喬治亞》作為少數以手工玩具為話題的文學作品,內容豐富有趣,蘊含著獨特的敘事藝術。西西將各類知識、信息、經歷拼貼在一起,呈現出一部關于娃娃屋和18世紀英國的百科全書。她的寫作充滿細節,親切幽默富有想象力,并努力與讀者做朋友。此外,西西也嘗試將文學創作與手工建筑結合進行跨媒介敘事,形成新的文體風格。作品也不乏理性思考,西西借書中人物對話對18世紀英國殖民史進行反思的同時,也表達了她對美好住所、良好社會制度的向往與追求。
參考文獻:
[1]張宇.日常化的先鋒與世界化的本土——學術史視野下的西西小說新論[J].東吳學術,2020:109-117.
[2]西西.我的喬治亞[M].南京:譯林出版社,2020.
[3]西西.時間的話題[M].臺北:洪范書店,1995:158.
[4]凌逾.蟬聯想像曲式——西西小說的文體實驗[J].華文文學,2007:32-39.
[5]凌逾.創設“縫制體”跨媒介敘事:文學與手工符號的聯姻[J].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6):2-8.
作者簡介:張曉倩,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