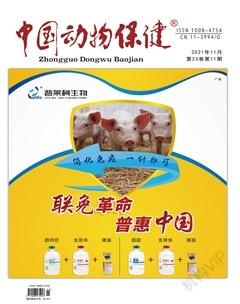畜間包蟲病的防治
doi:10.3969/j.issn.1008-4754.2021.11.027
摘要:畜間包蟲病為人畜共患的寄生蟲病,多發生在哺乳動物小腸、肝臟中,主要由細粒棘球絳蟲和多房棘球絳蟲感染引起。許多研究將前者稱為包蟲病(hydatid disease)。在歐洲、北美以及動物醫療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中,都存在畜間包蟲病,易被忽視,新藥和有效治療方法的開發進展緩慢。畜間包蟲病發生的范圍極廣,其發病率取決于對該病的認識和檢測能力,對社會經濟危害巨大。本文以該寄生蟲病的介紹、診斷和治療、預防三個大的方面進行綜述,以期為該病的控制提供參考。
關鍵詞:畜間包蟲病;診斷;預防
細粒棘球絳蟲(echinococcus granulosus,CE,囊型)的囊體是大小不一的囊,通常很大,充滿透明液體,歷史上被認為是退化的腺體,囊中液體是積累的血清或黏液。1685年俄國科學家Philip Jacob Hartmann證實了其生物性,1801年德國科學家Carl Asmund Rudolphi命名為棘球絳蟲(echinococcus)。我國畜間包蟲病感染率驚人,1992年青海畜牧總站檢查發現綿羊感染率為53.72%,牦牛感染率為54.43%,該數據與1980年基本相同。據研究,羊和牛感染包蟲病后平均產肉量分別減少1.15和7.21kg,經濟損失嚴重。有研究對2013—2016年青海甘南牧區牦牛和藏羊屠宰場進行檢疫,發現該地區內牦牛和藏羊的包蟲感染率分別達14.19%和12.32%,牦牛的感染率稍高,作者推測是因為牦牛的飼養周期更長[1]。
1 包蟲病的介紹
引起畜間包蟲病的寄生蟲在生命周期中存在雙宿主,一般會感染兩種哺乳動物[1]。其中,最終宿主是寄生蟲進行繁殖的宿主,一般為食肉動物或雜食動物。最終宿主的小腸中藏有絳蟲,寄生蟲經2~3個月后成熟,釋放蟲卵,隨糞便排出體外,完成生命周期。寄生蟲生長發育但尚未性成熟階段主要發生在中間宿主體內,一般是食草動物或雜食動物因攝入蟲卵而被感染。人類作為絳蟲的最終宿主或中間宿主,感染后出現嚴重的臨床癥狀甚至是死亡。
CE的最終宿主包括野狗、狼、豺等犬科動物,中間宿主包括綿羊、山羊、牛、豬、馬等。利用線粒體DNA序列對CE已鑒定出10種不同的遺傳類型,綿羊品系(G1)最具世界性。相比于CE,多房棘球絳蟲(echinococcus multilocularis,AE,泡型)的流行病學更加復雜,主要以狐貍、郊狼、寵物狗等為最終宿主,以嚙齒動物為中間宿主。為降低寵物主人的潛在感染風險,應當在流行地區對可能捕獲嚙齒動物的狗和貓進行定期吡喹酮治療。不同于CE在全世界都有著較高的流行率,AE在歐洲和北美地區的報道較少,但在中國流行率較高,已有8個省、自治區發現,但尚不清楚是因為疫區擴大還是剛被發現。引起畜間包蟲病的寄生蟲除CE和AE外,如今非洲棘球絳蟲(echinococcus vogeli,PE)和少棘球絳蟲(echinococcus oligarthrus,UE)也有報道[2],共有16種棘球絳蟲被報道,其中能夠感染人體的有6種,包括CE、AE、PE和UE。PE的最終宿主為大型寵物犬,中間宿主為豚鼠等。UE的最終宿主為夜貓,中間宿主為豚鼠和負鼠。
2 畜間包蟲病的診斷和治療
除了剖檢和對死后動物腸道內容物菌株提取檢測外,通過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檢測糞便樣品中的棘球絳蟲特異性抗原的方法是常被使用的檢測方法。高靈敏度和高特異性DNA檢測,可以鑒定棘球絳蟲的種類和菌株。對于中間宿主難以診斷,除DNA檢測外,對特定抗體的血清學檢測技術發展較快。超聲、核磁共振、斷層掃描是被廣泛使用的成像技術,可以直接確定囊腫的數量、部位、大小,并能推測其生長和轉移活力。
畜間包蟲病的治療,對于人類感染而言,最早對囊腫用套管穿刺,用注射器抽吸液體,并將碘酊、硫酸銅、硼酸、水楊酸、1%甲醛等注射到穿刺的囊腫中。穿刺技術經過發展,現在的新型穿刺技術(PAIR)包括以下步驟:超聲引導穿刺囊腫;抽吸大部分囊腫液;注射殺寄生蟲溶液(20%氯化鈉溶液或95%乙醇),注射量大約相當于抽吸囊腫液的1/3;注射乙醇5min后重新抽吸,注射氯化鈉則至少15min后抽吸[3]。
外科手術是解決急性病的特殊手段,手術可能引起并發癥如繼發感染、急性過敏反應和復發等,以及其對于醫生操作的要求,使得手術使用率有限。
藥物使用一般為苯并咪唑類藥物,大量的臨床試驗表明,長期口服阿苯達唑、芬苯達唑、氟苯達唑和甲苯達唑等苯并咪唑類藥物能夠顯著抑制AE的增殖和在體內的轉移,破壞寄生蟲結構,但藥物經復雜的藥代動力學通常無法達到殺死寄生蟲的目的。阿苯達唑(10~15mg/kg·bw·d)和甲苯達唑(40~50mg/kg·bw·d)對于CE的抑制效果也很顯著。已有其他藥物被測試,但迄今為止還沒有開發出優于苯并咪唑類藥物的新藥用于包蟲病的治療。使用吡喹酮能夠有效控制狗體內的CE和狗、狐貍體內的AE。氫溴酸檳榔堿、鹽酸布那脒、氯硝柳胺和硝基水楊酸鹽等驅蟲藥也能減緩一部分棘球絳蟲感染的負擔。吡喹酮和阿苯達唑聯用相比于阿苯達唑單獨使用也有著更好的療效。硝唑尼特和阿苯達唑聯用對于AE的殺蟲效果明顯。對于人類感染的藥物治療也應輔助補充去甲腎上腺素。
3 畜間包蟲病的預防
從野生動物宿主中消除畜間包蟲病并不現實,從實際出發,預防相比于診斷和治療更有意義。冰島、新西蘭、塞浦路斯等國家成功的控制經驗,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有計劃地使用吡喹酮,使人、狗、牲畜的感染率均下降。蘇聯解體后所引發的巨大社會變革使新建立的中亞國家(如哈薩克斯坦)畜間包蟲病發病率持續升高,對比可知針對棘球絳蟲的控制活動是長期的行動,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財政資源。中國最早于2006年在四川省開始實施控制方案,隨后擴大到7個省、自治區(四川、新疆、內蒙古、甘肅、青海、寧夏和西藏),四川省糞抗原陽性犬的比例從18%下降到15.9%[4]。我國所進行的“健康中國2030”、“一帶一路”等舉措,以及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進一步合作,對于這一疾病的研究和疫苗開發是一個巨大的機遇。2016年10月發布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計劃到2030年畜間包蟲病在縣級得到控制。而且中國所面臨的情況也更為復雜,一方面是國內基層獸醫部門對于畜間包蟲病的重視程度不足,檢測能力不夠,另一方面是國內巨大的動物源性食品缺口意味著每年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而這加速了畜間包蟲病的傳播。重組疫苗(EG95)的開發帶來了新的預防思路,在澳大利亞和阿根廷進行的EG95試驗中,86%的接種綿羊在接種1年后檢查時沒有發現活的包蟲囊腫,且因為疫苗的接種使囊腫的數量減少了99.3%[5]。
參考文獻:
[1] 何文,周貴同,楊耀.畜間棘球蚴病(包蟲病)感染情況調查及防治探討[J].畜牧獸醫雜志,2017,36(6):97-99.
[2] 王圓圓,李寧,李恩元,等.河北省承德市接壩地區畜間包蟲病感染風險因素研究[J].中國動物檢疫,2019,36(1):35-37.
[3] 馬站,瑪依拉·艾尼瓦,羅毅.關于畜間包蟲病綜合防治分析[J].獸醫導刊,2019(10):133.
[4] 袁東波,郝力力,周明忠,等.四川省"十三五"期間畜間包蟲病防治回顧與思考[J].中國動物保健,2020,22(11):1-2.
[5] 周拉.畜間包蟲病防制工作措施[J].中國畜禽種業,2019,15(8):76.
作者簡介:安曉紅(1977.1— ),女,內蒙古察哈爾右翼前旗人,本科,獸醫師,主要從事動物疫病防控,檢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