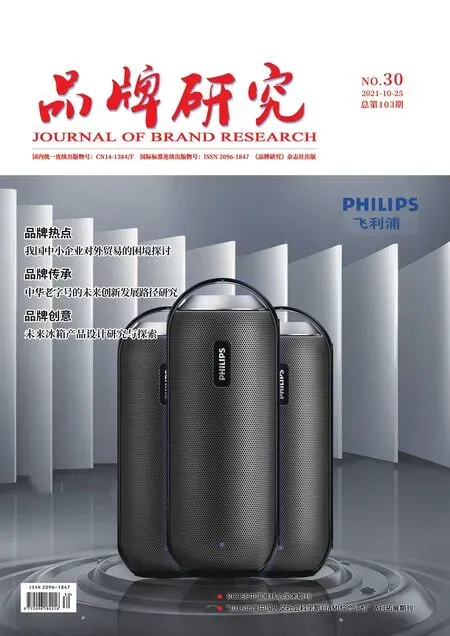專屬經濟區與公海的同異及專屬經濟區的剩余權利
文/劉新月(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
一、專屬經濟區制度與公海制度的同異對比
1972年肯尼亞提出專屬經濟區這個法律概念,之后在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肯定和國際法的確認,最終體現在《公約》的法律條款之中。1982年《公約》規定,專屬經濟區的劃分為鄰接領海的區域,從測量領海基線算起200海里范圍內。專屬經濟區是現代海洋法發展中的一個新生法律概念,其法律屬性也不同于領海和公海,而是一個特殊的法律區域,一個擁有獨立法律地位的區域。《公約》第55-75條對專屬經濟區內的權利、義務、資源開發利用、管轄權等做了詳細的規定,為沿海國利用專屬經濟區開發自然資源、生物資源管理以及為其他國家的在專屬經濟區內的合法活動,提供了法律保障。
公海在國際法上指各國內水、領海、群島水域和專屬經濟區以外不受任何國家主權管轄和支配的海洋部分。依據1958年《公海公約》,公海是不包括國家領海或內水的全部海域。但隨著海洋技術的進步和人類對海洋資源開發的進展,沿海國管轄權擴大,產生了專屬經濟區和群島水域等新概念和制度,縮小了公海的面積。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公海是不包括在國家的專屬經濟區、領海或內水或群島國的群島水域以內的全部海域。公海供所有國家平等地共同使用,它不是任何國家領土的組成部分,因而不處于任何國家的主權之下;任何國家不得將公海的任何部分據為己有,不得對公海本身行使管轄權。
專屬經濟區制度與公海制度主要相同之處在于:首先,兩者均是由《公約》以法律條文形式確立下來的法律制度,各自擁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屬性,對締約國有約束力。其次,沒有國家對專屬經濟區和公海存在主權,不屬于任何國家的領土范圍之內,相較于領海制度,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公共屬性。此外,在專屬經濟區和公海內,不同程度上均可以實現航行、飛越,船舶、飛機可以通航,可以鋪設海底電纜、管道;可以實現捕魚自由,可以建設人工島嶼等設施,可以進行科學研究以及都必須遵守保護海洋環境、海洋生物資源的法律義務。最后,專屬經濟區和公海都是人類可以進各種經濟、政治、軍事活動的區域,但各國在專屬經濟區和公海內的各種活動,都應遵守《公約》的宗旨,一切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
專屬經濟區制度與公海制度的主要不同之處在于:首先,兩者的地理范圍不同,專屬經濟區是鄰接領海的區域,是從測量領海基線算起的200海里范圍內的海域。而公海是不包括在國家的專屬經濟區、領海或內水或群島國的群島水域以內的全部海域。從范圍上看,公海遠遠大于專屬經濟區的。
其次,兩者最大的區別在于沿海國對專屬經濟區擁有專屬的主權權利、管轄權和義務,而公海的權利主體是所有國家,但同時也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宣稱對公海的主權。沿海國的專屬經濟區是一項綜合性的專屬權利,沿海國可以針對不超過200海里范圍內的資源利用和海域管轄行使《公約》所賦予的各項權利,其它沿海國家或內陸國家在非與沿海國協商一致情況下,不得違反《公約》的有關規定開發利用他國的沿海資源,這一區域的特殊法律地位顯然有別于傳統的公海自由權,對專屬經濟區內的資源開發利用做出了限制性的規定,沿海國經濟利益從法律層面獲得了保障。另外,專屬經濟區中涉及的主要是經濟開發和生物資源保護這兩大方面,而公海則除了經濟活動外,還涉及了大量的政治、軍事、人道主義方面的規定,例如打擊海盜、救助義務等。
二、專屬經濟區的剩余權利
剩余權利是歷史的產物,隨著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海洋資源逐漸成為各個國家追逐的對象,沿海國管轄權與公海自由之間矛盾不斷激化,發展中國家與海洋強國之間矛盾也不斷升級。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召開的1970年代,一批國家獲得獨立,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必然伴隨著對海洋資源的謀求,而打破了海洋大國對海洋資源的壟斷局面。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會議歷時九年,從1973年到1982年,期間召開了11期15次會議,經過反復磋商交涉,于1982年最終完成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次會議參加國家多、規模大、時間久,幾乎涵蓋了大部分的海洋國家,這也意味著《公約》是多方利益角逐的產物,必然存在不完善的內容,是一份妥協的產物。因此,《公約》中存在著大量言辭含糊的法條,很多敏感問題也沒有明確規定和明令禁止,這就給了剩余權利存在的空間。海洋法中的剩余權利,“是國際法上合法的權利主體(國家或地區),在遵守《公約》的宗旨和原則規定,不違背國際法強行法則以及禁止性法則的前提下,通過法理推定而產生的權利。”①如果更加簡化的理解剩余權利概念,那就是:“法典中有諸多的未以法律條文直接加以規定的權利和法律措辭含糊的權利,即國際海洋法學界稱之為“剩余權利”( Residual Rights)或是“海洋法中的剩余權利”( Residual Rights of UNCLOS)。”①
剩余權利主要集中在領海制度、專屬經濟區制度、大陸架制度、國際海底區域等制度中,其中尤以專屬經濟區中剩余權利居多。但整部公約中的剩余權利不僅局限于此,在公海制度、用于國際航行的海峽制度、海洋科學研究制等制度中都有所體現。
在專屬經濟區制度中集中出現了大部分剩余權利的問題,其中,比較鮮明的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專屬經濟區中的生物資源利用問題
《公約》第62條第1款“沿海國應在不妨害第六十一條的情形下促進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最適度利用的目的。”“最適度利用”,然而公約中并沒有對“最適度利用”給出可以作為衡量的標準或測算方式,于是就給了剩余權利這個問題留下了空間。因為專屬經濟區內的漁業資源一直是沿海國與其他內陸國家相爭之地,“最適度利用”的規定,立場不同的國家一定會得出不同答案。由于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占據主動和優勢的地位,因此沿海國可以依據《公約》對其他國家或內陸國在其專屬經濟區內的海洋生物資源開發和利用進行限制,然而這樣缺乏明確規定的條文,必然會引起幾個鄰國之間的糾紛。
第61條第2款“沿海國應決定其捕撈專屬經濟區內生物資源的能力。沿海國在沒有能力捕撈全部可捕量的情形下,應通過協定或其他安排,并根據第4款所指的條款條件、法律和規章準許其他國家捕撈可捕量的剩余部分,特別顧及第六十九和第七十條的規定,尤其是關于其中所提到的發展中國家的部分。”而這一條款則會引起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關于專屬經濟區內剩余捕撈量的爭議。“最適度利用”仍然成為牽絆這一問題的關鍵。由于世界各個區域的漁業資源、漁業需求都是不平衡的,那么如何測算出恰當的捕撈量,進而去確定捕撈量的剩余部分,也成為了相關國際機構需要回應的問題。
(二)專屬經濟區中的軍事活動問題
《公約》第五部分沒有將軍事相關問題以明確法律條文的形式加以規定,但是,專屬經濟區內的軍事安全會切實影響到沿海國的國家安全。專屬經濟區中的軍事問題主要涉及到就是航行自由、飛越自由和軍事演習問題。
《公約》第58條第1款“在沿海國所屬的專屬經濟區管轄范圍之內,不對沿海國和內陸國的法律地位做出區分,其在《公約》的宗旨和規定的限定之下,均享有同等的國際法上的權利,這些權利包括航行、鋪設海底電纜以及與次有用途上相類似的行為均是在《公約》允許的范圍之列的。”《公約》第58條的規定讓非沿海國家也擁有在經濟層面的自由通行的權利。然而在軍事層面上,不同國家根據第58條第1款做出了不同的選擇。第59條第1款,在專屬經濟區中,有關《公約》第87條的自由權利的享有問題上,對沿海國或非沿海國均未作出必要的劃分。雖然《公約》給予了非沿海國通過專屬經濟區的權利,但是,這些國家也有需要適當顧及沿海國權益的義務。問題在于《公約》給出了相對明確的權利,卻沒有給出權力行使的界限,其他國家“適當顧及”的義務應該遵循何種標準或程序,是否需要告知沿海國、是否需要告知并得到沿海國同意,還是不需要告知沿海國,這些剩余權利又留下了談論的空間。軍事船舶、飛行器的活動是否可以被定義成以和平目的而進行的活動,也是值得商榷的問題。
此外,軍事演習也成為近年來爭議的熱點問題。首先,沿海國對專屬經濟區擁有管轄權,而在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的軍事演習活動會給沿海國帶來影響。但是一些發達國家認為,公海自由權在專屬經濟區中不應當受到限制,只要其軍事演習沒有侵犯其他國家的主權,那么,軍事演習就是合乎國際法規定。然而,沿海國為了維護其專屬經濟區內的自然資源和出于國家安全考量,都不可能任其演習,畢竟任何軍事演習都不能給沿海國造成不利于國家安全的影響,也不能給沿海國帶來經濟和環境上的損失。
(三)專屬經濟區中的海洋科學研究
海洋科學研究的具體法律內涵應該指向哪些方面,《公約》并沒有明確規定,這就出現了海洋科學研究的剩余權利問題。《公約》第246條第2款規定“其他國家在征得沿海國許可后,可以在專屬經濟區范圍內從事有關科研活動。”由此,我們可以明確看出,《公約》在將專屬經濟區內的海洋科研權利管轄權交給沿海國的同時,又給了發達國家以解釋“海洋科學研究”的余地。《公約》中“公海應只用于和平目的”的規定,其目的是為了建立新的海洋法律秩序,進而建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②對于出自于“和平目的”有利于全人類的海洋研究行為,其他國家也擁有在專屬經濟區探測研究的權利。然而,沿海國擁有的管轄權,可以讓沿海國在審查他國提交的計劃時給出拒絕的答案。這樣的制度,平衡了沿海國與其他國家在專屬經濟區內的科研權利。
(四)防治海洋污染
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擁有保護海洋環境的管轄權。由于他國在沿海國專屬經濟區內的航行自由很有可能會污染海洋,例如船舶行駛排污、海運事故、傾倒性污染等都會導致沿海國的海洋資源受影響。《公約》對于沿海國保護環境的管轄權的行使作了相應規定,強調了沿海國有權制定相關規則,在此水域活動其他國家應當遵守;另一方面,又規定了沿海國對海洋環境保護的立法權和管轄權限于“可通用的國際規則和標準并使其有效的該國的法律和規章”。因此,對于專屬經濟區內與防治污染相關的剩余權利,沿海國一方面擁有對其專屬經濟區的防治污染、保護海洋環境的管轄權,另一方面,沿海國的這種權利也受到一定的制約,同時不影響其他國家針對同一對象的管轄權,如船旗國也同時享有此類事項的管轄權。1專屬經濟區內與防治污染利用相關的剩余權利包括對船舶行駛排污、海運事故、傾倒性污染的管轄權。對于不同的海洋污染情形,沿海國和船旗國、其他相關國家的管轄權限分享比例有所不同,但整體還是沿海國家占據優勢。
三、總結
專屬經濟區制度與公海制度的異同是在時代發展中逐漸產生的,從1958年《日內瓦海洋公約》到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進步和變革讓世界海洋秩序更加合乎當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但同時由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自身存在的滯后性、妥協性,也使得《公約》在很多問題上仍然沒能擺脫時代的局限性。專屬經濟區制度和公海制度權利未能完全分割清晰的灰色地帶,將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沿海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利益角逐,在兩個區域間的剩余權利問題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本文主要是通過對《公約》法條的閱讀和對比,找出導致剩余權利存在的關鍵模糊措辭,對專屬經濟區與公海的異同、專屬經濟區中的海洋生物資源的利用、軍事活動、海洋科學研究、海洋污染防治等剩余價值問題進行了分析。
注釋
①孫曉哲.海洋法中剩余權利與我國海洋權益維護的研究[D].青島:中國海洋大學,2012.
②中國新聞周刊:《解放軍公海軍演:遇外軍闖入只能驅趕不可開火》,http://mil.news.sina.com.cn/2013-11-07/09037483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