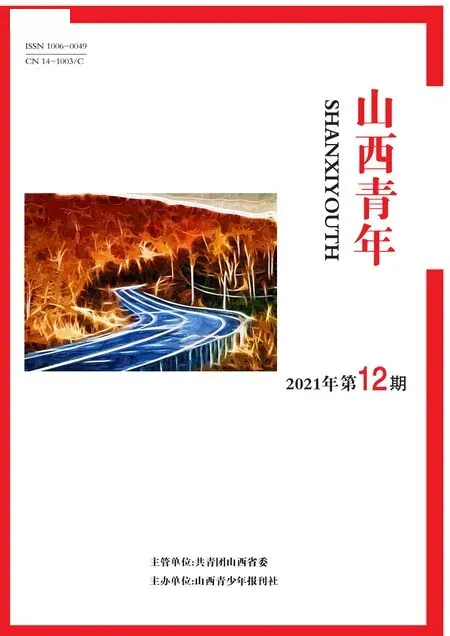再論高中歷史課堂中史料教學問題
王清華
(渤海大學,遼寧 錦州 121013)
何謂史料?李劍鳴曾在《歷史學家的修養與技藝》一書中指出:“凡治史過程中使用的研究性文獻和常識以外的資料,都屬于史料”[1]。那么,史料教學又是什么呢?國內學者一般認為,史料教學是指按照歷史教學的需要,圍繞歷史學習目標和教學任務,引用恰當的歷史材料,并引導學生利用史料得出歷史認識的一種教學方法和教學活動。筆者通過對高中歷史課堂史料教學的再研究,認為在史料教學過程中存在以下幾個新的需要值得注意的問題。
一、對教科書基礎史料的忽視
教科書《中外歷史綱要上》中,每一課都有1-2個“史料閱讀”,此外,“學思之窗”和“探究與拓展”板塊,也都含有豐富的史料。教科書中的史料是經過眾多專家和研究員反復甄別挑選出來的,其質量可以說是相當優良,因此在一課時的授課時間內,教師如果能將這些史料充分挖掘,并以此為基礎,適當補充,那么對學生史料實證素養的培養來說是最優化的方案。但是許多教師在進行史料教學時往往“舍近求遠”,忽略教科書中的史料,而在其他地方尋求史料,使得學生對教科書中的基本史料掌握程度低,對老師所找的課外史料又有所質疑,這就大大降低了史料教學的質量。
比如在《秦統一多民族封建國家的建立》一課,關于“秦統一六國的條件(從人才角度分析)”一知識點的講解中,兩位教師分別采用教科書中所用史料(材料一[2])和課外史料(材料二[3])進行教學:
材料一:“臣聞地廣者栗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而愿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司馬遷《史記· 李斯列傳》
材料二:“秦自孝公以后各代君王,推行人才強國戰略,因國力強盛而逐漸確立了‘席卷天下,包舉宇內’的價值取向。秦王政時,通過廣納賢良來‘并天下’,游士奔秦,蔚然成風。”
——賈霄峰、解梅《論秦人的價值取向與秦國的人才強國戰略》
對比兩則史料,材料一選自《史記》,兼具文學性和史學性,材料二則選自白話文著作,雖然也能說明問題,得出結論,但是相較于材料一,材料二在質量上則相形見絀。新版教科書剛剛應用,其中又增添了許多新的史料,因此,對于新教科書中史料的挖掘和運用是當下歷史老師面臨的一大挑戰。
二、對選取史料的難易程度把握不當
筆者在家鄉當地某所高中進行歷史實習時,曾經觀摩過不同老師的歷史課堂,也在網絡上看過許多高中歷史公開課。結果發現,不論是在線下還是線上的歷史課堂中普遍存在這樣一種情況,歷史教師在進行史料教學時,選取的史料往往是一些簡單的史料,因此運用這些史料進行史料教學時與學生互動非常順暢,表面上這些課都在“形式”上完成了史料教學的任務,同時也讓學生加深了對教科書內容的認識,可謂“一舉兩得”。殊不知,如此形式的史料教學實際上是低效的,這樣的一種低效率的史料教學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史料實證和歷史解釋等方面核心素養的培養。如一位教師在講授東漢末年至三國局勢時,應用《隆中對》中的史料(材料三):
材料三: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隆中對》
高中學生在語文課堂上早已將《隆中對》一文爛熟于心,歷史老師拿來用來進行歷史課堂上的史料教學,對于學生來說實在是太過簡單,用這則史料進行教學不僅不會取得很好的效果,相反會因為二次學習引起學生的厭煩情緒,形成一種無效教學。
史料實證是指對獲取的史料進行辨析,并運用可信的史料努力重現歷史真實的態度與方法[4]。史料具有不可逆的特性,過去發生的事情,即便是相同的事件,也會因為記錄者的主觀想法不同而出現截然相反的解釋。所以,要想說明某個問題,需要我們盡可能多地搜集與此相關的歷史資料,并對搜集到的歷史資料進行整理、研究和辨析,通過從史料中提取有效的歷史信息,這樣才能夠養成歷史教學目標中所期望的實證意識,才能在論述時能將有價值的史料作為論證的依據。
歷史學家傅斯年曾經說過,“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而在許多一線教師的歷史課堂中,筆者分析認為造成選取史料質量過低的根本原因還是教師對史料教學不夠重視,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去尋找、研讀和分析史料。
不同年級的學生認知能力和學習能力不同,同一年級不同班級的學生之間學習能力也有所差異。因此教師在選取史料時,首先要結合學情,“因材施教”,根據所教學生的實際能力來選擇史料,一定要注意選取史料的難易和生僻程度,既不能太簡單,也不能太難,盡量讓學生“跳一跳”,能“夠得著”。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學習是學生主動地以已有經驗為基礎建構內部認知結構的過程”,在這種理論下,學生不是簡單地被動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動建構知識,這種建構是無法由他人來代替的。因此,只有教師通過引導學生把新知識融入他們原有的知識結構中,才能達到一個較好的教學效果。
三、老師參與過多,史料教學有效利用程度降低
英國歷史教育學家湯普森在《理解歷史》一文中曾說:“學習歷史知識不只是為了歷史本身,更應該將焦點集中于我們如何得到正確的歷史認識,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廣泛地搜集史料,篩選真實史料,加以運用和思考。”[5]
自從2001年課程改革以來,就一直倡導“教師主導,學生主體”的教學模式,強調變“要學生學”為“學生要學”,同時要求教師要改變傳統的教學理念,拋棄過去那種“灌輸式”的包辦教學。但綜合這么多年的實際情況來看,許多老師僅是由過去的“一言堂”向“學生為主體”轉換就已經很吃力,而且即便轉換過來的教師,教學風格仍然留有濃厚的傳統教學模式的色彩,“學生為主體”仍然體現在一些簡單的知識的“附和”上。具體到史料教學方面,其情況也同樣讓人感到不容樂觀。
在歷年高考題目和一些真題中,筆者發現,有些題目中的史料只是干擾選項,這就對學生甄別、運用和分析史料的能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如下題:
關于啟的繼位,古書有不同記載。《史記· 夏本紀》寫道:“益(禹晚年培養的接班人)讓帝禹之子啟。”《戰國策· 燕策一》記載:“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其實令啟自取之。”由此可見( )
A 歷史敘述具有主觀性
B 離事件更近的《戰國策》更接近真相
C 歷史真相無法考證
D 作為《正史》的《史記》觀點更可信
這道題目的正確答案是A。在該題目中,《史記》和《戰國策》作為極具價值的史學資料,學生會下意識地從B和D中選擇答案,這樣就直接跳進了出題人設置的陷阱中,其實這道題目中引用《史記》和《戰國策》實際上僅僅起的是例子的作用,假如去掉這兩則史料題目仍然相對完整。
在平時的史料教學中,許多歷史教師在選取史料時,擔心學生史學素養低,往往會提前幫學生把無用史料剔除出去,只選擇和題目或者結論契合的史料,這就使得學生在平時學習中得不到史料甄別和篩選能力的鍛煉。老師“包辦”太多,反而會使得學生形成一種依賴老師的心理,同時也不利于學生獨立思考和鑒別能力的培養。
針對以上幾個問題,筆者認為要解決這幾個問題一線教師需要做好這幾方面的工作。首先,要重視教科書中史料的挖掘、研究和使用,在選取課外史料時,一定要謹慎、謹慎再謹慎,避免以論代史、史論脫節的現象出現。其次,在選擇課外史料時,一定要做到勤找、勤思,要做到要因材施教,避免形式主義教學。與此同時,教師運用史料時還應該考慮到史料類型的多樣化,我們最常用的史料是文字史料,除此之外,還可以適當地添加一些圖片史料,不管是文字史料還是圖片史料,一定要注意史料數量和質量,不僅要保證所選取的史料與所學重點難點的匹配,還要保證所選史料要符合學生的學習能力,避免學生出現厭學行為,得不償失。最后,老師既要避免“包辦式”教學,還避免“灌輸式”教學,在教學過程中要突出“學生是學習的主人”,要把課堂交給學生,通過教師的引導,來激發學生學習歷史的積極性,這樣才能讓學生由被動轉化為主動,才能更好地參與到學習中去,要時刻保持教學的新鮮感,讓學生享受課堂、享受學習的過程。
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說,“史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痕跡,是我們研究歷史的證據”[6],在現代教育理念不斷發展和教學改革的不斷深入的背景下,史料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史料教學的重要性也受到越來越多歷史教學研究者和一線歷史教師的關注,運用史料進行教學,是中學歷史課堂中不可缺少的一環,這種教學方式對學生綜合能力與素質的提升大有裨益。因此,如何能恰如其分地將有價值的史料運用到每一節歷史課堂中,是每一個一線歷史教師和歷史研究者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