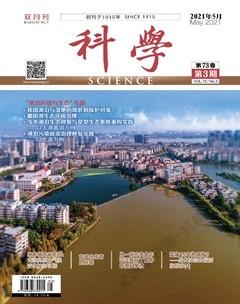面向工程的中醫現代化探索
中醫的思想來源(陰陽五行)、診斷手段(望、聞、問、切)和處置方式(中藥方劑),與西醫病理解剖、生理檢測和藥理治療大相徑庭,背后則是文化傳統與思維方式的差異。中醫著眼整體,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西醫對此其實并不排斥;中醫中觀的辨證關注陰陽、虛實、寒熱、表里的“辯證法”,實際上是從大類區分開始的逐步聚焦過程,思路可以理解,原則較為特殊;中醫因人而異的診治相對而言是微觀手段,西醫則同時注意規范、標準,并試圖認識生命機理。無論中醫還是西醫醫生,要成為專家,離不開工作積累和不斷反思,只是目前中醫治病由于特殊性遠離普遍性,從而缺乏代表性和普適性。
中、西醫不僅救死扶傷、治病救人的目標一致,做法上也不是非此即彼,所以才會有中西醫互補的愿景與實踐,有中醫走向現代化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就現代科技服務醫學而言,筆者研究“體征感知、辨證分型及其推陳出新──心血管病醫方生成”,涉及整體思維(方法論)、便捷操作(脈診模擬)與互補途徑(比如智能系統),是從臨床和用戶需求出發的機器輔助醫療的一系列工程化途徑及其部署與精化。
工程觀念
錢學森提出的現代科學技術體系橫向有11大科學技術部門[1],那是一個開放的知識系統及其完善過程,包括思維科學、人體科學等。每一部門又分為“基礎理論”“技術科學”和“應用技術”,比如,對應于思維科學分別是思維學、模式識別等內容和人工智能等技術。本文所言工程,亦即人體科學中與人工智能技術的對應部分,至少具備如下三個特點。
第一,針對臨床。工程是利用科學理論、技術方法展開的面向用戶需要或實際環境的解決應用問題的活動,就醫學系統而言,一是指問題來自臨床,不管研制儀器設備,還是開發服務軟件,抑或設計分析算法,應當針對由臨床醫生或醫療機構提出的各種需要;二是所有結果是否有效、其優劣程度如何均由臨床測試和用戶反饋得出結論,評價的原則來自實際醫療環境,“閉門造車”滿足不了要求。
第二,統計計算。 針對臨床的計算機系統的效果,需要數量足夠、表征全面、分布合理的實際數據予以支撐。比如,現在普遍應用的機器學習算法要將訓練數據與測試數據集分開以期有針對性,否則結果只是“看上去”不錯;要區分對象內和對象間數據,用同一個對象的數據而非不同對象不同時刻的數據會降低數據的代表性、削弱算法的泛化能力,不能“坐而論道”。
第三,科學基礎。工程化工作所依托的思想、理論、方法不能違背科學結論、不可超越既有限制,都需要符合生物機理和客觀規律。只有根植于基礎研究成果的技術、工程,才能保證其有效性、可靠性和普適性。應該努力避免的是與臨床目標和需求無關聯的所謂研究、一味為了“科研”而進行的數據分析、到頭來經不起實踐驗證的論文等。
新冠疫情期間,各種數據包括關于疫情的數據猛增,所謂的“大數據”涌現了,結合一些分析算法,它們將有助于體征篩查、關系發掘、現狀判斷、趨勢預測,人工智能可在醫學診斷思維的模擬及其在基層的普及應用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那既是人工智能典型的應用場景,又有助于厘清關于中醫的一些基本爭議。林毅夫曾指出[2]:“能否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在于理論背后有多么復雜的邏輯,而在于理論解釋的現象有多么重要。”關于中醫,當下更重要的不是其固有理論的可靠性和背后機理的合理性(希望有朝一日有結論),而在于可否解決當前的一些困惑。
方劑地位
現今的中醫處方是經過一代代人摸索和調整過的,僅知道各種藥材的性質與功用,但不清楚不同藥材搭配的“君、臣、佐、使”關系及整體作用,不清楚各自比例和分量,是出不了處方的。那種認為只要熟讀中醫經典,不必背處方,自然可出處方的觀點是不切實際的。現實生活中不僅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也不是有了理論就有答案,中間是先例、經驗、細節。然而,真要創新,諸如提升已有方劑的治療效果、治療目前束手無策的疾病,或者說要發揮較以往更大的作用,就得突破傳統、回到根本。本文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希望能對疑難雜癥給出治療方劑,或者對常見疾病給出更優方劑。因為中醫的效果主要由方劑體現,歷史告訴我們值得挖掘,甚至就其成分、機理而言可以與西藥思路統一,形成共同基礎。
許倬云先生認為[3]:“中醫若要融入世界,則是藥的部分而不在醫的理論部分……”中醫藥要證明其效用或發揮更大作用,歸根結底看治療效果,那是靠中藥產生的,因此中藥的方劑是關鍵環節,其配方、用量及其各成分的相互作用方面還缺乏很多細節支撐。現在面臨的是經方范圍有限、治療方式宏觀、特病方劑闕如的局面,獲得有依據、有針對性、有良好效果的中藥方劑則可以“綱舉目張”。然而發現新藥需要巨資投入,在關注百姓健康、弘揚傳統文化、智能合成新藥的社會和技術背景下,我們將目標鎖定在傳統中藥方劑的優化和新方劑的發現上。
對癥尋藥
臨床上,醫生根據患者所述形成初步的、大范圍的判斷,然后做一些儀器檢查,根據其強度、相關性和患者特點,得到癥名,辨證分型、分期論治,在四診合參的前提下,形成處理意見和醫方[4]。

其中,隱性知識[5]學習是關鍵,就中醫而言,是指經過長期臨床實踐、對治療某些疾病有特別意義、但又難以言表的那部分經驗知識,有待與臨床醫生不斷交流和精化。我們強調長期的、主動的、不斷超越的、取精用弘的獨特經驗,并不是每一個有數十年相關工作經歷的醫生都能達到的境界。
出處方時棘手的是不確定性:一是醫生需要進行嘗試,比如可能是什么癥、可能要用什么處方與用量,由于每個患者都有其特殊性,需要調整、改寫陳方,那往往是增減一味藥或調整某幾味藥的分量;二是沒有現成醫案,包括用哪味藥和用多少分量,同時要努力避免各味藥材可能不良的相互作用,亦即開出全新的處方。
這里對中醫成功的案例不作進一步推究,而是將其與西醫治好的醫案一樣對待,即暫不考慮副作用、誤診等,因那是醫學的共性問題。我們的策略,不是一開始就直接從數千種藥材出發獲得全新治療方劑,恰恰相反,需要有自如應用經方的醫生,需要其診病經驗。以現在的計算機系統開發為例,多數工作都利用了開源平臺,這固然便捷,效率也高,可以應對一般情況,但遇到“卡脖子”問題就被動。不僅如此,新的問題無法完全依賴現有基礎,再者,要積累核心競爭力也必須“從頭”做起。日、韓在中醫的不少方面走在前列是例子。
研究前景
這項研究工作的意義在于:一是不同疾病需要有針對性的治療藥物;二是對于各種中藥材特性,機器可以“記憶”得更為全面;三是更為全面、系統、科學地討論中醫藥的合理性。
相應的研究脈絡是一開始的體征感知與最后的開方一體化,注重挖掘隱性知識,并以特定慢性病先行,可以“證實”也可“證偽”中醫的某些具體結論[6]。對中醫出方過程進行機器模擬,不意味著默認四診結果皆是“正確”的,而是“可行”的。我們希望更多的患者得到有經驗醫生的診斷,而這類醫生數量有限,于是期待人工智能的幫助,但強調那是“計算機輔助分析”,即人機交互、各有分工,而非將“活”一股腦兒“交”給計算機,機器是助手,是減“負”者,是“團隊”成員,而非獨當一面的“另類”醫生(盡管某些場合未嘗不可)。
我們的探索工作已具備如下基礎:
脈象感知:專門設計的柔性陣列式傳感器與美國產品功能相當;
硬件載體:在商業化腕表基礎上設計具備感知功能的新型號;
體征分析:心電圖分析算法具備顯然的優勢;
特病系統:借鑒國醫大師糖網病診治經驗的原型研究;
經方模塊:方劑的查詢、匹配、顯示策略。
接下來的研究工作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步,以既有特病專家系統原型為基礎,實現出新方功能(不限于已有陳方),需要增加一個數據庫,包含約200種基礎單方;
第二步,刻畫較為完整的診病過程,融合規則推理與機器學習,這是人工智能的關鍵工作,需要與有經驗的中醫專家不斷交流;
第三步,完善數據庫,使之包含《中醫藥大詞典》約6000種單方,測試豐富案例,并針對各種藥材的化學成分等,考慮與西藥庫的接口。
技術的輔助意義與價值是清晰的,而更重要的是中醫的自證。就如一個患者,要想康復,首先自己要積極面對、努力治療,光等著醫生開藥、做手術是不夠的,有時還會適得其反。工程的觀點,也就是實踐的觀點、系統的觀點、驗證的觀點,按照現代科技理念分析的觀點。
[1]顧吉環, 李明, 涂元季. 錢學森文集(卷六). 北京: 國防工業出版社, 2012: 383, 416.
[2]鄭東陽. 林毅夫: 跌宕人生路.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128.
[3]許倬云. 許倬云觀世界. 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8: 171.
[4]秦伯未. 中醫入門.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2006.
[5]董軍.“心跡”的計算——隱性知識的人工智能途徑. 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7: 59~64.
[6]董軍. 辯證中醫. 科學, 2020, 72(4): 39~42.
關鍵詞:中醫 工程 輔助分析 思維模擬 方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