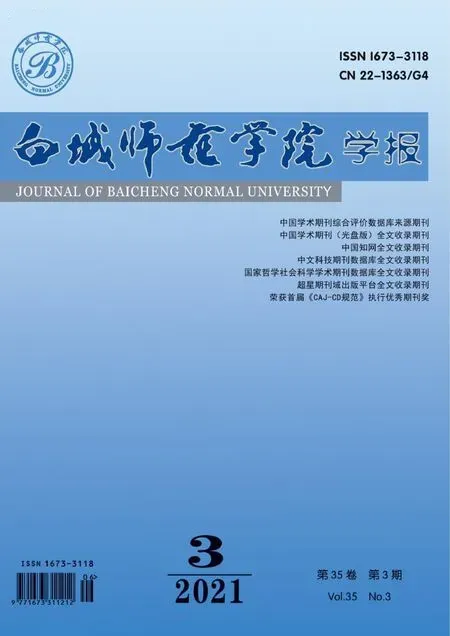乾嘉時期宮廷里的徽州人
徐道彬
(安徽大學 徽學研究中心,合肥 230039)
清代乾嘉時期的徽州,是一個經濟和文化輸出性的社會。它不僅以徽商的“無徽不成鎮”而享譽九州,也因書院眾多和科舉鼎盛而聞名全國。此處山川秀麗,地僻風淳,卻因歷代避亂而入,及其后來衍生出的人口,與有限的山地之間日益膨脹的矛盾,逐步衍化為土地緊張的生存問題。徽州人為了生存,四處經商與科舉仕途便成為擺脫經濟貧困和實現人生價值的重要手段。對于徽州人而言,早年皆走讀四書、中科舉的道路。如果考場失意,仕途不通,那就轉而經商,以求維持家族生計。所以,徽州人都曾是讀書人,即使一生經商,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文化修養也往往優越于其他商幫,“十家之村,不廢誦讀”;“雖為賈者,咸近士風”,故世人多稱之為“賈而好儒”的“儒商”。
徽商得以發展的迅猛時期,也正是徽州科舉極為鼎盛、徽州人才大量輸出的時期。“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書”“同胞翰林”等名號,常為世所艷羨,成為徽州人最為自豪的文壇佳話。這其中,大部分是因家族經商而寓居于外的徽商子弟,他們走出山野,在本土之外的科舉仕途上會獲得更多、走得更遠。檢視《明清進士題名碑錄》,可知徽州人科舉成就的突出,確為世人所公認。這些人日后有仕途順達而為官僚者,有崇尚性靈抒寫而為文人者,有好古敏求的純粹學者,以及厭棄官場、優游林下的方外居士。乾嘉時期活躍在宮廷內的徽州人很多,如武英殿大學士曹振鏞、文淵閣大學士程景伊和戴均元、協辦大學士戴衢亨等。若再縮小范圍,僅從文士學者的角度來觀察,譬如參與纂修《四庫全書》的徽州人中,就有副總裁曹文埴、提調官曹城、協勘總目官汪如藻和程晉芳,纂修官戴震、黃軒和汪如洋,武英殿總閱官汪廷玙和汪永錫、復校官程嘉謨、分校官金榜、洪梧、程昌期、汪昶、汪日章、汪日贊、吳紹浣、吳紹澯、吳紹昱、鄭曦、王照、王友亮、謝登雋、鄭曦、胡士震和吳錫齡等,他們趨從圣意,盡心盡責,終日青燈黃卷,焚膏繼晷,甚至于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這部永垂青史的經典叢書,貢獻出了全部的才智乃至生命,而這一幫“皖派”學者(無論是在館供職,或在館外助校謄錄),因其擅長輯佚古書,善于校勘辨偽,成為總纂官的倚重和館中的核心和主力。戴震、金榜、程瑤田、洪梧、凌廷堪、胡士震等,皆為四庫館中不務聲華、埋頭苦干的中堅力量。此外,在政治和經濟舞臺上的諸多徽州人,他們為朝廷翼贊謀猷,建功立業;或為民眾分憂解難,救死扶傷。無論是股肱之臣、翰林學士或是宮廷御醫,他們上下援引,效命朝廷,在政治經濟、學術文化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貢獻。茲簡選幾位乾嘉時期宮廷中的徽州人杰,考察他們在朝廷宮殿內的生活實態,闡揚他們為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事業的繁榮和強大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一、汪由敦、汪承霈父子
徽州人憑借聰明才智,從偏僻封閉的皖南山區走出去,融入外面的世界和時代的洪流中,“得風氣之先”,或因經商而為巨富,或因科舉而為重臣,或由苦讀而為學者,拼搏奮進,各得其所。休寧汪由敦(1692-1758),字師茗,號松泉,徽州休寧溪口人,就是因科舉而走上仕途,為朝廷重臣。汪氏先世從婺源遷休寧,以上溪口為居處,是典型的亦賈亦儒的徽商家庭。其父汪品佳為了家族生計而放棄學業,奔走于兩浙三吳之間。先娶休寧朱氏女為妻,繼娶常州龔氏,汪由敦即為龔氏所生之長子。由敦十歲時,因科舉應試籍貫的需要,而必須歸試于原籍休寧,故此后即往來于常州、杭州、鎮江、徽州之間。后以商籍就試于錢塘,被浙江巡撫徐元夢賞識,而以諸生充任明史館纂修,一時輿論榮之。此后由科舉進入朝廷內閣,頗得皇恩眷顧。
汪由敦在朝期間的履歷和事跡,我們可以參閱相關史料,借以考察出身于徽州的仕宦,是如何在朝廷中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的。《清史稿》曰:“汪由敦字師茗,浙江錢塘人,原籍安徽休寧。雍正二年二甲第一名進士,選庶吉士。遭父喪,以纂修明史,命在館守制。喪終,三遷內閣學士,直上書房。乾隆十一年,命在軍機處行走。十六年,調戶部侍郎。命同大學士高斌勘天津等處河工,請浚永定河下流,疏王慶坨引河,增鳳河堤壩。十七年,授工部尚書。十九年,加太子太傅,兼刑部尚書。二十年,準噶爾平,軍機大臣得議敘。二十一年,調工部尚書。二十二年,授吏部尚書。二十三年,卒,上親臨賜奠,贈太子太師,謚文端。由敦篤內行,記誦尤淹博,文章典重有體。內直幾三十年,以恭謹受上知。乾隆間,大臣初入直軍機處,上以日所制詩用丹筆作草,或口授令移錄,謂之‘詩片’。久無誤,乃使撰擬諭旨。由敦能強識,當上意。上出謁陵及巡幸必從,入承旨,耳受心識,出即傳寫,不遺一字。其卒也,諭稱其‘老誠端恪,敏慎安詳,學問淵深,文辭雅正’,并賦詩悼之。又以由敦善書,命館臣排次上石,曰時晴齋法帖。上賦懷舊詩,列五詞臣中,稱其書比張照云。”[1]年六十七卒,謚文端,葬于溪口木干村山上,著作由其子汪承霈搜集刊刻為《松泉詩文集》傳世。
汪由敦為人老誠敏慎,慮事周全,辦事敏練,在朝三十余年罕有過錯,實屬難能。因辦事甚合圣意,曾得賜御書“松泉”二字,故此后即以此自號,以示皇恩浩蕩,永世不忘。其學問淵深,文辭雅正,既是朝廷重臣,又兼內閣書家,為清代館閣體的代表書家。后值平定金川用兵,羽書頻傳,戰事緊急,乾隆帝親自坐鎮指揮,以汪由敦與湖南陳文肅草擬諭旨,皆合圣意。乾隆十七年(1752)初冬,乾隆帝垂問由敦家世,并賜御臨《快雪時晴帖》,因跋文中有“時晴快雪對時晴”之句,汪氏隨即自命齋名為“時晴齋”。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隨駕抵揚州,獲御賜“六典持衡”匾額,可謂榮耀一時,如此也盡顯汪氏“經邦華國、表正百僚”的名臣風范。從《松泉詩文集》所載唱和詩文來看,恭和御制詩文居多,與乾隆朝的重要人物都有密切交往,如張廷玉、錢陳群、劉統勛、趙翼、劉綸、紀昀等皆為超群之輩。汪氏屢做鄉試、會試主考官,一生提攜選拔人才眾多,但他洞悉世態,從不妄交,淡泊名利,嚴格自律。錢陳群稱其在朝為官之風范時,稱其“為人沉靜寡言笑,喜慍不少見于色,遇事有識,默定于中,不以議論捷給相尚。當群言紛沓,徐出一語,聞者厭心,以為不可及也。氣度端凝整暇,極倥傯中亦從容不失條理。雖以文學受主知,而簿書錢谷、刑名法律之事,亦無不究心焉。性尤慎密,每有贊畫,絕口不言,雖子弟親戚不使知,上由是益倚任,凡塞外行圍及四方巡幸,必以由敦從,恩禮賜賚,不可殫記。”[2]幾十年的宦海沉浮,及與乾隆帝的臣君交好,無不印證了汪氏心思縝密、辦事敏練的性格和能力。其中,清軍平定金川、準噶爾兩役之廷諭皆出其手,可謂“房謀杜斷,一身兼之”的天生大用之材。除了政績、軍功顯赫外,汪氏還主持過《大清一統志》《平定金川方略》《平定準噶爾方略》等官書的纂修,文武兼備,確為一代功臣良將。至今,時有海內外學人來休寧溪口鎮的汪氏墓前憑吊和紀念之。
汪由敦有三子:承沆、承霈、承澍。次子汪承霈(?-1805),字春農,號時齋,最為得力。《清史稿》載:由敦既卒,喪終,承霈以賜祭葬入謝。傅恒為言承霈書類由敦,授兵部主事,充軍機處章京。累遷郎中,除福建邵武知府。時母年八十,請軍機大臣為陳情,留京供職,復補戶部郎中。乾隆三十六年(1771),師討小金川,上命戶部侍郎桂林出督餉,以承霈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阿爾泰、宋元俊劾桂林以金與土酋贖所掠軍士,辭連承霈,命逮治。俄,事白,仍以郎中充軍機處章京。累遷工部右侍郎。乾隆四十年(1775),上校射,承霈連發中的,賞花翎。調戶部右侍郎。乾隆五十四年(1789),坐監臨順天鄉試失察,左遷通政使。累遷復至侍郎。嘉慶五年(1800),授左都御史,遷兵部尚書,兼領順天府尹。嘉慶六年(1801),永定河水溢,上命治賑,得旨獎敘。嘉慶七年(1802),上將幸木蘭,承霈請罷停圍,不許。尋改左都御史,署兵部尚書。北城盜發,上責承霈不稱職,以二品冠服致仕。嘉慶十年(1805)六月回籍時,卒于山東陽谷舟次,詔視尚書例議恤。”[3]承霈在公余之外,長于古詩文詞,能書擅畫,尤工山水人物及花卉,著有《墨香居畫識》《耕硯田齋筆記》《讀畫輯略》等。今故宮博物院里就藏有汪由敦、汪承霈、曹文埴臨帖及書畫卷軸若干,可以參閱。
此外,汪氏家族從政者還有由敦之弟汪鼎金(進士),之子汪承澍(龍川知縣),以及從商者汪貢金、汪元芝等。可見,汪氏一家族是為典型的徽商、學者和官僚三合一的家族代表,為推動社會的發展貢獻各自的力量。
二、曹文埴、曹振鏞父子
新安曹氏自宋代文澤公遷居徽州后,再分支流,枝葉繁茂,人才輩出,尤以婺源大墉、績溪旺川和歙縣雄村(一世祖曹永卿)為最。明清時期,雄村一脈尤為鼎盛,其中又以曹文埴(1735-1798,字近薇,號竹虛,歙縣雄村人)家族最為興旺,凡獲得科舉功名者,達六十余人,商總和官宦人數也最為突出。
曹文埴祖上以鹽業為生,有數人為淮揚鹽業商總,家族事業日漸隆裕。至其父曹景宸時,重建雄村曹氏宗祠,并獨力義建竹山書院,鼓勵子孫走科舉仕進之路。文埴少年聰穎,秉承父志,成功入仕為官,且清正廉明,設事以國家和百姓利益為重,辦案公正,定案準確。其以德器才識,屢受高宗賞識,深為倚重,朝廷公認其為“不徇隱,公正得大體”。《清史稿》載其于宮中行事道:“乾隆二十五年二甲第一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直懋勤殿,四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命在南書房行走。再遷詹事府詹事。居父喪,歸。乾隆四十二年,詣京師,謁孝圣憲皇后梓宮。喪終,仍在南書房行走,授左副都御史。遷侍郎,歷刑、兵、工、戶諸部,兼管順天府府尹。乾隆五十一年,命如浙江察倉庫虧缺。旋復命阿桂會文埴董理。乾隆五十二年,文埴以母老乞歸養,俞其請,加太子太保,御書賜其母。乾隆五十五年,文埴詣京師祝嘏,上賜文埴母大緞、貂皮。乾隆五十六年,御試翰詹,文埴子編修振鏞列三等。上以才可造,又為文埴子,擢侍講。寄賜文埴御制文勒石拓本。乾隆六十年,以上御極周甲子,文埴詣京師賀,上復賜文埴母御書、文綺、貂皮。嘉慶三年,卒。高宗方有疾,恤典未行。嘉慶五年,仁宗命予恤,謚文敏,并賜文埴母大緞、人參”。[4]由此可見,曹氏一生由科舉入仕途,不僅帶動了一族文化之提高,同時也增強了曹氏家族在商場上的經營力量。自此以后,雄村有“宰相故里”之稱,曹氏有“父子尚書”之名。曹氏其他子孫未能科舉入仕者也大多走經商之路,并通過官商互濟之道,完成了宗族強化之業。因此,根植于鹽商世家的曹氏家族代代相續,以其雄厚的人眾資財與顯赫的官宦地位,成為地方上的名門望族,影響至今。
縱觀曹文埴的一生,其早年孜孜不倦,潛心求學;中年馳騁于官場,忠君報國,為民生社稷奔波勞累,心憂天下,關心民生社稷,為國家出謀劃策,為百姓盡職盡責。為官數十年,長居臺閣,位高權重,因此與很多達官貴人、文人墨客交往甚繁。公事之余,潛心問學,著述頗豐,留下了眾多詩文,著有《石鼓硯齋文鈔》和《直廬集》等。晚年養親歸里,侍母孝親,積極從事于家鄉教育事業,為歙縣重建紫陽書院。作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官員,其所作所為堪稱中國古代優秀儒士的杰出代表。
尚書曹文埴之子振鏞(1755-1835),字儷笙,“青出于父”,歷任乾嘉道三朝達五十年,居相位二十二年之久,深受朝廷倚重。《清史稿》載其經歷曰:“乾隆四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考三等,高宗以振鏞大臣子,才可用,特擢侍講。累遷侍讀學士。嘉慶三年,大考二等,遷少詹事。父憂歸,服闋,授通政使。歷內閣學士,工部、吏部侍郎。嘉慶十一年,擢工部尚書。《高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調戶部,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嘉慶十八年,調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尋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晉太子太保。嘉慶二十五年,命振鏞為軍機大臣。宣宗治尚恭儉,振鏞小心謹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道光元年,晉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道光三年,萬壽節,幸萬壽山玉瀾堂,賜宴十五老臣,振鏞年齒居末,特命與宴繪像。道光四年,充上書房總師傅。道光六年,入直南書房。道光七年,回疆平,晉太子太師。道光八年,張格爾就擒,晉太傅,賜紫韁,圖形紫光閣,列功臣中。道光十一年,以萬壽慶典賜雙眼花翎。道光十五年,卒,年八十有一。詔曰:大學士曹振鏞人品端方,靖恭正直,凡所陳奏,務得大體。實心任事,外貌訥然,而獻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賴而人不知。揆諸謚法,足以當‘正’字而無愧,其予謚文正。并入祀賢良祠,擢次子曹恩濙四品卿”。[5]
關于曹振鏞的為官時間之長,所做貢獻之少,所受恩惠之多,后世一直都存在著許多爭議。大多數學者對曹振鏞的“清、慎、勤”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小心謹慎,遇事模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庸臣”,并且把“多磕頭,少說話”作為他自身人格的切實寫照。我們都不是當事人,自然不明就里,或許他有不得已的苦衷。若從積極一面來看,真實的曹振鏞也并非如此。他不僅在政治上有一套獨特的為官之道,在仕途上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無災無難。在學術文化的傳承方面也頗有成就。作為三朝元老,曹振鏞一生筆耕不輟,著書頗豐,總裁纂修《會典》《兩朝實錄》《河工方略》《明鑒》《皇朝文穎》《全唐文》等,輯有《宋四六選》二十四卷,合編有《平定回疆剿捻逆裔方略》等。個人著有《話云軒詠詩》《綸閣延輝文集》《綸閣延輝詩集》《曹文正公詩集》,如此豐富的著述,證明了曹振鏞并非不學無術、庸庸碌碌之輩,而是一名勤勤勉勉的學者,是一名韜光養晦的智者。也因如此,曹振鏞才能入直南書房,成為翰林院掌院學士,官至太傅、武英殿大學士,獲得世人終生夢想的最高榮耀。父子二人起家翰苑,擢任綸扉,受三朝知遇之隆,恩顯兩世贊襄偉績,“恩眷之隆,時無與比”。故徽州當地有名諺曰“宰相朝朝有,代君世間無”,也由此印證了曹振鏞父子作為君王的心腹之臣,深為倚重,在整個清朝歷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三、戴震、金榜與吳謙
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上,戴震(1724-1777),字東原,休寧隆阜人、金榜(1735-1801),字蕊中、輔之,歙縣巖寺人,是兩位繞不過的重要人物,尤其是戴震以其治學方法之獨到、學術成就之卓越,“啟導了十九世紀的一線曙光”。梁啟超說:“茍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6]足見其重要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今僅就戴震和金榜在朝廷四庫館中的行事略做介紹,借以考見徽州學者“為往圣繼絕學”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七月,四庫全書館總裁奏請進士邵晉涵、周永年、余集,舉人戴震、楊昌霖調取來京,同典秘籍,時稱“五征君”,后皆改入翰林,稱一時文典盛事。戴震出身于徽商,幼讀私塾,過目不忘且善思好問。三十三歲時,因與本家族豪強爭奪墳地而結仇,為避禍而入都,在京師得以與獻縣紀昀、大興朱筠、嘉定錢大昕、王鳴盛、余姚盧文弨、青浦王昶等“折節與交”,尚書秦蕙田纂《五禮通考》,“震任其事焉”。《清史稿》載東原進入四庫館后的事跡云:“乾隆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征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之職,總裁薦震充纂修。乾隆四十年,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震以文學受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震亦思勤修其職,晨夕披檢,無間寒暑。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所校《大戴禮記》《水經注》尤精核。又于《永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七種,皆王錫闡、梅文鼎所未見。震正訛補脫以進,得旨刊行。乾隆四十二年,卒於官,年五十有五。震為學精誠解辨,每立一義,初若創獲,乃參考之,果不可易。大約有三:曰小學,曰測算,曰典章制度。震卒后,其小學,則高郵王念孫、金壇段玉裁傳之;測算之學,則曲阜孔廣森傳之;典章制度之學,則興化任大椿傳之:皆其弟子也。后十馀年,高宗以震所校《水經注》問南書房諸臣曰:戴震尚在否?對曰:已死。上惋惜久之。”[7]
以上為正史所載,若從私人記載的文字也可見戴氏學問之深,功績之大。錢大昕述東原入館一事曰:“癸巳歲,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讎之職。總裁諸公疏薦先生,以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為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輒就咨訪,先生為考究巔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丁酉夏卒于官,年五十有五。”[8]東原進入四庫館時,才、學、識已臻極詣,加之朝廷中秘極其豐富的文獻資料,使其得天獨厚,如虎添翼。許多沉埋已久的古書,也借東原之手而重見天日。事實上,戴氏在館中所校《方言注》《水經注》《算經十書》等,早在入館之前,就已沉潛有年,別有心得,而后在館又加拾遺補闕,精心編輯,后皆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僅就輯佚《算經十書》而言,“戴震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倘無他的工作,有的算經,我們就會永遠看不到了,而且他提出了若干正確的校勘,對人們能通讀被冷落四百余年的這些算經,理解其數學內容,表彰其數學成就起了極大的作用。戴震的工作掀起了乾嘉學派研究中國傳統數學的高潮。微波榭本《算經十書》在有清一代被奉為圭臬,研究十部算經者大都以此為底本”。[9]戴氏不僅以整理古籍的杰出成就卓立于四庫館中,又因“多識古書原委”而別受殊恩。當然,也是承擔了館中難度最大的任務,整日里掇拾叢殘,部次條別,刪夷駢贅,疏通倫類,“非周察而得其實,不敢以為言;非精心于稽古,不敢輕筆之書”,故所輯佚皆為善本,嘉惠士林,裨益后世。
關于戴震在館期間的校書情況,其子戴中立記曰:“先君所辦《永樂大典》散篇,如《水經注》四十卷、《儀禮識誤》三卷、《中庸講義》四卷、《五經算術》二卷、《海島算經》六卷、《九章算術》十卷、《五曹算經》五卷、《夏侯陽算經》三卷、《孫子算經》三卷、《周髀算經》三卷、《項氏家說》十二卷、《儀禮集釋》三十卷、《儀禮釋宮》一卷、《方言》十三卷、《大戴禮記》十三卷。計官書十五種,俱武英殿刊刻。”[10]東原在館五年,不僅完成了《永樂大典》中疑難古書的輯佚和整理,還分校了許多“各省送到遺書”,辨別真偽,彌補瑕隙,“有一字不準六書,一字解不通貫群經,即無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復參證而后即安”,極大地帶動了館內外學者崇尚漢學考據之風。“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句墳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為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骎骎乎移風俗矣”。[11]開館之初,非翰林而為纂修者僅數人,戴東原“首膺其選”,引領學風,而使“游談心性,空言道理”者望而卻步,而經史考證之學蔚然成風。東原以一介書生,由山野一躍而為學界領袖,以窘迫落拓之運,引領著“名物考訂”之風,使一批“才略之士”改弦易轍,趨向漢學考據一路。
與戴震同在四庫館的徽州學者,還有金榜、洪梧等。他們既為師友,又為同事,相互援引,成為四庫館中顯赫一時的核心人物。金榜出身于徽商兼官宦之家,自幼即從鮑倚云學習制舉之學,也曾在西溪汪氏不疏園中,從江永、戴震等學習歷算、律呂、考工諸事,學有根基,言無枝葉。因“受經于江永慎修暨戴東原”。據《清史稿》載:“乾隆二十九年乙酉召試舉人,擢內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乾隆壬辰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效力于武英殿繕寫校正《四庫全書》分校官。在館期間,金氏與洪氏三兄弟(樸、榜、梧)一起,對戴氏關懷備至,諸事多有承擔。戴震去世后,也隨即任山西鄉試副考官,此后乞歸故里,著書自娛,卒年六十七歲,著有《禮箋》三卷。金榜家族屬于典型的徽商:先祖因戰亂而避居古徽州,明清時期因生活所迫而經商于外。在金榜之父金長溥以后,‘父子三進士’‘兄弟同朝奉’,成為徽商家族的杰出典范。金榜之所以能夠名垂青史,并非因其姓名特殊而又‘金榜第一’,而在其‘以才華為天下望’,以不朽之作《禮箋》而‘與江、戴巍然并峙’,成為乾嘉學術的中堅,誠如李慈銘所云:‘國朝狀元通經學者,以輔之為巨擘。’”[12]《禮箋》一書為清代禮學研究中一部重要的標志性成果。
乾嘉時期,我國的科技和醫學落伍于西方近代科學,但在皖南徽州卻出現了名醫輩出、醫籍充棟的特殊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僅清代而言,就有數十位引領醫學發展的名家里手,供職于朝野上下,為生民救死扶傷,如汪昂、吳謙、葉昶、鄭宏綱、程國彭等。其中,乾隆時期的吳謙就是長期供職于宮廷太醫院的天下名醫。據《清史稿》載:“吳謙字六吉,安徽歙縣人,官太醫院判,供奉內廷,屢被恩賚。乾隆中,敕編醫書,太醫院使錢斗保請發內府藏書,并征集天下家藏秘籍,及世傳經驗良方,分門聚類,刪其駁雜,采其精粹,發其余蘊,補其未備,為書二部。小而約者,以為初學誦讀;大而博者,以為學成參考。既而征書之令中止,議專編一書,期速成,命謙及同官劉裕鐸為總修官。謙以古醫書有法無方,惟《傷寒論》《金匱要略》《雜病論》始有法有方。《靈》《素》而后,二書實一脈相承。義理淵深,方法微奧,領會不易,遂多訛錯。舊注隨文附會,難以傳信。謙自為刪定,書成八九,及是,請就謙未成之書,更加增減。于二書訛錯者,悉為訂正,逐條注釋,復集諸家舊注實足闡發微義者,以資參考,為全書之首,標示正軌。次刪補名醫方論,次四診要訣,次諸病心法要訣,次正骨心法要旨。書成,賜名《醫宗金鑒》。雖出眾手編輯,而訂正《傷寒》《金匱》,本于謙所自撰。”[13]由此則史料可知,吳謙是從徽州走出的一位杰出的新安醫學家,他不僅具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得以在深宮中行醫施藥,為皇親國戚治病養生,“供奉內廷,屢被恩賚”,而且還具備高深的理論知識,擔任重要醫籍的整理研究和校勘編纂任務,受到皇帝的褒獎。他所奉敕編纂的《醫宗金鑒》就是一部中醫學界重要的經典醫籍,“此編仰體圣主仁育之心,根據古義而能得其變通,參酌時宜而必求其證驗。寒熱不執成見,攻補無所偏施,于以拯濟生民,同登壽域,涵濡培養之澤,真無微之不至矣”。[14]
作為一名宮廷御醫,吳謙精通醫學各科,臨床上尤其以傷科見長,成為療傷整骨的一代圣手。在醫案與效方、養生與保健方面,為宮廷醫療機構的醫學實踐和理論發展,建立了較為全面而實用的醫學體系。由于他醫術精湛,醫德高尚,曾受到朝廷上下廣泛贊譽。乾隆元年(1736)以后,吳氏任太醫院右院判,組織征集了很多傳世驗方和家藏秘籍,并分門別類,執簡馭繁,去偽存真。乾隆四年(1739),詔令其編纂醫書,訂正醫學典籍,對歷代醫籍加以校勘、刪補。所纂《醫宗金鑒》一書凡九十卷,類分十一科,乾隆七年(1742)刊于武英殿,敬呈御覽,得欽賜嘉名。該書特別注重臨證實際,圖、說、方、論具備,并附歌訣和圖表,內容豐富,選方平穩,流傳很廣,成為當時太醫院的教科書,也是現代中醫從業者的必讀書目。吳氏作為太醫院右院判,善于總結清以前的中醫成就,又擅長“酌古準今”,對當時乃至近代以來的中醫學理論研究、臨床實踐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此之故,吳謙也得以與張璐、喻嘉言一起并稱“清初三大名醫”的美譽。[15]
吳氏之所以能夠成為宮廷名醫,究其實,與其出生的地域文化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作為“程朱闕里”的徽州人,吳謙思想上必受宋明理學的深刻影響,“格物致知”與“仁德性命”之說,及“不為良相,必為良醫”的儒家情懷,使得新安醫家特別注重“天人合一”和“固本培元”,講求“平衡氣血脾胃”“醫門八法”等,認為“大醫必本于大儒”,“必先通儒而后學醫”,因此而有新安醫者為儒醫的說法。加之徽州獨特的山區地理與氣候條件,為中醫學和中草藥學的興盛準備了必要的適合土壤和區域環境。同時,明清徽商與外界大規模的商業往來和強力的經濟支撐,使得古代醫書得以大量刊刻,并廣泛普及和傳播。因此,新安醫學在世代傳承的基礎上,又得以開拓創新,蜚聲海內外。吳謙及其所代表的新安醫學,在中醫經典的闡發和普及、臨床各科的運用以及本草及養生保健的研究等方面,為推動中華醫學的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四、在朝徽州人的互助關系
乾嘉時期儒風獨茂的徽州,英才輩出,燦若群星,富商巨賈、藝苑名流、疆臣能吏和名賢大儒令人欽羨,這些顯達之士在各個領域皆為辛勤勞作的“徽駱駝”,且智慧高超,貢獻卓著,尤其是在宮廷中的名臣和大儒的政治與學術活動,更為歷史長河及中華文化留下了濃郁而又遒勁的篇章,為后人所無限敬仰。上述幾位宮廷里的徽州名人之間,也是相互援引,共同進步,為效命朝廷,也為家族興盛和徽州文化的繁榮和發展貢獻出了他們杰出的才華。事實上,從乾嘉時期的幾位徽州人之間的交游材料,可以窺見其間之關系,作為本文之注腳。
一是曹文埴與汪由敦的關系,可參見曹氏所撰《御制汪承霈進其父由敦詩文集因題句當序》一文,歷敘往日“劇談”所論“懷賈誼”與“慚趙奢”,為汪氏的詩文才華和政事功業贊述表彰,云:“時晴書早壽苕華,子舍茲呈遺稿佳嘉。詩與古期歸雅正,文非時調去浮夸。席前我偶懷賈誼,書讀爾休慚趙奢。舊日西清劇談輩,只今誰在惹咨嗟?”[16]二是曹文埴與戴震的關系,可以考見在《四庫全書》編纂之前六年,東原曾依靠同鄉曹文埴(日后為四庫館副總裁)的幫助,從《永樂大典》中查閱古算學之書,作為研究之用,云:“丁亥歲,因吾鄉曹編修往一觀,則離散錯出。思綴集之,未之能也。出都后,恒寤寐乎是。及癸巳夏,奉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躬逢國家盛典,乃得盡心纂次,訂其訛舛。”[17]三是戴震與汪由敦的關系,可以參見戴氏為汪氏代寫孫迅發《三字經箋注》的序文,其文收錄在《戴東原先生文》中。[18]四是曹文埴所在的歙縣雄村與金榜所在的巖寺是鄰村,且曹氏與金氏之間世有聯姻關系。金榜與曹文埴同齡,但考中進士則遲緩十余年。兩者之間的關系,由以下信札可見一斑。金榜曰:“前肅布一函,仰荷慈照,并知轉寄之件已蒙郵至塞垣,感戢無似。比惟三兄大人臺候清勝,足慰馳仰。現在大功告成,天顏有喜,賡揚禁近,歌詠太平,瞻望下風,鼓舞增氣。日昨祗造尊潭,欣侍年伯大人杖履,精神健勝,頤養清腴,闔宅一一康福,可寬遠抱。家嚴藉庇眠食安穩,十一月壽辰,諄諭毋得領賀。奉求款聯,便中希即揮賜,更懇代買紙絹數對,轉乞南齋諸鉅公大筆,以增光寵。得于閏月初旬,寄至大哥親翁處轉交,至感至感!家兄近患瘧未愈,未得另布。晚趨侍鈞教,須俟初春。入冬儤直更勤,尤冀加意珍愛。臨楮不盡依溯。竹虛三兄大前輩。家父命筆申候。年姻晚生禫金榜頓首。”[19]
綜上可知,明清時代的徽州人“寄命于商”,憑著吃苦耐勞的“徽駱駝”精神,從山野走向外面的世界,在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成就豐富多彩的人生,為國家和民眾作出過重要貢獻,得以留名青史。溯其根源,徽州人“賈而好儒”,儒家倫理是其為學、為政及經商的道德根本。他們講究以誠待人,注重人文修養,故“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伴隨終生。這種以血緣和鄉誼為紐帶,相互提攜,共同進取,容易形成一種團隊精神,在社會競爭中自然成為集體優勢。無論是在經濟上或文化上,在朝抑或在野,“徽州商幫”及“皖南學派”,都是為世公認的一種贊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