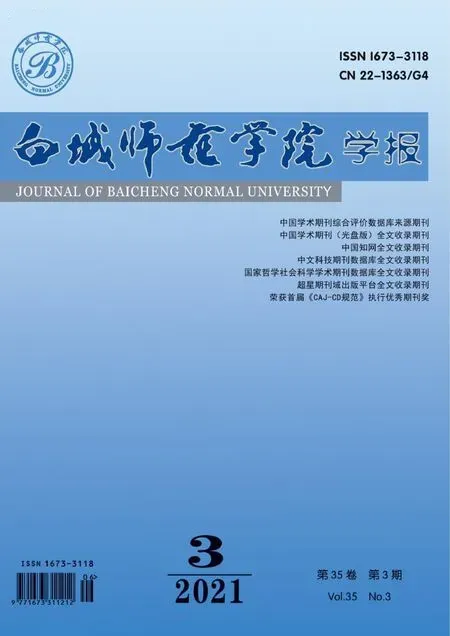《呼蘭河傳》中蕭紅的主體精神
耿 菲
(黑龍江大學 文學院,哈爾濱 150000)
蕭紅作為現代文學史中杰出的東北籍作家,她的小說多以東北小城呼蘭為敘述空間,書寫的是底層世界生活著的人與發生過的事,這使她成為現代文學史中少有的存在。獨特的地緣性讓蕭紅的小說創作具備了同時代女作家所缺少的大氣與坦率,清新自然的鄉土小說風格備受文壇巨匠魯迅的推崇。正如魯迅所評價的,蕭紅的小說寫出了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
一、記憶中的小城
《呼蘭河傳》作為蕭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描寫的依然是蕭紅記憶中熟悉的小城呼蘭。呼蘭是蕭紅出生與成長的地方,那里的自然條件頗為復雜:一方面,它位于呼蘭河的河口處,地勢平坦,土壤肥沃,優越的地理位置自古便是農民的宜居之所;另一方面,它坐落于黑龍江省中部,黑龍江省作為古代懲治犯人的流放之地,極寒的氣候特征極不利于人類的生存。《呼蘭河傳》開篇就點明了東北鮮明獨特的地域特征與風土人情,作家真實而具象地描寫了在呼蘭小城的嚴寒天氣之下人們的生存狀態。在那個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的北方大地,一群小人物僅為了“活著”就已經用盡了所有的氣力。
小說的前兩章集中地描繪了呼蘭的地理風貌、傳統習俗與小城人們的生存狀態,表現了小城狹仄閉塞的環境氛圍與人們得過且過的精神狀態。首先,第一章從宏觀上對呼蘭小城的空間結構進行了細致的勾勒。一個不怎么繁華的小城在作家的筆下躍然紙上:全城除了較為繁華的十字街,就只有兩條街,街上零星地開著幾家鋪子。這四條街貫穿全城,構成了小城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全部。在這里,人們“對生、老、病、死,都沒有什么表示。”[1]一切苦難都可以糊里糊涂地過去。蕭紅在這一章濃墨重彩地描繪了東二街道上的大泥坑,這個只有五六尺深的大泥坑聚焦了小城人的目光,在這里發生的一幕幕鬧劇為人們提供了談資與消遣,給小城平淡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其次,小說的第二章主要描寫了呼蘭小城的風俗人情,蕭紅于平凡瑣碎的實際生活外對小城中人們麻木混沌的精神生活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像跳大神、逛廟會這種活動在中國存在了幾千年,已經形成了一個自在的信仰體系,它充當了護佑民眾心靈安穩的一種社會心理機制。呼蘭小城中的人們習慣把萬事歸咎于命運,把命運又交給鬼神。生活在呼蘭河畔的人們便在這些信仰風俗中尋找生活的樂趣與精神的慰藉。
呼蘭小城的封建閉塞與中國古老的農耕文明相關聯。農耕社會時期,人和土地之間建立了深厚的聯系,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體制使農村全無與外界交流的必要,導致了底層民間世界的閉塞與落后。相應地,這種生存環境養成了農民安分守己、樂天知命的性格特征。他們在思維的慣性中帶著沉重的歷史枷鎖前行,喪失了思考的本能,并自甘沉陷于傳統的泥藻之中。由此,小城的閉塞與人們的愚昧相互作用,進而發展成為一個“死循環”。然而,無論鄉土社會的封建傳統觀念有多么根深蒂固,也無法阻擋現代文明的發展趨勢。蕭紅的覺醒,源自她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受到了西方思想的滋養。在藝術與文學的雙重熏陶下,蕭紅形成了獨特的觀察能力與扎實的文學功底。一方面,底層社會出身的蕭紅具有豐富的民間生活經驗,這使她看到了鄉土民間的純粹良善;另一方面,啟蒙的視角使蕭紅意識到呼蘭小城存在的弊端與丑陋,因而能夠對被遮蔽的民間世界進行真實客觀的還原。
《呼蘭河傳》從第五章到第七章集中筆墨塑造了呼蘭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們是生活在東北偏安一隅的普通農民,物質經濟條件貧困,自然生存環境惡劣,生活在這里的人安于現狀、自得其樂。蕭紅在《呼蘭河傳》中塑造的人物群像折射出當時整個中國農民的面貌。有二伯是“我”家的一個長工,只被供食宿,沒有工錢,過著渾渾噩噩的生活,他秉持著類似于阿Q 的精神勝利法,是身份上的奴隸、思想上的主子,麻木地忍受著被剝削壓迫的生活。作為社會的弱者被別人恥笑羞辱,卻還要用可笑的方式維護面子。除此之外,蕭紅以憤懣悲涼的筆觸寫到了小城人民蒙昧愚笨的一面。他們崇信封建傳統習俗,對鬼神盲目迷信奉承,以非人的文化摧殘生命卻不自知。小團圓媳婦作為小說塑造的主要女性人物形象,作家描繪了她如何被婆家壓抑天性,逐漸失去了少女的靈氣與爛漫,又如何在病痛中備受折磨直至死去。她的死不能歸結于任何人的主觀意志,但貌似又無人能逃脫致死的罪責。“看客文化”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陋習頑固地遺留在小城人的思維之中。他們抱著看熱鬧的心態漠視著別人的不幸,在愚昧麻木中充當著加害者的幫兇。蕭紅對東北農民群像還原式的塑造啟迪著個體人對自身生命價值和生存意義的深刻思考。
二、自由生命狀態的追尋
敘述視角是作家在文學創作中對作品內容進行觀察和講述的特定角度,敘述視角的選取影響著作品最終效果的呈現。兒童視角作為敘述視角的一種,是以兒童作為敘述者的敘事策略,展現的是兒童眼中所觀察到的世界以及兒童心靈所感受到的世界。由于兒童尚未受到社會文化與意識形態的規約,因此他們保持著一顆稚嫩本真的童心。童心在文學創作中具有的重要作用,明代學者李贄曾提出“童心說”,他認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2]在李贄看來,童心是文學創作的源泉,是衡量文學作品價值的重要標準。在現代,運用兒童視角進行敘事就是作家具有童心的一種表現。
五四新文化運動標志著中國文學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思想的解放使人們更加關注個體的獨立與精神的覺醒。在外國各種思潮的影響下,中國現代文學誕生了大量新的敘事視角,兒童視角就是其一。隨著婦女與兒童的被關注,許多作家都開始嘗試運用兒童視角進行文學創作。其中,蕭紅的文學作品便以兒童敘事見長,她以一個小女孩特有的純真視角憶述自己的童年生活。《呼蘭河傳》就是蕭紅運用兒童視角進行創作的一部極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說的第三章與第四章描寫了蕭紅的童年記憶,展現了作家童年時期在呼蘭河畔度過的難忘時光。其中,第三章是整部小說頗為出彩的一個章節,該章一改前兩章的全知全能視角,以第一人稱視角“我”為敘述中心,追憶了童年時期祖父的陪伴與教導,構建了一個絢彩精致的“后花園”世界,書寫了蕭紅一生中少有的美好。
“呼蘭河這小城里邊住著我的祖父”,[3]第三章開篇便表明了蕭紅在追憶童年時代“我”和祖父之間發生的故事。與祖父的形象相對照,蕭紅還簡筆帶過了祖母這一人物形象,然而,字里行間展現的卻是蕭紅對祖母的壞印象。祖母因為蕭紅淘氣總是訓誡她,所以,即便祖母從未苛待過蕭紅,但她依然不喜歡祖母,記憶中的“壞”祖母形象是兒童視角的一種顯現,祖母的行為實際上是管教孩子的一種方式,但是這種管教必然會壓制孩子活潑頑劣的天性,所以被兒童所不喜。與祖母的嚴厲不同,祖父對蕭紅幾乎是百依百順的。他容忍蕭紅的各種小脾氣,任其自由成長嬉鬧,這種溺愛致使蕭紅眼中的祖父一直都是溫暖慈愛的。祖父不僅是蕭紅兒時的“玩伴”,還是她學習的啟蒙導師。在那個女子不需要接受教育的時代,祖父每天教蕭紅背詩,但彼時年幼的蕭紅并不能真正理解古詩所蘊含的意義,只是玩鬧著把詩大聲地喊出來,用孩童的直觀感受體悟哪句話好聽,哪首詩喜歡。祖父給予蕭紅的是心靈上的自由,對她的呵護與寵愛讓她擁有了一個幸福快樂、無拘無束的童年,是蕭紅暗淡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如果說蕭紅的祖父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那么她家的后花園應該算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后花園作為蕭紅小說中經常出現的意象,構成了她童年生活的私人小天地,這個特定的時空帶給蕭紅的幸福與滿足慰藉了她流浪漂泊的后半生,成為她內心深處的精神家園。因此,蕭紅筆下的后花園意象具有空間與精神的雙重意義。從空間上看,蕭紅的整個童年幾乎都與祖父在那里度過。在后花園中,“我”、祖父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祖父每天在花園里種菜、栽花、拔草,而“我”則陪在祖父身邊撲蜻蜓、捉螞蚱,偶爾也去地里給祖父搗亂,玩累了便用帽子遮住臉美美地睡上一覺,兒童眼中折射出的后花園便是如此幸福安逸的存在。從精神上看,蕭紅出生在傳統禮教根深蒂固的大家族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傳統禮教的約束,但是童年生活的棲居地——后花園使她擁有了一個逃避桎梏、釋放天性的游樂場。在這里,她可以與大自然做心靈上的溝通,感受生命的自然生長。在兒童眼中,自然萬物與人一樣是具有生命的,它們擁有自己的思想,想怎么樣就怎么樣,這種隨心與肆意正是蕭紅的心之所向。童年是人最本真的狀態,成人眼中普通的后花園在兒童眼中充滿了未知世界的神秘感,對萬事萬物的探尋解密使童真的生活變得自由歡樂。蕭紅通過對后花園有聲有色的描寫,揭示了一種自由無為的生命狀態,表現了對那種無拘無束的自在狀態的憧憬與神往。
三、自由潛流下的孤寂
“對于生活曾經給予美好的希望但又屢次‘幻滅’了的人,是寂寞的;對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對于自己的工作也有遠大的計劃,但是生活的苦酒卻又使她頗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悶焦躁的人,當然會加倍的寂寞。”[4]茅盾認為蕭紅是寂寞的,這種寂寞從童年直至生命逝去一直都伴隨著蕭紅。
蕭紅的寂寞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首先,蕭紅的童年是寂寞的。舊式鄉紳家庭使蕭紅深受禮教文化的迫害,這也是她一生漂泊離鄉、無所歸依的一個重要緣由。東北重男輕女的傳統思維定勢讓蕭紅為日趨沒落的家族所不喜。母親的早逝、繼母的冷眼與父親的淡漠讓她感受不到家庭的溫暖,自小成長在這樣家庭環境中的蕭紅是寂寞的。其次,蕭紅的情感是寂寞的。包辦的婚姻,未婚夫的逃跑、愛人的背棄致使她飽嘗婚姻愛情的苦痛,感情上的一再受傷讓她的內心寂寞。最后,蕭紅的寂寞還要歸因于她生活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在那個男女不能真正平權的時代,女性身份本身便足以讓蕭紅處于孤立無援的寂寞境地。正如蕭紅臨終前所言:“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卻是因為我是個女人。”[5]魯迅曾在中國現實問題的基礎上提出“娜拉走后怎樣”的深刻命題。作為意識覺醒的新女性,娜拉們勇敢地出走后是否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與解放?對于蕭紅而言,她與那個時代下的千千萬萬個娜拉一樣,果敢地與舊家庭決裂,到“新世界”去追求人格的獨立與婚姻的自主。幸運的是,她并沒有墜入娜拉出走后的窠臼——墮落或回來。然而這條“別人沒有走過的路”注定如同“苦酒”,只會讓蕭紅“加倍的寂寞”。
“蕭紅寫《呼蘭河傳》的時候,心境是寂寞的。”[6]《呼蘭河傳》孕育于1936年蕭紅東渡日本,日本陌生的生存環境讓寂寞的她異常地思念故土,“東京落雪了,好象看到千里外的故鄉。”[7]蕭紅將郁結于心的鄉思融入到小詩集《沙粒》之中,流露出作家“從異鄉又奔向異鄉”的悲戚孤零之感。時隔三年,蕭紅在武漢開始創作《呼蘭河傳》,三年后于香港完稿。《呼蘭河傳》的構思與創作過程正處于抗日戰爭艱苦緊迫的時期,家國的淪陷迫使文人過著逃亡的生活,蕭紅蟄居香港后,身邊更是缺少往昔朋友的陪伴。民族危機的憂患意識與心力交瘁的人生經歷雜糅在一起,導致蕭紅無論是精神還是肉體都處在寂寞的狀態之中。1941 年蕭紅病危之際曾要求駱賓基將她送回呼蘭,并計劃創作《呼蘭河傳》第二部,但是這個愿望在國內日漸嚴峻的形勢下終究付之東流,蕭紅帶著滿心的不甘苦悶地離開:“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8]
《呼蘭河傳》充滿了荒涼感,展現出來的是蕭紅寂寞的童年。“所謂的童年期回憶并不真是記憶的痕跡,而是后來潤飾過了的產品,這種潤飾承受多種日后發展的心智力量的影響。”[9]《呼蘭河傳》通過兒童視角對作家的童年生活進行追憶,但實際上小說仍是以成人作為創作的主體,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交織著兒童與成人的雙重視角,構成了敘事上的復調。由于成人視角的介入,作家個性化的情感體驗時而會在文中顯現出來。兒童視角下的世界是有聲有色、簡單跳脫的,作家在表述上具有孩子式的稚氣與隨意。從寒冬到大街,從商鋪到泥坑,從蝴蝶到白菜,由此及彼,沒有中心,隨性而為,將眼中新鮮的、漂亮的一股腦地傾倒出來。然而,小說在兒童的詩性話語中隱藏著蕭紅作為一個歷經滄桑的成年人的寂寞感。即使是回憶最溫馨的童年生活、最愛自己的祖父、最自在的后花園,這種寂寞感的流露也是自然且不可遏制的。“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了。”[10]時間上的跨度指出“我”的成長以及祖父生命的消逝,表現出美好短暫、無法停留的失落感。真正迫使“我”從童年的“后花園”中走出,進入成人世界的是祖母的死。祖母過世的時候,“我”不諳世事地頂著缸帽子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卻被祖父一腳踹開,這一腳將“我”帶離年少無知的懵懂狀態,意味著“我”應該“懂事”了。蕭紅在寂寞的心境下進行創作,使回憶中的景象變得格外荒涼。兒童眼中的奇異世界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院子的雜亂蕭條,房子的腐朽破敗,生活的艱辛窮苦,人們的逆來順受……
文章的尾聲使蕭紅的寂寞得以升華。蕭紅自1931 年逃到哈爾濱,開始漂泊的生活,直到1942年病逝都沒有再踏入過故土,所以呼蘭的樣貌變得如何她只能依靠想象與道聽途說而得知。蕭紅在《呼蘭河傳》的尾聲中勾勒的是她想象中的呼蘭小城,此時的她已經走出了自身的記憶與童年的時光,回歸于現實生活。記憶與現實的反差襯托出一種蒼涼之感,道出了呼蘭小城的物是人非,道出了自己對故土的懷念與眷戀。
四、結語
《呼蘭河傳》無論在藝術上還是思想上都較之前作品更為成熟。她出離于民族與國家的主流話語,開始注重個人話語的言說,彰顯的是個體飽經滄桑的情感體驗。因此,《呼蘭河傳》無疑是理解蕭紅個體精神與主體思想的關鍵所在。蕭紅對于故鄉呼蘭的情感是復雜的,一方面,她在這里度過了孤獨且寂寞的青少年時期,農村的生活經驗使她在回望鄉土時覺察到呼蘭小城精彩多樣生活背后的刻板單調,并窺見了當地百姓平凡卑瑣的生存狀態以及得過且過、平庸愚昧的精神狀態;另一方面,呼蘭又是承載她最為珍貴溫暖回憶的地方,祖父和后花園讓她擁有了最為自在安逸的童年,孩童時期所具有的自由無羈的生存天地是蕭紅后半生都在追逐找尋的“理想國”。蕭紅寫作的力量便汲取自記憶中留存的那些美好,個人的苦難與家國的淪陷并沒有讓蕭紅的文字變得優柔怨憤,反而成為支撐她創作的動力,使她的文字在飄零孤寂的生存狀態中依然溫暖而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