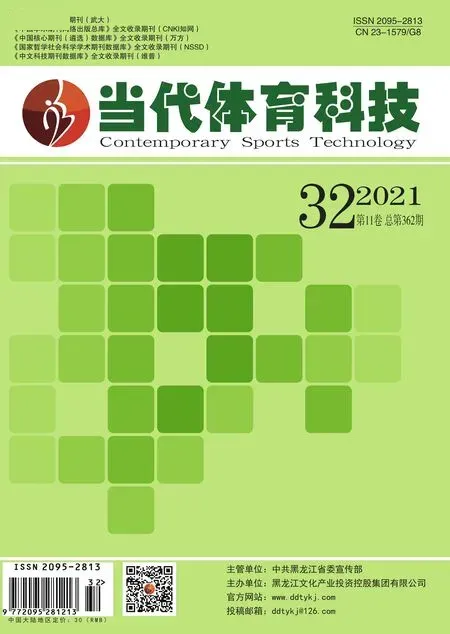“自甘風險”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的適用研究
靳子涵 潘書波
(沈陽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 遼寧沈陽 110034)
學校體育是指以學生為參與主體的體育活動,其目的在于通過培養學生的體育興趣、態度、習慣、知識和能力,增強學生的身體素質,培養學生的道德和意志品質,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1]。學校體育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了體育課、由學校或學生自行組織的課外體育活動、課外運動訓練和競賽以及早操和課間操等內容。而體育運動本身存在一定的固有風險,同時還具有對抗性、競爭性等特征,因此學校在學生進行體育運動的過程中承擔著重要的責任。隨著學校體育的不斷發展,學生在校的體育運動項目也逐漸豐富,所存在的風險也隨之增加,給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責任認定帶來了不少的困難,“自甘風險”的出臺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為司法實踐帶來準確依據。
1 自甘風險
1.1 自甘風險的概念
在2021年1月1日起實施的《民法典》第1176條作出了關于“自愿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自甘風險”的規定,這是我國首次對自甘風險做出法律規定。自甘風險又稱自甘冒險、甘冒風險、風險自擔,在體育方面是指當事人自愿承擔體育運動項目的潛在固有風險所帶來的損害結果,它可以減輕或免除一方當事人的法律責任,也是法律免責事由之一[2]。有學者認為,自甘風險不僅具有全部免除行為人責任的法律意義,還有產生在比較過失的基礎上減輕責任的效果,沒有清晰規定自甘風險在侵權法上的法律意義,比如和過失相抵的效果相似,則其獨立存在性就存在疑惑。而有的學者認為,自甘風險在法律上應當看作是一個免責事由,即徹底免除行為人實施的加害行為所致使損害結果的責任。適合自甘風險對于風險發生實質損害,將會導致賠償的責任是免除保護當事人對于行為潛在風險的理性認知。因此,自甘風險應該是一個具有獨立存在性的法律責任完全免除事由,在雙方都無過錯的情況下,受害人應當自甘風險。
1.2 體育中自甘風險的構成要件
1.2.1 受害人明知風險
受害人明知風險也就是指在受害人參與體育運動前,對其將要參加的體育項目所存在的固有風險具有相當的認知與理解能力,知道所存在的風險或者可能帶來的損害結果。但在司法實踐中,有很多受害人稱自己根本不知道會發生這樣的結果,對體育項目本身所存在的風險“一無所知”。在司法實踐中,應根據受害人的實際年齡、生活閱歷、知識等方面綜合考慮受害人是否真的不知風險,若根據受害人的綜合情況來看,其并不能預知風險,則不能認為其自甘風險[3]。目前,很多學校在學生參與體育比賽或活動前讓學生簽署免責協議,對學生進行身體檢查并告知其將要參加的體育比賽或活動所存在的風險,讓學生事先對風險預知。
1.2.2 客觀存在的固有風險
體育所存在的固有風險具有一定的可預見性,且不可避免。比如,在籃球、足球、橄欖球等一些存在身體對抗性的體育項目中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定的損害結果。如在籃球運動中,球員間的身體碰撞可能會導致球員摔傷、扭傷腳踝等;球員在進行扣籃、上籃等動作時肌肉拉傷,或因技術動作錯誤導致受傷。這都是體育運動中所存在的固有風險,是顯而易見的、可以預見的風險。且這些固有風險具有不確定性,其何時發生、到底會不會發生、會發生在誰身上、在哪發生、以怎樣的方式發生、會造成怎樣的結果等都是不確定的。
1.2.3 受害人自愿
受害人自愿是指受害人在明知風險的情況下,自愿參與某項體育運動,并自愿承擔其存在的固有風險所可能導致的損害結果。受害人自愿是自甘風險重要的構成因素。當事人應當在真實的意思表示下做出自我決策,也就是當事人在毫無他人脅迫、威脅的情況下,遵從自己的內心意識并根據自己的選擇權所做出的決定[4]。比如,學生在明確籃球運動風險后,出于對籃球運動的喜愛,以及讓自己放松的心理,自發進行籃球運動,就屬于“自愿”。在司法實踐中,口頭約定、免責協議等都能表明當事人是自愿參加并承擔風險。
1.3 學校體育中的自甘風險
2002 年,教育部頒布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中規定,在對抗性或者具有風險性的體育競賽活動中發生意外傷害的,學校已經履行了相應職責,行為并無不當,無法律責任。此規定也可看作是自甘風險規則的雛形[5]。
學校有安全保障責任,根據《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的相關規定:第一,保障學校體育設施安全是學校的法定義務;第二,學校在組織學生參加體育活動時有對學生進行安全教育的義務;第三,學校應結合學校學生的年齡以及身體情況,安排適宜的體育運動,并且對于患有特殊疾病而不適宜參加體育運動的學生給予特別注意,如為這類學生開設體育保健課程等;第四,在發生體育傷害事故時,學校應該第一時間對學生進行救助并及時通知受害人(受傷學生)的監護人。同樣,學生作為學校的主體,也有義務遵守法律規定、遵守學校規定;聽從教師安排,盡可能地避免自己處于危險中;同時,若自身患有疾病或在進行體育運動前感到身體不適,應及時報告給學校。
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若學校盡到了其安全保障的義務,并無過錯存在,那么應當免除學校的相關責任。同時,若學生未盡到義務或存在過錯,那么應當自甘風險;若學生也無過錯,可以結合自甘風險、公平責任原則進行判決。
2 自甘風險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適用問題與建議
通過聚法案例網、裁判文書網等,輸入“學校體育+傷害”并結合“自甘風險”“自甘冒險”“風險自負”等關鍵詞,檢索近10 年來一審、二審的判決文書,共獲得8例,其中適用自甘風險的有5例(見表1)。這里所說的適用是指判決中單獨依據自甘風險原則,或者與公平責任原則、過錯責任原則相結合適用的情況。

表1 判決適用原則(n=5)
2.1 適用范圍的問題
在前文中提到,學校體育由體育課、課外體育活動、課外運動訓練隊和體育比賽以及早操和課間操等構成。不同情況下,自甘風險的使用情況也不同。筆者認為,若在體育課、早操或課間操中發生體育傷害事故,若學生無過錯,則不能適用自甘風險。在學校組織的課外活動、課外訓練隊和體育比賽中發生體育傷害事故,若學校無過錯,并盡到應盡義務,那結合實際情況選擇是否適用自甘風險。在學生自發組織的課外體育活動或體育比賽中發生體育傷害事故,若學校無過錯,并盡到應盡義務,則應當適用自甘風險,免除學校相應責任[6]。因此,由于學校體育的內容不同,導致自甘風險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的適用范圍相對較小,適用起來也相對困難,不好界定適用范圍。
2.2 對于未成年人的適用問題
學校體育的對象是全體在校學生,包含了中小學以及高等學校的在校生,對于年齡問題自甘風險沒有作出相關規定。對于未成年人是否適用自甘風險的問題,在國內外的司法實踐中,并未將未成年人排除在外。有些學生雖然未成年,但其心智較為成熟,對于體育運動的固有風險有認知能力。而且,現在體育發展是大勢所趨,很多家長也會選擇讓孩子從小學習某種體育項目,對于體育的固有風險,學生和其監護人都有認知能力,也自愿參與,這滿足自甘風險的構成要件,根據實際情況應當適用自甘風險。對于未成年人的問題,不能以偏概全,可以進行年齡劃分,也可根據實際情況判定,但若不進行劃分,對于司法實踐來說是一個難題,法官也不好作出判定。但若不結合實際情況,單純以年齡來判定也有失公平。
2.3 能否獨立適用的問題
在筆者檢索到的110件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被認定自甘風險的占4.5%。在8 份案例中,同一案件一審未適用,但二審改判適用的案件有2例。
目前,國內的司法實踐中,很少有獨立適用自甘風險的案件,大多案件都是在適用自甘風險的同時,若雙方都無過錯,則同時適用公平責任原則;或者認定學校在體育傷害事故中存在部分過錯,而同時適用過錯責任原則;或者三種原則混合適用,從而由學校分擔受害人的部分損失。筆者認為,這實際上降低了自甘風險的適用價值,在某種程度上對于學校也有失公平。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若學生自發組織體育活動,學校在無過錯也盡到應盡義務的情況下,應當有受害人自甘風險,免除學校責任。若一味地由學校來承擔賠償責任,則不利于學校體育的發展,對體育的發展也是一種損失。
3 結語
雖然《民法典》確立了自甘風險的法律地位,但對于如何界定其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的適用范圍、未成年人適用范圍以及能否獨立適用等問題,仍然存在爭議和挑戰,這對于自甘風險在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的適用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需對學校體育適用范圍、未成年人適用問題等進行進一步的劃分,完善自甘風險規則。將自甘風險適用到學校體育傷害事故中,有利于學校體育的發展,使開展體育活動的學校不用再承擔賠償責任。《民法典》對于公平責任原則進行了限制,使開展體育活動的學校不至于再按照公平責任原則分擔賠償責任。應明確規定學校的安全保障義務以及學生的義務,這樣更有利于自甘風險的適用。同時,也能夠減少學校體育傷害事故的發生,更好地促進學校體育的發展,加強學生身體素質,從而促進國家體育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