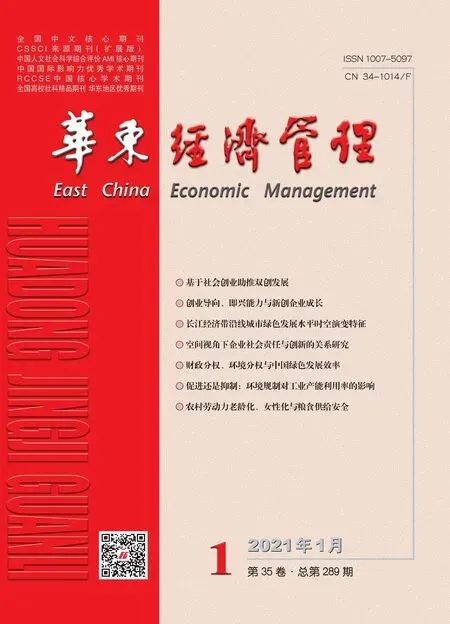長(zhǎng)江經(jīng)濟(jì)帶沿線城市綠色發(fā)展水平時(shí)空演變特征
韓 晶,陳 曦
(北京師范大學(xué) 經(jīng)濟(jì)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一、引 言
2016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guò)《長(zhǎng)江經(jīng)濟(jì)帶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是推動(dòng)長(zhǎng)江經(jīng)濟(jì)帶發(fā)展重大國(guó)家戰(zhàn)略的綱領(lǐng)性文件,標(biāo)志著長(zhǎng)江經(jīng)濟(jì)帶的發(fā)展正式進(jìn)入快車(chē)道。但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經(jīng)濟(jì)的快速增長(zhǎng)和資源的過(guò)度開(kāi)發(fā)使得長(zhǎng)江流域生態(tài)功能退化嚴(yán)重,三分之一的重要湖庫(kù)長(zhǎng)期處于“富養(yǎng)化”狀態(tài),生物完整性指數(shù)接近低端,沿江產(chǎn)業(yè)三廢排放量居高不下,飲用水質(zhì)安全頻頻受到威脅,嚴(yán)峻的環(huán)境狀況成為長(zhǎng)江經(jīng)濟(jì)帶發(fā)展的明顯短板,也成為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最牽掛的問(wèn)題之一。2016年1月,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在重慶召開(kāi)的推動(dòng)長(zhǎng)江經(jīng)濟(jì)帶發(fā)展座談會(huì)上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前和今后相當(dāng)長(zhǎng)一個(gè)時(shí)期,要把修復(fù)長(zhǎng)江生態(tài)環(huán)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hù),不搞大開(kāi)發(fā)。”因此,如何在堅(jiān)持生態(tài)保護(hù)的前提下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環(huán)境改善,探索出綠色發(fā)展的新路子,是擺在長(zhǎng)江經(jīng)濟(jì)帶沿線每一個(gè)城市面前的熱點(diǎn)和關(guān)鍵問(wèn)題。
自1989年大衛(wèi)·皮爾斯首次提出以環(huán)境保護(hù)為核心的綠色發(fā)展理念以來(lái),綠色發(fā)展相關(guān)的研究一直是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之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gè)方面:首先是綠色發(fā)展的內(nèi)涵界定。學(xué)者們?cè)谘芯烤G色發(fā)展時(shí),大多側(cè)重于經(jīng)濟(jì)、生態(tài)環(huán)境和資源的角度,認(rèn)為綠色發(fā)展是三者達(dá)到和諧統(tǒng)一的動(dòng)態(tài)平衡過(guò)程[1-2]。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類福祉、社會(huì)福利也被納入綠色發(fā)展的研究框架之下[3-4],即綠色發(fā)展是指活動(dòng)主體以資源節(jié)約、環(huán)境友好的方式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cái)富、生態(tài)財(cái)富和文化財(cái)富,以實(shí)現(xiàn)自然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包容性增長(zh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