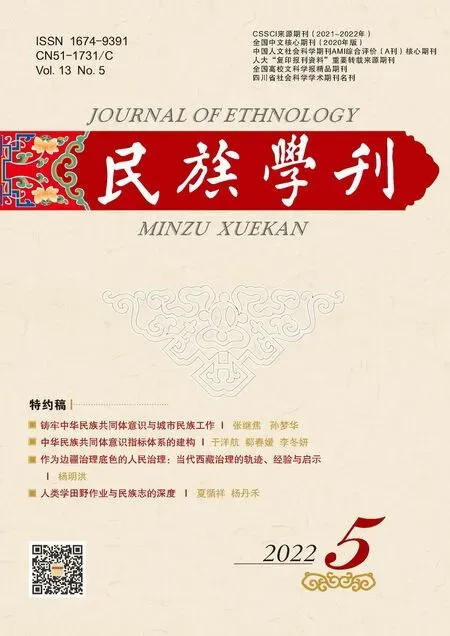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哀牢內(nèi)屬研究
杜周軍 林 科 鐘樂海 劉 陽
“綏哀牢,開永昌”是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上影響深遠(yuǎn)的盛事,秦漢“經(jīng)略西南”,促使哀牢“內(nèi)屬”,由此積淀了兩千多年的永昌文化,就成為了探索建構(gòu)中華民族共同體最為寶貴的歷史經(jīng)驗(yàn),以及促進(jìn)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tuán)結(jié)、興邊富民和共同富裕最為重要的理想原型。哀牢地處我國西南橫斷山區(qū)南部,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條國際商道“蜀身毒道”必經(jīng)之地,古代各大文明都天然地以此地作為交流聯(lián)系的重要樞紐,是古代中國與東南亞、南亞乃至由此走向更遠(yuǎn)的西亞、非洲、歐洲交流的“世界十字路口”。兩千年前,哀牢因族群同源和文化認(rèn)同而逐步內(nèi)屬華夏中原政權(quán),由此基本上確定了我國西南的大體疆界,貫通了中原地區(qū)與西南邊地的聯(lián)系,加速民族融合,鞏固國家統(tǒng)一,助推邊地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全面發(fā)展,直接促進(jìn)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fā)展。本文通過探索哀牢漫長的內(nèi)屬之路,分析其中的民族交流融合、文化互動(dòng)共生的典型案例,希冀重啟這一“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門戶,為建構(gòu)中華民族共同體、區(qū)域發(fā)展共同體和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提供更多的審視與思考。
一、史籍尋蹤:還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演進(jìn)歷程
“哀牢”一詞首現(xiàn)于東漢思想家、文學(xué)批評家王充(27年—約97年)《論衡》一書,在《宣漢》《恢國》《佚文》三篇中各出現(xiàn)了一次。其中《論衡·佚文》提到了東漢孝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冬,成都人楊終(?—100年,字子山)進(jìn)獻(xiàn)《哀牢傳》,“孝明奇之,征在蘭臺(tái)”一事。[1]312《哀牢傳》是東漢校書郎楊終根據(jù)哀牢使臣講述而作的記述哀牢人歷史的最早資料,但卷帙無考,或早已佚失。東漢孝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9年)春,哀牢內(nèi)屬并設(shè)置永昌郡,首次載于《東觀漢記》(60年—160年)“十二年,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眾慕化,地曠遠(yuǎn),置永昌郡。”[2]20東漢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班固(32年—92年)在《東都賦》里也記錄了這一盛況,“春王三朝,會(huì)同漢京。”[3]1364哀牢內(nèi)屬的盛事在后世典籍都悉數(shù)收錄,特別是年代相近的東晉史學(xué)家常璩(約291—約361年)《華陽國志》和南朝宋時(shí)期史學(xué)家范曄(398年—445年)《后漢書》都較為詳細(xì)地記述了哀牢內(nèi)屬和設(shè)置永昌郡前后的事跡。哀牢內(nèi)屬之前不見于被稱為中國“史學(xué)雙璧”的《史記》和《漢書》,疑是因其在內(nèi)屬之前或語言存在溝通障礙,或交通存在山川阻隔,不被中原人士所了解而不得記;亦或是《史記》《漢書》記載之事分別止于公元前122年和公元23年,而這時(shí)的哀牢部落聯(lián)盟正處于發(fā)展時(shí)期,和中原鮮有接觸且名號未定而不得記。哀牢部落聯(lián)盟興起之世正值漢武帝時(shí)期(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哀牢不曾有自己的史書典籍,我們只有嘗試從此時(shí)開始,在浩瀚的歷史典籍中尋覓蛛絲馬跡,以求厘清哀牢發(fā)展脈絡(luò)的同時(shí)探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演進(jìn)歷程。
(一)投石問路:求道西南
1.從蜀宜徑,主動(dòng)經(jīng)營
“張騫通西域”的歷史故事流芳百世,張騫因“鑿空”之舉名垂青史,更因其提及“蜀身毒道”,成功將世人的目光聚焦于中國西南。“蜀身毒道”這條國際貿(mào)易之路直到此時(shí)才進(jìn)入中原人的視野,但其開通之時(shí)可追溯至春秋戰(zhàn)國時(shí)期或者更早,民間“蜀賈”有首辟之功,是中國最古老的國際通道之一,現(xiàn)世譽(yù)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或“南絲路”“西南絲綢之路”。蜀地作為“蜀身毒道”的起點(diǎn),最遲不晚于公元前四世紀(jì)就有民間“蜀賈”將蜀地的“蜀布”“邛竹杖”和絲綢等物品運(yùn)抵哀牢地域,在此以物易物、互市貿(mào)易、互通有無,更有甚者走向更遠(yuǎn)的身毒地界直接交易也未有可知。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國出兵攻占巴蜀,秦滅巴蜀后改行郡縣制,達(dá)到了“富國、廣地、強(qiáng)兵”目的的同時(shí)客觀上加強(qiáng)了中原與西南地區(qū)的聯(lián)系,促進(jìn)了巴蜀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秦始皇一統(tǒng)中國后,秦國經(jīng)營巴蜀已近百年,貫通了直達(dá)滇東北的“五尺道”,加強(qiáng)了對西南地區(qū)的控制。秦滅漢興之時(shí)因?yàn)椤瓣P(guān)蜀故徼”,蜀郡通往西南的官道曾一度關(guān)閉,但不影響巴蜀之民私出西南“故徼”開展民間商貿(mào)活動(dòng)。這是因?yàn)椴煌诒狈酵潦菈χ畤摹叭保戏街衲緰艡诨蚪雍疄橄薜摹搬琛保且粋€(gè)隨著時(shí)空變換、極富彈性的邊界。隨后歷經(jīng)文景之治,漢武帝“威加海內(nèi)”,曾“欲通西南夷,費(fèi)多道不通,罷之。”[4]7288西漢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漢武帝聽取張騫關(guān)于“蜀身毒道”的匯報(bào)和“從蜀宜徑”的建議后,為了“指求身毒國”而“復(fù)事西南夷”。由此開啟了長達(dá)兩百多年由近及遠(yuǎn)、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經(jīng)略西南,在此期間西南各民族文化逐漸相互適應(yīng)、吸收、融合,最后都走上了仰慕漢德而內(nèi)屬和歸附之路。
2.治以故俗,推行郡縣
西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26年分兩期開發(fā)西南地區(qū),第一期止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設(shè)立犍為郡;第二期是在間隔四年后的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開始的,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先后設(shè)置牂柯郡、越雟郡、沈黎郡、汶山郡和武都郡,并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設(shè)立益州郡,至此成就了“卒為七郡”的“非常之功”。并在歸順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分封了夜郎王和滇王,實(shí)行具有郡縣和王國雙軌政體的初郡制。“以其故俗治”為核心理念的初郡制度,是漢朝在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初次設(shè)郡的一項(xiàng)制度,保留各個(gè)民族特有的風(fēng)俗習(xí)慣及人文風(fēng)情,免征賦稅和輕賦,實(shí)行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王、侯、邑長等土官體系與中原王朝的守、令、長平級并行,這就是后世“羈縻制度”的雛形。這是在“無為而治”“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等治國理念下,萌發(fā)的“以人為本”“差異治理”政治思想創(chuàng)新,可以說是中國最早期的“一國兩制”思想。其中,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漢武帝將呂嘉(呂不韋的后人)族人從南越流放到西南,并親賜“不韋縣”,此地與巂唐緊靠哀牢地域,此二縣的設(shè)立是后世“哀牢內(nèi)屬”所下的先手棋。“漢德廣,開不賓。”[3]2849隨著初郡連為一體,又新開通了寬敞的“靈關(guān)道”(也叫零關(guān)道、西夷道、零官道、洱海道)等官道,西南道路進(jìn)一步連接貫通,各族人民大量集群聚落,橫斷山區(qū)的南部形成了暢通無阻的民族走廊和文化通道。中原王朝通過和親通婚、經(jīng)貿(mào)互市、文德教化、徙民實(shí)邊等舉措積極經(jīng)營西南,既鞏固了國家統(tǒng)一,促進(jìn)了興邊富民,又加強(qiáng)了各民族交流融合,最終達(dá)到了“宣示漢德,威懷遠(yuǎn)夷”的終極目的。
(二)順勢而為:哀牢內(nèi)屬
在天下統(tǒng)一觀的施政方針指導(dǎo)下,歷代中原王朝在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施以“仁政”、感之“德化”,越來越多的“徼外”之民漸受熏染、去俗歸德,自愿改變自己原有的風(fēng)俗走上歸附中原之路,逐步融入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促進(jìn)國家統(tǒng)一,進(jìn)一步推動(dòng)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歷經(jīng)秦漢兩百余年“以文化遠(yuǎn)”“以德懷遠(yuǎn)”經(jīng)略西南的文德歸化過程,西南地區(qū)與中原互動(dòng)交往日益頻繁,逐步實(shí)現(xiàn)了族群融通、物資流通、政令暢通、文化匯通的良好局面,逐漸強(qiáng)化的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奠定了哀牢內(nèi)屬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礎(chǔ)。哀牢內(nèi)屬是順應(yīng)“大一統(tǒng)”形勢的必然之舉,史籍中記載的“兩次戰(zhàn)爭”和“兩次內(nèi)屬”表明了哀牢內(nèi)屬時(shí)審慎的心路歷程以及務(wù)實(shí)的明智之舉。
1.兩次戰(zhàn)爭:戰(zhàn)威逼人
(1)平叛棟蠶
巂唐、不韋二縣設(shè)立后涌入了大量來自內(nèi)地的遷徙之民,帶了先進(jìn)的思想文化和技術(shù)工藝,直接促進(jìn)了西南邊地的經(jīng)濟(jì)繁榮、文化昌盛和人民富足,益州郡等徼內(nèi)人民過上了令人羨慕的好日子。但因各族人民風(fēng)俗習(xí)慣、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禮儀秩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族群沖突偶或難免,加之在初郡政策實(shí)施過程中“人為”因素較大,如遇郡縣守令長官清正廉明、勤政愛民則可保一時(shí)一地太平,但是遇上貪官污吏、繁刑重賦就會(huì)引發(fā)一些反抗斗爭甚至武裝沖突。東漢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年),益州郡內(nèi)的西南夷首領(lǐng)棟蠶聯(lián)合滇池、昆明等部落反叛,不僅殺死了長吏,還擊退了益州太守繁勝的鎮(zhèn)壓。次年,朝廷派遣武威將軍劉尚率廣漢、犍為、蜀和朱提四地各族軍民13000人征討,叛軍聞風(fēng)喪膽,棄壘逃散,節(jié)節(jié)敗退至臨近哀牢的不韋縣。劉尚率軍連戰(zhàn)數(shù)月,窮追不舍,在不韋縣與棟蠶叛軍展開了最后決戰(zhàn),戰(zhàn)況十分慘烈,最后棟蠶兵敗被斬。三年的平叛棟蠶之戰(zhàn),期間雖有波瀾,但最終還是以漢軍大獲全勝而平息。斬首7000余人、生俘5700人并繳獲戰(zhàn)馬3000匹、牛羊30000余頭的戰(zhàn)果,讓哀牢人直接見識(shí)了漢朝強(qiáng)大的軍事實(shí)力,從而心生敬畏。
(2)鹿茤之戰(zhàn)
平叛棟蠶的戰(zhàn)爭就發(fā)生在哀牢國境附近,持續(xù)三年之久的戰(zhàn)爭雖然給予了哀牢人極大震撼,但正值哀牢國強(qiáng)盛之時(shí)不可一世,為了擴(kuò)大聯(lián)盟活動(dòng)區(qū)域,開始攻伐臨近的其他部落。作為一方霸主的哀牢王可能覺得直接與漢朝產(chǎn)生正面沖突大可不必,于是選擇剛內(nèi)屬的弱小的鹿茤來敲山震虎,一來可以展露聯(lián)盟不可一世的強(qiáng)大實(shí)力,二來可以試探中原王朝對于內(nèi)屬部落的態(tài)度。建武二十三年(47年),哀牢部落首領(lǐng)賢栗(即扈栗)遣兵乘箄船沿江而下攻打內(nèi)附漢朝的民眾弱小的鹿茤部落。怎料哀牢進(jìn)軍途中突遇雷雨風(fēng)暴,使得河水逆流,狂風(fēng)怒浪將哀牢人所乘竹木筏掀翻沉沒,溺死了數(shù)千人。哀牢出師不利心有不甘,隨后又增派六個(gè)邑王率萬人攻打鹿茤。鹿茤王親自迎戰(zhàn),在漢朝軍民的幫助下殺死了哀牢六王,大破進(jìn)犯的哀牢軍。兵敗鹿茤之后,哀牢人在戰(zhàn)爭中再次感受到了中原王朝的強(qiáng)大威懾力,以及在其庇護(hù)之下免受欺負(fù)的安全感。畏懼中央王朝派出大軍前來討伐,為了避免一場沒有必要發(fā)生的而有可能一觸即發(fā)的大戰(zhàn),哀牢王采取權(quán)宜之計(jì),派遣信使告知越嶲太守,愿意率領(lǐng)所屬族人歸義奉貢,請求內(nèi)屬。
2.兩次內(nèi)屬:歸附漢朝
(1)賢(扈)栗內(nèi)屬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哀牢部落首領(lǐng)賢(扈)栗信守承諾率領(lǐng)所轄的2700余戶1.7萬哀牢人正式歸附中原王朝,被封為君長,在保留其部落首領(lǐng)所有權(quán)益的同時(shí),其轄地內(nèi)的所有人民還是由其管理,每年只需進(jìn)朝納貢。永平十年(67年),東漢中央政府又在賢(扈)栗所轄部落區(qū)域和益州郡西部的不韋、巂唐、比蘇、楪榆、邪龍、云南等六縣基礎(chǔ)上設(shè)立了“益州西部屬國”,委任為官清廉的四川廣漢郡郪縣人鄭純?yōu)閷賴嘉荆畹妹裥暮秃駩邸賴窃谶吙w附的少民族地區(qū)設(shè)立的一種民族管理制度,“稍有分縣,治民比郡”,普遍得到所轄各族人民的擁護(hù)屬國都尉則是屬國內(nèi)的最高軍政主官。
(2)柳貌內(nèi)屬
在同宗同祖“四海為家”的“大一統(tǒng)”思想熏陶下,對于已經(jīng)內(nèi)屬的哀牢人民發(fā)展進(jìn)步較快的現(xiàn)實(shí)情況,哀牢王柳貌心生羨慕。其子扈栗在歸漢18年以來一直得到了善待,埋藏于柳貌心中所有的顧慮日漸消除,歸漢意識(shí)也就日益強(qiáng)化。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全境77個(gè)部落55萬余人,在哀牢國王柳貌率領(lǐng)之下全部歸附東漢中央王朝。漢明帝在哀牢所轄地區(qū)又設(shè)置了哀牢和博南二縣,并與益州西部都尉所轄六縣合設(shè)永昌郡。至此哀牢全部歸附,西南實(shí)現(xiàn)統(tǒng)一,“綏哀牢,開永昌”作為國家盛事,以一場盛大的宮廷慶典被載入史冊。
(三)精心經(jīng)營:永昌治理
我國在西南“極邊之地”設(shè)立了東漢全國第二大郡“永昌郡”,“永昌”之寓意堪比“長安”之盛名,寄托著“邊疆永固、永世昌盛”的美好愿望。范曄盛贊“俾建永昌,同編億兆”[3]2861,郭義恭稱頌“永昌一郡,見龍之耀,日月相屬”。秦漢精心經(jīng)營西南數(shù)百年,終于迎來了“襟滄江而帶怒水”永昌郡的設(shè)立,很早就劃定了我國西南邊疆的大體范圍,加上行之有效的永昌治理延續(xù)千年,成就“殊方異域之地”“西南一大都會(huì)”的美譽(yù),為構(gòu)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1.以故俗治、漸遷其俗
永昌治理沿用“賢人之治”的初郡制度,選用深受哀牢等各族人民愛戴、政績顯著的鄭純?yōu)槭兹翁乩^續(xù)施政倡教,安撫民眾,團(tuán)結(jié)帶領(lǐng)各族人民因地制宜、因俗而治,共同開展民族區(qū)域管理,得到了永昌郡內(nèi)少數(shù)民族群眾的普遍擁護(hù),起到了固邊興民和勤政愛民的表率作用。特別是鄭純規(guī)范施政行為,因地創(chuàng)立哀牢人易于接受的“常賦”而被記載于史籍。“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lǐng),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3]2851西南各族人民在“以故俗治”的潛移默化中自愿“漸遷其俗”,先后慕義貢獻(xiàn)。鄭純?nèi)温毝嘉尽⑻毓灿?jì)十年直至去世,永昌郡內(nèi)各族人民感念其德政,歌頌其美德,建立祠堂世代祭祀他。漢明帝還把他與開國功臣的畫像陳列于東觀(類似于國家圖書館)之中紀(jì)念其“身化蠻夷”之功。永昌徼內(nèi)外各族人民漸遷其俗,主動(dòng)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設(shè)之中。
2.恩威并施、撫順抑逆
哀牢慕義傾服、歸順東漢,設(shè)置永昌郡,諸侯朝覲會(huì)同洛京,為哀牢王頒發(fā)了“哀牢王章”,以及在哀牢施以德政,推行輕徭薄賦政策,毫毛不犯邊地生民,這些都是施行恩義撫順之舉。斬首類牢之類的武裝鎮(zhèn)壓則是開展軍威抑逆的舉措。建初元年(76年),永昌郡哀牢王侯類牢與守令發(fā)生爭執(zhí)后殺死守令,隨即率領(lǐng)3000余哀牢人反叛,還進(jìn)攻了巂唐(今云南永平西)和博南(今云南永平南),一路燒殺搶掠。永昌郡太守王尋逃奔楪榆(今云南大理北)避其鋒芒。漢章帝派人招募永昌各族人民9000余人討伐,其中邪龍縣昆明夷首領(lǐng)鹵承等應(yīng)募加入討伐類牢的隊(duì)伍,一起進(jìn)攻退守博南的類牢。鹵承率隊(duì)一舉大破反叛的哀牢一族,斬殺了最后一位哀牢王侯類牢,被封為破虜傍邑侯,賜帛萬匹。為儆效尤,類牢首級一路傳至洛陽,震懾四方,有效宣揚(yáng)了中央王朝的威嚴(yán)。平叛最后一代哀牢王侯類牢后,哀牢就此滅國,退出歷史舞臺(tái),其族民分流衍化為眾多現(xiàn)代民族。哀牢滅國不僅給心懷“二心”之人發(fā)出威懾信號,增強(qiáng)了中央王朝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進(jìn)一步維護(hù)了邊境的統(tǒng)一與和平,營造了安定融洽的環(huán)境。南方絲綢之路廣闊官道隨即貫通,徼外敦忍乙王、撣國王、焦僥種夷紛紛遣重譯奉獻(xiàn)奇珍異寶,中央王朝均回賜印綬、金銀,可謂是“威加四海”“德服天下”。
二、族源神話:有待挖掘的中華民族文化認(rèn)同富礦
“神話終止于何處?而歷史又從何處開始?”[5]58愚認(rèn)為神話終止于歷史被文字記載之時(shí),歷史從神話開始直到被文字記載時(shí)即成為信史。流傳于西南多個(gè)民族的“九隆神話”作為哀牢族群沒有文字記錄、沒有史料留存的集體記憶,是哀牢地域內(nèi)眾多民族的自我認(rèn)識(shí)和歷史樣態(tài),也是解讀哀牢內(nèi)屬對中華民族文化認(rèn)同的富礦。文化認(rèn)同形成凝聚合力,為民族融合打下思想文化根基。“九隆神話”被詳盡記載于《華陽國志·南中志》《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等漢籍正史中,標(biāo)志著趨于成熟、基本定型的哀牢神話完成了歷史化的蛻變,是哀牢內(nèi)屬尋求民族認(rèn)同的重要表現(xiàn),也蘊(yùn)含著哀牢等各族人民認(rèn)同中華文化和合向心的隱喻。
(一)兩個(gè)版本傳承
千百年來“九隆神話”極富生命力,跨越了漫長的歷史考驗(yàn)而不絕于史書,至今還在云南白族、布朗族、彝族、傣族等少數(shù)民族中傳頌。由于文本記載和口耳相傳存在差異,于是就有兩個(gè)版本傳承于世。兩個(gè)版本的變與不變之處,都是研究中華民族文化認(rèn)同的標(biāo)本和活化石。
1.文獻(xiàn)文本
漢籍文獻(xiàn)傳承的神話作為被寫定的歷史,具有相對較強(qiáng)的穩(wěn)定性和較全的完整性,有助于讀者重構(gòu)歷史場景和還原歷史面貌。自東漢首載“九隆神話”的《哀牢傳》問世,被后世歷代的正史和方志悉數(shù)收錄,雖然也存在文獻(xiàn)編著者的不斷加工,但整體呈現(xiàn)出文獻(xiàn)特有的歷史傳承固態(tài),已由歷史文本轉(zhuǎn)變?yōu)榇私庾x的文化標(biāo)本。“九隆神話”被反復(fù)記錄于冊,提醒著后來人重視哀牢內(nèi)屬這段歷史,學(xué)習(xí)借鑒這一中華民族文化認(rèn)同的典型案例。
2.口耳相傳
口耳相傳的神話故事存在較大差異,后世覆蓋添加、附會(huì)改編在所難免,在不同民族中也就會(huì)有不同的版本,但對比看來基本上都保留了存世文獻(xiàn)基本的人物設(shè)置。流傳“九隆神話”的眾多民族中,只有白族現(xiàn)存的神話傳說接近于漢籍文本原貌,很有可能是漢籍經(jīng)典文本廣泛傳播后又回流至民間而深入人心,最終內(nèi)化為白族共同的心理認(rèn)同。這一現(xiàn)象也從側(cè)面反映文化認(rèn)同是一個(gè)雙向互動(dòng)的過程。
(二)兩次文化整合
回顧漢籍中所記載“九隆神話”的文字,明顯存在文化積沉的現(xiàn)象,不像是一時(shí)或一人完成的。“九隆神話”首次被翻譯成漢文前,至少經(jīng)歷了兩次文化的整合,最終為了實(shí)現(xiàn)哀牢內(nèi)屬的現(xiàn)實(shí)需要,又被精心加工過。這兩次文化整合是哀牢族群心之所向的集體無意識(shí)記憶,也是對于中華民族文化認(rèn)同的集中展現(xiàn)。文化在整合和被整合之中,得到了相互接受和被接受。
1.引入龍文化
哀牢人崇拜龍,自稱是龍的傳人,其祖先就是他們的始祖母與“沉木”化龍的始祖父所生的,為了實(shí)現(xiàn)內(nèi)屬的愿望,還托詞是龍寵愛的傳人。從其他感生神話看,婦人觸沉木而孕,即完成了始祖母崇拜的感生神話敘述,后來隨著龍文化在橫斷民族走廊滲透,哀牢人開始接受了以“龍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認(rèn)同,將“沉木”化龍追認(rèn)為始祖父,從此以“龍的傳人”自居。“沉木化為龍”是九隆神話中最為精彩傳奇之處,龍的出現(xiàn)成為族群認(rèn)同的重要依據(jù)。九隆因?yàn)榈玫烬垺绑露铩保鳛椤褒堖x之子”被推選為首任哀牢王。在崇龍觀念影響下,哀牢族人“刻畫其身,象龍文”[3]2848,在身上紋上龍紋,積極展示龍圖騰,是龍文化的繼承者、傳播者,將其作為族群身份認(rèn)同的外顯標(biāo)志。
2.與王權(quán)整合
哀牢的始祖母名叫“沙壹”,未曾記載始祖父的名字。只知道母親的名字,不知道父親的名字,暗指“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會(huì)。“龍父”的出現(xiàn)暗指母系社會(huì)向父系社會(huì)的過渡。再到“九隆為王”,則是哀牢建國的現(xiàn)實(shí)需要和歷史追認(rèn),這是與王權(quán)結(jié)合的政治文化表達(dá),有助于哀牢王室權(quán)威的塑造和維系。“王”的概念應(yīng)該出現(xiàn)于哀牢國興起前后,這是哀牢王族追溯政權(quán)來歷神圣性和正統(tǒng)性,直接在原始感生神話基礎(chǔ)上再次創(chuàng)作構(gòu)擬的。神話與政權(quán)的結(jié)合,明顯是哀牢王族作為一支強(qiáng)有力的政治力量強(qiáng)勢介入而產(chǎn)生的。九隆被“共推以為王”說明哀牢形成了血緣型社會(huì)組織,作為幼子而王,這是幼子繼承制和“貴小”的體現(xiàn),也可以在華夏族的祖先傳說“黃帝幼子玄囂(青陽)繼大位”中找到同源性。“分置小王”“邑居”則說明哀牢實(shí)行分封性質(zhì)的地緣型、軍政制社會(huì)組織。
(三)雙向文化認(rèn)同
哀牢內(nèi)屬前后流傳于中原和哀牢地區(qū)的“九隆神話”是一個(gè)雙向文化認(rèn)同的過程,正因?yàn)橥垂沧妫鲃?dòng)加入中華民族的文化認(rèn)同譜系,在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共創(chuàng)、共生、共享發(fā)展成果。九隆神話在哀牢與中原雙向文化認(rèn)同下,經(jīng)歷了文化傳播交融和積淀整合發(fā)展等一系列漫長的演進(jìn)過程而形成的,是一個(gè)立體多維文化整合的典型,在滿足民間信仰、塑造社會(huì)形態(tài)和鞏固政治話語等不同層面發(fā)揮著文化認(rèn)同的關(guān)鍵性合力。
1.吸收中原文化
“九隆神話”引入龍文化是哀牢對中原文化的認(rèn)同和吸收。中原典籍《楚辭·天問》中的“水濱之木,得比小子”和《呂氏春秋·去私》中的“堯有子十人”或許給予哀牢人創(chuàng)立“九隆神話”提供了足夠的靈感,這是中原文化在哀牢族群意識(shí)的反映。九隆神話中的“沈木”即沉木,“沈”和“沉”二字從漢代開始隸變分離。沉木是一種祭祀儀式,沉祭是從夏朝開始興起的祭祀水神或河神的儀式,因向水中投祭品而得名,祭品包括牛、羊、物品甚至人。作為沉木的木必是貴重之物,疑是獨(dú)木舟、木筏,或是雕刻有龍形圖案的龍舟。舟船是涉水捕魚必備的重要之物,《物原·器原》記載“伏羲始乘桴,軒轅作舟楫”,說明舟船起源很早。“沉祭”這一古老儀式和制造舟船這一實(shí)用技術(shù),早已被以“捕魚”為生的哀牢人學(xué)習(xí)借鑒。哀牢始祖母說“鳥語”但能聽懂“龍語”,而“龍語”從文獻(xiàn)敘述來看明顯是漢語的表達(dá),這說明哀牢受中原文化影響較大,學(xué)習(xí)過漢語,能聽懂漢語。
2.接納哀牢文化
將哀牢文化寫進(jìn)正史,是中原王朝對哀牢的文化認(rèn)同和接納,被人們所熟知。哀牢文化以及集其大成的永昌文化被傳承至今,表明了作為中華文化重要一支被認(rèn)可和重視。“九隆”二字是鳥語的音譯詞,借用漢字轉(zhuǎn)寫鳥語“背和坐”的語音,不能用漢字的意思去理解。文獻(xiàn)中直接記錄了哀牢語言,沒有追求漢語意義的理解,保持了哀牢文化的獨(dú)立性。這就進(jìn)一步表明哀牢先民與中原文化有著密切聯(lián)系同為龍的傳人,隱喻其文明實(shí)質(zhì)是與華夏文明共通的。中原文化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接受與哀牢共享“龍的傳人”這一獨(dú)特殊榮。哀牢內(nèi)屬時(shí)就以龍最寵愛的傳人為理由,求得中原王朝的認(rèn)可并如愿歸附,還獲得一致贊許和崇高嘉獎(jiǎng)。
三、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共生構(gòu)建中華民族共同體
橫斷山區(qū)作為最為古老的民族走廊、文化通道,眾多族群相同、文化相似、習(xí)俗相近的不同民族長期在此共生共存,形成了“大雜居、小聚居、交錯(cuò)居、互嵌居”的民族分布格局,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離彼此、相互依存”的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共同體,這是自古及今在中華大地上生活、繁衍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締造的奇跡。文化共生是多民族交往共存共榮的必然選擇,也是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必由之路。哀牢內(nèi)屬經(jīng)歷了相互碰撞、雙向吸收、彼此融入、同生共長的漸進(jìn)過程,經(jīng)歷了陣痛、融洽、互利、平衡等不同階段的動(dòng)態(tài)演進(jìn),最終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才得以有機(jī)會(huì)協(xié)同發(fā)展,共同開發(fā)祖國錦繡河山,攜手創(chuàng)造中華優(yōu)秀文化。
(一)文化圈層互動(dòng)
哀牢內(nèi)屬作為中華民族族群推進(jìn)及地緣疆域推進(jìn)過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是以強(qiáng)大的中原文化為內(nèi)核圈層通過不斷凝聚周邊各民族,從而逐步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典型縮影。隨著中央政權(quán)對邊疆治理的深化和中原文化對邊疆地區(qū)的輻射,西南各民族同胞團(tuán)結(jié)協(xié)作不斷增強(qiáng)了中華文化的向心力,日益深化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從民族群體和文化圈層視角來探討“中原”和“西南”之間的民族文化互動(dòng),有助于理解多元文化共生的演化過程。不能只從行政疆域或是政權(quán)中心的角度來理解中原,而要更多地從民族文化分布的核心區(qū)和輻射區(qū)動(dòng)態(tài)看待中原。中原文化具有高勢能的優(yōu)勢,擁有較強(qiáng)的向心力和影響力,可以像水波漣漪一樣向四周發(fā)散,當(dāng)然面對不同的環(huán)境,對外影響程度也會(huì)呈現(xiàn)不同的遞減趨勢。中原民族文化圈不斷向外輻射,并形成了以中原為核心,不斷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優(yōu)勢,以此加深不同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認(rèn)同。西南民族文化圈因?yàn)榈乩憝h(huán)境的隔絕,相對比較封閉,加上民族復(fù)雜且相對獨(dú)立,是一個(gè)文化勢能相對弱小的復(fù)合型多元民族文化圈。隨著中原文化對西南由北向南、由近及遠(yuǎn)、由淺入深的影響,最終增強(qiáng)了西南民族對中華文化的認(rèn)同度,逐漸奠定了“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形成和發(fā)展的基礎(chǔ)。哀牢內(nèi)屬即可看作是“中原”和“西南”文化圈層互動(dòng)融合直接促成的結(jié)果。
(二)多元一體發(fā)展
西南各民族經(jīng)過漫長歷史發(fā)展,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之所以團(tuán)結(jié)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jīng)濟(jì)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tuán)結(jié)統(tǒng)一的內(nèi)生動(dòng)力。”[6]各民族在相互交融中深化了中華民族意識(shí),在中央政權(quán)的治理下結(jié)成文化相通、血脈相融、命運(yùn)相連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秦漢經(jīng)略西南形成的諸多經(jīng)驗(yàn)客觀上促進(jìn)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發(fā)展。其中,促成哀牢內(nèi)屬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一體化”發(fā)展的經(jīng)驗(yàn)包括:一是因俗就俗。在不改變原有統(tǒng)治方式、管理體制的基礎(chǔ)上,封賞初郡地區(qū)原有的王、侯,團(tuán)結(jié)貴族進(jìn)行聯(lián)合統(tǒng)治。二是采用各類傾斜性政策。通過免征賦稅、輕賦稅、厚賜贈(zèng)帛減少初郡地區(qū)的負(fù)擔(dān),增強(qiáng)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人民對中央王朝以及中原人民的好感,從而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民族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三是促進(jìn)交通聯(lián)通。打通邊區(qū)通往內(nèi)地的道路,以交通促進(jìn)初郡地區(qū)與其他地區(qū)的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四是實(shí)施移民屯墾政策。通過招募選派內(nèi)地人到初郡地區(qū)屯墾,在保證了初郡地區(qū)自給自足的同時(shí)又傳播了內(nèi)地地區(qū)的先進(jìn)生產(chǎn)經(jīng)驗(yàn)。五是選拔任用清官良吏。通過選派廉潔官吏到初郡地區(qū)建功立業(yè),達(dá)到政令暢通、維護(hù)統(tǒng)一、增強(qiáng)信賴的目的。六是促進(jìn)民心相通。通過在初郡地區(qū)辦學(xué)興教,傳授先進(jìn)的生產(chǎn)技術(shù)和思想文化,促進(jìn)初郡地區(qū)人民與內(nèi)地人民之間民心相通,促成文化認(rèn)同和文化共生,“真正實(shí)現(xiàn)以文載道化人、以德鑄魂育人”[7]86。
(三)和而不同共生
“‘和諧’既是我們追求的終極理想,又是我們實(shí)現(xiàn)這一終極理想所需的手段。”[8]104哀牢經(jīng)過中原文化幾百年的浸潤,期間的民族融合是一個(gè)漸進(jìn)、平緩進(jìn)行的過程,經(jīng)歷和而不同、文化共生演進(jìn)后,走上了內(nèi)屬的必然之路。司馬遷在親自游歷考察西南,收集了大量少數(shù)民族資料后,首創(chuàng)了民族史,很有見地的感慨道“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勾吳,兄弟也。”[4]2490哀牢和炎黃子孫同屬一脈,同為龍的傳人,研究哀牢內(nèi)屬過程中的民族關(guān)系,實(shí)際上就是探索西南各民族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部分的發(fā)展路徑。因?yàn)椤皬V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禮記·王制》),各民族在不斷遷移融合的過程中,又產(chǎn)生新的不同民族。現(xiàn)在世居哀牢故地的民族至少包括彝族、白族、傣族、壯族、拉祜族、佤族、景頗族、布朗族、德昂族、怒族等10多個(gè)民族。受橫斷山區(qū)地形地貌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影響,由哀牢分化出來的后裔民族呈現(xiàn)垂直立體化分布:白族、壯族和傣族生活在河谷平壩,彝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和景頗族生活在低山地區(qū),怒族生活在高寒山區(qū)。中華民族共同體兼容并蓄的特性,注定其必然具有絢麗多姿的風(fēng)采,這是眾多民族同源異流和異源合流融合發(fā)展的結(jié)果。
哀牢內(nèi)屬千古盛事,流傳至今不絕于史書,永昌盛名馳名中外,暢達(dá)南方絲綢之路。千百年來西南各族人民秉承“天下一家”“四海為家”的理念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在官方主導(dǎo)推動(dòng)和民間自發(fā)推進(jìn)的雙軌并行下相知相交相吸,實(shí)現(xiàn)了商品貨物的互通有無和技術(shù)技藝的吸收借鑒,走上了共生共融共長、和睦和諧和平的發(fā)展之路,促進(jìn)了西南各族人民生產(chǎn)生活的聯(lián)動(dòng)發(fā)展和思想文化的共同進(jìn)步,共同書寫了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波瀾壯闊的西南歷史畫卷。秦漢經(jīng)營西南始為求道,后得一統(tǒng),在“中原”與“西南”圈層互動(dòng)融合影響之下,哀牢因文化認(rèn)同求得內(nèi)屬,進(jìn)而積極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具有典型的征候意義。哀牢內(nèi)屬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fā)展作出了獨(dú)特的原型貢獻(xiàn),深刻詮釋了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共同發(fā)展的宏闊理論和各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偉大實(shí)踐。從史籍脈絡(luò)和神話隱喻中縱橫梳理哀牢內(nèi)屬尋求中華民族認(rèn)同歷程的方法,以及通過“文化圈層互動(dòng)、雙向文化認(rèn)同、多元一體發(fā)展以及和而不同共生”分析哀牢內(nèi)屬中華民族的相關(guān)理論,同樣可以用于探索橫斷山區(qū)其他民族乃至其他區(qū)域的各個(gè)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經(jīng)驗(yàn),與此同時(shí),也可以為進(jìn)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以及構(gòu)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區(qū)域發(fā)展共同體和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提供經(jīng)典案例借鑒。職是之故,對史籍記載的民族融合線索以及學(xué)界關(guān)注的族源神話問題加以系統(tǒng)梳理和探討,其學(xué)術(shù)理論意義及其現(xiàn)實(shí)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本文淺嘗輒止,意在拋磚引玉,更期與志合者不斷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