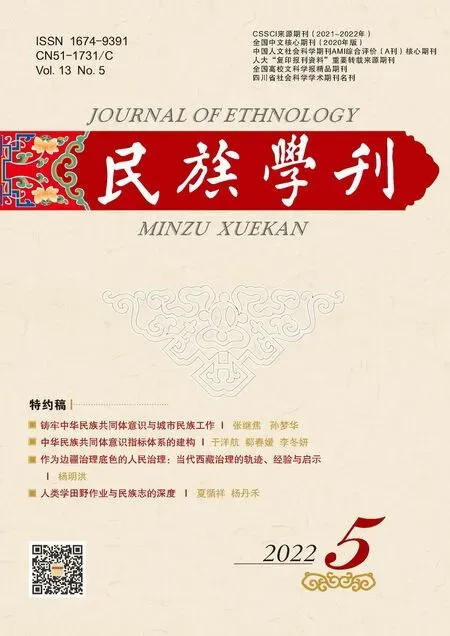全球化下的多樣時間呈現與現代時間反思:凱文·伯斯的時間研究
木粲成
時間是人類經驗與實踐不可或缺的基本維度,[1]也是多學科長期關注的一個關鍵議題。[2]人類學的時間研究曾經更注重整體、孤立、差異化地描繪與比較不同社會文化的時間,而今,全球化與現代化下多樣時間在具身實踐和不同場景之中的交織、沖突、協調已逐步成為其研究重點之一。①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人類學系教授凱文·伯斯自1989年起投身相關領域,陸續出版了《任何時間都是特立尼達時間:社會意義與時間意識》[3]《時間之物:事物如何塑造時間性》[4]《時間盲目:感知其他時間性面臨的問題》[5]三部專著和一系列論文,通過對全球化下多樣時間的呈現與現代時間的反思,有力地推動了時間人類學[6]的當代進展。鑒于其作品尚未引起中文人類學界重視,筆者將依托時間人類學的基本脈絡,對集中體現伯斯研究成就的三部著作予以梳理,并指陳其洞見,以資后續研究參考。
一、21世紀以前時間人類學的基本進展
全球化伴隨著人、物、技術、觀念、制度在世界范圍內的加速流動,其中也包括歐美地區逐步確立起來的現代時間體系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從14世紀到19世紀中后期,在資本市場擴張、民族國家建設、科學技術革命的催動下,歐美地區逐步發展出了以鐘表-格里高利歷為主導的計時方式,以工作-休閑二分法為核心的工業時間紀律,以持續加速為特征的生活節奏,以及以社會進步為主調的歷史意識與未來觀念時間從人們的思想與實踐過程中被高度地抽象出來,并被賦予了“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進步”的文化意義。②隨著西方貿易、傳教、殖民活動在世界范圍內的鋪開,上述時間技術、時間制度、時間觀念逐步在非西方世界傳播,并通過19世紀中期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交通與通訊技術飛躍,進一步加強了其全球影響。③
在全球化過程中興起于歐美的現代人類學,最初以非西方或古代社群為主要研究對象。“他者”的時間技術、制度、觀念,作為富有跨社會文化比較意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很早就進入了人類學的視野。從1874年英國科學促進會《人類學的記錄與詢問》將計時方式列入人類學調查的必要項目,到1960年代布迪厄對卡比爾人時間意識的討論,人類學積累了包括采集漁獵、農耕、畜牧社會在內的大量時間民族志與歷史材料,④并通過它們與歐美工業社會時間的對比,逐步形成了非工業社會的時間范型。各式各樣的非工業社會被認為在計時方式上更依賴自然現象與具體人類活動,不夠精確化、數值化、抽象化、商品化,其日常生活缺乏分秒必爭的嚴苛時間紀律,其社會的相對穩態則呼應著一種漠視時間流逝、重視過去或現在而忽視未來的基本特點。⑤在多樣時間類型的比較中,人類學也逐步確立起了時間受社會文化建構;不同人群的計時方式、社會節奏、生命歷程、過去-現在-未來觀念因生態環境、生計方式、社會結構、信仰觀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時間不只是均質、量化的時長測量單位,也具有豐富的社會文化質性;要注重從被研究者角度呈現其對時間的理解等一系列基本觀點。⑥
這些成果極大地拓展了關于時間社會文化多樣性的認識,也促進了對現代時間的反思,但也留下了很多拓展空間。其一,在社會文化有機整體論的影響下,時間意識常以全社會成員整體一致的式樣被呈現,社會內部的時間分層、差異與互動并未成為研究重點;其二,由于社會文化機械決定論的影響,時間的實踐性、場景性、策略性未被突出;其三,即便現代時間體系早已影響了人類學家們所描繪的那些非西方社會,但非歷史、重差異、本質化的靜態文化視角,使得其全球在地化的狀況并未得到深究;其四、由于主要注重探尋他異的時間,現代時間更多被用作粗略的、隱含的、甚至理所當然的解釋或比較尺度,對其予以細致探討或系統反思的工作有所欠缺;其五、因疏于結合跨學科的時間研究成果,人類學的時間本體論與認識論基礎并不穩固,這與對現代時間的反思不足一起,助長了時間表征的形而上學化與他我時間的極端相對化傾向。⑥
從1970到1990年代,結構馬克思主義、實踐理論、政治經濟學派、后現代與后殖民主義引發了對社會文化有機整體論、非歷史的孤立社會與文化本質化視角、以及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⑦隨著新自由主義對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推動,全球化與現代化下的社會互嵌、文化交融、權力失衡、生態危機漸受重視;⑧此外,注重兼顧跨學科成果的認知人類學持續跟進著對人類基本分類范疇的研究。⑨在此綜合影響下,同一社會內部存在多種相互關聯甚至彼此沖突的時間類型的觀點開始被提出;多樣時間維度內嵌于具身活動及其具體場景的實踐視角逐步受到重視;民族國家與工商業化下的時間特點得到更為細致的討論,反思現代時間觀如何影響了人類學理論與民族志呈現的作品也陸續登場;考察全球化下非西方社會時間的現代變遷與討論古代文明體系時間政治的研究也開始出現;此外,人類可能享有普同的基本時間認知機制,需審慎對待時間認知極端文化相對論的主張也被明確提出。這些成果進一步推動了人類學的時間研究,也使其從整體、孤立、差異化地描繪與比較不同社會文化的時間,開始轉向探索基于一定(可能普同的)時間認知機制的多樣時間在具身實踐過程與特定場景中的交織、沖突與協調,這一視角既被運用到古代文明或傳統社會,更被拓展到全球化與現代化背景下的時間研究,“時間人類學”的提法也于這一時期正式登上人類學舞臺,與同時期逐步發展起來的時間社會學等多種學科產生著交叉與呼應。
二、凱文·伯斯的“時間三部曲”
伯斯于1980年代末在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人類學系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受社會人類學與心理人類學訓練,因為機緣巧合地交叉閱讀到加勒比研究專家弗萊利希(Morris Freilich)對特立尼達人時間取向的討論,康德對先驗時間結構的剖析,以及陶西格(Michael Taussig)曾簡要提及的資本主義時間商品化,從而產生了對時間問題的興趣。[3]xi1989年,他決定奔赴特立尼達開展以時間意識的社會建構為論題的博士論文田野調查,由此正式開始了他的時間研究之旅。這些學術背景與民族志區域起點,使得他的研究在繼承與發揚上述時間人類學成就的基礎上,更混溶了美國人類學注重復雜社會研究的傳統,以及南美區域研究注重全球政治經濟過程、多元文化交互與霸權批判的風格。他將這些影響融匯于對全球化下多樣時間的呈現與現代時間反思,并陸續推出了三部著作。
(一)任何時間都是特立尼達時間:全球化下地方社區的多樣時間及其互動
伯斯基于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第一部專著《任何時間都是特立尼達時間》于1999年問世。其研究點是加勒比海南端特立尼達島上一個被化名為阿納馬特(Anamat)的村莊,它擁有漫長的被殖民史,以小農種植和雇傭工作為主業,由克里奧人和印度人共同組成。[3]6伯斯認為,時間受社會文化建構,它不僅是人們用以思考周遭循環和變化的一種觀念,也是組織活動和協調社會關系的一種手段,它既從活動中產生,也被應用于活動的展開,從根本上說,“每一個具有節奏或循環的活動都會產生相應的時間模式”,[3]9而在阿納馬特這樣一個長期深受全球歷史影響、工農互嵌、文化復合、族群雜糅的復雜社區,多樣時間的分布就顯得更加突出。在他看來,那句常被當地人掛在嘴邊的“任何時間都是特立尼達時間”(any time is Trinidad time)無疑是對這種時間多樣性的集中體現。[3]2
伯斯以一種細致有加兼備系統的方式,考察了這一社區中多樣時間的共存、互動及其社會建構。他首先回顧了特立尼達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政治經濟變遷對阿納馬特的影響,指出嵌入全球聯系的社區歷史深刻塑造了當地的生計方式、社會分工和人口結構,也帶來了人們因不同時期的勞動經歷形成的時間觀念代際差別。[3]53隨后他將重點從歷史轉入現實,剖析了村內的多樣職業牽涉的多樣時間節律,從家務勞動、各類農業勞動到零時務工、小型客貨運、經營商店,每種職業產生的節律有所不同,每種職業都需應對多樣節律的交織,而且許多人兼營著多種職業,這使人們隨時需要應對大量的時間沖突與協調,但由于大部分工作都具有一定時間靈活性,給時間協調與工作順利開展留下了余地。[3]76其后,伯斯探討了村內多樣時間觀念的社會角色分布,他指出,由于當地時間多樣且靈活易變,特定時間模式實際上并不能完全嚴整地對應于特定社會角色,但人們還是傾向于按照年齡、性別、地位將特定時間模式或時間期待貼附在特定社會角色上,并據此來展開與他人的互動。[3]93接下來,伯斯考察了制度化情境中的時間協調,呈現了如監工、宗教專家等在特定機構中擁有權力的人物如何負責維護與行使相應機構的時間規定,以及這些時間規定如何可能被人們自覺遵循,但也可能被脅迫推行或遭到隱秘或公然的抵抗;與之相反,狂歡節等節慶場景則表現出制度化時間的結構性對反,其中沒有任何機構或個人有權掌控時間,時間規定會遭到普遍的不敬與蔑視。[3]120最后,伯斯轉向了對非制度化情境中的時間協調的探究,他指出,社區內的日常生活其實更多地是在缺乏正式時間規定的狀況下展開的,而面對多樣的時間差異與頻繁的時間沖突,人們傾向以兩種基本方式加以應對,并隨之形成兩種不同的社會關系后果:其一,通過運用“任何時間都是特立尼達時間”等習語來模糊時間,或主動變更時間,時間差異與沖突會被緩和,社會關系中的凝聚力隨之加強;[3]141其二,通過強調性別、代際、職業、階級、族群的時間差異與時間刻板印象(stereotypes),或明確拒絕作出時間讓步,時間差異與沖突被公開呈現甚至放大,與之相應,社會分歧被突出,社會關系中的對抗性也隨之強化。[3]162
通過上述考察,伯斯認為,他在這個特立尼達社區中發現的狀況實際上反映了全球化下大多數復雜社會的時間特點:多樣時間既分布在不同的性別、代際、族群、職業、階層上,也分布于不同的機構與場景中,它們隨著日常生活的展開不斷交織、沖突、協調與變換,使社會關系也隨之處在對抗與團結的持續辨證過程當中。[3]166據此他強調:“正如全球化下的文化理論已經從將文化描述為同質化轉變為理解各種不同共享觀念的分布和相互作用,對各種時間觀念的研究也應從追求對某一個社會之時間的特征化轉向對多樣時間及其相互關系的討論”。[3]4而從特立尼達的這份研究經歷中獲得的對時間多樣性的洞察力,也給伯斯的后續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時間之物:全球化下主導式計時方式的認知塑造及其具身后果
在關于時間的第二部專著《時間之物》中,伯斯將議題集中于時鐘與西歷對時間認知的影響,把他對全球化下時間狀況的討論推向了更廣闊的領域。他認為,時間認知必須依賴周圍的環境或物,而其中有些物則是人造的,比如時鐘和西歷,這些被用以辨認時間的人工制品在歷史中充分凝縮了一系列特定的認知考慮與社會權力關系,并隨著全球化的過程廣泛散布和高度具身化,使人們的時間認知越來越無意識地依賴它們,這既給使用者帶來便捷,但也導致了相應的認知能力弱化與其他更為嚴重的社會與生物后果,而若想克服這些缺陷,就需要揭示上述過程與局限,以喚起人們對時間多樣性的敏感。[4]1-2
為闡明上述觀點,伯斯充分調動了民族志、歷史、心理學、社會理論、生物學的相關知識。他首先綜合了心理學的認知工具研究、薩丕爾-沃爾夫假說關于語言塑造認知的觀點與馬克思對商品拜物教的討論,指出時間認知工具既協助但也限制認知,而且可能造成使用者對其中所蘊含的認知原則與社會關系的無知。[4]5-16他認為,反省時間認知工具局限的關鍵在于識別出與實踐共同體相關的多樣時間及其關系,而亞當(Barbara Adam)的“時間景觀”(timescapes)與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節奏分析”(rhythmanalysis)理論恰都旨在發掘從身心、環境到社會文化的多樣時間及其復雜互動,因此可被綜合用作這一探索任務的基本方法。[4]31-32
基于上述視角,伯斯系統梳理了時鐘與西歷的演變與傳播,指出它們混溶了源于不同文化體系的時間認知原則,在多樣時間景觀中武斷選取了一些日漸脫離具體環境的特定周期,還合并了時機(timing)把握與時間持續(duration)度量,以至弱化了人們對環境中多樣時間線索的感知。[4]68,96為展現比較,伯斯還提供了一系列來自中世紀歐洲和當代特立尼達的時間認知案例,強調時間認知可以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協同參照天象物候、動物活動、植物枯榮、人類社會行為等豐富線索來實現,時鐘與西歷無非是這多樣時間景觀中的一種。[4]67而且,恰因時鐘與西歷指示的主要是脫離具體情境的時間,所以單獨參照它們有時并不能很好地把握實際任務所需靈活應對的多樣時間沖突與權變。[4]117-118據此,伯斯重申在時間認識論層面:“有必要讓時間是語境的、過程的、情境的,正如身份等其他問題已經開始從這些角度來看一樣。”[4]118
接下來,伯斯借助時間生物學的成果,對全球通用時鐘與西歷的負面后果展開了有力批判。他指出,由于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斷旋轉著的地球上,因此協調世界時、交通-通訊技術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合力加劇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其實不能真正造就“一個扁平的地球”(a flat earth),[4]152而是帶來了多樣時間的沖突:一是不同地方時之間的沖突,這主要表現在如紐約、倫敦、東京等全球性城市的時區因其政治經濟影響而擁有讓世界上其他區域扭曲自己的地方時間并依據前者來安排時間的能力,從而導致了從屬地區的時間紊亂;[4]133,150二是社會節奏與生物節奏的沖突,這主要表現在夜班工作與跨時區長途飛行會嚴重擾亂日常環境(如晝夜循環)與人體多樣荷爾蒙激素循環(如皮質醇、促甲狀腺素、褪黑素)的良性協調,以致產生了一系列健康危害、藥物依賴與公共風險。[4]130-148據此,伯斯諷刺道,那些強調空間壓縮而忽視時間沖突的全球化社會理論實際上只描述了一種“沒有球體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without a globe),[4]153并以此提請人們不要忘記自己乃是生活在一個不斷旋轉著的地球上,從而也隨時隨地需要具身地應對與周圍環境的良性時間協調。
最后,伯斯簡要回顧了國際計量局(BIPM)如何對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若干銫原子鐘數據加以協調而規定出“秒”這一單位,以及國際電信聯盟無線電通信部門(ITU-R)近年來關于取消閏秒的爭論,指出目前的全球計時標準與其說是測量的產物不如說是國際機構協議的結果,[4]156而且它已幾乎要將時間測量從地球自轉中徹底解放出來,極度逼近自愛因斯坦相對論誕生以來就已被物理學家拋棄的牛頓絕對時間理想。[4]160據此,伯斯強調,推動計時體系不斷標準化的主要動因其實并非技術進步,而是大型機構希望不受環境限制地控制和協調遠距離活動的愿望[4]163,他將這種過程稱之為“漸進中的認知同一時間性(homochronicity)與地球時間的終結”[4]155,以提醒人們對全球現代計時體系遮蔽多樣時間與掩蓋權力關系的局限保持警覺。
(三)時間盲目:全球化下的現代時間霸權及其多樣時間遮蔽
伯斯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時間盲目》中,把他對全球化下多樣時間的呈現與現代時間的批判推進到了學術反思領域。伯斯強調,源于西歐的鐘表、日歷、紀年法所構成的現代計時體系已成為一種讓世界上所有時間都需以它為尺度來調校的“霸權校準”(Hegemonic Calibration),它帶來了均質、空洞、統一時間觀念的自然化,也讓“同一時間性”滲透于包括人類學在內的各個領域,威脅乃至扭曲著人們對時間多樣性的理解與呈現。[5]30他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時間盲目”(time blind),并依托他的特立尼達時間研究經驗,在民族志時間呈現、時間生物學、勞動時間論、記憶和未來研究等領域檢視了時間盲目的具體表現,探索了克服它的可能方法。
伯斯首先簡要回顧了人類學史上對西歐時間預設的堅持與反思,并指出,即便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對特洛布里恩德島民計時方式的討論中就已經強調,若要妥善地理解其他形式的時間,就“應該擺脫我們的心理和文化習慣”,[8]209而費邊(Johannes Fabian)[9]、格林豪斯(Carol Greenhouse)[10]等人也對相關現象進行了反思,但始終沒有完全解決人類學所面臨的時間困境,與其他領域一樣,“西方時間概念的強加仍然存在于對非西方的、其他的節奏和時間系統的描述之中。”[5]28
隨后,伯斯考察了這種強加在時間生物學領域的表現,他認為,正如曾在特立尼達研究過瘧蚊的時間生物學先驅皮滕德里(Colin Pittendrigh)所指出的那樣,生物活動的時間性關乎多樣時間因素相互交織的“生態時間龕位”(ecological temporal niche),其中包括隨著季節與天氣等因素而不斷變化的日光、濕度等,因此它并非均勻一致的;[5]35但一些生物學家卻因為運用“平均時間”來呈現野外觀察數據或根據時鐘時間來建構實驗室環境,抹除了生物活動與不斷變化的周圍環境之間的靈活時間關系,將時鐘隱喻混入了生物時間節律的呈現。[5]38
而后,伯斯通過運用重視質性的“時機”(timing/Kairos)與強調質量的“時間持續”(duration/Chronos)這一分析性對比,[5]49指出資本主義時間邏輯傾向以后者壓制或替代前者,由此平均并掩蓋了勞動者的多樣性與能動性、勞動本身的情境性與易變性、以及勞動過程中靈活把握時機與協調多樣時間的關鍵性。他以大量來自特立尼達的民族志案例和當地人“小時并不造就勞動”(hours don’t make work)的洞見[5]56,指出以馬克思與泰勒(Frederick Taylor)為代表的“平均勞動時間”概念其實并不足以妥善地捕捉與呈現實際勞動的時間豐富性。[5]68
接下來,伯斯分別考察了西式紀年法的事件編排與實際記憶中的過去與憧憬中的未來的不一致性。他以特立尼達的案例表明,人們記憶中的過去實際上圍繞兩種方式聚集:具有社會意義的事件和文化認可的生命階段與轉變;[5]88而人們憧憬的未來則會關聯于如經濟危機與政局動蕩等具有重大影響的現實狀況而伸縮或歧分。[5]100據此,他強調,過去和未來其實是根據富有深刻社會文化意義的地標性事件來構想的,這些地標性事件會將其他事件吸引到自己的周遭,從而留下很大的年代空隙,這種時間性從西式紀年法的角度來看雖然是“不規則的”,但卻是富有意義與能動性的;相比之下,紀年法的時間性則是同質、空洞、統一的,其中一個時刻與另一個時刻相比并沒有更大的意義,由此,依據它其實很難呈現甚至抹煞了人們主觀意識中過去與未來的實相。[5]100-101
最后,伯斯轉向了對民族志時間呈現的進一步反思。費邊曾指出霸權式的西方時間線性進步時間觀產生的異時論(allochronism)阻礙了人類學對其研究對象的恰當呈現,并倡議以一種強調同時代性(coevalness)的民族志寫位來克服這一局限。[9]但伯斯卻認為,費邊所謂同時代性其實仍舊隱含著西方中心主義的同一時間論(homochronsim),它具有把民族志對象從他們自己的時間性中轉移出來,融化到學術式的歷史話語之中的風險。[5]124基于自己在特立尼達的時間研究經驗,伯斯提出了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同時代性呈現所面臨的四大挑戰:其一是民族志工作者既作為撰寫者又作為被敘述對象的時間分裂;其二是民族志工作者所謂普遍歷史與民族志對象的本地歷史之間的時間張力;其三是民族志工作者與民族志對象在現象學層面對現在的體驗可能不同;其四是不同民族本體論(ethno-ontologies)對存在(being)、生成(becoming)與時間的關系或有不同理解。[5]137據此,伯斯倡議,充分發掘并采用各種地方時間性或是貼近同時代性民族志呈現的一種可能途徑。[5]138
三、時間、全球化與時間人類學
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曾感嘆到:“時間是什么?無人問我,我還知道,若要解釋,卻又茫然”,[11]247這也常被人類學家們當作對研究時間之艱難的經典表述。雖然伯斯并不像杰爾(Alfred Gell)那樣試圖以一套清晰的時間本體論與認識論來直接回應這一難題,但從上述工作中,仍可以看出他為尋找相應答案作出的不懈努力。伯斯筆下的時間作為人們“用以思考周圍環境的循環與變化”的一種概念,[3]1牽涉到計時方式、生活節奏、生命歷程、過去-現在-未來意識等多種維度,并與生態環境、生理機制、認知運作、符號象征、實踐活動、權力博弈、社會結構、文化觀念等多種因素嵌合在一起,呈現出一種紛繁復雜、應場景而交織和變易的多樣性。這種判斷與芒恩的“時間化”(temporalization)理論[1]116和亞當的“時間景觀”概念[2]144形成呼應,這些洞見意味著,依據任意單一層面把時間簡單地等同于“節奏”“周期”或“歷史”的做法,或按照主觀/客觀、自然/文化、社會/個體、循環/線性、自我/他者等二元論作出的時間對分,可能都需要面對時間本身的多維性、綜合性、實踐性、情境性的挑戰。
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曾經指出:“當今全球互動的核心問題是文化同質化與異質化之間的張力”,[12]41并倡議以“景觀”(scapes)視角來研究全球化下文化交融的狀況。[12]43伯斯的上述研究恰從時間的多樣性與同一性之辨出發,為我們呈現出了全球化下時間交互的一些基本輪廓:其一、全球化背景下,多樣時間不僅存在于不同社會之間,也存在于同一社會之內與不同實踐場景之中,它們的持續交織、沖突、協調不斷構造著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其二、全球化下的流動性增強與社會加速帶來的“時空壓縮”其實并未完全消除時間的多樣性,反而加劇了多樣時間之間的沖突;其三、現代性的時間同質化傾向已隨著全球化的過程嵌入到了不同的區域和不同層次的場景中,并試圖掩蓋或壓制時間的多樣性,這給時間多樣性所牽涉的生態多樣性、人的能動性、人與環境的緊密關聯、以及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阿帕杜萊提供的族群景觀、媒體景觀、技術景觀、金融景觀、意識形態景觀之外,也許還能再增添一個“時間景觀”的維度,以促進對時間與全球化研究的互惠并進。
杰爾曾展望到:“我相信未來的時間人類學必須是開放的、兼收并蓄的、經驗主義的”,[6]328并以對跨學科資源的運用、對各種對立時間論的嘗試超越、以及對民族志等經驗材料的重視為此作出了示范。而作為自“時間人類學”被明確提出以來,將職業生涯全心傾注于該領域的第一代人類學家,伯斯的上述工作恰好也繼續發揚了這一趨勢,他從扎實系統的時間民族志逐步邁向更加寬廣的時間議題,并在此過程中將當地人的時間經驗、人類學家的時間洞見與多學科時間研究成果靈活地交叉匯融,達成了一種具身-區域/情景-全球的時間論域,并能微妙地揭示出其中隱而不顯的認知扭曲、權力失衡與生態危機。這既響應著馬林諾夫斯基所謂“再現當地人的觀點”于人類學時間研究的基礎性與重要性,[8]204也暗示著人類學的整體論(holism)可能是推進跨學科協同面對時間之遍及性(pervasiveness)和全球化下現代性之漫布(modernity at large)的一個絕佳支點。協同這一系列啟示,相信能對時間人類學的繼續進展頗有裨益。
注釋:
①本文第一部分對此有詳細說明。
②基本依據請見:E.P.Thompson.Time,Work and Discipline in Industrial Capitalism[J].Past and Present,1967(38):56-97;Nigel Thrift.The Making of a Capitalist Time Consciousness[A].John Hassard.The Sociology of Time[C].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90:105-129;[英]伯瑞.進步的觀念[M].范祥燾譯,上海三聯書店,2005;[德]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康樂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德]羅薩.加速:現代社會中時間結構的改變[M].董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英]鮑曼.流動的現代性[M].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美]奧格爾.時間的全球史[M].郭科等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
③如中國,早自明末鐘表與格里高利歷就已由西方傳教士傳入宮廷與官僚階層;鴉片戰爭以后,工作-休閑二分的工業時間紀律逐步在上海等新興現代城市發展起來;隨后,社會進步史觀開始在精英群體中流行;民國初年,臨時國民政府開始推行時區制度和格里高利歷,基本確立起了一套現代式的時間制度。詳見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朱文哲.西歷·國歷·公歷:近代中國的歷法“正名”[J].史林,2019(6):127-137;封磊.從海關時到北京時:近代中國的“時區政治”及其嬗替[J].史林,2020(4):127-137.
④從芒恩(Nancy Munn)與杰爾(Alfred Gell)的梳理工作中可獲得比較詳盡的相關文獻目錄,詳見[1]、[6]。
⑤提出相應觀點的代表作,如:E.E.Evans-Pritchard.Nuer Time-Reckoning[J].Afr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1939,12(2):189-216;Clifford Geertz,Person,Time and Conduct in Bali(1965)[A].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C].New York:Basic Books,1973:360-411;Pierre Bourdieu.The Attitude of the Algerian Peasant towards Time[A].J.Pitt-Rivers.Mediterranean Countryman:Essays in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the Mediterranean[C].Paris:Mouton,1963:55-72.
⑥相應觀點梳理過程詳見木粲成.實踐中的時間[D].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20:7-29。
⑦詳見Sherry Ortner.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84,26(1):126-166.
⑧詳見Sherry Ortner.Dark Anthropology and its Others:Theory since the Eighties[J].HAU: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2016,6(1):47-73.
⑨詳見Roy D’Andrade.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