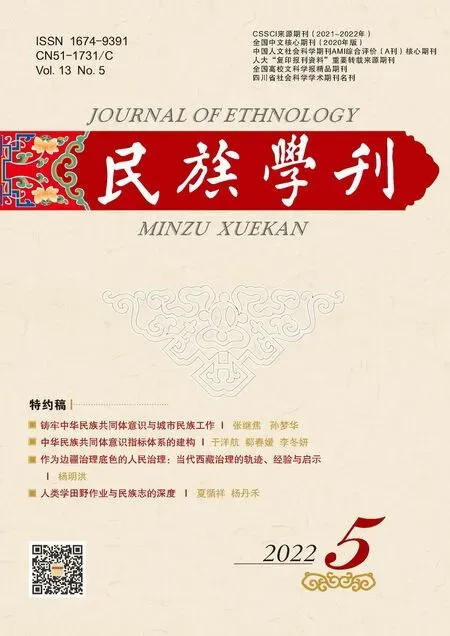土廣東、東山客族與四川客家
——洛帶閩粵贛移民后裔的身份變遷
李思睿
“湖廣填四川”是清代的一次大規模移民運動,四川的移民大多數是在“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中移居四川的,本文所論述的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洛帶古鎮客家人(閩粵贛移民后裔)也是如此。1999年以來,洛帶古鎮成為成都周邊知名的旅游古鎮之一,被譽為“西部客家第一鎮”,以客家建筑和民俗風情為旅游特色,洛帶閩粵贛移民后裔作為“四川客家人”的身份被廣為傳播。本文分析清代以來洛帶閩粵贛移民后裔的身份變遷,解釋這一移民群體自20世紀末以來成為“四川客家”的族群形成過程。
一、四川客家研究與移民研究
在歷史上,閩粵贛移民在遷往各地后有不同的境遇,成為客家只是其中一種可能。在重構客家的形成過程方面,梁肇庭(Sow-Theng Leong)的著作頗有啟發意義。他使用人類學的族群理論、國內移民史和施堅雅(William Skinner)的區域系統發展模式,重新解釋客家族群形成過程。第一,梁肇庭提出,在客家研究中要區分文化群和族群。根據美國學者奧特森(Orland Patterson)的定義,“一個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共享一種共同文化和傳統的群體,只能被稱為是文化群。只有當這個文化群與其他群體產生競爭,他們有意識地選取一些共同的文化標簽來動員和提升凝聚力,以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源,這個文化群才能稱之為一個族群”。[1]1-2第二,梁肇庭受到科恩(Abner Cohen)和巴斯(Fredrik Barth)的啟發,認為族群性與不同文化群之間的互動相關。[1]2他結合這兩種觀點來解釋客家族群的形成,將14-15世紀視為客家的醞釀期,在19世紀客家族群意識最終形成。他的分析指出,只有從16-17世紀開始從閩粵贛邊不斷遷至嶺南的那部分人,才能稱之為“客家族群”。[1]8也就是說,文化群中一部分人成為一個族群的事實,并不意味著這個文化群中所有成員都變成了一個族群。
科大衛(David Faure)提出在客家研究中,應區分認同的歷史和移民的歷史。認同往往是國家與地方、地方團體與團體之間、個人參與社會活動各種互動引致的后果;移民的歷史是認知的過程,不一定是認同的理由,也不表示族群必然有其特點。[2]8意即移民的歷史是認同的必要非充分條件,考察族群形成的過程還需要關注族群互動和政治過程。正如科大衛指出的,認同的歷史與移民的歷史,既有關聯,又是兩套不同的學術問題、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筆者認為在四川客家研究中,首先要區分文化群和族群、區分閩粵贛移民的歷史和客家認同的歷史。
移民史的主要研究對象為移民的遷移過程、移民的影響、移民運動的規律。[3]23-37在“客家熱”波及四川之前,四川的閩粵贛移民研究大多屬于移民史的研究范疇。[4][5][6]20世紀90年代受到“客家熱”影響之后,四川才產生了大量的客家研究成果。在自20世紀末開始的系統四川客家研究中,客家源流問題仍是基本問題之一。[7][8][9]相關研究以歷史學學科為主,同時強調應用研究;研究內容涉及客家社會與文化的各個方面,包括民俗文化[10][11]、教育[12]、建筑[13]、客家女性[14][15]、旅游開發[16][17]等。
四川客家認同的歷史,主要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學者關于四川客家的研究,則可追溯至20世紀30-40年代,這一時期的閩粵贛移民后裔被稱為“東山客族”。[18][19]近年有一些文章探討了客家移民社會的形成和認同的變遷,涉及了客家認同的問題。[20][21][22]在現代民族國家和市場經濟的背景下,人們的族群歸屬并非完全是由他們自己選擇,而與政府的推動和市場的運作息息相關。在如此復雜的背景之下,族群不應被當作一種既存的社會現實,而應該從互動和過程的角度加以考量,關注其背后豐富的歷史和社會意涵。
盧森斯(Eugeen Roosens)指出,族群形成(ethnogenesis)是一個受到國家制度所影響的政治過程。[23]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將族群形成的過程定義為“族群關系和族群認同的創造過程”[24]78,并從歷史變遷的角度分析了這一過程。筆者認為,族群形成的視野有助于理解四川閩粵贛移民后裔的身份變遷。本文中凡未注明出處之訪談、論據均來自筆者2015年至2016年在成都市龍泉驛區洛帶鎮的田野調查。
二、“土廣東”:原籍、互動與族群形成
洛帶鎮位于成都市東郊,是一個商貿集鎮,幅員面積43平方公里,場鎮面積1.42平方公里。洛帶附近地形三分之二為稱作壩區的淺丘,三分之一為低山。成都東郊的東山地區被稱為東山客家方言區,其地理范圍指成都市區以東到龍泉山之間的淺丘區,包括龍泉驛區大部、成華區東部和新都、金堂、青白江等部分地區,面積約460萬平方千米。[8]7成都通行的語言是西南官話,東山地區通行一種被認為難懂的方言。使用這種方言的人們自稱“廣東人”,稱自己的語言為“廣東話”,講西南官話的人們則將他們稱之為“土廣東”,將其語言稱為“土廣東話”。“土廣東”這一族群身份建立在移民的原籍之上,其形成與當地的階級、文化、人群互動息息相關。
(一)移民的歷史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的戰亂導致當地人口急劇減少。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廣行省人口最多。清前期的湖廣填四川,本質上是一場典型的經濟類型的移民運動。[25]9四川境內的客家人多來自粵、贛、閩三省,尤以來自廣東者居多,多為經濟性移民。[4]移民的入川方式主要是家庭遷移[5]83,移民到達四川之后,人數眾多、分布廣泛,從事的職業多樣,涉及農業、工商業、手工業等。移民的開墾和經營,對四川經濟和社會的復蘇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樣來自閩粵贛地區,入川閩粵贛移民在四川各地的發展卻有較大差別。移民在四川大多選擇聚族而居,形成了成都東山聚居區,川中榮昌、隆昌聚居區,川北儀隴縣聚居區,西昌聚居區,沿江居住區等。同時,也有少數的閩粵贛移民散居區,如四川三臺縣。據考證,洛帶所在的成都東山聚居區的閩粵贛移民來源于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多數是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從廣東嘉應州的五屬(梅縣、蕉嶺、平遠、五華、興寧)和惠州府的龍川、連平、河源等州縣,以“墾民”身份遷來四川的;還有一部分移民來自江西贛南。[16]現存洛帶的族譜顯示,當地移民大多來自廣東和江西。洛帶鎮《巫氏族譜》記載了巫氏入川始祖巫錫偉,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自廣東長樂徙重慶府榮昌縣大草坪,后又遷永川縣王家坪”[26]281的經過。
移民會館是同籍移民聚居同一地區的直接反映,出于安全、互助、娛樂等原因,移民紛紛建立會館。四川是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中移民最主要的接收地,因此四川移民會館林立的狀況,在全國都十分突出。四川境內十分之九以上的州縣都有會館,其中以江西、福建、廣東三省移民會館最多。遍布四川城鄉的各種移民會館,積極協調移民之間的關系并參與當地的公共事務,為重建清代四川社會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作為移民大省,不同省籍的移民入川后,在較長的時期內仍保持或沿用原籍的風俗習慣。如今,洛帶鎮內還保存著廣東會館、江西會館和湖廣會館。廣東會館又稱南華宮,興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建于光緒九年(1884年)。江西會館又名萬壽宮,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嘉慶十二年(1815年)重建。湖廣會館是清代初年建筑,至今保存完好。廣東會館又稱南華宮,體現出會館與傳統祠廟、道觀的種種關系,廣東會館現供奉“客家魂”牌位一座。會館反映了移民之初各省移民的省籍劃分意識,在這種意識的作用下,洛帶移民們慢慢開始有了“自我”與“他者”的區分觀念。
清初湖廣填四川以后,洛帶逐漸形成了江西、廣東、湖廣、陜西等各省份移民雜居的狀態,移民們慢慢開始產生省籍劃分意識。湖廣人雖在四川范圍內是優勢群體,但具體到丘陵地區為主的東山地區,閩粵贛移民后裔由于善于山地耕作而逐漸成為當地的主流群體。民國以來,洛帶形成了“廣東人”為主的移民社會,形成了新的族群整合和認同。[21]
(二)認同的歷史
韓起瀾(Emily Honig)通過分析“蘇北人”在上海的形成過程,指出在中國條件下,除了種族、宗族或國籍,族群身份還可以通過原籍得以建構。[27]清代至民國時期,洛帶的閩粵贛移民后裔首先是基于籍貫觀念、建立移民會館,形成以原籍為區分的人群,并在民國初期逐漸本地化成為“四川人”。民國時期,閩粵贛移民后裔又因為與當地另一主流人群湖廣人的競爭,逐漸形成以“廣東人”或“土廣東”為主體的族群。
土廣東的分類以原籍和方言為核心特征,區別于當地另一主要人群湖廣人。“土”字最初明顯帶有貶義,講西南官話的人們認為閩粵贛移民說的方言是“土氣”的。加之閩粵贛移民在東山地區多為農民,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土”也帶有與階層相關的含義。家住洛帶公園的劉叔(62歲)講述了自家的移民歷史和對土廣東的看法:“聽爺爺輩說我家是300年前從廣東惠州移民洛帶的。洛帶旅游開發前,我們叫說客家話的人是土廣東。小時候我說湖廣話,很多沒有文化的農民講一口流利的土廣東話,我都覺得奇怪!上世紀70年代城鄉區別很大,洛帶街上吃國家供應糧的都講湖廣話,只有洛帶周圍的農民才是滿口土廣東話。當時一說土廣東話,我們就知道他是農民,還覺得我們洛帶街上說湖廣話的高人一等。”
洛帶流傳著“住山不住壩”、“不和湖廣人通婚”等口傳故事,蘊含著豐富的族群區分意識。“住山不住壩”的故事講述湖廣人和廣東人到四川后圈地盤,大家都想住在平壩而爭得冤冤不解。湖廣人因長得高大,十分霸道,廣東人就只能集中住到山上和高的地方。[28]152這一故事展現了閩粵贛移民家族集中居住的特點,也展現了他們與湖廣人的競爭,最后只能住在地勢較高處。“不和湖廣人通婚”[28]153則反映了兩個族群之間的沖突和區隔。
清代至民國時期,在湖廣人、廣東人兩大族群的長期互動之下,許多原籍地并非湖廣、廣東的移民也選擇性地融入了這兩大族群。洛帶的江西人甚至有“江西廣東”這樣的稱呼,指的是原籍江西的土廣東人。湖廣人與土廣東人中都包含了其他省份的移民,事實上,兩個族群都已經是經過整合而擴大了的族群。在當時特定的社會經濟情境中,兩個族群以共同族源來凝聚彼此,強調共同的起源記憶與特定族稱以排除異己,建立并保持族群邊界,從而達到了族群整合的目的。這一過程表明,中國的族群身份可以通過原籍得以建構,原籍是一種有伸縮性的建構方式。
時至今日,經歷長時間的社會互動和人群融合,以及一系列社會主義運動,東山地區的族譜、宗祠大多不復存在,土廣東逐漸對自己的家族歷史知之甚少。與自稱來自麻城孝感的湖廣人一樣,土廣東的祖先是否來自廣東,事實上已經虛實難辨。如今“土”字帶有的蔑視意味已經淡化,土廣東和廣東人之稱可以混用,土廣東也從他稱變成了自稱。
三、東山客族:客家民系與族群形成
歷史上(至少20世紀之前)客家人從未形成一個跨區域的族群整體,是梁肇庭的一個重要論述。[1]20世紀30年代,以羅香林所著《客家研究導論》的出版為標志,客家人形成了一個跨區域的不按籍貫命名的族群。在歷史上,不論是在客家、還是潮汕人、廣府人的族群形成中,文化精英都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程美寶分析指出所謂“廣東文化”,視乎當時的人怎樣去定義,更重要的是,在怎樣的歷史文化環境里,哪些人有權利和資源去定義。[29]40在當代,文化精英在客家族群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四川客家族群形成亦受到整體性的客家族群形成和地方文化精英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通過籍貫生發的人群結合情況,在19世紀的中國并未隨著會館制度的衰落而消失。在海外華人領域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籍貫觀念與階級、文化、政治的觀念結合得更為緊密,結合形式更為復雜。潮州人、福建人、廣府人、海南人等地域群體,往往構成了基本的社團組織,完成了最初的社會整合。當然,地緣、親緣、業緣、神緣等紐帶的關系盤根錯節,不可一概而論,但是籍貫觀念在華人世界的重要性,幾乎不可回避。同時,也出現不以原籍命名的族群——客家人,客家成為中國少數(也許是唯一一個)不按籍貫命名的族群。
四川閩粵贛移民后裔與客家觀念的“相遇”,可追溯到民國時期關于“東山客族”的論述。1933年,羅香林在《客家研究導論》中建立了“客家人源自中原,經過五次遷徙,最后于宋代在閩粵贛形成獨立民系”的客家學說體系。[30]這一客家“中原正統說”影響深遠,其追隨者都承認一個共同的前提,即族源和血統直接決定了民系的文化特質。這一“民系-文化”研究范式認為客家是漢族的一個分支,其文化與其他周邊民系相比具有一定的特質;這種特質是和客家的來源直接有關的,因此有許多學者致力于從族源上去界定客家。許多關注客家起源的本地性的研究,也是這一范式的延續。在這樣的研究中,客家人形象被不斷塑造,客家人的身份被不斷強化,超越傳統地緣意識的客家認同也被有心無意地培育起來。
羅香林根據根據康熙末年入川移民的文獻資料,以及從原鄉和四川所能搜集到的譜碟資料,對四川客家的源流和分布作了推測和闡述。他以民國年間現行的縣區為單位,對四川省的客家分布作出推測:“涪陵、巴縣、榮昌、隆昌、滬縣、內江、資中、新都、廣漢、成都等十縣……這些地方的客人,都是清初自粵贛二省遷去的,亦與湘贛系人雜居。”[30]20世紀40年代,在民國時期的四川學界,受到這一范式影響也零星出現了對四川閩粵贛移民的相關研究,稱之為“東山客族”。
1941年,廣東梅縣移民后裔、畢業于四川大學歷史系的鐘祿元于1941年、1943 年先后發表題為《蜀北客族風光》[18]、《東山客族風俗一瞥》[19]的文章。他寫道:“只要步出成都東門外五華里,就可以聽見那難懂的語言”“這些客人都仍保存他們的語言風俗習慣,由此山地風光,與四周俱異。”1946年,語言學家董同龢對家鄉成都華陽涼水井客家方言進行了調查,撰寫《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一書。[31]這一時期的研究已經開始注意到客家人的文化特質,主要從風俗和語言方面對其進行研究和探討,這些早期研究為上世紀末土廣東轉變為四川客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1945年到1950年,施堅雅在成都東部山區做過田野調查,記錄了這一地區閩粵贛移民后裔語言的使用和生活習俗的情況。他發現當地大部分農業人口是200多年前清雍正時期客家移民的后裔,他們在公共場所使用四川話,在家里則使用客家話,主要生活習俗也沿襲客家的傳統。施堅雅用成都東部山區移民后裔的例子,指出客家移民后代的語言和文化并非都被當地社會同化,稱之為“雙語模式和二元文化殘留”。[1]21雖然施堅雅只是在自己的區域研究中順帶注意到了東山客家,并未展開分析,也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觀察資料。成都東郊的閩粵贛移民的確在語言和風俗上有自己的特點,到了20世紀90年代地方發展的新時期,這些文化特點則成為挖掘地方文化的源泉。
四、四川客家:文化精英與族群形成
在旅游發展之前,洛帶的閩粵贛移民后裔的族群身份為“土廣東”,他們普遍對“客家”不甚了解。1999年,在地方發展和文化精英的推動下,洛帶閩粵贛移民后裔被認定為客家人,族群名稱從“土廣東”變成了“客家人”。這一族群身份在2005年舉辦的“世界客屬第20屆懇親大會”(以下簡稱世客會)得到全面展現和表達,世客會讓客家作為一個集體形象在洛帶亮相,增進了四川人對客家的了解和彼此的聯系。此后,當地四川閩粵贛后裔的主觀認同,也開始發生從“土廣東”到“客家人”的轉變。洛帶隨之由傳統集鎮變為旅游古鎮,“文化興鎮,產業強鎮”的洛帶模式趨于成型。
(一)四川客家身份認定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各類華人地域群體相繼成立全球性的社團組織,華人宗親、地緣、姓氏和文化團體相繼復興,并迅速全球化。全球性的華人社團以建立和擴大海外華人的生意網絡為目的,尋求更開闊的發展空間,海外華人利用某些舊紐帶,跨越地區和國界重新整合,形成新的全球關系網絡。[32]表明華人的原籍觀念從未消失,在人群結合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并隨著時代不斷擴展和變化。從外部環境而言,四川和全球客家網絡的聯結得益于全球客家網絡的形成;在四川,則得益于地方政府、相關組織及文化精英的配合。四川客家研究的開展離不開政府的需要,客家研究中心的學者一開始便自覺將客家文化與四川對外開放、招商引資聯系起來,把挖掘整理、推廣客家文化當成一個戰略目標。
自20世紀末開始,由于四川省對外開放、招商引資的內在動力,“客家”和“潮人”等群體一起,成為四川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以下簡稱省僑辦)開展招商引資工作的對象。四川客家海外聯誼會(以下簡稱客聯會)成立,重視與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客家社團增強互動。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客家研究中心(2008年已更名為“移民與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客家研究中心)成立后,四川客家歷史文化資源的整理與研究成績豐碩。借助客家研究中心平臺,以陳世松、劉義章、劉正剛諸先生為代表的學者及四川各縣市地方學人對四川尤其是東山客家地區的歷史文化資源、民俗風情、譜牒等進行系統的收集整理,形成了一大批研究四川客家的鄉土資料。
四川客家身份的認定,是政府和學者自上而下的推動,共同作用的結果。1999年四川省社科院、四川旅游資源研發中心、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為制定出了《洛帶旅游發展總體規劃》,規劃認為洛帶客家古鎮基本保存完好,85%的居民為客家人,約19000人。在2009年洛帶鎮政府一份名為《洛帶60年歷程》的文件中,客家人口數字變成了90%,文中寫道,“洛帶鎮人口90%以上屬客家人,是距大都市最近的客家方言島”。洛帶乃至四川客家人口的數量,是客家研究中心早期的一些研究者根據一個區域的總人口數量和客家人的比例來估算的。估算的依據主要是參照族譜等資料推斷村里的姓氏來源。當時客家身份的認定,并未納入主觀認同這一因素。
由于客家身份的認定是自上而下的結果,對于民眾而言,尚且需要一個較長的接受過程。在旅游發展之前,洛帶的閩粵贛移民后裔普遍對“客家”知之甚少,仍然自稱“土廣東”。筆者于2015年至2016年在洛帶鎮做田野調查期間,接觸的各類人士對客家的接受程度有較大的差異,在普通民眾中大致而言分為以下幾種情況。第一種認為會說客家話就是客家人。“我認為的話,會說客家話就是客家人。以前客家人都要求在家要說客家話,在家不說客家話會被罵。”第二種認為客籍即客家,將客家等同于移民的概念。“客而家焉就是客家人,全四川的人都可以說是客家人。”第三種是基本接受了專家關于客家的定義,將語言、祖籍、文化和主觀認同視為識別標準。“我認為,一是語言,上溯三代人會說客家話,且在家說客家話;二是根源祖籍,要通過族譜或者口述追溯其祖先來自閩粵贛地區;三是習俗,看堂屋供奉的是否歷代先祖考妣神位,還有婚俗等。此外,并不是不能說客家話就不是客家人了,不會說客家話也可能是客家后裔。”
在洛帶普通民眾眼中,客家有時候被認為是一個用籍貫和方言辨別的群體(說“廣東話”的閩粵贛移民后裔),有時候被認為是文化上有特點的群體(相較于當地另一主要人群“湖廣人”),有時候強調主觀認同(“不會說客家話也可以是客家人”)。總之,洛帶的“客家”是一種自上而下被歸類的族群身份,官方一直在試圖將洛帶客家標準化,但在當地人口中,客家的邊界和內涵極富彈性和爭議,普通民眾對此的解釋是含混不清的。
(二)四川客家身份表述
四川客家研究學者秉持“學以致用”的理念,將學術研究作為推動四川客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文化動力,洛帶的旅游開發是一個政府、學者、媒體、村民共同合作的項目。旅游開發之前,政府組織專家們事先開展了對洛帶客家文化旅游資源的調查。1999年,客家研究中心為洛帶制定“中國西部客家第一鎮”的旅游發展定位,2000年初,通過“首屆西部客家火龍節”推出洛帶客家特色旅游活動;2001年7月,洛帶又繼續推出“西部客家水龍節”,主打客家文化旅游。洛帶的廣東、江西、湖廣移民會館也轉變為客家會館,其展示內容重在回顧客家遷徙記憶、宣傳客家文化。2001年,洛帶鎮已被列入四川省省級歷史文化名鎮。
四川客家的形成及洛帶的旅游開發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有文化精英的參與。首先,早在旅游開發的籌備階段,客聯會和客家研究中心便參與了對地方文化的建構和表達。此外,他們與海內外的客家社團保持長期聯系和定期的互動,致力于將“客家”能帶來的社會資本、象征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乃至政治資本,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和文化產業建設。其次,他們不但是四川客家與海內外客家社團的溝通者,也是旅游開發中的設計者。洛帶從1999年開始的發展規劃書均由客家研究中心負責,中心的工作人員還參與旅游產品開發。他們推動策劃的一系列學術會議,往往與地方旅游活動相結合,互相助力,僅2000年至2002年就召開4次四川客家相關的學術研討會。
2005年,由四川省政府主辦、成都市政府和客聯會承辦的世客會在成都舉辦,成為洛帶發展中濃墨重彩的一筆。洛帶成為世客會的分會場和懇親聯誼的主體會場,古鎮宣傳定位隨之變成了“世界的洛帶,永遠的客家”。洛帶游客中心的李姓工作人員(女,35歲)回憶了這一盛會帶來的影響:“我從小生長在洛帶,小時候和同學去成都,那時候也窮,我們兩個人操著土廣東話在公交車上交流的時候,全車人都看著我們,就好像看到兩個又窮又土的怪物一樣。從此,我再也不敢在公眾場合講自己的方言了。直到2005年世客會在洛帶召開,五千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人涌入洛帶的那一刻,所有洛帶人都沸騰了,原來世界上還有那么多和自己講著同一種方言的人。在歡迎的紅地毯上,我們打出橫幅,‘三百年來終于等到這一天’,仿佛是流落在外的游子見到失散多年的親人一樣。”
短短幾年內,洛帶鎮大力發展客家特色旅游,四川客家和洛帶古鎮都聲名遠播。在旅游發展初見成效,旅游區逐漸成熟之后,不斷有世界各地的客人來洛帶參訪、咨詢、學習、洽談合作,各類客家專家的解釋、溝通作用越來越重要。2006年開始,洛帶鎮政府每年舉辦客家旅游活動,成立“客家藝術團”,每年參加全國客家山歌演唱大賽,日常在洛帶進行常規演出。在空間方面,政府繼續通過改造移民會館、打造客家土樓和客家博物館等旅游空間使洛帶的文化景觀不斷“客家化”,這些改造都有各類專家學者的持續參與。
通過洛帶古鎮實體的空間展示,配合一系列文化展演、身份表述,洛帶不斷將地方元素和客家身份相結合,強化著自身的客家形象和文化特色。與此同時,在一些當地人中間發生了土廣東到客家人的認同變化,感到自己從前“土廣東”的污名記憶“被正名”。洛帶當地文化名人李老師(56歲)的描述頗具代表性:“在十五年、二十年前,四川的客家人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只知道自己是土廣東人。其實很多學者、政治領袖都是客家人,但是以前我們沒有這種意識。以前我們說廣東話很羞澀,其他移民都是說湖廣話、普通話,我們說的是土廣東話,在成都都要低著頭走路,不敢開口。十幾二十年前大家才知道客家人精英遍布全世界,客家是一支偉大的民系,是東方的猶太人,才開始有了自信。”
五、結語
本文首先從歷史的脈絡、族群互動的角度,區分了清代“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中洛帶閩粵贛移民的移民史,及其后裔成為“土廣東”的認同歷史。在清代至民國時期移民本土化過程中,洛帶的閩粵贛移民后裔與湖廣人之間的族群互動,促使“土廣東”這一族群形成。從認同各自的省籍到認同為土廣東,東山地區的閩粵贛移民后裔經過了一個由分到合、由保持強烈的原鄉認同到轉向新鄉認同的過程,這一過程是族群互動、移民社會長期整合的結果。
再次,本文從整體性的客家族群形成、全球化的脈絡來看待當代洛帶客家乃至四川客家的形成過程。20世紀40年代,受到羅香林建立的“民系-文化”研究范式影響,四川學界零星出現了對洛帶閩粵贛移民后裔的研究,稱之為“東山客族”,客家認同在四川緩慢發展。1999年開始,洛帶的閩粵贛移民后裔發生了從“土廣東”到“客家人”這一族群名稱和認同的變化。這一身份變化與全球性的客家網絡和地方的旅游發展緊密相關,文化精英扮演了溝通者、轉譯者的角色,參與書寫客家的歷史和文化。在洛帶的文化轉型和地方社會變遷中,從前期的資料收集和挖掘,到制定旅游發展規劃,到旅游發展中與游客和各界人士的溝通,地方精英和專家學者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洛帶閩粵贛移民后裔自世紀之交以來的客家身份更新,已與土廣東的族群形成有很大區別。四川客家的認同不再是當地族群互動的結果,而是在現代民族國家和市場經濟的背景下,一次自上而下的建構過程。這一身份變遷的過程表明,族群意識的形成產生于群體的歷史經驗,同時,族群往往又會根據主觀認識與現實境遇不斷調試,也會根據現實重構自己的歷史。從土廣東到四川客家,閩粵贛移民后裔的身份變遷也不斷重構和豐富著作為整體的客家歷史,并讓全球性的客家網絡不斷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