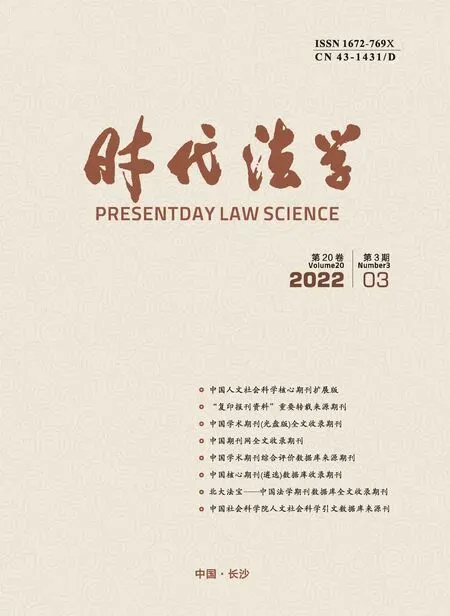論對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行為的法律規制*
肖姍姍
(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 湖南 長沙 410081)
未成年運動員是指18周歲以下,愿意在專門人員的監督下從事與其年齡相適應的專業體育活動的運動員(1)基于未成年運動員監管的特點,本文所指的未成年運動員,主要是指未成年人專業運動員,并不包括職業運動員、業余運動員。。近年來,未成年運動員被暴力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現象屢見不鮮,如2009年我國14歲的足球少年母詩灝被教練體罰致死案、我國舉重冠軍鄒春蘭自16歲時起食用“大力補”致不育事件、2016年美國國家體操隊隊醫性拉里·納賽爾性侵多名未成年運動員案等。運動員的培養周期較長,其運動生涯幾乎全在年幼時開啟,如一名體操運動員的運動生涯大致如此:從12~14歲開始參加全國性錦標賽,15歲開始參加國際比賽,15歲至17歲是體操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的黃金年齡階段,成年以后退役。研究表明,運動員的優秀資質越來越呈現低齡化的特點,如在當代體操比賽中,運動員競技水平的高峰期為14~16周歲,在20世紀60年代時,運動競技水平的高峰期則為25周歲(2)SeeDavid, Paulo.Children’s Rights and Spor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Rights, 1999,7(1):53-82.。然而,由于體育訓練的高壓性、封閉性等特征,未成年運動員長期處于脫離其父母和家庭監護的狀態,其極易受到違法犯罪行為的侵害。對此,應當從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現狀出發,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為基礎,完善對未成年運動員的法律保護。
一、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主要行為類型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簡稱UNICEF)于2010年發布的一項研究結果將暴力侵害未成年遠動員權利的行為總結為12類,即基于性別、體型或表現實施羞辱、為取得優異成績而施加過度壓力、將性別視為團隊選擇或特權的先決條件、身體傷害或性侵害、營養和減肥制度導致未成年運動員飲食失調(如厭食癥或其他健康問題)、毆打或其他體罰形式刺激未成年運動員以提高表現、在極端環境中通過強迫冒險造成的傷害、使用興奮劑或其他能提高成績的藥物、同齡人使用酒精或成癮藥物的壓力、利用體育鍛煉作為懲罰、拒絕充分的休息和照顧(3)See UNICEF, Innocenti Resource Centre,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Violence in Sport[J]. A Review with a Focus o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2010).。我國學者林瓊博士根據實證調研,對未成年運動員的暴力現象予以泛化處理,運用扎根理論將對未成年運動員的泛暴力化行為分為硬暴力與軟暴力,并進一步將前者分為軀體暴力和體罰暴力,將后者分為語言暴力、經濟暴力、冷暴力與心理暴力(4)林瓊.教練員對未成年運動員泛暴力化研究——以福建省為例[D].福建師范大學,2015.3.。本文認為,上述這兩類劃分模式均過于寬泛,超越了法律的張力范疇,有些行為應被納入職業道德規范的范疇,如對未成年運動員冷暴力、性別歧視等。法律范疇中的暴力( violence),是指不正當或未經授權而非法使用暴力,違背公眾自由、法律或公共權利,造成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害的行為(5)薛波,潘漢典.元照英美法詞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404.。結合我國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實際情況,我認為主要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類:
(一)體罰暴力行為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釋義,體罰是指“用罰站、罰跪、打手心等方式來處罰兒童的錯誤教育方法”(6)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1129.。根據《教育大辭典》的釋義,體罰是指“以損傷人體為手段的處罰方法”,同時將留堂、餓飯、罰勞動、重復寫字幾百幾千等行為定義為“變相體罰”(7)顧明遠.教育大辭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535.。體育學、運動學中的“體罰”概念,顯然有別于日常運用于教育學的“體罰”。結合實證研究來看,體育運動中的體罰大多體現為非直接性地身體毆打,其可同于變相體罰,通常通過罰站、罰跪、蛙跳、倒立、扎馬步、加量訓練等方式對未成年運動員實施大量高強度超負荷訓練(簡稱強迫式訓練)、懲罰式訓練等非人道訓練。
運動員進行重復運動的主要目的在于幫助其創建自動反應和無故障執行,訓練可以發展運動員的耐力、力量、技能或表現水平。持續時間和強度是定義訓練活動的兩個維度。不同年齡階段的未成年運動員所接受的運動強度和時間都應該有一定量的標準,在標準范圍內實施體育訓練有助于未成年運動員的發展。然而,在許多受歡迎但要求非常嚴格的運動項目中,例如體操,網球,滑冰和潛水,兒童在很小的時候(通常在4至6歲之間)就被迫接受強迫式訓練。對這些年齡尚小、身心發育尚未完全的未成年人,多大的訓練強度和多久的訓練時間為合適?對此,存在區分合理的訓練與強迫訓練的困難。毫無疑問,未成年運動員要想在運動中取得成功,就必須付出汗水和痛苦,但基于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的有限性,他們不一定知道或理解這一區別。有證據表明,參與強迫式訓練的未成年人為了取悅成年人而努力工作,以至于當他們達到身心極限時,也無法發展出對父母或教練說“不”的能力。然而,一些教練有濫用服從的傾向,要求未成年人絕對服從,并迫使未成年運動員做對他們來說太難的運動。強迫式訓練會造成暴力的無限循環,并不值得為了極低的獲獎概率而強迫未成年運動員從事超出其身心承受范圍內的訓練。懲罰式訓練主要是指在運動語境下,將體育訓練作為一種懲罰方式要求運動員參加。對此,需要從以下幾個維度去理解:
其一,懲罰性訓練的定義應該與它所包含的行為相關,而不是依賴于這種行為對相關運動員的影響。因此,懲罰式訓練并不要求發生物理或其他形式實質性傷害結果或潛在可能危險。其二,在界定懲罰性訓練時,無需考察其目的何在。不論以何種目的為理由將體育訓練作為懲罰,都是對運動員的人格尊嚴以及身心健康的摧殘。其三,應該從未成年運動員是否同意及教練施以懲罰性訓練的目的兩個角度來區分懲罰式訓練與合理訓練(8)See Ron Ensom,Joan Durrant.Punishment of Children in Sport and Recreation: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J]. Coaches Plan,2010,17(2): 43-44.。一方面,未成年運動員同意從事某些體育訓練,以發展他們的能力,而非同意接受以羞辱或懲罰的形式參加訓練;另一方面,前文強調的是實施懲罰式訓練為行為目標,而此處強調的是教練等主體對未成年運動員施以懲罰式訓練的主觀目的何在,即他們是為了激發未成年運動員的運動技能,還是為了懲罰或造成身體或心理上的不適。
體罰暴力行為雖然不同于直接外化的身體打擊傷害,也不一定對未成年運動員造成醫學鑒定意義上的輕傷害、重傷害結果,但對這一群體的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的傷害一點都不亞于暴力打擊行為。結合實證研究來看,對未成年運動員施以體罰暴力,不僅可能破壞未成年運動員的心血管系統,造成心率過快、心肌肥厚、心臟肥大、血紅蛋白失常等損害結果,同時容易造成未成年運動員骨骼肌肉的畸形發育或骨骼受損,還可能導致未成年運動員因激素分泌增量而致使免疫系統降低或破壞。對未成年運動員實施體罰暴力行為顯然有悖于生長發育的連續性與階段性的自然特征,即使行為后果不立馬顯現,體罰暴力行為將給未成年運動員的職業生涯、身體健康、生命長短帶來不可預估的長足危害。
(二)興奮劑濫用行為
“興奮劑”被視為阻礙體育運動事業健康良性發展的“頑疾”,也被稱為體育賽場的“亞毒品”(9)于沖,陳培.從孫楊案看“興奮劑”為何“入刑”[J].人民法治,2020(06):46-49.。未成年運動員也未能幸免于興奮劑的濫用。與成年運動員濫用興奮劑相同的是,未成年運動員濫用興奮劑也有著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原因。例如,在體操比賽中,訓練者經常鼓勵未成年女性運動員在重要比賽前服用利尿劑來減重。在舉重項目中,未成年男性運動員通常被要求使用類固醇來增加力量。未成年游泳運動員、短跑運動員和自行車運動員也常被要求濫用藥物來增加他們的肌肉量。與成年運動員不同的是,未成年運動員更具可控性。對于教練來說,這非常具有誘惑力,因為未成年運動員把自己的全部信任都寄托在教練身上,而教練卻在濫用他們的信任,欺騙或強迫他們服用違禁藥品用以提高成績,有時甚至將這些藥品冒充為維生素,但實際上很可能有害于未成年人的身體健康。
濫用興奮劑的行為違反了大多數體育聯合會的現有規定,如果成年人欺騙或強迫未成年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即使在未成年運動員被告知并意識到興奮劑的性質,這一行為都直接侵犯了其健康權,違反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性要求。濫用興奮劑將給未成年運動員的身心健康帶來極大的危害,如產生藥物依賴,導致細胞和器官功能異常,產生過敏反應,損害免疫力,引起各種感染(如肝炎和艾滋病)、心力衰竭、激動狂躁等。濫用興奮劑的危害主要來自激素類和刺激劑類的藥物,藥品種類繁多,且處于不斷地更新調整中。特別令人擔憂的是,許多有害作用只是在數年之后才表現出來,而且即使是醫生也分辨不出哪些未成年運動員正處于危險期,哪些暫時還不會出問題。國家、社會、家庭、教練等相關組織和人員都有義務保護未成年運動員免受興奮劑的傷害。
(三) 性侵害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中的性侵害并非僅指《刑法》中規定的強奸罪,應為包括強迫性行為、強奸或性侵犯、猥褻等在內的侵犯未成年人性自主權或身心健康權的行為。有數據顯示,在年滿18周歲以前,每5個女孩中就有1人被性侵害,每20個男孩中就有1人被性侵害,兒童性侵害的比例在8%~18%之間。體育訓練場被視為了性侵兒童的理想場所,因為教練、隊醫等身份的特殊性,使他們接觸兒童的身體成為可能,同時也取得了其父母的同意。由此,身體接觸可能會在失當行為與性侵害行為之間產生灰色地帶,從而導致信息披露不充分,低估了體育運動中針對兒童的性暴力(2%~8%)(10)SeeLaurie Koller.Sage Sports:Protecting Athletes From Sexual Abuse[J].Oklahoma Bar Journal,2018,89(26):7-9.。從媒體報道的159例體育運動性暴力案件中分析發現,98%的施暴者是16至63歲的教練、教師或指導員(11)SeeBrackenridge C H, Bishop D, Moussalli S, & Tapp J.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xual abuse in sport: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of events described in media repor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2008, 6(4):385-406.。也有調查顯示,同伴運動員也成為了性侵行為主體之一(12)See Mountjoy M, Brackenridge C, Arrington M, Blauwet C.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consensus statement: Harassment and abuse (non-accidental violence) in sport[J].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16, 50(17):1019-1029.。此外,在體育運動中,對未成年運動員實施性侵害的行為主體多為男性,女性也逐漸發展成為性侵主體之一(13)Brackenridge C.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violence in sport : A review with a focus o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2010.。當然,無論何種年齡、何種性別、何種類別的行為主體,對未成年運動員實施性侵害的過程通常包括四個步驟,即鎖定目標——建立信任——創造獨處的機會——實施性侵害行為。
從未成年運動員主體來看,其主要體現為易被性侵害、難以察覺被性侵害和性侵害后難以披露。教練員、隊醫等專業人士在日常生活中有諸多機會與未成年運動員接觸,并建立起一種非同尋常的“親密關系”。未成年人運動員年幼弱小,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加之運動服裝的暴露和對教練等專業人士的盲從與依賴,導致其容易成為性侵人員所鎖定的“獵物”,極易成為被性侵害的對象。相對于成年運動員,未成年運動員由于性知識的缺乏導致其難以發覺性侵害的發生,甚至成為長期被性侵的對象。如在2016年美國體操隊丑聞中,涉案隊醫以檢查、康復的名義觸碰運動員的身體,對未成年女性運動員實施性侵害,但諸多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并未及時認清自己是被醫療救治還是被性侵害,甚至在成年后都未察覺在幼年時已被性侵害。未成年運動員性侵害的難以披露性與體育運動的特性密切相關。就有組織性的體育運動來看,未成年運動員在遭受性侵害后并沒有正當的性侵害報告程序,其無法尋求適當的幫助與披露機制。同時,性侵害被視為個別主體的問題,而非機構內部發生的問題,通常通過開除性侵害主體的辦法以求“息事寧人”。此外,體育運動訓練的封閉性和父母對培訓機構、教練等人員的盲目信任助長了性侵未成年運動員的火焰,致使未成年運動員沒辦法或不敢向他人披露自己被性侵害的事實。
未成年免受性侵害的前提條件是對未成年人性權利的法律承認。相較于成年人,未成年人的性權利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健康利益,具有明顯的排他性、被動性、脆弱性等特點。由于未成年人處于身心發展尚未完全的階段,性侵害給未成年人帶來的損害是無法預估的。兒童時期的性侵害,是誘發人們一系列心理問題的重要風險因素,如抑郁癥、恐懼癥、強迫癥、恐慌癥、創傷后應激障礙、性障礙和自殺傾向等(14)See Briere J, & Elliott D M. Prevalence and Psychological Sequelae of Self-reported Childhood Physical and Sexual Abuse in a General Population Sample of Men and Women[J]. Child Abuse and Neglect,2003,27(10):1205.。這種身心傷害雖然在成人后會有所緩和,但“污名化”和創傷后的二次適應社會問題將給他們帶來無限困擾,亦有在被性侵害后惡逆變為性侵害實施行為主體的情形。因此,加強事前預防與事后救濟成為了解決未成年運動員性侵害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成為了完善未成年運動員法律保護體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除卻上述三種主要的暴力侵犯未成年運動員權利的行為外,語言暴力也充斥著體育運動場,貶低壓抑、嘲諷挖苦、威脅恐嚇、哀求抱怨、粗口謾罵、侮辱尊親等語言暴力方式十分普遍,傷害了未成年運動員的自尊與自信,導致未成年運動員的性格暴躁,甚至人格變態(15)林瓊.福建省教練員對未成年運動員語言暴力研究[J].南京體育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14(4):58-63.。強迫未成年運動員節食以保持體重或抑制發育等情形也為運動場所常見的暴力現象,體育運動員之間的欺凌行為,尤其是年幼的運動員遭受年長運動員的欺凌現象也十分常見。隨著競技體育的快速發展,隨著體育業的市場化、產業化,一種更加平等、公開、強調教練與隊員之間相互交流的“師徒關系”才是現代體育的主流。類似于家長制的傳統師徒關系,師傅權威凌駕于個人權利和隱私之上,未成年人沒有反抗的余地,只有服從。一旦反抗或試圖脫離,那就意味著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如何有效地對侵害未成年運動員合法權利的行為予以法律規制,是保障我國體育事業長足發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構建法治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暴力侵害行為法律規制的體系性考察
目前,我國對暴力侵犯未成年運動員權利行為的法律規制主要散見于《刑法》《民法》《行政法》《未成年人保護》《教育法》《反興奮劑條例》和《體育法》等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中,并呈現以下特征:
(一)以專門法原則性規定為基礎
未成年運動員的主體身份具有雙重屬性,即運動性與未成年性,對他們的行為規范及權利保護的專門法律法規有《體育法》《反興奮劑條例》和《未成年人保護法》。《體育法》作為規制體育活動的專門性法律,對基于體育運動的特殊性可能存在的侵害未成年運動員行為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如該法第27條明確提出了應當對運動員實行嚴格、科學、文明的訓練和管理;第34條規定了體育競賽實行公平競爭的原則,在體育運動中嚴禁適用禁用的藥物和方法,禁用藥物檢查機構應當對禁用的藥物和方法進行嚴格檢查。《反興奮劑條例》第3條明確規定禁止使用興奮劑,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向體育運動參加者提供或者變相提供興奮劑。對于性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體育法》并未有專門性的法條予以規定。但《未成年人保護法》有多個條文涉及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如該法第21條明確規定不得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第41條規定“禁止拐賣、綁架、虐待未成年人,禁止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害”。
就具體侵害未成年運動員行為的法律規制來看,專門法規定了應當以體育社會團體章程中的行業規制和行政處分作為前置處罰手段。如對于體罰暴力行為的規制,前提在于區分體罰暴力行為的適當性與違法性。雖然適當的體罰一定程度上能夠激發未成年運動員的運動機能、有效提高未成年運動員的運動水平,但應當注意該行為是否符合體育訓練的限度標準。若超出必要的范圍,則構成違法。同時,對于體罰暴力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應當通過體罰類型、體罰程度、被體罰運動員的年齡和精神狀況、參與體罰的自愿性等四個要素的綜合考量。對于此種行為,根據《體育法》第49條、第50條規定,首先應當由社會團體按照章程規定給予處罰,對于國家工作人員中的直接責任人員這一特殊主體,則依法給以行政處分。《體育法》對于興奮劑濫用的行為規制,也可追溯至上述兩個法律規范。《反興奮劑條例》對興奮劑濫用行為雖設專章規定了法律責任,但從其具體規定來看,仍將行業規制和行政處分作為前置處罰手段,并對特定情形作出了二年或四年的從業禁止規定。對于性侵害未成年運動員權利的行為,專門法并未就這一特殊侵害行為的法律責任予以明確規定,而是將其作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一種形式,在《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29條予以原則性規定,即“違反本法規定,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違反本法規定,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體育法》《反興奮劑條例》和《未成年人保護法》均以抽象的原則性規定為主導,行業章程中通常規定停職、停薪、行政記過等一系列處分方式,這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對相關行為違規性與違法性的銜接。同時,也體現了對體育活動中違反工作要求、操作規程、職業道德或者其他有關規定的行為的職業性與規范性要求,為規范運動員所在單位責任與教練員責任具有一定的指導性意義。
(二)以行政處分與民事賠償為補充
除卻專門法的原則性規定外,我國對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規定了相應的行政處分,對違法性的體罰暴力行為的具體法律規制主要體現在行政處分與《民法》中的侵權責任篇中。
行政處分,是指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對隸屬于它的犯有違紀行為或輕微違法行為但尚未構成犯罪的行政人員的一種行政制裁。行政處分分為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降職、撤職、開除留用察看和開除八種。結合實施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行為主體身份的特殊性,我國現有法律體系規定了對教練員等特殊主體的行政處分措施。在實踐中,對于具有特殊身份的暴力侵害主體,其所在單位或主管部門視情節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解聘。如在遼寧省錦州市“教練體罰學生用便池水洗臉”一案中,“便池水洗臉”是一種人格侮辱式體罰,作為專業培養體育人才、負責全市競技體育訓練基礎工作的事業單位,錦州市文化旅游體育服務中心就此對涉案跆拳道教練員戴某某進行警告處分,并將其調離教練員崗位;在“江蘇宿遷市賽艇隊教練體罰”一案中,宿遷市體育局對涉案教練方某作出停職、停薪、行政記過等一系列處分;在“馬俊仁強迫隊員服用興奮劑的丑聞”一案中,前國家田徑運動隊教練馬俊仁被開除出國家隊等。上述行政處分措施,大幅度降低了施暴主體再次實施暴力傷害行為的可能性。然而,非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的教練、訓練員的職業禁止問題成為了我國現行法律體系的留白之處。
我國《民法典》第1176條規定:“自愿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因其他參加者的行為受到損害的,受害人不得請求其他參加者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其他參加者對損害的發生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除外。”這一法條確定了風險自擔或自甘風險原則在體育運動中的適用。但是,這并非意味著運動員對體罰暴力行為自甘風險。對于體罰暴力行為,應當適用一般侵權的法律規定。根據我國《民法典》第1165條和第1166條規定,民事侵權責任可分為過錯責任原則、推定過錯責任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根據體罰暴力行為特征,并基于未成年運動員對教練的嚴重依賴性與依附性,筆者認為適用推定過錯責任更為妥當,即在體罰暴力行為中,推定實施體罰的行為主體具有過錯,若其不能證明無過錯的,則應當承擔民事侵權責任。若采用過錯責任,則忽視了運動訓練的封閉性,加大了證明難度,無法及時有效保障未成年運動員的合法權利;若采用無過錯責任,則容易造成教練指導員等專業人員的不作為,不利于未成年運動員技能與水平的提升。對于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行為的民事賠償責任,我國《民法典》第1179條規定了損害賠償范圍,包括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營養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殘疾的,應當賠償輔助器具費和殘疾賠償金;造成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除追究施暴主體的民事賠償責任外,還可比照該法第1197條至1121條的規定追究體育訓練機構或管理部門的民事責任。
(三)以刑事處罰為最后保障手段
作為最后一道法律防線,刑法所特有的法益保護機能要求其必須為未成年運動員提供最后的法律保護屏障。在我國的《刑法》體系規范中,對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刑法規制主要體現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一章。
1.對體罰暴力行為的刑法規制
根據體罰實施主體的主觀方面差異性,可適用的罪名包括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過失致人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及虐待罪。在司法實踐中,鑒于主觀認定的難度,體罰暴力適用于故意類犯罪的相對較少,且過失重傷罪要求達到重傷害的結果,過失致人死亡罪要求達到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在體育訓練過程中體育致人傷殘、死亡的情形并不常見,因此,過失型罪名的適用也相對較少。
我國《刑法修正案(九)》對虐待罪的修改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應對教練等人員體罰暴力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刑法修正案(九)》修訂之前,我國虐待罪的犯罪主體僅限定于家庭成員,此次修正案在《刑法》第260條虐待罪后增加“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規定“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殘疾人等負有監護、看護職責的人虐待被監護、看護的人,情節惡劣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有第一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根據構成要件理論,此罪的客觀表現形式通常表現為行為人采用毆打、凍餓、有病不給治療、強迫進行超體力勞動等肉體摧殘手段,以及侮辱、限制行動自由等精神折磨手段,對被害人的身心進行經常性的摧殘和折磨,使被害人遭受到肉體上、精神上的痛苦。由此,在封閉式訓練中,教練取代父母角色,特定情形下成為未成年運動員的被委托監護人,其在監護期間對未成年運動員進行體罰的行為,可構成虐待被監護人罪。對于體罰情節嚴重構成過失致人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的,按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2.對興奮劑濫用行為的刑法規制
對于未成年運動員興奮劑濫用行為的刑法規制,2020年底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確對此予以入刑處理,在《刑法》第355條后增加“妨害興奮劑管理罪”這一新罪名,規定“引誘、教唆、欺騙運動員使用興奮劑參加國內、國際重大體育競賽,或者明知運動員參加上述競賽而向其提供興奮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組織、強迫運動員使用興奮劑參加國內、國際重大體育競賽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從這一最新法條規定來看,引誘、教唆、欺騙運動員使用興奮劑,提供興奮劑、組織、強迫使用興奮劑等妨害興奮劑管理的行為均被納入到刑事處罰的范疇,為未成年運動員的公平競爭權與身體健康權免受興奮劑濫用行為的侵害提供了最后的法律屏障。
3.對性侵未成年運動員行為的刑法規制
我國現有《刑法》對侵害未成年運動員性權利行為的刑法規制主要涉及強奸罪、猥褻兒童罪。這兩個罪名在構成要件上有較大的差異,在犯罪客體和犯罪對象上體現尤為明顯。《刑法修正案(十一)》對第236條強奸罪予以修訂,增設“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對特定主體與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的予以定罪處罰。結合修訂后的這兩個條文,我們可以將未成年女性劃分為四個年齡層次:
其一,16周歲至18周歲未成年女性。此類女性基于身心發展已基本等同于成年女性,我國《刑法》并未對其性權利予以特殊規定,而是籠統歸于強奸罪的犯罪對象——婦女之中。
其二,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女性。我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第236條后增加一款,作為第236條之一,即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對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該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惡劣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這一規定并未完全否定14周歲以上16周歲以下未成年人的性自主權,但是與其負有監護、收養、看護、教育、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人員,與該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的,即使取得該未成年女性的同意,亦構成犯罪。這一規定的立法目的在于預防和規制負有照護職責人員利用法律地位、法律行為或職務上的便利性侵未成年女性。
其三,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女性。這一年齡階段的未成年女性在刑法上被稱為“幼女”。我國《刑法》第236條規定,對奸淫幼女的行為,應當以強奸罪論處,從重處罰。從這一規定來看,奸淫幼女行為的犯罪構成,并不需要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為基礎,該罪保護的法益不僅包括了幼女的性權利,同時也侵犯了幼女的身心健康權。由此可知,我國法律是否認14周歲以下的幼女具有性自主權的。對于奸淫幼女的行為,規定從重處罰的同時,《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在公共場所當眾奸淫幼女的”“造成幼女傷害的”作為加重處罰情形,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
其四,不滿10周歲的幼女。《刑法修正案(十一)》對10周歲以下的幼女的性權利保護予以了特殊規定,增加了強奸罪的加重處罰情形:“(五)奸淫不滿10周歲的幼女”,對于奸淫10周歲以下的幼女的,應當加重處罰,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
強奸罪的保護對象僅限于女性,對于男性未成年運動員的性權利保護,可依據我國《刑法》第237條之一“猥褻兒童罪”的規定。《刑法修正案(十一)》將原本“猥褻兒童罪”規定的“猥褻兒童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從重處罰”修改為具體的兩種情形,針對猥褻兒童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規定4種加重處罰情形,具體包括:(一)猥褻兒童多人或者多次的;(二)聚眾猥褻兒童的,或者在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情節惡劣的;(三)造成兒童傷害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四)猥褻手段惡劣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
綜上所述,雖然我國《刑法》并未將未成年運動員的性權利予以特殊化處理,但從我國對未成年人性權利的刑法保護發展來看,為有效預防教練、醫護人員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性侵害未成年運動員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對現有法律體系規定的反思
雖然我國有多個部門法多個法律條文涉及對暴力侵害行為的規制,特別是《民法典》的出臺與《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頒布進一步規范了暴力侵犯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但從體系性方面考察,我國現有的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法律規制仍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未成年運動員保護理念不足
未成年運動員的雙重屬性未得以重視,缺乏對未成年運動員權利保護的觀念。即使是作為運動員權利專門法的《體育法》和作為未成年人保護專門法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也僅作出部分原則性規定,鮮有法律條文將“未成年運動員”這一主體予以特殊化規定。未成年運動員具有雙重身份屬性,即未成年人和運動員。相較于一般的運動員,作為未成年人的運動員,身心發展尚未完全,自我保護意識更為薄弱;相較于一般的未成年人,作為運動員的未成年人,一般在寄宿制體育學校,不能得到正常的父母監護,長期與教練、隊醫等年齡較長的成年人相處,容易導致其處于服從地位。由于自我保護意識與自我保護能力薄弱,加之訓練環境的封閉性與訓練活動的盲從性,導致未成年運動員容易受到他人的暴力傷害。然而,現有的法律規范并未凸顯對未成年運動員的特殊保護。未成年運動員特殊保護的法律規定和觀念的缺失,導致當前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無法得到有效規制。未成年運動員與家長在暴力侵害事件發生后,大多選擇不了了之。然而,暴力侵害給未成年運動員所帶來的傷害是無法估量的。
(二)缺乏明確的法律概念
“概念是構造理論的磚石,它是研究范圍內同一類現象的概括性表述。”(16)袁方.社會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55.現有法律規范并未對“暴力”“體罰”“性侵害”等與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行為密切相關的術語予以法律界定。“體罰”一詞常出現在體育訓練與競技場中,也常出現在教育教學場所中。然而,“體罰”這一概念并非是規范法學的法律用語,而是屬于犯罪學中對現象予以歸納或概括的事實用語。法律規范要求明確性,尤其是作為最后保障規范的刑法,在涉及對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規制中,應當從規范的角度入手,而不能直接搬用犯罪學中所描述犯罪現象時所使用的概念(17)張明楷.刑法學中的概念使用與創制[J].法商研究,2021,38(1):11.。何謂“體罰”?體罰與懲戒行為的界限何在?達到何種程度即構成體罰?《體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教育法》均未對此予以明確界定。此外,“性侵”亦為如此,在刑法規范中,有“強奸罪”“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猥褻兒童罪”等罪名,但是對于“性權利”的性質屬性,我國民法、刑法等法律規范并未加以明確規定,而是將其通歸于“生命健康權”。
(三)缺乏對未成年運動員與教練等專業指導人員的權利義務關系規范
未成年運動員與教練等專業指導人員均具有自然人所享有的民事法律地位,不因指導地位而發生改變。但是,未成年運動員長期與教練、隊醫等年齡較長的成年人相處時,容易導致其處于服從地位,教練與未成年人運動員的基本法律權利義務關系主體扭曲化為“特殊權力——服從關系”,甚至呈現“家長主義”色彩。家長主義一般認為是精英們基于行為對象利益的考量而對其行為或選擇作出的干預,其前提條件在于,由于受主客觀條件的影響與制約,并非每一法律主體都能根據自我意志和事實認知作出對自身利益最佳的選擇(18)肖姍姍.少年司法之國家親權理念——兼論對我國少年司法的啟示[J].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4):39(4):94.。家長主義起源于羅馬法中的家父權制度,后家長主義發展為法律家長主義,即國家作為精英的集大成者,為了兒童或精神錯亂者的利益,可以允許實施家長式干預。根據少年司法的理論,國家可以基于未成年人利益的考量,而對未成年人的行為實施干預,但禁止個人或單位對未成年人實施家長主義。然而,明確的權利義務關系的缺失,導致“家長主義”作風仍在體育訓練、競技場盛行,如教練等專業指導人員強迫、組織未成年運動員使用興奮劑、以激發未成年人運動機能為由加大對未成年運動員的訓練力度甚至“體罰”。
如何結合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現狀,給予未成年運動員以有效的法律保障,從而更進一步地推動國家體育事業的發展成為新時代體育事業發展進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四、新時代未成年運動員法律保護的完善
暴力侵害是威脅未成年運動員安全和健康的重要隱患,具有體育特殊性和專業性。在一般規定的基礎上,國家有義務和責任通過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規,對特殊主體人員的權利義務邊界予以明確,規范職業要求,規定從業禁止制度以降低教練、醫護人員等專業人員給未成年運動員暴力傷害所帶來的風險,從而減少對未成年運動員的暴力侵害,保障未成年運動員的職業安全與身心健康發展安全。
(一)確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基本原則
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源于英美法中的“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亦有學者將其譯為“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但由于“最大化”“最佳”不符合中文的用語習慣,因此這一概念一直被詬病。2020年10月17日修訂通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在總則第4條明確規定“保護未成年人,應當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最有利于未成年人這一原則,貫穿在《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方方面面,也為與未成年人相關的法律法規修訂提供了指導,如《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就明確了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則。
未成年運動員的雙重身份屬性要求在《體育法》中必須明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因此,筆者建議將總則中的第5條修改為:“國家應當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對青年、少年、兒童的體育活動給予特別保障,增進青年、少年、兒童的身心健康。”在此原則的指導下,確立社會體育、學校體育、競技體育中對未成年運動員的特殊保護,為未成年運動員體育事業的發展提供特殊的保障條件。如結合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的特點,確定未成年運動員的休息權、獲取勞動報酬權等。以此原則為基礎,指導《反興奮劑條例》等與未成年運動員權利相關的法律法規的修訂。
(二)進一步明確未成年人運動員的傾斜性權利
未成年運動員的權利不僅為一種自然權利,也應當為一種法律權利。這種權利的內容不僅包括一般自然人所享有的權利內容,還應當賦予其作為未成年人與運動員雙重主體身份的特殊權利,如在有權接受體育訓練的同時享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有鑒于此,本文將“未成年運動員權利”定義為“依照法律規定,十八周歲以下的運動員在參加各項體育運動實踐中所產生和擁有的各項消極權利與積極權利的總和”。其中,消極權利是指“要求權利相對人予以尊重和容忍的權利”,積極權利是指“要求權利相對人予以給付和作為的權利”(19)周剛志.論“消極權利”與“積極權利”——中國憲法權利性質之實證分析[J].法學評論,2015,33(03):40-47.。在未成年運動員保護體系中,這一特殊主體處于弱勢地位,其消極權利占主導地位,如生命健康權、免受興奮劑侵害的自由、注冊和轉會的自由權等。當然,也應當享有一系列的積極權利如受教育權、公平競爭權、獲取勞動報酬權、監護權等。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為原則,通過修訂《體育法》或制定《未成年運動員保護條例》,將未成年運動員的特殊權利落到實處。
1.明確未成年運動員的人格權
在我國《民法典》出臺之前,這一類權利被稱為“生命健康權”或“身體健康權”。《民法典》將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作為人格權的基本組成部分,在第1002條至1004條予以明確規定。其中,生命權包括生命安全和生命尊嚴,身體權包括身體完整和行動自由,健康權包括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這一系列權利也被《世界人權宣言》所確定,其第3條明確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奧林匹克憲章》更是將保護運動員的權利作為國際奧委會的基本職能之一,明確要求不得實施有害于運動員生命權、身體權與健康權的行為,如要求男女平等、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鼓勵消除暴力、反對興奮劑的使用等。
生命權、身體權和健康權是人格權的基本內容,它們是“維系整個體育運動發展的生命要素”。這一系列權利決定了未成年人是否能成為一名優秀的運動員,同時也決定了其運動生涯的長短。未成年運動員由于其處于特殊的身心發展階段,自我保護能力較低,加之常處于脫離家庭與父母的監護和封閉或半封閉的環境之中,因此,其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更應予以重視。
實則,職業安全權和免受興奮劑侵害的權利,也應當被歸入人格權的實質范疇。反興奮劑使用是每一名運動員的義務,同時也是運動員消極權利的體現。使用興奮劑具有極大的風險,輕者可導致運動員內分泌紊亂,重者可導致運動員重傷或死亡。對于未成年運動員這一自我保護意識與自我防御意識相對薄弱很多的特殊群體,更應當加強對其反興奮劑侵害權利的保護。職業安全權這一積極性權利,要求相關部門在未成年人運動員實施體育訓練、體育競技比賽時,應當根據其身心發展特點、參與項目的高難度等,配置適合的、符合安全標準的運動設備、場所及其他必要的條件和保護措施,以保障其訓練的安全性。否則,將未成年運動員置于無限的風險之中,給未成年運動員身心所帶來的危害結果和潛在隱患將不可估量。這兩項職業性權利既是人格權的實質性要求,同時也是未成年運動員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的具體呈現。
2.明確未成年運動員的公平競爭權
公平競爭是體育競技運動的靈魂所在,公平競爭權是未成年運動員享有的最重要的職業性權利。因此,也有學者將此權利稱為“職業公平權”(20)錢侃侃.運動員權利的法理探析[J].法學評論,2015,33(01):191-196.。公平競爭,是指在體育競技比賽中,各相關主體為了爭奪有限的體育發展資源(物質或精神)或對自己有利的存續條件,以規則公平為前提,在許可的技術運用范圍內,以同樣的規則為標準進行裁定的競爭(21)程靜靜,鐘明寶,張春燕.體育競賽公平競爭的概念與規定性探究[J].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08(04):17-21.。我國《體育法》第37條明確規定了公平競爭在競技體育中的原則性地位。
未成年運動員的公平競爭權不應當僅限于運動競技場,其適用范圍應當擴大到選拔、參賽、裁判與獎勵等各階段。首先,就訓練條件而言,未成年運動員應當享有符合其身心發展特點的訓練、表演和競賽的條件,應當符合人權標準;其次,就參賽資格而言,應當以未成年運動員的運動水平為依據,避免其他不正當利益或其他博弈因素的介入考量;再次,就裁判而言,應當強調裁判員執法和成績判定的公平,拒絕一切“假球、黑哨”現象,以防對未成年運動員造成精神和物質上的打擊。此外,也應當注意對未成年運動員的獎勵制度的平等,獲得成績的未成年運動員應當享有與同一俱樂部、同一訓練隊或同一項目的成年運動員相當的獎勵,不能因為運動員未成年的身份而將相應的獎勵予以折扣,應根據其實際表現予以發放。
3.保障未成年運動員的受教育權
“在運動員成長過程中,早期的專業化訓練迫使其入隊年齡越來越年輕化......,為了取得更好的競訓成績,他們的文化學習時間長期被大量擠占,運動員文化程度低已成為長期存在的普遍現實。”(22)鄭麗,曹麗,壽在勇.論“舉國體制”下運動員在校受教育權的弱化與回歸[J].體育與科學,2014,35(02):101-104+100.這一現狀顯然有悖于法律授予未成年運動員的受教育權。受教育權是我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主要包括兩個基本要素:一是公民均有上學接受教育的權利;二是國家提供教育設施,培養教師,為公民受教育創造必要機會和物質條件。
對于未成年運動員,國家首先應當確保其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國家及相關部門,不得以未成年運動員以參加體育訓練、比賽為借口剝奪其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不得以體育成績來取代對未成年運動員文化成績的要求。國家及相關部門應當積極創造條件幫助未成年運動員的文化學習,以保證其接受完整、公平的義務教育。當然,受教育權既是公民的權利,也是公民的義務。對于未成年運動員厭惡文化學習,以體育訓練、比賽為借口拒絕文化學習的情形,其監護人應當與相關部門相互監督、相互配合,采取積極干預措施,提高未成年運動員對于接受義務教育重要性的認知,在特殊情況下,對適學適齡未成年運動員采取約束性措施,幫助其完成義務教育。
此外,還應當注意對未成年運動員升學優待權利的保護。我國《體育法》第28條雖然明確規定了“國家對優秀運動員在就業或者升學方面給予優待”,但這并不意味著未成年運動員可以獲得免試升學的機會。基于教育公平,應當對未成年運動員采用加試或加分的方式,在升學時充分考慮其體育方面的成績,同時也不忽視對其文化成績的考核。由此,才能更進一步提升未成年運動員本人、家庭及相關部門對義務教育權的重視,進而提高未成年運動員的綜合素質,為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提供更為堅固的后備力量。
4.落實未成年運動員的獲取勞動報酬權與社會保障權
獲取勞動報酬和社會保障是國家賦予未成年運動員的積極性權利。體育運動是一項特殊的勞動,運動員是特殊的勞動者,具有專業性與特殊性。體育運動多從未成年幼小階段開始,通過開發體育潛質以求最大限度地發掘其運動機能。運動中的訓練、比賽等活動對未成年運動員而言就是勞動,他們有權通過這一系列勞動獲得相應的物質報酬。同時,未成年運動員的獲取勞動報酬權也應當具有平等性,這一平等性體現在對同工同酬方面,不因年齡差異性而區別對待未成年運動員與成年運動員,未成年運動員應當獲得與其運動水平、訓練強度等相當的工資、報酬、津貼等。
社會保障權則強調對未成年運動員物質層面的保障。未成年運動員除卻獲得普通勞動者所享有的社會保險外,還應當享有與其主體特性、所從事的項目特色相符合的特殊社會保險保障。履行未成年運動員社會保險保障義務的主體不僅限于政府相關主管部門,他們所在的俱樂部或運動會的組辦者都應當為其購買相關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傷殘保險和失業保險等(23)陳林祥,李業武.我國優秀運動員社會保障體系的研究[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02,36(3):12-15.。運動傷害是威脅未成年運動員安全和健康的主要隱患。因此,國家有義務要求和監督運動員所屬單位建立健全未成年運動員醫療服務和保障制度,并及時、全面地處理運動傷害。同時,應當提供相關的保障制度和具體的措施,幫助未成年運動員受傷后的康復治療、恢復訓練等;或在未成年運動員康復不能或退役的情況下,提供相關的就業和優撫保障。
(三)加大對教練等專業人員的限制性規定
從目前對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行為人的限制性規定來看,主要體現在《反興奮劑條例》第39條、第40條對體育社會團體和運動員管理單位相關主管人員和責任人員、運動員輔助人員向運動員提供興奮劑,或者組織、強迫、欺騙運動員在體育運動中使用興奮劑的,或非法持有興奮劑的行為規定了2年、4年和終生不得從事體育工作和運動員輔助工作的處罰。然而,對于其他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并未有明確的禁止性規定。因此,本文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規制暴力侵犯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
1.擴大從業禁止的適用范圍
從業禁止,是指人民法院對因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被判處刑罰的人,根據其犯罪情況和預防犯罪的需要,禁止其在一定時期內從事相關職業。從現有的對侵犯未成年運動員行為人的規定來看,呈現出主體單一、從業禁止范圍過窄等問題。對暴力侵犯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人而言,可以從以下兩個層面入手,加大對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行為人的限制規定。
其一,擴大適用從業禁止的主體范圍。結合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現狀,應當將從業禁止的適用主體范圍擴大到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人,尤其是性侵行為人,而不僅限于妨害興奮劑管理的行為人。從業禁止的主體適用范圍不僅包括因強奸、強制猥褻、猥褻兒童犯罪等被作出有罪判決的人員,還包括因上述犯罪被檢察院作出相對不起訴決定的人員以及因猥褻,容留、介紹賣淫等涉性違法行為被行政處罰的人員。將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主體納入到從業禁止的適用范疇,無疑突破了原有刑法中規定的犯罪且被判處刑罰的前提條件,加大了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力度和范圍。這也是為了應對目前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嚴峻形勢,最大程度保護未成年運動員免受性侵害的應有之義。
其二,擴大從業禁止的從業范圍。當前對暴力侵犯未成年運動員人員的從業禁止僅限于對妨害興奮劑管理的行為人,禁止他們從事體育工作和運動員輔助工作。然而,根據當前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現狀,應當禁止暴力侵害主體參與至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的工作單位之中。這里的“接觸”主要是指人與人之間的物理性接觸。具體而言,這些工作單位包括學校、幼兒園、校外培訓等教育機構、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兒童福利機構等未成年人安置、救助機構;校外托管、臨時看護機構、為未成年人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療機構,以及其他對未成年人負有教育、培訓、監護、救助、看護、醫療等職責的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審查對象既包括教師、培訓師、教練、保育員、醫生等直接對未成年人負有職責的工作人員,也包括行政工作人員以及保安、門衛、駕駛員、保潔員和各級各類民辦學校的創辦者、理事會或者董事會成員、監事等雖不直接負有特殊職責,但具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工作便利的其他工作人員。
2.完善信息公開制度
目前,我國多個省市和地區嘗試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人員予以信息公開。筆者認為,可以將這一舉措納入到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人限制性規定范疇。但是,為了維護違法犯罪人員的正當權利,這種信息公開應當有所限制:
其一,有條件的限制公開。并非對所有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人的信息進行公開,公開的范圍限定于對未成年運動員造成了嚴重傷害的行為人。嚴重性的判斷應當結合被害人的情況以及性侵行為人的情況進行綜合判定:一方面,可以考慮對被害人造成的嚴重后果,比如身體損傷程度、心理健康情況以及是否剝奪了其生命等;另一方面,對其犯罪情節的嚴重程度、再犯的可能性大小、是否具有病態心理以及他人對其評價等進行綜合考察評估。
其二,建立全國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人員信息庫。在目前強化政法工作信息化的背景下,可以借助政法專用網絡和共享平臺發展的契機,多部門協同發力,由第一時間掌握信息來源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作為違法犯罪記錄的主要提供機關,將各自工作中處理的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案件信息及時匯總并主動錄入,再由負責信息管理的部門對相關信息扎口進行形式審核,對于符合要求的統一上傳至全國信息庫。為了準確識別暴力侵害者,登記的信息內容應當全面,一般應當包括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行為人的基本信息、違法犯罪信息和識別信息。需要登記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別、身份證號、住所地等。
其三,制定風險評估機制,決定公開的期限。基于對行為人的人身危險程度和社會危害性的整體考量,對不同暴力侵害行為人的再犯風險程度、人身危險性和病態心理進行評估,并以此為依據來進行分級管理。如果暴力侵害行為人在公開期限內沒有再次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則可以裁定取消對其信息公開。對不同危險程度的暴力侵害行為人施以不同的信息公開期,進行分級管理。將公開期限分為兩檔,五年的信息公開期限是原則性要求,終身公開個人信息為例外情況。
3.推進體育行業中強制報告制度的適用
202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有關部門出臺了《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從國家層面確立了強制報告制度,并對強制報告的主體、應當報告的情形,以及未履行報告職責的法律后果等予以明確。2020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從立法層面確定了強制報告制度的法律地位。推進體育行業的強制報告,可以促使負有報告義務的單位和個人了解自己的報告義務、應當報告的情形以及報告的對象,積極履行報告職責。
其一,規定對體育運動訓練相關求職者的強制報告義務。要求求職者在應聘時應當如實告知本人是否有過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違法犯罪行為,促使負有報告義務的體育從業人員了解自己的報告義務,積極履行報告職責。
其二,規定用人單位的嚴格審查義務。顯然,嚴格規范用人單位的審查義務,相比事后處罰,具有事先預防的優勢,在招聘環節就能將有性侵記錄的人排除在外。同時,用人單位具有人員排查的便利條件,對于已在職的工作人員是否存在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記錄,能夠第一時間發現并辭退。
其三,建立強制報告獎懲制度。對于因及時報案使未成年運動員擺脫困境,讓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人受到依法懲治的,應當給予獎勵和表彰;對于負有報告義務的單位及其工作人員未履行報告職責,造成嚴重后果的,如導致犯罪行為持續發生,未成年運動員身心健康受到嚴重傷害的,應當給予相應處分,取消其評優、評獎資格;對于阻止報告的,要從嚴處罰;對于公職人員不重視強制報告工作、不按規定落實的,應當由監察委員會進行問責。由此,將使報告義務落到實處,進而推動對未成年運動員被害人及其家庭提供傷害救治、心理疏導、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相關舉措的完善(24)宋英輝,劉銳玲.強制報告:提升未成年人保護水平[N].檢察日報,2021-03-21(003).。
五、結語
未成年人運動員的雙重屬性,導致他們受到暴力侵害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對這一弱勢群體予以特殊的法律保護勢在必行。體罰暴力、性侵害、興奮劑濫用等暴力侵害未成年運動員的行為雖然受到部分法律條文的規制,但實際上并未阻卻這一現象的發生。為打破傳統的運動員與教練等專業人員不對等的關系,應當從立法層面明確最有利于未成年運動員原則,對未成年運動員的權利作出傾斜性規定,并從從業禁止、信息公開、強制報告等司法措施入手,加大對這一部分違法犯罪人員的限制性規定。
——評《休閑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