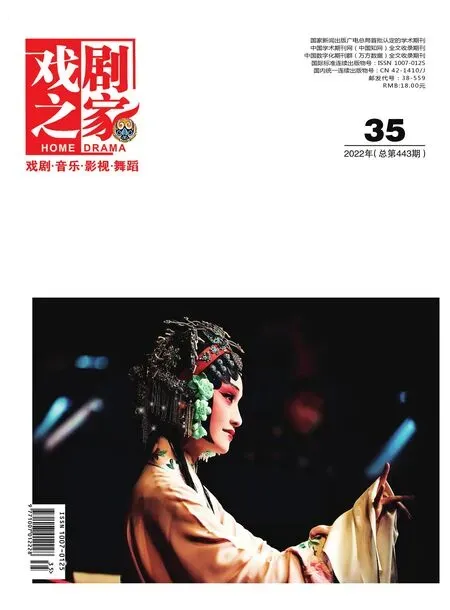人性的回歸
——解析舞劇《雷和雨》
郭璐璐
(北京舞蹈學(xué)院 北京 100081)
一、形式主義對《雷和雨》的解讀
(一)陌生化的舞劇運用
1.重復(fù)手段的情感渲染
(1)動作的重復(fù)
該舞劇對重復(fù)這一形式的運用首先體現(xiàn)在舞劇的動作層面。在舞劇第一幕的圈舞中,重復(fù)的動作一方面交代了六個人物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另一方面也加強了每個人物的情感訴說。圈舞中,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動作多次重復(fù)出現(xiàn),以抬手追尋動作為例,在圈舞這一片段中,這一動作出現(xiàn)了七次。第一次,周樸園抬手追尋周沖,這一動作表達了父親對兒子的愛,而面對父親的追尋,周沖黯然轉(zhuǎn)身離去,表達了他對周樸園的排斥;第二次,繁漪與魯侍萍相互追逐,二人的身體呈現(xiàn)前傾姿態(tài),反映了一種對峙的心理狀態(tài);第三次,追尋動作的發(fā)起者是周沖,他的動作積極且陽剛,但他的追尋卻是一場空;第四次,周萍追尋著四鳳;第五次,繁漪追尋著周萍;第六次,魯侍萍追尋著四鳳……同樣的動作,因為發(fā)起者不同,動作的質(zhì)感也截然不同,所表達的情感也不同。動作的每一次重復(fù)都在前一次的情感上加重一筆。圓形調(diào)度中,所有動作的重復(fù)交代的是六人之間命運的輪回和矛盾的交錯,將周家混亂不堪的局面展現(xiàn)在觀者眼前。
(2)調(diào)度的重復(fù)
圓形調(diào)度是第一幕的主要調(diào)度形式。六人之間的關(guān)系表達從“圓”開始,以“圓”結(jié)束。圓滿、和諧的“圓”,在這里反而成了永遠都出不去的牢籠,展現(xiàn)著人物之間的矛盾沖突——人物之間的矛盾尖銳到無法調(diào)解,透出一股“至死方休”的窒息感。編導(dǎo)對重復(fù)形式的運用也體現(xiàn)在對調(diào)度的重復(fù)運用方面。調(diào)度在這部作品中承擔(dān)了表意功能,錯綜復(fù)雜的人物關(guān)系通過清晰的調(diào)度路線得到一步一步的交代。第一幕通過一個主要的“圓圈”式的調(diào)度揭開了戲劇情節(jié)的開端。六個主要人物在圓圈式的順時針的追趕中依次以雙人托舉、雙人配合的形式交代了三組不同的愛情線索與矛盾糾葛。繁漪追趕著周萍,周沖心系著四鳳,周樸園向往著侍萍……
第三幕,在繁漪與周萍的雙人舞中,導(dǎo)演通過一來一回兩條橫線調(diào)度將兩人“愛”與“被愛”的關(guān)系表現(xiàn)到極致。在兩人向舞臺西面行進時,繁漪一次次地緊緊抱住周萍,渴望與他同行,苦苦哀求他,卻被他一次次無情地甩開,最后,他甚至直接將繁漪狠狠摔落在地,當(dāng)周萍向舞臺南面轉(zhuǎn)身離開時,繁漪依然沒有放棄,而是用跪地行走的方式跟在周萍身后,表現(xiàn)了一種失去“尊嚴(yán)”的愛。
(3)語言的重復(fù)
編導(dǎo)對重復(fù)的運用也表現(xiàn)在語言的重復(fù)上。在舞劇第四幕,舞劇情節(jié)走向高潮,當(dāng)所有的矛盾、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壓抑都無法解決的時候,舞劇中的人物高呼“讓我喘口氣吧!”“讓我喘口氣吧!”“讓我喘口氣吧!”“把門打開!”“打開!”“沒有門!”“沒有門”“帶我走吧!”“帶我走吧!”并且一遍遍地重復(fù),將六個人物內(nèi)心中的窒息感、壓抑感推向高潮。當(dāng)肢體動作不能極致傳達人物情感的時候,一遍遍重復(fù)的話將編導(dǎo)想要傳達的思想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
2.間離效果的情感表達
劇中兩個主要的女性角色是繁漪與魯侍萍,在第四幕“破滅”中,導(dǎo)演通過魯侍萍這一角色的“間離”,將原文中角色壓抑的情感進行了合理釋放。原著中的魯侍萍是一個傳統(tǒng)的、沉默的、被壓迫著的女性形象,但舞劇中的魯侍萍卻將自己比作“青春之神”,大膽地說出“一個女人只有認同保全自己告別的姿勢,才能獲得最終的魅力”。此時,魯侍萍口中的話已經(jīng)超越了角色本身,達到了一種“間離效果”,說出了作品中隱含的王玫自己想對觀眾說的話。這種對愛情的理解雖然是從角色魯侍萍的口中說出,但實則是王玫個人的經(jīng)歷和個人的感悟,與話劇《雷雨》產(chǎn)生了差異。
3.非線性敘事的結(jié)構(gòu)語言
編導(dǎo)通過“陌生化”增強舞劇情感效果的第三種方式,就是運用非線性敘事打破觀眾對話劇《雷雨》的固有認知。《雷雨》雖然有一定的群眾基礎(chǔ),但大部分觀眾對原有話劇有固定的認知,因此,編導(dǎo)在進行舞劇編創(chuàng)時,也面臨一定的困難。如何在已有的認知下對觀眾形成新的感官刺激?對此,編導(dǎo)選擇了非線性的敘事結(jié)構(gòu)和敘事語言,沒有按照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順序進行講述,而是在表達人物情感的基礎(chǔ)上對敘事進行了重構(gòu)。例如,舞劇一開場的摔藥碗場景,六個聚光燈先是打到六個主人公的下肢,然后對局促、顫抖的手部動作進行特寫。“摔藥碗”這個長達4 分鐘的段落沒有悅耳的旋律音樂,只有低沉的呼吸聲,沒有舞蹈動作,只有起伏、捏、撓、抓的身體。為何把“摔藥碗”這一動作作為舞劇的開篇?其實,編導(dǎo)在一開頭就交代了她想要表達的中心思想,那就是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在《雷和雨》的故事所處的年代中,它表現(xiàn)為對封建壓迫勢力的反抗,同時,這也讓我們思考舞劇對新時代女性的啟發(fā)。
(二)人物角色的背后隱喻
在第四幕中,導(dǎo)演以一段周樸園、侍萍和繁漪的三人舞刻畫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在周樸園和侍萍的雙人舞中,侍萍多次把重心依附在周樸園身上,兩人在多次的托舉中,一次次地糾纏在一起,卻又在剎那間猛然分開,表達了這段愛情中二人的糾葛,而繁漪像第三視角般在舞臺暗處,面朝東方,以“隔空”的形式旁觀另外的一切,慢慢走向侍萍,并以拍手這一動作表達對侍萍的暗諷,以張開雙臂向前逼近的身體語言表達對侍萍的逼問,侍萍則做出以手掩面的動作,表達了她內(nèi)心的痛苦與對現(xiàn)實世界的失望。在這一幕中,三個人物通過動作語言,揭示了兩個女人在“男權(quán)”社會中圍繞一個男人所產(chǎn)生的無奈,以及社會階級的枷鎖、人倫綱常的束縛,這些都讓女性感到壓抑和窒息。
(三)沖突之下的深刻反諷
1.心理空間與現(xiàn)實空間的沖突
編導(dǎo)在對舞劇進行情感刻畫的同時,運用了心理空間與現(xiàn)實空間對比的創(chuàng)作手法,使主人公繁漪的人物形象更加豐滿。在舞劇第四幕中,編導(dǎo)對雨夜中的繁漪進行了心理空間的刻畫,在繁漪的夢境中,一個女人緩緩向她走來,而當(dāng)繁漪想要張開雙臂擁抱這溫暖時,卻猛然發(fā)現(xiàn),這個女人是四鳳的化身。四鳳的動作充滿著挑釁與驕傲,刺痛了她內(nèi)心深處的傷痛,但剎那間,四鳳卻消失了。緊接著,一群女舞者上場,用抽象的純舞蹈刻畫了繁漪心中的彷徨、無助、壓抑。此時,群舞成了“虛”,繁漪自身成了“實”,導(dǎo)演用“虛實相交”的編舞手法烘托了繁漪的精神狀態(tài),刻畫了“現(xiàn)實”與“夢境”的殘酷。
在舞劇的第三幕中,出現(xiàn)了不符合現(xiàn)實原則的一幕,先是三個女性角色共舞,而三個舞者的身體狀態(tài)與情感狀態(tài)具有一致性,我們可以推斷,這一段舞蹈是在描寫女性角色的心理空間,表達繁漪和魯侍萍對“青春之神”的向往。這段舞蹈中多次出現(xiàn)頂跨擺手這一動作,強調(diào)了女性的生理曲線特征。三人舞結(jié)束后,三位男性角色上場,他們環(huán)繞在女性角色周邊,動作中出現(xiàn)“討好”意味。群舞演員依次上場,把六個主人公環(huán)繞住。此時,群舞演員的著裝引人注目,色彩艷麗的胸衣搭配短裙,有著詮釋“青春之神”的審美意味。
2.人物倫理關(guān)系的沖突
在舞劇《雷和雨》中,六個人物之間的愛恨關(guān)系有悖普遍認同的倫理規(guī)范。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人們極重人倫關(guān)系,這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特點。劇中的周萍與繁漪一直有著一段不可告人的關(guān)系,周萍對這段關(guān)系一直持以否認的態(tài)度。在社會大環(huán)境的壓迫下,他被傳統(tǒng)的倫理關(guān)系所束縛,難以接受自己與繼母之間不可告人的關(guān)系。相反,在另一方面,繁漪在追求愛情上有著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她在周樸園的壓迫下,一直勇于追愛周萍,她的這一表現(xiàn)在傳統(tǒng)的男權(quán)社會中很罕見。傳統(tǒng)文化要求女子對男性百依百順,男性的意見就是自己的行為指南,“夫為妻綱”的道德準(zhǔn)則是為人妻子所應(yīng)當(dāng)恪守的,所以,女性在愛情中一直是受支配的一方。但在本劇開頭的第一幕中,繁漪摔破藥碗這一動作就表現(xiàn)出繁漪是一位敢于反抗、有思想追求的“新”女性,她在周樸園的強權(quán)之下并沒有妥協(xié)。在舞劇中,作者對傳統(tǒng)倫理中的不合理成分進行了質(zhì)疑,并對傳統(tǒng)社會的男尊女卑觀念進行了批判。
二、以歷史唯物主義重思悲劇的“必然”
在西方倫理學(xué)中,女性被看作男性的附屬品,女性因為“性”,才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這是一種對女性個人價值的嚴(yán)重低估和個人權(quán)利的嚴(yán)重剝削,而這種現(xiàn)象在東方同樣存在。傳統(tǒng)倫理道德多在強調(diào)男性的意志,維護男性在家庭和社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雷和雨》中,我們看到的是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和對人性的踐踏,在劇中三個女性角色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歷史唯物主義下的“普遍性”。
舞劇作為一種藝術(shù)活動,其本質(zhì)是表達精神訴求。編導(dǎo)通過舞劇傳達人活在現(xiàn)世的感受,由此溝通過去和未來。舞劇的訴求表達不能僅停留在舞或劇上,而應(yīng)在精神層面,強調(diào)對人生的思考和對人類的關(guān)懷,并將其終端直指人生。編導(dǎo)王玫認為,《雷和雨》是“一個從《雷雨》中走來的故事”,她說,《雷雨》的故事距今已近百年,可是,故事中的人物好像還活在我們的身邊,還是那么似曾相識,似曾相識的感情、似曾相識的故事、似曾相識的痛苦、似曾相識的歡愉。劇中三個女性角色的悲劇,表現(xiàn)了一種歷史的“必然”,塑造了“典型環(huán)境下的典型性格”。在階級對立的背景下,侍萍與四鳳這一對母女的經(jīng)歷是如此地相似,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看,看似偶然、實則必然。封建社會中,女性地位低下,淪為身居高位的男人的“玩物”,尊嚴(yán)一次次被踐踏。而繁漪最后看透了世態(tài)炎涼,她的令人不齒的愛情,在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中,是不能被大眾所接受的,但同時,繁漪又代表了一種反抗封建壓迫的精神。
話劇《雷雨》作為一部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意義的作品,被賦予了宏大的歷史意義,而這種意義到了舞劇《雷和雨》中則變成了私人情感的外溢。舞劇《雷和雨》的改編打破了觀眾對這部文學(xué)作品的固有認知,更不同于其他舞劇版本的《雷雨》。芭蕾舞劇《雷雨》編導(dǎo)胡蓉蓉貢獻了民族芭蕾舞劇人物的“性格化”與中國舞劇的“民族化”。現(xiàn)代舞劇的《舞·雷雨》透過現(xiàn)代舞與無言劇場的表演,實現(xiàn)了人物內(nèi)心情感的外化。而王玫版本的《雷和雨》對原著進行了“解構(gòu)”,以身體動作為載體,從女性視角出發(fā),傳達了編導(dǎo)自己的人生故事和體驗,引發(fā)觀者思考“個人矛盾”與“社會矛盾”。在舞劇最后一個篇章“宿愿”中,編導(dǎo)進行了從“人物”到“人性”的雙重反思,透過這一悲劇,警醒人們珍惜當(dāng)下的生活,這也是編導(dǎo)自我愿望的抒發(fā),讓觀者思考,在逃不脫的社會環(huán)境中,人性中蘊含的“人本精神”。
三、結(jié)語
《雷和雨》這部現(xiàn)代舞劇打破了觀者以往的對話劇《雷雨》的刻板印象,從女性視角出發(fā)講述女人和男人之間的故事。故事中的六個主人公不再被話劇中的角色所束縛,他們的遭遇代表了所有人可能面對的困境,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社會在變、時代在變,但是,普遍的人性不會輕易改變。在舞劇《雷和雨》中,編導(dǎo)試圖用舞蹈對人的生存價值進行解釋,并在舞劇的最后一個篇章給出了答案——他們歡笑、他們舞蹈,他們生活在一個和諧、真誠的世界中,這個世界不再有恩怨情仇,不再有人性的不公,他們在潔白的世界中起舞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