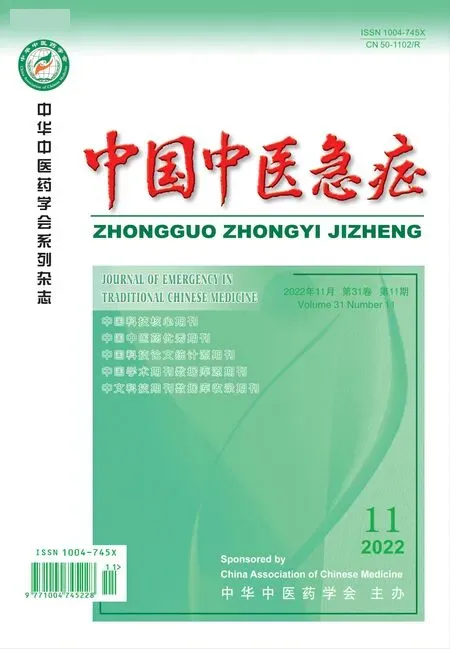疾脈源流考*
張夢楚 解天驍 趙倩倩 郭 睿 王憶勤 燕海霞
(上海中醫藥大學,上海市健康辨識與評估重點實驗室,上海 201203)
脈診是中醫臨床極具特色的診察方法。《黃帝內經》記載脈象21種,《脈經》提出24種脈象,《瀕湖脈學》提出27種,李士材的《診家正眼》又增加疾脈,故近代多從28種脈論述。因此,疾脈是二十八脈中最晚單列出的脈象。脈診文獻將疾脈的脈象特征描述為脈來急疾,較數脈尤甚,成人一息七八至(相當于脈搏120~140次/min);臨床意義為主陽極陰竭,元氣將脫[1]。本文對疾脈的古代脈名、脈象特征、臨床意義及現代研究進行歸納總結,以期為疾脈的脈象規范化、客觀化研究奠定基礎。
1 疾脈的古籍論述
1.1 疾脈的脈名源流研究
秦漢時期未明確記載疾脈,但有相關內容描述,如《素問·三部九候論》“何以知病之所在?歧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其脈不往來者死”[2],“疾”描述了脈率“快”的特征。《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言“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薄,讀為迫,言其迫急速之意[3]。由于“疾”字中含有“矢”,“矢”在離弦后是迅速、急速的,清代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說“按經傳多訓為急也,速也”[4],所以“疾”引申出“快”“急速”的意思,“薄疾”是指急迫速疾,喻脈象急促相迫。從脈象特征描述上看,符合疾脈的特征,但并未明確提出“疾脈”脈名。《素問·脈要精微論篇第十七》言“夫脈者,血之府,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為煩心”[2],有隋代楊上善的《黃帝內經太素》注有“動疾曰數”[5],解釋說明數脈的特征中包含了“疾”,疾與數,都有快、急、速的含義,更有張山雷的《脈學正義》曰“疾之與數,皆以急速為義,訓詁之學,此二字無甚分別”[3]。
因此,西晉王叔和的《脈經》,未將疾脈作為一個獨立的脈象進行具體描述,而是將疾脈附在“數脈”條中,僅用來表達脈象疾快的程度,如:“脈大疾者,生”“脈來疾者,為風也”[6]。元代滑壽首次描述了疾脈的脈象特征,把一息七至之脈稱為“疾”,《診家樞要·諸脈條辨》言“疾一名極。總是急速之形”。《診家樞要·脈陰陽類成》提到“疾,盛也。快于數而疾。呼吸之間脈七至”[7]。
明代李時珍所撰《瀕湖脈學》增至二十七脈,仍未把疾脈單獨列出,只在數脈相類詩中提到“數甚為疾”[8],同樣表達了疾比數更快。直到明代李中梓在《診家正眼》中增疾脈而為二十八脈,首次將疾脈別立為單獨一種脈象,為后世沿用,并具體闡述疾脈的體象“疾為急疾,數之至極;七至八至,脈流薄疾”“六至以上,脈有兩稱,或名曰疾,或名曰極,總是急速之形,數之甚者也”[9],可見疾脈是作為比數脈的脈率更加快的脈象而單列出的,強調了疾脈急速的形態,疾脈這一脈名被正式提出。
1.2 疾脈的脈象特征發展源流
疾脈的脈象特征主要體現為脈率較快。《診家樞要·脈陰陽類成》提到“疾,盛也。快于數而疾。呼吸之間脈七至”[7],表明了疾脈是比一息六至的數脈更快,為一息七至,明確區別于數脈。明代王紹隆傳清代潘楫增注的《醫燈續焰》曰“一息七至,氣更速快,故曰疾”[10],以上論述確定了疾脈的具體脈率為一息七至。
后世醫家對于疾脈的脈率也有不同論述。明代龔信《古今醫鑒·脈訣》言“數者,脈來速也,一息六、七至。而疾、促皆數之類也”[11],粗略地將疾脈歸為一息六七至的數脈一類,并沒有明確疾脈的頻率。在正式分列出疾脈的《診家正眼》中提到“疾為急疾,數之至極;七至八至,脈流薄疾”[9],將疾脈的脈率描述為一息七八至,后世對疾脈的描述多以此為基礎。后世《脈訣匯辨》《脈理宗經》對疾脈的體象描述均同《診家正眼》,奠定了后世對疾脈特征描述的基礎。又有張璐《診宗三味》曰“疾脈者,呼吸之間,脈七八至,雖急疾而不實大,不似洪脈之既大且數,卻無躁急之形也”[12],強調了疾脈是單因素脈象,以脈來去疾速為主,只是具有脈率上的變化,特征上兼有虛實大小變化時則為其他脈象,如疾速兼實大的是洪脈,以此與洪脈區別開來。《脈如》《脈理會參》《四診抉微》《脈理求真》《診家索隱》《脈說》等古籍基本都沿用此說法。清代張山雷《脈學正義》言“近人周氏澄之,乃謂疾脈當以形勢之急疾為主,不僅以至數為段,凡來勢急遽,奔馳迅利者,當謂之疾,與數脈之呼吸六至者,情狀不同云云”[3],這一說法實際上也表達了疾脈脈率較數脈更快,與數脈有區別,且強調了疾脈的來勢急遽,奔馳迅利的脈形與脈勢。“十二五”規劃教材《中醫診斷學》對疾脈的描述為“脈來急疾,一息七八至”[1],現代中醫教學沿用了脈率為“一息七八至”這一說法。
文獻中亦記載了一息超過八至的脈象。如《難經》云“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絕,此至之脈也”[13],《察病指南》亦云“一呼一吸脈六至者曰數,為始得病,七至者曰極,八至者曰脫,九至者曰死,十至者曰墓,沉細者困在夜,浮大者困在晝,十一、十二至者曰死,沉細夜死,浮大晝死,此為陽病之至脈也,故曰陽病脈數”[14],吳昆的《脈語》“疾:即數也。所謂躁者亦疾也,所謂駃者亦疾也”“數,醫者一呼一吸,病者脈來六至曰數。若七至八至,則又數也。九至、十至、十一至、十二至,則數之極矣”[15],將一息七八至稱為又數,又數的這一描述其實就是后世公認的疾脈脈率描述。八至以上的脈并沒有相應的脈名。但從以上論述來看,脈率一息八至以上者,多為脫、死、命絕者,提示病情危重,預后不良,與疾脈的臨床意義一致。因此有學者[16]認為,可將一息八至以上的脈象歸入疾脈,疾脈的脈率定為一息七至以上、脈搏140次/min以上可能更為合適。
2 疾脈的臨床意義
2.1 生理性疾脈
疾脈并非都是病脈,也可見于正常人,即生理性疾脈。生理性疾脈可見于劇烈運動后[17]。疾脈也可見于嬰幼兒。《脈語》曰“三歲以上,乃以一指取寸關尺之處,常以七至為率”[15],《脈訣刊誤集解》“惟小兒之脈,一呼吸間八至而細數者,為平耳”[18],明代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嬰兒孺子之脈疾,三四歲者呼吸之間脈當七至”[19],皆說明小兒脈率較快,屬于正常脈象。
疾脈亦可見于妊娠者,有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婦人妊娠病諸候上》“診其妊娠脈滑疾,重以手按之散者,胎已三月也”“診其妊娠脈,重手按之不散,但疾不滑者,五月也”[20],說明疾脈可見于妊娠婦女,又有“診其妊娠四月,欲知男女,左脈疾為男,右脈疾為女,左右俱疾,為生二子”可通過疾脈判斷胎兒的男女性別的記載。清代陳修園《女科要旨》“故脈疾而歇,至此數月之胎也。不知者斷為病脈,則令人恥笑”[21],強調疾脈有可能是孕脈,不能將疾脈一概作為病脈而論。孕婦臨產見疾脈者,稱為離經脈,《診家正眼》“至夫孕婦將產,亦得離經之脈,此又非以七八至得名”[9]。
2.2 病理性疾脈
古代醫學著作對疾脈主病有較多記載。其中《診家正眼》全面總結了疾脈的主病,并分述了左右寸關尺六部見疾脈的主病:“疾為陽極,陰氣欲竭。脈號離經,虛魂將絕。漸進漸疾,旦夕殞滅。左寸居疾,弗戢自焚。右寸居疾,金被火乘。左關疾也,肝陰已絕。右關疾也,脾陰消竭。左尺疾兮,涸轍難濡。右尺疾兮,赫曦過極”[9]。
2.2.1 判斷病證的虛實
1)主實證:疾脈主陽熱亢盛。實熱證出現疾脈是由于熱邪迫血運行加速所致。《脈經》“脈來疾者,為風也”“洪數滑疾為熱”“但有陰脈,來疾去疾,此相為水氣之毒也”[6]。《活人書》“陰毒,脈疾七至八至以上,疾不可數者,正是陰毒已深也,六脈沉細而疾,尺部斷小,寸口或大”[22]。認為疾脈與風病、熱病、陰病有關。北宋王貺《全生指迷方·辨脈形及變化所主病證法》“脈疾為伏陽內熱”[23],認為疾脈與內熱有關。《雞峰》“此由肺氣不調,邪熱乘客,上焦不降,其脈疾大”[24],《衛生寶鑒》“熱勝則脈疾”[25],可見疾脈與熱邪有關。明代徐春甫《古今醫統大全·瀉泄門》“如熱者脈疾,身多動,聲響亮,暴注下迫,此陽也”“凡瀉而脈沉細者為虛為寒,疾而數者為熱為積”[19],說明疾脈可見于泄瀉屬實熱證者。《診家樞要》“疾一名極,總是急速之形,數之盛者也,惟傷寒熱極,方見此脈,非他疾所恒有也”“熱極之脈也,在陽猶可,在陰為逆”[7]。也都認為疾脈的形成是陽熱極盛所致,見于傷寒熱疾。近代曹穎甫《經方實驗錄》“加以脈象疾數無倫,遍體灼熱,神昏流涎,在在均露熱征”[26],描述了疾脈多見于熱性病熱邪極盛的階段。因小兒本來脈率偏快,發熱在39~40℃時,其脈多疾而有力。多見于大葉性肺炎、流腦、膿毒敗血癥等感染性或傳染性疾病[27]。
疾脈也可主燥主火。明代秦景明《癥因脈治·痿癥論》“洪大數疾,燥火加臨”“右脈躁疾,燥火傷氣;左脈躁疾,燥火傷血”[28],清代魏之琇《續名醫類案》“疾者氣燥……氣燥則其行速,速則米粒不能安,宜其如飛也”[29],皆認為疾脈與燥火、氣燥有關。
臨床上,疾脈多與其他脈象相兼出現。新病可見疾脈與浮滑脈象,如《脈經》“脈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6]。百合病見浮緊滑疾脈,如《醫學入門·諸脈相兼主病》“浮緊滑疾百合辜;百合,傷寒病也”[30]。
2)主虛證:虛損勞傷體質虛弱者見疾脈,多是危重證候,乃陰氣欲竭所致。《診家正眼》“若勞瘵虛憊之人,亦或見之,則陰髓下竭,陽光上亢,有日無月,可與之決短期矣。陰陽易病者,脈常七八至,號為離經,是已登死籍者也”[9]。
脈疾按之堅是陽亢無制,真陰垂危之候;按之虛弱無力是陰液枯竭,陽氣外越之候,元氣將脫。明代肖京《軒岐救正論·如數脈》“又有快脈即疾脈。快疾即如數脈。非真數也。若假熱之病。誤服涼劑。脈亦見數也。每見舉世醫流。診得息數急疾。竟不知新病久病有力無力鼓與不鼓之異。一概混投苦寒。遽絕胃氣。安得不速人于死乎”[31]。《脈理求真》“疾似亢陽無制,亦有寒熱陰陽真假之異。若果疾兼洪大而堅,是明真陰垂絕,陽極難遏。如系按之不鼓,又為陰邪炎威虛陽發露之征”[32],醫者應當辨別清楚疾脈主熱證之真假,是陽盛陰竭還是陰盛虛陽外越之候,從而對癥下藥。
2.2.2 判斷疾病的進退與預后
由數脈變為疾脈是病進,由疾脈轉數脈是病退,病時見疾脈大多預示疾病加重,預后不良。《傷寒論》“脈浮而滑,浮為陽,滑為實,陽實相搏,其脈數疾,衛氣失度,浮滑之脈數疾,發熱汗出者,此為不治”[33],浮滑脈兼數疾,發熱汗出者不易治愈。《外臺秘要》曰“凡溫病患,三二日身軀熱,脈疾頭痛,食飲如故,脈直疾,八日死。四五日頭痛脈疾喜吐,脈來細,十二日死”[34],溫病見疾脈預示病情加重。《圣濟總錄·血痢》“其脈見虛小者生,身熱疾數者難治”[35],《脈訣乳海》“數疾且大有熱者死”[36],認為脈疾數身熱的患者難以治愈。元代戴啟宗《脈訣刊誤》“咳而尿血羸瘦形。其脈疾大命難任……金瘡血〔盛〕(出)虛細活。急疾大數必危身”“寸口〔澀〕(焱)疾不調死。沉細附骨不絕生”[18],《永類鈐方》:“脈疾急數,脾神絕……皆不治”[24],論及雜病,見疾脈則提示病情嚴重,甚至可危及生命。《脈因證治·崩漏》“洪數而疾。漏血下赤白,日下數升。脈急疾者死”[37],《萬病回春·產后》“產后緩滑,沉細亦宜;實大弦牢,澀疾皆危”[38],《壽世保元·諸脈宜忌生死》“心腹痛宜沉細遲。忌浮大弦長堅疾。婦人帶下,宜遲滑。忌浮虛急疾。病風不仁痿。脈虛者生。堅疾者死”[39],由此可見,婦人崩漏、產后、帶下見疾脈多為病危之勢。
2.3 疾脈的現代臨床研究
陶燕楠等[40]研究了病態竇房結綜合征的特殊類型——慢快綜合征的脈象特征,認為該病屬中醫學“脈遲證”“心悸”“厥證”等范疇,其脈象以遲脈、結代脈和疾脈為主,嚴重者可發展為脫脈。病久陽損及陰,氣陰兩虛,陰虛生熱,或血脈瘀阻,瘀久化熱,則出現疾脈或促脈。郭子光[41]對心律失常患者的異常脈象進行分類辨治,論述了數、疾脈與促脈,釜沸脈與雀啄脈等脈率快的脈象的辨證要點,由數而疾是病進,由疾轉數是病退,常見于竇性心動過速、陣發性心動過速。文秀華[42]對肺心病患者寸脈脈圖與中醫證型相關性進行了研究,發現肺心病患者左、右寸脈均以浮脈、數類脈(包括數脈、促脈、疾脈)和有歇止的脈象(包括結脈、促脈)為主,與正常組比較有顯著差異。在87例肺心病患者中,左寸疾脈脈象2例(2.30%),右寸疾脈脈象1例(1.15%),其中32例痰熱蘊肺型患者中浮而疾脈1例(3.13%),疾脈1例(3.13%)。肺心病病機總屬肺氣虧虛,心脈瘀阻;氣虛導致陽虛,虛陽浮越,推動血行加速;同時心脈瘀阻,血行不通,瘀久化熱。現代醫學認為,慢性肺源性心臟病常出現右心衰甚至全心衰,心輸出量不能滿足機體需求,心率代償性加快。張志辰等[43]動態采集急性腦梗死患者的體溫、血壓、中醫四診信息及NIHSS評分,對采集的數據分別進行相關性分析、建立Logistic回歸方程、主成分分,以體溫與血壓為因變量建立的回歸方程表明疾脈等四診信息與NIHSS評分之間存在一定聯系,其中疾脈與NIHSS評分的相關系數為r=1.905,P=0.009,提示疾脈可能與急性腦梗死患者的神經缺損程度有一定關系。宓余強等[44]應用聚類分析研究72例慢性乙型重型肝炎患者的證候特點,研究結果將遲脈、疾脈分別單獨聚為一類,提示慢性乙型重型肝炎久病則多臟器受累,氣血瘀滯、虛損,陰陽耗傷,病情兇險,辨證較為復雜。奚鳳霖[45]在胸痹病中醫治驗中提出,陰虛內熱型胸痹病多見數脈、疾脈,但數有虛實之辨,虛者即所謂“愈數則愈虛也”。
3 疾脈與相似脈
數脈與疾脈主要體現在脈率的不同,對數脈的定義有多種,一般以一息五至以上。如《脈理求真》曰“數則呼吸定息,每見五至六至,應指甚數”。《中醫診斷學》教材(第五版)定義為“數脈,一息脈來五至以上(相當于脈搏90次/min以上)”[46]。也有以一息六至以上為數脈,如《診家樞要》“數,一息六至,過平脈兩至也”。又有一息六至為數脈,一息七至為疾脈,一息八至為極脈等等,但三者主病無本質區別,常歸納統稱為數脈[47]。主病相似皆分虛實,但疾脈比數脈的主病在程度上更加嚴重,《景岳全書·脈神章》曰“數脈五至六至以上,凡急疾緊促之屬,皆其類也。為寒熱,為虛勞,為外邪,為癰瘍。滑數、洪數者多熱,澀數、細數者多寒。暴數者多外邪,久數者必虛損。數脈有陰有陽”。又曰“凡患虛損者,脈無不數,數脈主病,唯損最多,愈虛則愈數,愈數則愈危,豈數皆熱病乎。若以虛數做熱數,則萬無不敗者矣”[48],現代學者也認為,血虛及氣血之證出現數脈是相當常見的,正常人中體質愈虛則脈愈數。
釜沸脈,指脈率一息九至以上,脈位浮淺,脈形或大或小,脈勢極弱稍按即無之象。可見釜沸脈比疾脈脈率更快,主病更加嚴重。
4 小 結
縱觀歷代醫家有關疾脈的論述可見,疾脈是從數脈類中單列出來的,確定了疾脈的脈率為一息七到八至,脈搏120~140次/min。病理性疾脈主陽極陰竭,元氣將脫,生理性疾脈可見劇烈運動后、嬰幼兒以及妊娠婦女。疾脈主實證主要病因是熱、燥、火、瘀等;而虛證多是由陰液枯竭,陽氣外越欲脫或勞瘥導致。疾脈可與其他脈象相兼,多提示疾病的加重,預后不良。近年來,研究者結合現代醫學的認識,利用中醫四診信息數據的采集與分析方法,開展疾脈的臨床研究,以進一步探究疾脈與中醫證候的相關性,拓寬與發展了疾脈的研究領域。疾脈與其他相似脈的區別主要體現在脈率和主病病情嚴重程度上的不同。近年來脈診客觀化研究成果為進一步研究疾脈特征奠定了基礎,為豐富脈學理論提供了重要支撐。
結合古籍中有關疾脈脈象特征、臨床意義和疾脈現代臨床研究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古今醫家對疾脈主病的認識基本一致,但現今的教材中未提及妊娠婦女的生理性疾脈;對疾脈脈率一息七八至和一息七至以上的定義,還有待商討。現代對疾脈的客觀化、標準化研究較少,可能與疾脈的臨床病例較少有關。隨著現代醫學對疾病認識的發展,疾脈的臨床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拓展。同時臨床研究應注重四診、脈-證-病、相兼脈合參,才能提高臨床診斷準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