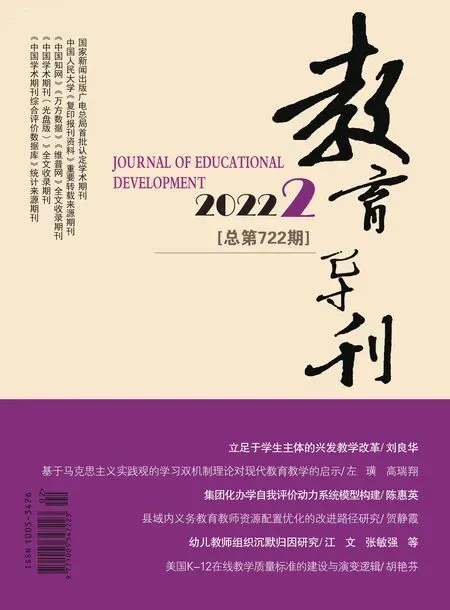中學語文課堂中構建中華經典研讀范式芻議
——以《論語·學而篇》第一章為例
(深圳大學 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廣東深圳 518060)
要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教育普及方面的創造性傳承、創新性發展,就離不開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體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繼承和發展,就離不開系統、深入、細致地研讀儒家經典,尤其是納入經學范圍的儒家經典。對于研讀儒家經典即經學的意義,徐敬修說:“所謂經學者,經世之學也。研究之者,則進足以治理國政,退足以修己獨善;考究其典章制度,則又有資于讀史;而治文學者,則又可以審文體之變遷;治地理者,則可以識方輿之沿革。蓋經為中國文學之祖,古來政治之源,其所概甚廣,學者所不可不知也。”〔1〕對于要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新時期專業從業者,自不待言,就是對于廣大非專業人士的中等文化以上程度者而言,也要認識到儒家經典對于文化傳承和創新的源頭和基礎作用。但經典傳承問題的核心不在儒家經典文本自身,而在于研讀儒家經典的閱讀者是否真正做到批判性繼承、開拓性發展;儒家經典研讀者以何種方式進入文本的意義世界并將之轉化為當下和未來的精神生活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經典研讀教學范式的過程設置。這一過程展開后所確立的教學范式,能有效保證研讀者的學習效果。
一、中華經典研讀范式的演進
如何研讀經典,歷代多有論述,而系統論讀書方法的當推南宋的朱熹,以其“書讀百遍,其義自見”而影響久遠。“凡讀書,須整頓幾案,令潔凈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有不到乎?”〔2〕此段文字對讀書的環境預設、態度要求、讀書步驟、讀書方法等做了細致的規定,后來的私塾教育對朱熹的讀書法有繼承和發展,成為研讀經典的有效范式之一,但在今天追求高效率的課堂教學上,由于課時的限制,學習目標的不同,只能是部分地繼承,很難完全按照此方式展開教學。
晚清處于中西學遽然轉換之際,民國時期則處在中西文化交融、交鋒的激戰時期,傳統經典的學習內容如何處置,始終是學習內容爭論的核心問題。張之洞的《書目答問》、胡適的“中學國故叢書”目錄、梁啟超的“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魯迅的大學國文系應讀文學書目、錢穆的7部“中國人所人人必讀的書”,都是圍繞選擇哪些著作進行研讀而展開,連帶就如何研讀經典的方式方法略有介紹,但大體停留在哪些章節可以讀,哪些人注釋的書可以讀,書中哪些內容要精讀,哪些內容可以略讀瀏覽,對于如何具體研讀雖有提及,但沒有一種有效的研讀經典范式確立〔3〕。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持續到21世紀的海峽兩岸的讀經現象,引人注目。關于“讀經現象”,胡曉明教授在《讀經:啟蒙還是蒙昧·序》中說:“即一場有語文工作者、媒體工作者、文化批評家、教師、出版商、教育基金會以及學生和家長們多方參與,有思潮、有綱領,也有爭論和批評,自下而上,有一定規模和影響的活動。”〔4〕該現象緣起于1995年第八屆全國政協會議上趙樸初、冰心等九位老人聯名提交《建立幼年古典學校的緊急呼吁》的議案。他們提議建立一所古典學校,招收一批幼兒,由他們親自指導,專職攻讀古代經典。但在當時,這個議案雖有實踐嘗試,但最終沒能有效落地,也沒有留下明確的經典研讀教學經驗。到了2007年,教育部、國家語委、中央文明辦聯合主辦了“中華誦·經典誦讀行動”,開展了中華誦經典誦讀大賽、規范漢字書寫大賽等活動,特別是誦讀、書寫、講解等傳承經典方式的提出,極大地推動了傳統經典尤其是儒家經典通過教育途徑開展傳播。
然而,在教學實踐中,經典的誦讀、書寫、講解,更多只是作為一種學校綜合實踐活動方案的實施方式,當下課堂上研讀儒家經典則表現在選擇性閱讀為主,主題式閱讀、專題式研讀為主,零碎的、功利的、片面的研讀經典為主,沒有形成一種有效的儒家經典研讀課堂教學范式。如何構建一種儒家經典研讀的課堂教學范式,能依靠學習者的主動性,隨著研讀儒家經典文本過程的展開,就能系統、深入、細致地讀懂經典,得到思維的訓練,思想的啟迪,人格的完善,自然這也成為當下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發展、構建貫穿國民教育體系始終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和教材體系的重要課堂教學實踐環節。
儒家經典研讀的課堂教學范式的構建,關鍵是“有效性”。這里的“有效性”有幾方面涵義:
第一是研讀者的普遍有效。由于經典自身的文本古奧,時間久遠,文言文與現代文之間差距過大,經典文本自身的開放性和多義性,一般研讀者如果沒有一定的訓練,輕易不敢研讀。如果研讀方式得當,可以改變這一狀況,促使所有受教育的國民都是經典的研讀者。對于儒家經典的研讀,應該享有“國民待遇”,人人有機會因儒家經典研讀范式的確立而敢于且能夠研讀儒家經典,不能只是高端人群、專業人士或特殊人群享有研讀經典的權利。
第二是指時間有效。研讀者在教學范式實施過程中獲取的歷時性知識是可靠的、有學術依據的、經得起長時間檢驗的;所獲得的共時性知識不是教授者一時一地傳遞出的偶然性知識,是有學理依據的知識傳承或創新。
第三是指系統有效。此種經典研讀教學范式能夠確保研讀者感受到儒家經典自身的豐富而不是碎片的、零散的知識體系,不能只顧一點不及其他,不能讓經典的解讀毫不顧及文本自身的邏輯自洽,更不能望文生義、牽強附會、胡編亂造。
第四是主體有效。此種經典研讀教學范式能夠確保研讀者能根據自身的求知需求,選擇系統的經典知識和解讀資料,而不是事先安排的抽取排列的知識,研讀過程的展開確保主體的全程參與,主動性探究學習始終處于主體地位,貫穿研讀的全過程。
第五是導向有效。此種經典研讀教學范式可以讓研讀者在完成學習過程后,得到思維的訓練和價值引領,通過辨析歷代的解釋,結合自身的認知,修正完善自己的認知,確立基本正確的民族文化的情感、態度、價值觀。此種導向不可能通過一次性的研讀而快速完成,但是需要確保研讀者能在探究性學習中得到多方面的觸動,從而主動確立其認識的方向之維。
二、中華經典研讀教學七步驟實踐舉例
下面以《論語·學而篇》第一章為例,來探討在當下如何依靠自我學習過程的展開,從處理文本理解的不同方式中,不斷加深乃至最終讀懂經典(1)以下的經典讀書法,充分借鑒了張志公先生《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的研究成果,曾慶寧先生的“《大學》三鼎家學”的理論和實踐,以及中國臺灣地區始于1968年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教學實踐總結,即十六字課堂教學經驗總結:“通其訓詁,掌握精義。觸類旁通,融入生活。”當然,十六字課堂教學經驗總結只是就教學的要求做了原則性規定,不是經典教學范式,此處不展開討論。。
《論語·學而篇》第一章: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
此章內容,初中文化以上程度的國人,應該耳熟能詳,對其意義也略有了解,但就是這么一章廣為流傳的內容,我們如何能做到系統、深入、細致地研讀,從而訓練我們的思維,鞏固我們的價值立場,完善我們的人格呢?
為了確保學習者能正確、深刻地理解經典文本,得到經典傳承的基本訓練,擬按照七個步驟來開展(實際教學可以適當調節):誦讀經典、書寫經典、注譯經典、參讀注譯、完善注譯、講解經典、踐習經典。
第一步:誦讀經典。
誦讀時,句讀要正確,不可讀破句子;正確讀出文本字音;最佳境界是能按照古文的聲律讀出韻律之美,體味古人的意境。由于漢字是表意文字,經典文本大多數是單音節字,所以一般要求慢讀,邊讀邊體味其意境,作為理解文本的一個入門。
第二步:書寫經典。
由于本章文本較短,可以抄寫經典文本一遍;對于長文,則可以選擇文中重要的段落或句子進行抄寫,以對經典原文加深印象,但盡可能能默寫出關鍵字詞,這是必要的訓練。此處,可以結合識字教學,對個別的關鍵字,就其字體源流、構字之理、用字之法來進行文字學解讀。
第三步:注譯經典。
這一步驟主要依靠研讀者的知識積累和人生閱歷,對經典文本展開注釋闡述、翻譯轉換和情景假設,以調動個人的全部認識去理解文本,以實現當下的經典文本轉換和主體性解讀。此一步驟又可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方面,注釋關鍵字詞,如:1.子;2.學(2)為了節約文字,有些關鍵字詞不在這里展開,比如本章的“時”“習”“慍”,尤其是“君子”,讀者如果有興趣,可以自己進行對讀。。注釋文字要盡可能簡短、嚴謹、周密,不要存在歧義。
第二方面, 翻譯全章,要求內容準確、語句通順、用詞典雅。
第三方面,章旨辨析,研讀者可以思考孔子當時說話的對象、時間、地點,什么問題促使孔子這么回答?說話目的是什么?能做到嗎?有什么不足?
每個學習者都有自己的理解,就會有不同的注釋和翻譯,只要忠實地記錄下來,那么就完成了這一步工作:自己注譯經典文本。
第四步:參照注譯。
選取歷代名家的注解本,通過比較諸家在經典原文的注釋、翻譯、解讀的不同,來理解不同時期學者的問題意識、學術路徑和思想差異。本文選取朱熹《四書章句集注》〔5〕、楊伯峻《論語譯注》〔6〕、錢穆《論語新解》〔7〕、孫欽善《論語注譯》〔8〕、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9〕(以下引文俱出自前列各書,不再單獨出注)等五位學者的解讀本來參照(選取版本的范圍,當然可以根據研讀者的自身條件和目的而有不同,此處只是做一個示范)。此一步驟也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方面 :比照閱讀眾家的注釋文字,通過比較文字的不同,領略各自作者的關注差異,從而迅速找到理解文本的角度。
1.“子”的不同注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不注。
楊伯峻《論語譯注》:《論語》“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而言。
錢穆《論語新解》:或說:“子,男子之通稱。”或說:“五等爵名。”春秋以后,執政之卿亦稱子,其后匹夫為學者所宗亦稱子,孔子、墨子是也。或說:“孔子為魯司寇,其門人稱之曰子。稱子不成辭則曰夫子。”《論語》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單稱子僅一見。
孫欽善《論語注譯》:古時男子的尊稱。《論語》中的 “子曰”皆用來稱孔子,等于說先生。
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子曰”,是孔子說。《論語》全書的“子曰”都是孔子說。古代子書,是以“子”稱老師。如《孫子》十三篇,每篇開頭多作“孫子曰”;《墨子》的《尚賢》等十篇,每篇開頭也作“子墨子曰”。這樣的“子”是對老師的尊稱。研究《論語》,我們要知道,中國最早的老師怎么叫,學生稱孔子為“子”,這個“子”是什么意思。“子”本來是貴族子弟的稱呼。西周時期,貴族子弟多被稱為“小子”,就連王,在神祖面前也自稱“小子”。春秋時期,人們以“夫子”或“子”稱呼卿大夫,即當時的貴族官僚。“夫子”是第三人稱,相當他老人家。“子”是第二人稱,相當您老人家。“夫子”也可簡稱為“子”。“夫子”和“子”都是尊稱。孔子當過魯大夫,很短,只有三年,但他的學生是用這個頭銜稱他們的老師。這里的“子”是“夫子”的省略。古代最初只有一門學問,即做官的學問,長官就是老師,這叫官師之學。孔子強調,讀書要做官,這不是他的發明,而是官師之學的傳統。“諸子”的“子”是來源于官師,稱呼老師和稱呼首長是一樣的。
2.“學”的不同注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后,后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楊伯峻《論語譯注》:不注。
錢穆《論語新解》:學,誦,習義。凡誦讀練習皆是學。舊說:“學,覺也,效也,后覺習效先覺之所謂謂之學。”然社會文化日興,文字使用日盛,后覺習效先覺,不能不誦讀先覺之著述,則二義仍相通。
孫欽善《論語注譯》:不注。
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不注。
這五個版本的關鍵字詞注釋,作為研讀者,如何理解不同的注釋文字,理解其不同的闡釋角度,乃至于思想分析,究竟哪一個更適合當下的解讀,或者有助于當下的解讀,這就需要我們準確理解注釋者的學術立場和闡釋原則,這十分有助于研讀者在短期內了解學術思想的變遷和儒家文化的內在豐富性。
比如,怎么來注解“子”,簡單化處理,“子”就是指孔子。但要說“子”就是孔子,會帶來很多麻煩,《論語》中還有有子、曾子,更重要的還有“南子”,那個“子”還指一個女的,所以“《論語》‘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這個注解就比較完備,比較準確,不多一個字,也不能少一個字。如何完整、準確、嚴謹地注釋經典文字,這是一個讀懂經典很重要的方面。在過去,這門學問叫訓詁,楊伯峻先生使用的訓詁方法是義項法。而孫欽善先生的注釋,既有對魏晉注釋家的繼承,也有對楊伯峻先生注釋的吸收,更有對孔子敬意的表達,應該說是后來學者對歷代注釋的全面吸收。而李零先生的注釋則考證文字多而思路清晰,也頗有見地。
再來看“學”的注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后,后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楊伯峻《論語譯注》:不注。錢穆《論語新解》:“學,誦,習義。凡誦讀練習皆是學。舊說:‘學,覺也,效也,后覺習效先覺之所為謂之學。’然社會文化日興,文字使用日盛,后覺習效先覺,不能不誦讀先覺之著述,則二義仍相通。”孫欽善《論語注譯》:不注。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不注。這五個注釋,選擇哪個?為什么朱熹和錢穆對“學”注釋內容甚多,而楊伯峻、孫欽善、李零對“學”都沒有注釋,是因為“學”太簡單而不需要注釋,還是太復雜而無法注釋?那么我們就要從譯文來看了,也就是第四步的第二個方面,比照不同注釋家的譯文: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無譯文。
楊伯峻《論語譯注》:孔子說:“學了,然后按一定的時間去實習它,不也高興嗎?有志同道合的人從遠處來,不也快樂嗎?人家不了解我,我卻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嗎?
錢穆《論語新解》:先生說:“學能時時反復習之,我心不很覺欣暢嗎?有許多朋友從遠而來,我心不更感快樂嗎?別人不知道我,我心不存些微怫郁不歡之意,不真是一位修養有成德的君子嗎?”
孫欽善《論語注譯》:孔子說:“學了以后而又按時復習,不也是很高興的嗎?有朋友從遠方來相會,不也是很快樂的嗎?人家不了解自己而自己又不惱火,不也是君子嗎?”
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無譯文。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沒有譯文,楊伯峻《論語譯注》譯文是“孔子說:學了,然后……”錢穆《論語新解》翻譯為:“先生說:學能……”他把“而”翻譯成“能”。孫欽善《論語注譯》翻譯為:“孔子說:學了以后而又……”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沒有譯文。楊伯峻先生、錢穆先生和孫欽善先生的譯文都對“學”沒有直接翻譯,有的直接保留了這個“學”字,有了在“學”后加了一個“了”字,甚至加了一個逗號。
“學”怎么翻譯?沒法翻譯!這就涉及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度理解。
為什么沒法翻譯?因為在現在的漢語詞匯里找不出一個詞對應它。所以錢穆先生、楊伯峻先生和孫欽善先生干脆不翻譯了,翻譯了就是不準確的,還不如不翻譯。就如同“仁”“禮樂”“孝”等中華文化的核心詞匯,無法找到對應的有效的西方英語單詞。
將不同注釋文本做一比較后,就能看出哪一位注釋作者偏重文獻,哪一位注釋者偏重理學,哪一位注釋者偏重儒學的當代融合發展,哪一位注釋者是實學立場。比如朱熹先生的理學闡釋,錢穆先生的海外新儒家立場,楊伯峻先生嚴謹的實學立場,孫欽善先生的綜合諸家擇善而從,李零先生的文獻梳理。
第三方面:不同注釋家的章旨辨析。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楊伯峻《論語譯注》:無。
錢穆《論語新解》:本章乃敘述一理想學者之畢生經歷,實亦孔子畢生為學之自述。學而時習,乃初學事,孔子十五志學以后當之。有朋遠來,則中年成學后事,孔子三十而立后當之。茍非學邃行尊,達于最高境界,不宜輕言人不我知,孔子五十知命后當之。學者惟當牢守學而時習之一境,斯可有遠方朋來之樂。最后一境,本非學者所望。學求深造日進,至于人不能知,乃屬無可奈何。圣人深造之已極,自知彌深,自信彌篤,乃曰:“知我者其天乎”,然非淺學所當驟企也。
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學。孔子之教人以學,重在學為人之道。本篇各章,多務本之義,乃學者之先務,故《論語》編者列之全書之首。又以本章列本篇之首,實有深義。學者循此為學,時時反驗之于己心,可以自考其學之虛實淺深,而其進不能自已矣。
學者讀《論語》,當知反求諸己之義。如讀此章,若不切實學而時習,寧知不亦悅乎之真義?孔子之學,皆由真修實踐來。無此真修實踐,即無由明其義蘊。本章“學”字,乃兼所學之事與為學之功言。孔門論學,范圍雖廣,然必兼心地修養與人格完成之兩義。學者誠能如此章所言,自始即可有逢源之妙,而終身率循,亦不能盡所蘊之深。此圣人之言所以為上下一致,終始一轍也。
孔子距今已逾二千五百年,今之為學,自不能盡同于孔子之時。然即在今日,仍有時習,仍有朋來,仍有人不能知之一境。學者內心,仍亦有悅、有樂、有慍、不慍之辨。即再逾兩千五百年,亦當如是。故知孔子之所啟示,乃屬一種通義,不受時限,通于古今,而義無不然,故為可貴。讀者不可不知。
孫欽善《論語注譯》:無。
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這一章好像研究生入學,導師給他們訓話,主要是講學習的快樂。第一樂是個人的快樂,你們來到我的門下,聽我傳道,按時復習,樂在其中。第二樂是和同學在一起,你們不光自己學,還不斷有人慕名而來,成為 你們的同學,弦歌一堂,豈不快哉?第三樂是師門以外,別人不了解,千萬別生氣,因為你學習的目標,是 成為君子,學習是為自己學,別人不知道,照樣是君子,你有君子的快樂, 內心的快樂,不也很好嗎?孔了好學,把學習當快樂,認為求知的快樂比求知本身還重要(《雍也》 6.20)。這幾句話,共同點是快樂。“說”即悅,是愉悅,“樂”是快樂,“不慍” 也還是愉悅或快樂。《論語》以此為第一章,很好。
通過比較眾家的章旨辨析,可以加深對此章的背景和思想的理解。
第五步:完善譯注。
在完成上面兩步之后,依照第四步的參照,修正自注的注釋、譯文和章旨內容,形成自己認為相對準確、相對合理的注釋和譯文,重新做一遍注釋、翻譯和章旨辨析工作。
第六步:講解經典。
有了上述的自己注譯文字、參照諸家注譯、重新完善自己的注譯,無論是從字詞句的理解,還是章旨的辨析,都有了一個扎實的基礎,不再是感性的意見性理解,在此基礎上,可以通過自我復述大意或者講解文本內容,鞏固和加深對文本的理解。
第七步:踐習經典。
儒家經典是講究經世致用或者說是用來修身致用的,不是為了純粹知識的積累,當在較為全面的理解文本之后,就可以把這句經典的精神或原則帶入到日常行為當中去。比如,在傳統文化課上開展《論語》研讀,如果把“子曰”的“子”翻譯成“先生”,那么后輩對先賢的敬意一下子就顯現出來,比“孔子說”要好。這個稱謂也反映了態度、立場、價值取向。當我們習慣了“先生說”,那就是在課堂上的行為落實。“學”要綜合來考慮,不僅僅是知識的學習,還有內在人格境界的提升,那我們就會對“學”有一個全面的理解。
三、構建中華經典研讀教學范式的意義
當今社會,教育越來越普及,知識生產越來越豐富,科學技術快速發展,但無論如何,人性的養育、品性的提升、人格的完善,并不能隨著知識和技術的發展而自動完成,必須借助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才有可能營造一個人人向善向上的育人氛圍,而這離不開傳統文化的代代傳承,在解決這一問題上,上述研讀儒家經典課堂教學范式具有極其強烈的時代意義:
第一,實現了儒家經典研讀者從精英人群到大眾讀者的轉變。
傳統社會,由于特定的社會環境,形成了支撐儒家經典研讀的國家制度,尤其是科舉制的發展和成熟,使儒家經典的研讀局限于少數的讀書人,也就是士人,但當今是國民教育時代,要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貫穿國民教育體系始終的任務,新的研讀范式建立,就可以滿足大眾讀者對儒家經典系統、深入、細致研讀的精神生活需要。
第二,既保證了經典傳承中解讀的時效性,又保證了經典傳承中內容的系統性和豐富性,還在批判性的研讀中訓練了研讀者的思維,實現了價值引領的教育功能。
這一研讀儒家經典范式,化解了儒家經典傳承中的灌輸式學習、碎片化學習、標準答案式學習方式,研讀者通過對歷時性的經典內容注釋的了解,在理解不同時代、不同區域、不同立場的注釋者的闡釋后,就可以在經典闡釋的豐富內容中,通過比較異同、排比范圍、推理概念乃至深度思考,實現了對研讀者自身的共時性思維訓練和價值達成。
第三,實現儒家經典傳承的教師本位到學生本位的教學轉換。
這一研讀儒家經典范式,充分尊重研讀者的認知主體,不是讓注釋者完全主導研讀者的學習過程,而是在協助研讀者完善自身知識結構的過程中實現學習。
雖然上述研讀經典的課堂教學范式是以儒家經典為主來構建的,但并不局限于儒家經典。樓宇烈先生倡導中國人讀好“三玄四書五經”(3)“三玄”是指《老子》《莊子》《周易》,“四書”是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五經”是指《周易》《禮記》《尚書》《詩經》《春秋左傳》,《大學》和《中庸》都是從《禮記》當中抽出來的,本來各是一篇文章,《周易》是重復的,所以讀九本書就可以對中國文化的根源性的典籍有了解了。參見:樓宇烈.中國的品格〔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67-87。,讀完這些儒家和道家的基本典籍,就是讀懂了中國文化的根源性典籍,就能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思想有基本的把握。樓氏認為,中華民族的經典雖然數量繁多,但是統之有序,眾多的經典之間是“述而不作,理念相通”的。“三玄四書五經”是代表了眾多經典的內在一致性的。
確立了經典的學習范圍,再結合有效的研讀范式,對渴望進入傳統文化大門的中等文化以上程度的學習者而言,通過“一門深入,七步漸修”,完全可以在當今社會實現對經典的系統、深入、細致的研讀。一門深入,就是選一部自己喜歡的經典,比如樓氏推薦的任何一部,尤其是《四書》:《大學》朱熹改本1753個字,《論語》15836字(4)關于《論語》原文字數的統計,歷來有不同說法,有12750字一說,有13700字一說,此處取李零教授的說法:“現在的《論語》,字數有15836字,不包括重文186字。古人統計字數,習慣是不計重文。”見:李零.喪家狗:我讀《論語》〔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36。;《孟子》34685個字,《中庸》3568個字等,字數在今天來說,都不算多。怎么深入呢?就是上述的七個步驟的經典研讀范式,希望通過這樣的設計,實現《大學》里面說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中國人研讀經典的學習方式,并讓這種學習方式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從確立民族文化的歸屬感,生發出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