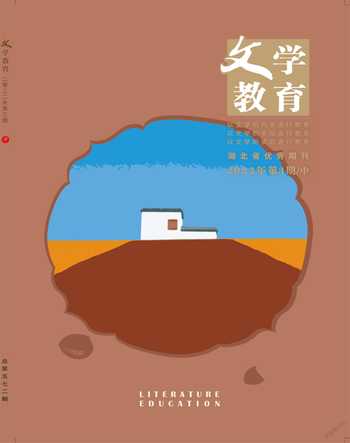《我的叔叔于勒》中的突變與錯位
嚴俊燕 劉冰冰
內容摘要:《我的叔叔于勒》是部編版語文九年級上冊第四單元的莫泊桑所寫的一篇經典短篇小說。這篇小說寫了菲利普夫婦與“我”在船上遇到于勒,把兩者對于勒情感態度的不同進行對比所產生的情感錯位,進而得出主題對人性回歸的呼喚。許多教師在教學該篇時,總是按照情節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方式去教授,不知該如何進一步解讀小說。通過研讀該篇小說,抓住這一篇課文的巧妙之處,即敘述視角與情節處理,引導以“我”之眼敘述小說的情節變化,通過探其“突變”、析情“錯位”兩大環節學習小說。通過探其“突變”,對菲利普夫婦的形象進行分析,了解到他們并非本性勢利,理解他們重視金錢、唯利是圖背后的心酸與無奈;通過析情“錯位”,感受“我”的純潔及本性善良;最后通過品析童年的“我”與成年的“我”,進而得出主題對人性回歸的呼喚。
關鍵詞:突變 錯位 人性回歸
短篇小說通常在于選取和描繪生活的橫截面,即富有典型意義的生活片段,極力去刻畫人物的性格特征,進而及時、迅速地反映社會生活的某一側面或生活內容。據此了解到《我的叔叔于勒》是莫泊桑短篇小說的經典之作,作者摒棄了以往的寫作方式,即開端——發展——高潮——結局,而是著重于對生活橫截面進行描寫,極力描寫菲利普夫婦及“我”在船上遇到于勒的片段,且所寫的菲利普夫婦性格形象上豐滿、意蘊豐厚,把其對于勒的態度表現得淋漓盡致,讀者可以深入文本,探尋菲利普夫婦形象性格背后的原因。
關于如何進一步解讀小說,王榮生老師說過:“小說教學的內容要隨小說的類型特征來確定;還需要研究這篇小說的文體體式,并據此來確定小說教學的內容,即具體的解讀方式。”《我的叔叔于勒》作為一篇短篇小說,是現代小說中的情節類的小說,重點要去把握人物的活動愿望、行動等。接下來便可以探其具體的解讀方式。王榮生老師在《小說教學教什么》一書中寫到小說解讀方式可分為三個層面,一是與表達方式直接相關的解讀方式,比如品味語詞、解析句式、掌握視角;二是表達對象,如情節、主題……[1]通過對文本的仔細推敲,發現《我的叔叔于勒》一文的妙處在于敘述視角與情節的處理上。
《我的叔叔于勒》采用的是內聚焦敘述,即第一人稱的敘述。文中的“我”小若瑟夫既參與了小說事件的過程,同時也可以離開作品環境面向讀者進行描述。一方面這種敘述視角可以讓讀者更容易理解小說,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另一方面由于該敘述視角受到角色身份的限制,有所遮蔽,因此不能敘述本角色所不知道的內。但也因為小說敘述視角的空白,才使得小說更具有張力與真實感。小說的情節構成是假定的、獨特的,具有情感因果性。因此,我們在讀小說時要注意對情節功能的分析,深挖情節的精彩之處。孫紹振老師說過好的小說情節,應該要有兩種功能。其一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規,進入第二環境,暴露第二心態。其二就是讓本來處于同一情感狀態的人物,發生情感“錯位”。[2]因此,筆者將從“我”之眼敘述小說的情節變化,通過探其“突變”、析情“錯位”解讀小說內容,進而分析小說主題。
一.探其“突變”
“突變”即是將人物打出常規,進入一個非常規的、意想不到的,使其來不及調整的境界中,進而探究人物內心潛在的情感,深層的奧秘。在《我的叔叔于勒》這篇文章中,首先分析在常規環境下,菲利普一家對于勒的態度。文章寫到于勒在以前是全家的恐怖,他不僅糟蹋錢,還占據“我”父親的一部分財產,所以他是不受菲利普一家待見的,也因此于勒被打發去了美洲。而現在他是我們一家人的唯一希望,原因是于勒去美洲不久后便寫了一封信回來。這封信成為了一個重點。因為于勒在信中寫到自己賺了點錢,發財了便會回來彌補菲利普一家的損失。而菲利普一家自從收到于勒的來信后,便期待“有錢”的于勒回來。這封信也因此被菲利普一家稱為福音書,可見他們一家對于勒回來的期盼程度。
加上有一位船長說于勒做著一樁很大的買賣,讓菲利普一家更加堅信于勒會發財,并且回來接濟他們,這也使得他們愈發期待于勒的回來,他們憧憬著于勒回來后的美好。也正因為如此,菲利普一家每周日都會衣冠整齊地到海邊棧橋上等待“好心的于勒”回來,并且堅持了十年之久。雖然這十年來于勒一直沒有出現過,但菲利普一家還是滿心期待于勒回來。莫泊桑在情節鋪墊上絲毫不吝嗇其筆墨,在期待于勒回來的情節上不斷蓄勢,把菲利普一家等待發了財的于勒回來的期盼程度寫得越來越高,將情節推至一個最高點。當情節置于最高點時,讀者的心也跟著到達頂點,此時讀者也在想象,接下來的情節會如何發展,是繼續蓄勢?還是了會出其不意,迎來突轉?
這時莫泊桑將情節引至二姐婚后,一家人去哲爾賽島上旅行的畫面。這時的菲利普一家還是很快活和驕傲的。可這是他們在船上遇到一個衣衫襤褸的年老水手,他們怎么也不會想到這個人是于勒,是他們等待了十年的于勒啊。此時的菲利普一家是否開心,快活?遇到他們心心念念的于勒難道不應該是一件皆大歡喜的事情嗎?小說的故事就此就可以結束了?其實不是,菲利普一家在去哲爾賽島的小輪船上遇到了于勒這一情節是一個轉折點,這時人物進入了一個意想不到、人物和自我心理關系來不及調整的境界中,也是小說達到扣人心弦的高潮之處,因此這一篇小說的巧妙之處在于莫泊桑對情節進行了突變,即菲利普夫婦遇到的不是自己所想的那個“有錢”人于勒,而是遇到一個比之前更差的于勒,一個衣衫襤褸,又老又臟的于勒。莫泊桑濃墨重彩地描寫了遇見于勒的情節,通過對菲利普一家形象的分析,進而分析人物的內心變化,探索其深層、不為人知的奧秘。
利昂·塞米利安說過“我們看一部小說主要看小說中對人物性格的揭示,這也就是構成小說的魅力和教育意義的因素。”[3]通過對文本進行分析可知,船上的相遇讓菲利普夫婦的美夢徹底破碎,此時他們見到的只是一個又老又臟、滿臉皺紋的于勒。這時菲利普夫婦內心最深層的奧秘被公之于眾,隨著于勒的身份的逐漸被證實,他們由失落到逐漸變得不安,他們害怕這個又老又臟的于勒認出他們,再次訛上他們,從他們的語言、動作、神態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他們恐懼、害怕、哆嗦、不安、躲避的心理。在莫泊桑筆下,菲利普夫婦的貪婪與自私被無限放大,但只通過這一情節便可見他們是一個勢利、唯利是圖的人?
莫泊桑筆下菲利普夫婦的形象并非如此簡單,由于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也是受到特定環境制約的[4],所以在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復雜的矛盾關系中會顯現出不同的性格。背景即環境;尤其是家庭內景,可以看做是對人物的轉喻性的或隱喻性的表現。[5]莫泊桑寫道在平時生活中,菲利普一家過著艱辛、困窘的生活,文中寫到“家里樣樣都要節省;母親對這種長期的拮據生活感到痛苦;姐姐也因為家里窮找不到對象……”但菲利普夫婦并沒有因此在精神上自甘墮落,他們對生活仍有追求,仍報有希望。文中寫到父親每天都很努力地工作,很晚才從辦公室回來;也因此才會相信那個“有錢”于勒會回來接濟他們,所以堅持每周日帶領我們衣冠整齊地去海邊散步;在船上時也會被高貴的吃法所打動,雖然知道家里沒有錢,但是還是想請我們吃牡蠣……,通過這些情節的描寫讓我們進一步體會到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菲利普夫婦背后的心酸與無奈,因此莫泊桑寫菲利普夫婦這個形象,不單單只是對成人世界的批判,也有對其生活不易的同情、理解及生活的困窘使他們變成勢利性格的惋惜。
二.析情“錯位”
小說情節的精彩在于小說中的幾個人物從相同的心態變成另外一種心態,即讓本來處于同一個情感狀態的人物,發生情感的“錯位”。[6]莫泊桑巧妙將菲利普夫婦在船上遇到于勒時的態度與“我”對于勒的態度進行了對比,進而產生了情感錯位。文中寫到收到于勒的來信后,“我們”一家人都滿心欣喜,一心期待于勒回來,可見于勒在我們家的地位明顯上升。但當菲利普夫婦真正遇到于勒,見到這個又老又臟的于勒時,菲利普夫婦與“我”的情感便產生了錯位。當菲利普夫婦得知這個撬牡蠣的水手是于勒時,他們表現得驚慌失措、氣急敗壞,菲利普夫人甚至稱呼于勒為“賊”“這個小子”“那個討飯的”“流氓”……可見父母對于勒已經沒有原先的親昵與牽掛,甚至害怕于勒認出他們,想對他避而遠之,所以讓“我”去給牡蠣的錢。
反而觀之,“我”對于勒的看法是不同于“我”的父母,“我”并沒有在意于勒是否有錢,“我”只在意他與“我”的關系,我們是親人啊。因此當“我”面對這個又老又臟的于勒時,“我”的內心仍是有所觸動的。“我”并不像“我”的父母一樣對于勒。“我”是尊重于勒的,因為他是“我”的親人。所以當“我”把錢給于勒時,稱其為“先生”。當他在找錢時,“我”認真地看了看他布滿皺紋的手及那蒼老的臉,那是飽經磨難的痕跡,“我”想他應該在船上工作了很久了,一想到他每天做著“低人一等”的工作時,“我”的內心是對親人生活艱辛的心疼。于是“我”在心里默念著“這是我的叔叔,父親的弟弟,我的親叔叔。”并且給了他十個銅子的小費。但是因為家庭的拮據,使“我”又不得不理解“我”父母的所作所為,因此“我”不能大聲地告訴于勒,“你是我的叔叔,父親的弟弟,我的親叔叔!”
小說的情節是人和人之間關系的動態過程,從縱向來說,有了人物深層心理的發現,從橫向來說,有了人物間錯位關系的分化,才可能有個性。[7]文中通過菲利普夫婦對于勒的態度與“我”對于勒情感態度的不同進行對比所產生的情感錯位,可以看出“我”的純真,“我”對親情的重視;文中通過“我”的一聲聲呼喊,可以看出“我”內心對人性的呼喚,也因此產生了對成人世界同情、諷刺和批判及“我”對人性回歸呼喚的效果。讀者讀到此意猶未盡,但似乎對文章的主題、作者的寫作意圖仍是一知半解,作者是單純想批判、諷刺成人世界嗎?或是理解、同情成人生活的不易嗎?還是兩者的結合?
這時回到文章的起點,探究該篇文章的敘述視角,通過“我”小若瑟夫的眼睛記錄著所發生的一切。小說是虛構的,作者通過虛構來表現主題,小說的主題就是作者的思想,體現作者的主觀情感。[8]《我的叔叔于勒》是以“我”之眼敘述小說的情節變化,作者將其情感寄予在“我”的身上,借此表達著作者的寫作意圖及文章的主題。
文章通過“我”之眼看到了父母在船上對于勒的丑惡嘴臉,但是又看到父母努力工作,努力生活的一面,了解到父母并非一開始就是如此自私自利、唯利是圖,即他們的本性并不是如此,只不過是生活的壓力致使他們變成自私自利、唯利是圖的樣子。文中通過“我”之眼看到了于勒似乎不再像以前一樣犯渾,此時的他在船上勤勤懇懇地工作著。從船長與“我”父親的對話中可知,于勒從去年就從美洲回來了,但是他一直沒有去找我們,因為他不想要拖累家人,因此選擇留在船上當剝牡蠣的水手,作者也把于勒的人設引向人性的善;再看“我”對于勒的態度,從“我”對于勒的稱呼,對他外貌的關注、內心對于勒的呼喚及“我”給了他小費,可見“我”對于勒的善。小說寫到此,已經慢慢表露出作者的心跡,文章最后寫到“我”在心里默念到“這是我的叔叔,父親的弟弟,我的親叔叔。”這一聲聲叔叔的呼喊,是“我”內心深處的呼喊,也是作者在“我”身上所注入的情感。作者想通過“我”的一聲聲呼喊,把人性的本真“喊”回來,想通過“我”觸摸人性的溫度。
最后通過還原被刪除片段,可以看到成年的“我”依舊沒有變,依舊保留著童年的本真,原文寫到“今后您還會看見我有時候會拿一個五法郎的銀幣給要飯的……”成年后的“我”看到像于勒一樣的弱者,仍然會伸出援手,盡自己的能力給予他們幫助。這時候文章的主題就凸顯出來了,即作者寫菲利普夫婦、于勒和“我”的形象,都是在呼喚人性的回歸,希望讀者都能保持人性的純真。
綜上所述,小說的解讀方式有多種,不管是王榮生老師的教小說解讀方式;余映潮老師的關注小說閱讀技能的訓練,把握小說作品閱讀欣賞教學的重要著眼點;孫紹振老師的打出常規,深化心理層次,拉開人物之間的錯位距離;還是張玉新老師的教文體特色……無論是哪一種教學小說的方法,作為教師都需要有所了解,有所掌握。根據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提出的具體要求“增強學生學習語文的自信心,養成良好的語文學習習慣,初步掌握學習語文的基本方法……具有獨立閱讀的能力,學會運用多種閱讀方法。”[9]因此,教師可以適當將閱讀方法體現在教學中,帶領學生走進文本,解讀文本,深入了解人性與命運的復雜交織。教師可以引導學生與文本對話,與作者對話,讓學生了解“這一篇”小說的獨特價值與獨特之處。學生可以充分感受與欣賞“這一篇”小說的獨特魅力,享受閱讀小說的樂趣,形成自己獨特的閱讀感悟,從而學會自主閱讀小說的方法。
參考文獻
[1]王榮生.小說教學教什么[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No.288,94.
[2][6][7]孫紹振,審美閱讀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No.202,21 -32.
[3][美]利昂·塞米利安:《現代小說美學》,宋協立譯,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38-140.
[4]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No.403,215.
[5][美]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260.
[8]程翔.點在要害處,方能撥千斤——例談小說教學[J].語文建設,2016(01):24-27.
[9]白慧潔.于“無聲”處聽驚雷——探究《我的叔叔于勒》的人性溫度[J].語文教學通訊·B刊,2016(2):55-57.
[10]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定.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作者單位:佛山科學技術學院人文與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