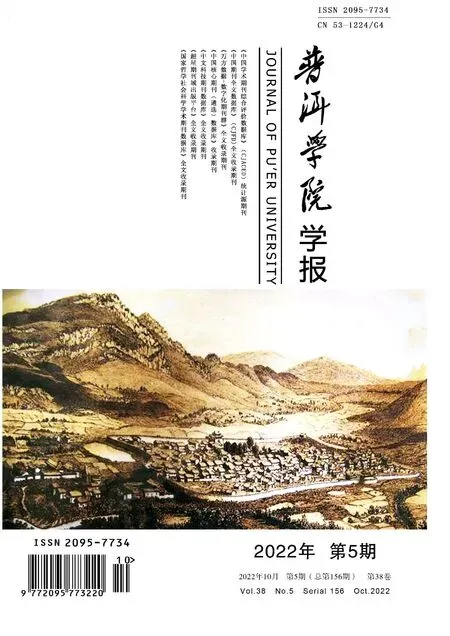再論《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寫作初衷及其被建構(gòu)的歷史影響
楊閻文
普洱學(xué)院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云南 普洱 665000
盧卡奇(Gy?rgy Lukács,1885.4.13~1971.6.4)被認(rèn)為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其標(biāo)志性的“物化理論”也經(jīng)常被用來與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相比較。他在未讀過馬克思《1844 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的情況下,根據(jù)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商品拜物教”觀點提出自己的物化理論,足見其理論的深邃性。然而部分學(xué)者[1][2]在比較研究的過程中認(rèn)為盧卡奇物化理論是對馬克思異化學(xué)說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或者認(rèn)為盧卡奇的物化理論是對馬克思異化思想的“微進(jìn)化”。筆者認(rèn)為,從盧卡奇提出“物化”概念的初衷出發(fā),類似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本文從探尋盧卡奇寫作《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初衷出發(fā),明確盧卡奇提出“物化”概念的最初想法及其在《歷史與階級意識》發(fā)表之時整個理論體系中的地位,隨后通過梳理后世思想界對《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建構(gòu)作用,反思思想史研究中應(yīng)當(dāng)堅持的方法原則。
一、盧卡奇的早年經(jīng)歷及匈牙利革命對其個人的影響
盧卡奇于1885 年4 月13 日生于匈牙利布達(dá)佩斯一個富裕的猶太銀行家家庭,然而他在宗教信仰上卻非猶太教徒,其在自傳中也明確表示:“猶太民族的意識形態(tài)對我的精神發(fā)展沒有任何影響”[3]。
早年的盧卡奇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02 年6 月高中畢業(yè)后,他先在1906 年10 月在科羅茨瓦皇家大學(xué)獲得法學(xué)博士學(xué)位,后于1909 年11 月在布達(dá)佩斯大學(xué)獲得哲學(xué)博士學(xué)位。1917 年他在一份為謀求海德堡大學(xué)哲學(xué)講席而擬的簡歷中提到,“狄爾泰的影響主要在于激起對文化史聯(lián)系的興趣,西美爾的影響則在于表明了社會方法和文化具體化的可能性。此外,麥克斯·韋伯的方法論著作對我起了澄清問題和開拓思路的作用”[3]。
1909 年秋到1911 年春,盧卡奇在柏林期間,興趣集中在德意志古典哲學(xué)上,但對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哲學(xué)的學(xué)習(xí)也促使其把關(guān)注的重心轉(zhuǎn)到現(xiàn)代德國哲學(xué),包括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和拉斯克的哲學(xué)中。其后他曾在佛羅倫薩短暫居住過1 年,之后便遷居海德堡,期間于1914 年春與海德堡同赫爾松地方自治局書記安德烈·米海伊洛維奇·格拉本科的女兒葉蓮娜·格拉本科結(jié)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及其后國際和匈牙利國內(nèi)局勢的急劇變化,使其人生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折。1915 年他返回布達(dá)佩斯,但因為精神衰弱癥而沒有服兵役,之后他在布達(dá)佩斯與其他一些知識分子組織了星期日社論(Sunday Circle)的沙龍。這個由知識分子組織的文化沙龍由于成員嚴(yán)重分裂的政治傾向而最終在1918 年解散,期間沙龍的部分成員介紹盧卡奇加入剛剛成立的匈牙利共產(chǎn)黨。
此時是盧卡奇思想發(fā)生轉(zhuǎn)變的重要時期,自傳中他將這一段經(jīng)歷命名為“走向命運的轉(zhuǎn)折點”。對戰(zhàn)爭的激烈反對促使其興趣中心從美學(xué)轉(zhuǎn)向倫理學(xué),并留下類似這樣的自傳提綱:“1917-1918 是決定性的一年;對俄國革命的反應(yīng)。我自己的道路:充滿矛盾、且?guī)в蟹磸?fù)的迷戀:1918 年加入共產(chǎn)黨”[3]。期間波爾什梯貝·蓋爾特魯?shù)拢ūR卡奇第二任妻子)對盧卡奇的影響尤其巨大。盧卡奇在自傳中表示,“我的路線總是堅定的;關(guān)系——甚至愛情——總是在既定的發(fā)展路線中,現(xiàn)在,每一個決定都有蓋爾特魯?shù)聫娪辛Φ膮⑴c;特別是那些最富有人性和有關(guān)個人的決定。她的反應(yīng)往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3]。
加入匈牙利共產(chǎn)黨之后,盧卡奇曾短暫的擔(dān)任過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主管文化和教育的人民委員及匈牙利紅軍第五師的政委。然而這段時間無論是盧卡奇?zhèn)€人、匈牙利共產(chǎn)黨還是整個匈牙利蘇維埃革命在思想層面都是極端混亂的。盧卡奇在自傳中坦言自己入黨時是完全沒有理論準(zhǔn)備的,匈牙利共產(chǎn)黨對如何進(jìn)行革命也沒有一套成熟的理論體系和行動方案,只是焦急地等待來自莫斯科的經(jīng)驗和指導(dǎo),然而結(jié)果就如盧卡奇所言:“從莫斯科來的人告訴我們的東西都很不高明”[3]。
正是在這樣倉促而混亂的背景下,匈牙利蘇維埃革命只堅持了130 余天便失敗了,包括盧卡奇在內(nèi)的一大批流亡者逃往維也納。隨后盧卡奇在維也納生活到1929 年末。此時,盧卡奇才真正開始對馬克思進(jìn)行系統(tǒng)的研究,這段時期也被他稱作“生活和思想的學(xué)徒期”。
二、《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寫作初衷及核心觀點
從盧卡奇早年的經(jīng)歷來看,即使在其加入匈牙利共產(chǎn)黨并出任黨的重要領(lǐng)導(dǎo)之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他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仍然是不夠深入的,甚至于到集結(jié)發(fā)表《歷史與階級意識》之時,也沒有到達(dá)思想的成熟階段。他本人也一再強調(diào)《歷史與階級意識》是一部過渡時期的作品,具有“馬克思主義學(xué)徒期的特征”。
那么盧卡奇寫作《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初衷到底是什么?這本書的核心又是什么?對于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先從他的自傳中窺見一二。
“即使作為軍隊中的政委,我曾多次看到農(nóng)民由于我們未能分配土地而不信任我們”[3];“當(dāng)捷克和羅馬尼亞的進(jìn)攻在4 月份開始時,人民委員會決定,半數(shù)的人民委員應(yīng)該到大的軍事單位去當(dāng)政治領(lǐng)導(dǎo)人……蒂薩費勒德的保衛(wèi)戰(zhàn)弄得很糟,因為布達(dá)佩斯的紅軍戰(zhàn)士不放一槍就逃跑了”[3];“在軍事上,我自然只能在明顯的情況下進(jìn)行干預(yù)。我為此找到了一種很好的方法。我們的特別反革命的參謀長一但我使用這個方法就要發(fā)火。我往往對他說:“瞧,你是當(dāng)兵的。你有你士兵的語言,我有我哲學(xué)家的語言。但是軍事問題我一竅不通。如果你要告訴我這個或那個營需要從一個地方調(diào)到另一個地方,你不必詳細(xì)談這樣集結(jié)或那樣集中以及諸如此類只有專家才懂的東西。對這些東西我毫無概念,所以你必須以那種使我這個外行人也能懂得你為什么要這樣做或那樣做的方式來進(jìn)行解釋”[3]。從以上三段話中我們可以窺見,在匈牙利革命這個短暫而混亂的時間里,作為革命領(lǐng)導(dǎo)者的匈牙利共產(chǎn)黨人與廣大工農(nóng)士兵的割裂和自身在思想、理論和組織上的不成熟。
我們做一個橫向的對比就可以發(fā)現(xiàn)匈牙利共產(chǎn)黨成立的時間遠(yuǎn)遠(yuǎn)晚于布爾什維克黨,其創(chuàng)始人庫恩·貝拉等人早年大多作為社會民主黨人的角色存在,其后更長期在國外開展革命工作。可見,匈牙利共產(chǎn)黨在匈牙利革命期間的群眾基礎(chǔ)極為薄弱,加之整個領(lǐng)導(dǎo)層對革命缺乏起碼的準(zhǔn)備,因此革命在如此錯綜復(fù)雜的環(huán)境中失敗也不足為怪了。
至此,我們可以探討一個問題,革命期間匈牙利廣大的工農(nóng)群眾在思想意識層面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tài)?我們知道,匈牙利自1867 年起便與奧地利組成了一種特殊的二元帝國政體,奧地利承認(rèn)匈牙利“歷史領(lǐng)土”的統(tǒng)一和完整,匈牙利則承認(rèn)皇帝對于二元帝國的外交與國防權(quán)力,兩者均設(shè)立自己的國會、兩院和行政機(jī)構(gòu),同時各由一個首相領(lǐng)導(dǎo)。艾倫·帕爾默認(rèn)為從技術(shù)性來說,“奧匈協(xié)議”所創(chuàng)造的是奧地利——匈牙利二元君主國,但馬扎爾人所得的好處極大,因此不如說“匈牙利——奧地利帝國”更為恰當(dāng)一些[4]。之后的匈牙利在薩蒂·卡爾曼家族領(lǐng)導(dǎo)的政府治理下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獲得了長足發(fā)展,鐵路網(wǎng)宣告完成,主要干線都由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通過匈牙利的唯一海港——阜姆的貿(mào)易值,15 年內(nèi)增長了12 倍,甚至開辟了橫跨大西洋直達(dá)紐約的航線[4]。工業(yè)的發(fā)展帶動了無產(chǎn)階級群體的發(fā)展與壯大,然而必須要明確的是,一個階級群體的發(fā)展與壯大并不直接意味著其相應(yīng)的階級意識的覺醒和成熟,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真正覺醒和最終成熟需要科學(xué)理論的指引,需要無產(chǎn)階級政黨持續(xù)的組織、宣傳和動員,然而這些條件在1918 年前的匈牙利都不具備。中東歐特殊的自然與歷史條件形塑了區(qū)域內(nèi)極端復(fù)雜的民族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各民族間的矛盾常常將階級矛盾掩蓋。同時19 世紀(jì)末到20 世紀(jì)初又是歐洲民族主義全勝的時期,它總是帶著兩幅面孔:一面是群眾起義,力求愛國愿望得到普遍承認(rèn);另一面則是內(nèi)心以某些美德的化身自居,似乎是要把一種傳統(tǒng)的繼承者同他們不甚幸運的鄰居截然分開[4]。許多蠱惑人心的政客談?wù)撝魇健按竺褡逯髁x”,它也構(gòu)成了歐洲19 世紀(jì)80 至90 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成長的基本輿論背景,而這些人在后來的人類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歷史的指針撥動到1918 年,隨著同盟國的崩潰,匈牙利面臨的是極端殘酷的歷史現(xiàn)實。且不論持續(xù)4 年的戰(zhàn)爭對匈牙利造成的直接影響,僅以戰(zhàn)勝國強迫匈牙利簽訂的《布里亞農(nóng)條約》而言,就意味著匈牙利失去了1867 年“奧匈協(xié)議”簽訂時所承認(rèn)的2/3 的領(lǐng)土,割讓給羅馬尼亞的領(lǐng)土面積甚至大于條約簽訂后匈牙利所剩的領(lǐng)土面積,可以想象這樣的結(jié)果是對一個民族何等巨大的打擊。故此,在1918 年的匈牙利革命中民族革命的色彩遠(yuǎn)遠(yuǎn)濃于階級革命,同時在這場革命的中后期作為革命的領(lǐng)導(dǎo)者的匈牙利共產(chǎn)黨,由于自身的巨大缺陷,未能有效領(lǐng)導(dǎo)匈牙利人民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
面對如此慘淡的現(xiàn)實,當(dāng)時的盧卡奇作為一個親身經(jīng)歷過革命的敏感的資產(chǎn)階級學(xué)者,不可能不對革命的種種進(jìn)行反思,加之他移居維也納后日漸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yǎng),最終將其引向了科學(xué)的馬克思主義指導(dǎo)下的階級斗爭分析路徑。然而作為一個剛剛從非馬克思主義的營壘中分化出來的學(xué)者,其自身所帶有的種種思想印記是不可能迅速消除的,加之客觀歷史環(huán)境的影響使其又滑向了過分強調(diào)主觀意識的唯心主義怪圈內(nèi)。
首先,盧卡奇寫作《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初衷,應(yīng)當(dāng)說隨著其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yǎng)的不斷提高,面對匈牙利革命的具體現(xiàn)實,促使其從階級斗爭的角度分析問題。匈牙利革命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興起又被反動勢力撲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族意識壓倒了階級意識,最終導(dǎo)致最富革命性和戰(zhàn)斗力的工人階級未被有效的組織動員起來。也正因為其政治覺悟和歷史主動性的缺乏,使得他們不能采取持續(xù)有力的革命行動。同時,作為革命領(lǐng)導(dǎo)者的匈牙利共產(chǎn)黨又未能提出實際的土地革命方案,致使農(nóng)民沒有支持革命。盧卡奇面對匈牙利革命具體的歷史條件,斷定要想獲得革命的最終勝利,就必須呼喚階級意識的覺醒。所以《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基調(diào)就是破除資本主義“自然永恒”的魔咒,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提高理論根據(jù)[4]。
其次,則如他本人在1922 為本書所作的序言中明確的:因為我們的任務(wù)——而這是本書的基本信念——就是正確地理解馬克思的方法的本質(zhì),并正確地加以運用。我們決不求在任何意義上“改進(jìn)”它。因此,我們堅持馬克思的學(xué)說,決不想偏離它、改進(jìn)或改正它。這些論述的目的是按馬克思的意思來解釋、闡明馬克思的學(xué)說[4]。所以,從盧卡奇寫作的初衷而言,他絕沒有打算對馬克思異化學(xué)說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其“物化”概念也不是對馬克思異化思想的“微進(jìn)化”。
反觀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實際上它是一本論文集,是盧卡奇1919 年至1922 年在維也納期間,對于黨的理論及組織進(jìn)行反思之后撰寫的8篇文章的集結(jié)。專門為本書撰寫的文章實際上只有2 篇,一是“物化和無產(chǎn)階級意識”,二是“關(guān)于組織問題的方法論”。就“物化和無產(chǎn)階級意識”這篇文章而言,盧卡奇先在第一部分對物化現(xiàn)象進(jìn)行了討論,而后在第二部分明確了古典哲學(xué)存在“二律背反”的局限性以及無產(chǎn)階級通過“把辯證的方法當(dāng)作歷史的方法”來超越古典哲學(xué)局限性的歷史使命。隨后盧卡奇便開始了對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討論。故此,我們可以認(rèn)為盧卡奇對于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討論才是《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核心,而“物化”概念僅是構(gòu)成這一核心的結(jié)構(gòu)性論點。
三、后世對“物化”概念的持續(xù)建構(gòu)
綜前所述,筆者認(rèn)為盧卡奇寫作《歷史與階級意識》[5]的初衷是其個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yǎng)不斷提高的基礎(chǔ)上,面對匈牙利及世界無產(chǎn)階級革命陷入低潮的具體歷史現(xiàn)實,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意圖通過呼喚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覺醒,完成無產(chǎn)階級的歷史使命。其中,關(guān)于物化的討論僅是構(gòu)成此核心理論的結(jié)構(gòu)性論點。
那么現(xiàn)在的問題在于為何部分學(xué)者會認(rèn)為盧卡奇的物化理論是對馬克思異化學(xué)說的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或者認(rèn)為盧卡奇的物化理論是對馬克思異化思想的“微進(jìn)化”,甚至在行文中將兩者等同起來?
類似不恰當(dāng)?shù)奶岱ù偈刮覀兎此嘉鞣今R克思主義的歷史構(gòu)建問題。在確切的意義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是在特定歷史敘事支持下的建構(gòu)。以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為起點來定義一部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與其他思想史研究一樣,都已經(jīng)是一種事先追溯。這種追溯旨在揭示一種另類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tǒng)發(fā)展的軌跡,分析馬克思主義理論發(fā)展的內(nèi)在張力,從而為理解當(dāng)代馬克思主義在全球多樣性發(fā)展提供一種歷史前提。這不僅要求我們的研究有更大的理論自覺,而且實際上會帶來歷史認(rèn)識的深化[6]。我們知道,對于一個既存的理論體系而言,其在后世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中會不斷受到“建構(gòu)”的影響。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一般民眾都會參與到這個“建構(gòu)”的過程當(dāng)中,因為后世對于某個既存理論體系的理解和運用必然經(jīng)過對其進(jìn)行“個性化把握”的過程。“個性化把握”的過程意味著作為把握主體的個人會根據(jù)現(xiàn)實及個人的需求對被把握的對象進(jìn)行一定的“解釋—闡釋”。
上述過程落實到《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現(xiàn)實經(jīng)歷中,我們可以認(rèn)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西方的歷史現(xiàn)實逼迫一大批知識分子反思資本主義社會,恰巧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對物化現(xiàn)象的分析成為其反思及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種種現(xiàn)狀的有力武器。因此,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也就在知識分子的書齋和沙龍中,在“五月風(fēng)暴”的學(xué)生手中逐漸脫離原作者撰寫本書的初衷,產(chǎn)生出超出作者想象的歷史效果。從這個分析框架出發(fā),可以認(rèn)為馬克思的《1844 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及其中的異化理論也遭遇了同樣的經(jīng)歷
四、結(jié)語
通過分析盧卡奇的早年經(jīng)歷,明確其寫作《歷史與階級意識》的初衷是個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yǎng)不斷提高的基礎(chǔ)上,面對匈牙利及世界無產(chǎn)階級革命陷入低潮的具體歷史現(xiàn)實,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前提下,意圖通過呼喚無產(chǎn)階級“階級意識”的覺醒,完成無產(chǎn)階級的歷史使命。其中關(guān)于物化的討論僅是構(gòu)成此核心理論的結(jié)構(gòu)性論點。可見,對于思想家的作品而言必先明確其寫作的初衷,同時在作品的初始語境下對其中反映出的理論體系進(jìn)行還原的理解。之后則是把握它被建構(gòu)的具體過程,理清它與其他理論體系的歷史關(guān)系,才能避免作出不恰當(dāng)?shù)慕忉尅?/p>